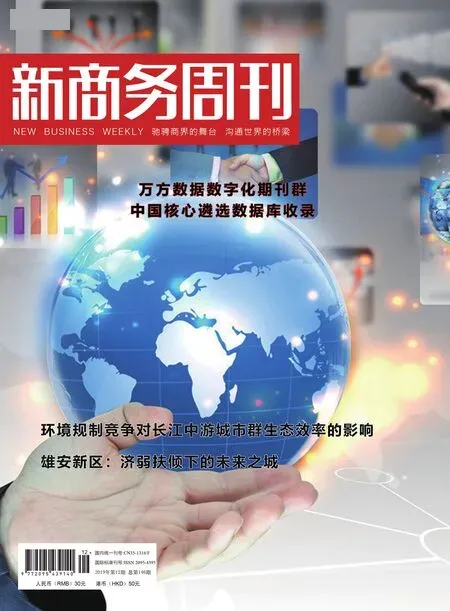一切皆有價
——論經濟中價格的作用
文/楊睿,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消費商品和服務成了現代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價格由自愿交易的買賣雙方根據各自預期的收益來決定。價格反映了人類的偏好。市場是人類有效的機制,能為消費者確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商品之間的價值關系,即它們的相對價格,與這些產品的屬性無關;相反,它取決于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1 價格整合信息
市場經濟中并不存在某個人或某個群體控制或調節所有的經濟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活動是毫無章法的。消費者、生產者、零售商、房東或工人都根據雙方共同商定的條件與他人進行單獨交易。價格不僅把這些條件傳遞給利益攸關的某個人,也把它們傳遍整個經濟體系,并且實際上是傳遍了整個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產品更好,或是同樣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更低,相關的信息就會傳開,不必由民選官員或計劃委員向消費者、生產者發號施令,人們就能夠通過價格采取行動。實際上,價格能夠比任何計劃者都要快速地整合信息,而這些信息正是計劃者發布命令的基礎。現代經濟體都包含了成千上萬種產品,期望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知曉所有這些產品已是過分,更不用說要他們去了解每一種資源分配到生產中的數量和比例了。每一種資源有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產成品怎樣轉移給數以百萬的人,在這些決定中,價格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一作用卻很少為公眾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員忽視。
2 價格提供決策
很多人只是把價格視為阻礙他們獲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礙。比如,那些想在海濱安家的人可能會因為濱海房產極其昂貴而放棄。但是,高價格并不是我們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現實情況是海濱的房子遠遠不夠分配,價格只是傳達了這個潛在的事實。當很多人競相購買數量很少的房子,這些房子就會因供求關系而變得十分昂貴。但是,并不是價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社會以及原始社會。即使現在政府實施一項“普及”海濱住房的“計劃”,并對這種資產的售價設置“上限”,也不會改變人口與海濱土地之比很高這一潛在事實。對于既定數量的人口和既定數量的海濱房產,若沒有價格,配給將不得不通過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隨機的方式來進行,因為配給總要實施。即使政府頒布命令說擁有海濱房屋是全體社會成員的一項“基本權利”,仍然絲毫不會改變潛在的短缺。價格像信使一樣傳遞著消息。有時候是壞消息,比如海濱房產的例子,渴望擁有海濱房產的人比可能住在海濱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消息,比如得益于技術進步,電腦飛速降價、升級。盡管高科技進步的絕大多數受益者對技術變化的具體內容全然不知,但是價格把最終的結果傳遞給了他們,使他們能夠做出決策、提高生產率,并通過使用電腦獲得了普遍的福利。
價格不僅是轉移貨幣的方式。價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種能夠影響人們使用資源和生產產品行為的經濟激勵。價格不僅指導著消費者,也指導著生產者。畢竟,生產者不可能知道數以百萬計的不同消費者想要什么。比如,汽車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們制造的某種汽車能賣個好價錢,不僅能夠收回收回生產成本,還能留下利潤空間,但是他們制造的另一種汽車可能會不好賣。為了處理掉這些滯銷的汽車,賣家必須削減價格,直到經銷商能夠處理掉庫存為止,即使這意味著要蒙受一些損失,否則他們就會因賣不出去這些汽車而遭受更大的損失。雖然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有時被稱為利潤體系,實際上它是一個盈虧體系,而且虧損對經濟效率同樣重要,因為虧損會告訴生產者應該停止做什么——停止生產什么、停止把資源投入哪里、停止投資什么。虧損迫使生產者停止生產消費者不想要的東西。雖然不能真正了解消費者為什么喜歡某些功能更勝于另一些,生產者會自發地多生產獲利的產品,少生產虧損的產品。也就是說,生產消費者想要的東西,停止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東西。盡管生產者只關心自己和公司的損益狀況,然而從經濟整體的角度來看,以價格為指導的決策能夠讓社會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資源。
3 價格可以跨越空間傳遞信號
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價格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網絡。不論是誰、不論在哪,只要是自由市場通行的地方,價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聯系起來,因而商品價格低廉的地方能夠讓自己的商品暢銷世界各地。這樣你才能夠穿上馬來西亞生產的襯衫、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加拿大生產的褲子,開著日本制造的汽車,而輪胎卻是法國生產的。利用價格來調節的市場使人們能夠向他人發出信號:想要多少產品,愿意支付什么價格。其他人也同樣會發出信號:在什么價格愿意提供什么產品。價格對供求做出反應,使得自然資源從豐富的地方(如澳大利亞)轉移到匱乏的地方(如日本)。因為比起澳大利亞人,日本人愿意為這些資源支付更高的價格。同樣的資源,澳大利亞因其本身富有這類資源而價格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價格不僅能夠彌補運輸成本,還能夠讓澳大利亞大賺一筆。
觀察價格被禁止發揮作用的情形,我們能夠更清晰地體會到自由市場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例如,在蘇聯政府管制經濟的時代,價格不是由供求決定,而是由中央計劃者設定的,他們通過直接命令的方式把資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并把價格提高或降低到他們認為合適的水平。兩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 olaiShmelev)和弗拉基米爾·波波夫(VladimirPopov)曾描述,蘇聯政府提高了鼴鼠毛皮的價格,導致獵人們去獵取更多的鼬鼠,并出售更多的鼴鼠毛皮。國家采購量增加了,現在所有的分配中心都堆滿了這些毛皮。工業無法消耗掉它們,在處理之前,它們往往就已經腐爛在倉庫里了。通過供求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消費者和生產者行為的影響,無數獨立的決策得到全面協調。讓價格來說話,人們只當聽眾,他們的反應通常要比中央計劃者整合報告資料快得多。雖然指揮人們采取行動看上去是一種更合理有序地調節經濟的方式,實踐中卻缺乏效率。在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時期,許多其他的商品也和鼴鼠毛皮一樣。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倉庫堆積大量滯銷商品,其他商品卻存在令人痛苦的短缺,而用于生產滯銷商品的資源本可以用來生產短缺商品。在市場經濟中,過剩商品的價格會根據供需關系自動下降,短缺商品的價格也會由于相同的原因自動提高,最終的結果是:當生產者追求利潤避免損失的時候,資源自動從過剩產品轉移到了短缺商品的生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