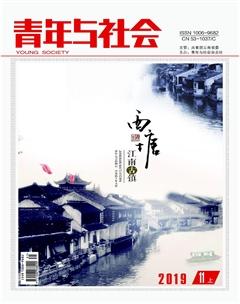反思后現代主義對歷史認識“客觀性”的沖擊
摘 要:二十世紀之前,對史學的“客觀性”問題的認識道路似乎是平坦的。實證主義史學的集大成者蘭克總結了一整套系統、嚴謹的史料考證方法,以期實現“客觀”的歷史認識。后現代主義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后,顛覆了西方歷史編纂學的基本預設和主流觀念——歷史的敘事問題和客觀性問題。從后現代主義模糊文史分界線和將史學文本化的視角出發,傳統史學所認識的客觀性就難以立足了。后現代主義促使學者重新思考史學認識的“客觀性” 問題,在批判后現代主義的“語言決定論”錯誤的同時,還應積極借鑒其語言理論,為史學研究開辟新的道路。
關鍵詞:史學認識;客觀性;傳統史學;后現代主義
自從史學誕生之日起,就有無數史學家開始苦心孤詣地追求其客觀性。在二十世紀之前,對史學客觀性的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似乎是一條坦途。然而進入二十世紀,相對主義特別是后現代主義以咄咄逼人的態勢顛覆了千百年來積淀的史學的客觀主義傳統。如何應對這種挑戰并重新思考史學的客觀性就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了。
一、傳統史學對歷史認識“客觀性” 的詮釋
早在西方史學的創立時期——古希臘的歷史學就受到邏輯學的影響,強調歷史只能與目擊者共存,同時古希臘史學力避文與史的結合,否則即影響史學的客觀性。 經過緩慢發展,到了近代,史學加速了專業化和科學化的步伐。一位史學家總結道:“19世紀是實證主義思潮彌漫的時期,它幾乎籠罩了一切學術思想的領域。風氣之所及,乃至一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都力爭自命為科學。”歷史學當然也落此窠臼。史學的科學化過程也是史學家發掘歷史學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過程。蘭克是客觀史學的集大成者,研究他的史學思想就可見世人理解的史學“客觀性”之一斑。“在柯林伍德看來,蘭克為代表的‘努力發現確鑿的歷史事實而不承認歷史普遍規律的‘蘭克模式就是實證主義歷史學的一種。蘭克史學的‘科學性基本上指史料批判方法的科學性,……專業化和客觀性也部分地包括在史料批判中。”可見,蘭克強調的史學的客觀性是指基于一整套嚴謹的史料批判的工作之上而獲得客觀歷史認識。
“客觀性”建立于其上的假設包含了對于過去實在的忠實、對于與那一實在相吻合的真理的忠實;在知者與所知、事實與價值而且尤其是歷史與虛構之間的分野。歷史事實被視為先于并獨立于解釋;一種解釋的價值是由它在多好的程度上解說了事實而加以判定的;倘若與事實相抵牾,就必須將其拋棄。真理只有一個,而非依視角而異。存在于歷史中的無論何種模式,是“被發現的” 而非“被創造出來的”。
二、后現代主義對史學“客觀性” 的顛覆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及之前的史學家們對歷史的認識始終堅守在實證主義和理性分析的立場上。隨著二十世紀新史學的出現,史學研究者對“歷史認識”的認識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由注重史學認識的客觀性轉而強調其主觀性。柯林伍德、克羅齊以及法國年鑒派大師馬克·布洛赫和費弗爾均持此種觀點。經歷了來自相對主義的挑戰之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更為激進了,它對史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提出了質疑,這就是所謂的“后現代轉向”或言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
具體說來,后現代主義對史學客觀性的沖擊,首先表現在它對文學與史學界線的模糊上。后現代主義者視歷史學等同于文學,都是“語言的游戲”。古今中外皆有“文史不分”的傳統,但是,19世紀以來的實證主義思潮使得史學與文學之間的距離漸行漸遠。后現代主義則徹底混淆了史學和文學。海登·懷特在其代表著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中認為,歷史學與文學之所以相似,就因為歷史學家與詩人、小說家一樣,必須依賴語言傳播其作品。而且,歷史學家所使用的語言,不能過分專業化,日常的“自然語言”,而非科學專用的“形式語言”,否則就無法與廣大讀者溝通。因此,他認為歷史學必須運用與文學相同性質的語言。這樣,歷史敘述就可能成為一種文學創作活動。
三、對史學認識的“客觀性”的反思
從歷史哲學角度講,后現代主義對蘭克為代表的傳統史學所認識的“客觀性”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傳統史學所堅持的樸素客觀主義或者稱為樸素實在主義,堅持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歷史事實并不等于史料,歷史事實也不等于歷史研究和歷史解釋。
一方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歷史客體相對于史學主體是客觀的。史料雖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歷史認識的客體,但有其客觀性。換言之,史料不具有歷史客體這樣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史料依然是獨立的客觀實體。“史料應從主體和客體雙重角度去認識,史料體現著主觀和客觀的辯證統一。”所以對于史料的客觀性不能過分夸大,而且客觀的史學認識也不能直接通過客觀的史料來實現。認為僅憑充足的史料和嚴謹的考證工作就會有公正的史學認識的愿望就變成了犀牛望月。
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擊中了樸素客觀主義或抽象經驗主義的要害,抽象經驗主義把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想當然地認為歷史語言能夠像鏡子那樣再現歷史實在,沒有認識到歷史認識過程的復雜性。”蘭克學派這種“如實直書”的依靠充足的文獻資料和排除主觀偏好的作用而使歷史認識臻于客觀的主張正是此類問題的恰切反映,當然無以在后現代主義的沖擊下立足。
總體說來,純客觀的歷史是寫不出來的。史學的客觀性只能作為一個彈性概念,作為一種永遠達不到的極限。“在歷史研究中,主體意識發揮的重要內容,并不是如何‘完全客觀地、‘真實地反映歷史所謂的‘真實面目,因為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客觀存在的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決定的。任何高明的歷史認識主體,都不可能窮極客觀的歷史真理,否則,歷史科學就將停滯而失去生命力。”但是作為歷史學的主體,史學家必須力求客觀。古今中外的許多優秀史學家都認識到,只要史學家堅持學術良知,運用科學的治史方法,史學認識還是有其客觀性可言的——至少還是能夠部分地反映歷史的客體的。所以,有的史學家認為未來的歷史學仍然應是客觀的,只不過,“不可能再回到實證主義的立場,而只有在歷史敘事與歷史事實之間重建有效的關聯,才是惟一可能的出路”。
所以,大部分中國學者傾向于對待后現代主義沖擊史學客觀性持批判接受的態度。批判的是語言決定論下的絕對的歷史觀,同時接受對后現代語言理論的合理應用。我們在史學觀念上也應當積極轉變:“我們惟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超越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綜合視野,接過后現代歷史哲學的主觀性原則,將其納入更高層次的理解系統中,使主觀性原則成為服務于新客觀性原則的要素。”在客觀性的概念上,“融合傳統經驗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視界,構建一種新型的歷史客觀性概念,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現在僅能從理論上實現這種發展路徑,學界尚不能將之用于具體的史學研究中,但畢竟表明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思考與努力。將這一發展路徑應用于史學實踐之中的宏愿不是朝夕之舉,必定要積全世界史學家的合力方能實現。
總之,通過反思,史學界對歷史認識“客觀性”的理解有了螺旋式的上升。這種試錯式前進方式或者說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的魅力所在。“這場客觀性危機或許是歷史學走向成熟所必經的一個階段。如此看來,后現代主義就并非歷史學的終結,而是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如果沒有外在的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史學無以應戰,也就無形中喪失了一條發展的渠道,史學就難有質的革新。面對后現代主義這樣的挑戰,史學家們有了更強勁的創新的沖動,在應戰中暴露的史學體系中固有的缺陷也得到了重新認識。同時,這既是挑戰也是交流,在與后現代主義的“交往” 中,史學之樹必定會彌堅、常新。
參考文獻
[1] 何兆武.對歷史學的反思.參見朱本源.歷史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朱本源.歷史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王晴佳,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
作者簡介:潘寧(1986.02-? ),男,山東淄博人,講師,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冷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