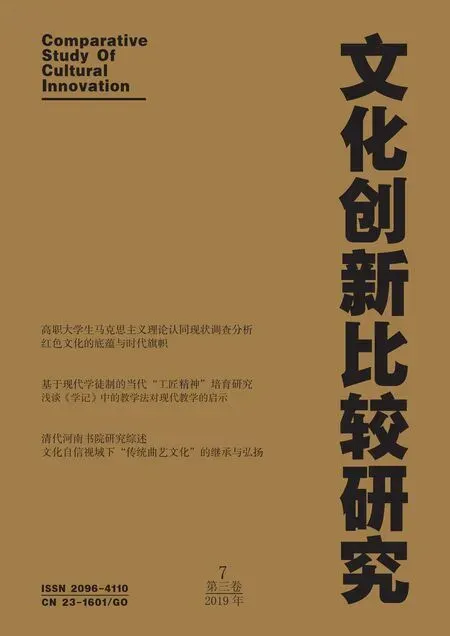試論蘇軾詞的自由性
胡喜之郎
(浙江省臺州市第一中學,浙江臺州 318000)
蘇軾具有中國古代文人身上的鮮明特點, 懷有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強烈追求。在儒家文化中,入仕為官是所有文人所追求的,蘇軾也不例外,但蘇軾的政治生涯并不是一帆風順,一生中數次被貶,這對他的人生哲學和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古代不少文人在政治生涯中挫折后便一蹶不振, 但蘇軾卻能用坦然的心態面對這些不平之事, 逆境反而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更多的靈感和激情,使他精心構筑自己的精神家園。儒道佛三教的思想資源為他提供了尋求、 創造和享受現世生活中的詩意和自由,在蘇軾的詞作中,我們常常可以感受到超然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藝術境界,筆者將之歸結為“自由性”。
1 蘇軾對人生自由的追求
性格決定命運,人生的歷程實際上是性情的反映。蘇軾是自小受儒家傳統教育的文人, 除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外,佛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也深深影響了蘇軾。蘇軾的詞創作都是他性情所然,在主體意識上,蘇軾詞大多表現為積極入世,核心就在于對自由的追求,不受任何教派約束。在蘇軾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心靈自由的追求,這不僅體現在生活之中,更表現在對人生意義與自我價值堅守方面。
1.1 對表層人生自由的追求
蘇軾具有傳統中國儒家文人的人格, 在烏臺詩案發生之前,他希望在政治生活中一展宏圖。他的自由表現在勇于建言的政治氣度,即對政治主張的堅持,不受權貴甚至皇帝的思想所左右。他不忘科舉之初心,牢記為官之使命,不怕得罪人,不當墻頭草,不在黨爭中站選邊,力陳自己的主張,卻最終為“言論自由”付出巨大的代價。而在被貶之后,逆境磨煉了蘇軾的性情,蘇軾隨遇而安、釋然超脫的性格在長期的磨煉中得到升華,讓他更加灑脫坦蕩。只是回首“高處不勝寒”時,發現宦海沉浮、官場險惡,不僅自己的政治抱負難以實現,更難以去追求人生自由,不免感慨萬千。
例如《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這首詞是蘇軾在調往密州的途中所作, 他一邊感嘆未來的不可知,一方面又追憶當年入朝做官的遠大抱負(“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而今只因為和新法派意見不合,便處處受阻,難以立足。因而蘇軾勸誡道:“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他化用《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話語,表達了“被任用或被棄置取決于時運,奔走仕途或遁世隱身在我自己”的人生觀。這種看似超然的人生態度,實際上仍是在抒發內心的不得志。只要身強體健,優游歲月,“休論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見前身”,我即便袖手旁觀又有何妨呢? 這是蘇軾面對殘酷現實的憤激之辭,也反映了他壯志難酬的內心痛苦。
蘇軾對自由的追求, 實際上是寄希望實現政治的遠大抱負,又能實現對自由的體驗與感悟,然而自由與實現政治抱負本身就是沖突的, 因而只能是一種鏡花水月,難以實現。蘇軾在去黃州之前,也就是他創作的早期,他對自由的追求,更多的是體現在他渴望以入世之法來追求人生自由。然而政治是復雜的,這種自我設計過于理想化,難以實現,必然導致他內心的沖突。蘇軾在入仕為官的過程中, 深深感受到政治的復雜與險惡,想要早日歸隱的思想在蘇軾的很多詞中多有表現。但這種歸隱之情是建立在功成名就的前提下, 他對自己的歸去提出了兩個前提。一是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這是歸隱后生活的必須, 否則身不由己; 二是功成名就,可以放下士大夫的責任和擔當。雖然蘇軾常常感慨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黑暗, 但蘇軾仍舊是中國儒家傳統中的典型人物。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即使在文化多元的今天,儒家思想仍舊在影響著中國人的方方面面, 更何況是自小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的蘇軾。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很多文人期待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 這甚至是不少文人的最高人生理想。“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待有良田是兒時”,這些都是蘇軾這種思想的體現。“待有”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種期待,這種期待正是因為不自由而體現的。
1.2 在矛盾中尋求精神的自由
矛盾存在于每個人的生活之中, 人生的追求往往與現實存在著巨大的沖突, 其心靈的展現也會受到各種限制。莊子所作逍遙游,其實也不過是古人對自由的美好向往,是一種理想的境界,生活中是幾乎難以實現的。蘇軾生活在現實之中,作為傳統的儒家文人,入世是最高的人生理想,但蘇軾又渴望自由。自由的人生境界與實際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存在著很大的反差,從蘇軾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看出, 蘇軾感到不自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對人生短暫的感慨,也有對漂泊無定的悲涼,同樣也有對難以功成名就,抱負無法實現的悲哀。種種現實,都是無法克服的矛盾。在面對矛盾的時候,蘇軾總是渴望探索,不停追求。
在《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首詞是蘇軾在被貶黃州之后所作。被貶黃州的蘇軾生活困苦,連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很有問題,斯文掃地、狼狽不堪。面對這種矛盾與困境,雖然蘇軾描繪了不少令人震驚的惡劣生活環境,但從內心來說,蘇軾并沒有因此而郁郁寡歡, 反而苦中作樂、 超然自得,將苦難轉化成審美的心境和情趣,表現出一種樂觀曠達的精神,“卿相之貴,千金之富,有所不屑”“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可樂觀曠達的背后,是政治枷鎖的重壓,“我欲乘風歸去”“歸去來兮,吾歸何處? ”蘇軾仍舊會感到寂寞、孤獨與無奈,這種內心的抗爭與悲涼是他人無法理解的。
好在蘇軾年少時曾拜入道士門下學習, 道家思想對蘇軾思想的形成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生死的看淡與超脫,才能促使蘇軾形成自由豁達的生活態度,表現出一般人少有的生命韌性。建立在對人生悲歡離合超脫的基礎之上,才能大徹大悟,進入更高、更自由的人生境界。在這個過程中,蘇軾以自我智性的發掘與性情的舒展來消解由生命苦難而生的悲愁。但這還不能滿足他對于心性自由的追求,他需要找到一個知音,當作精神支柱,那就是陶淵明。“我生不如陶,世事纏綿之。”這位超越時空隔閡與自己實現心靈交匯的前輩,讓蘇軾的一生都在不斷地追求超然的人生理想, 他向往那種山野為家的自由生活,向往那種“江海寄余生”的自由狀態,在詞中呈現出忘懷于世俗糾葛,瀟灑自然游走于天地人世間的博大情懷。這是“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王水照評價)。
2 蘇軾對藝術自由的追求
“詩為心聲”,文學創作是作者性情的展現。古今中外的文學家,大多有著與常人不一般的性格,為文學創作提供了不一樣的氣質。真摯、率性而為,是大多文學家的典型性格特征。蘇軾性格外露,狂放不羈,喜怒形之于色,自由奔放,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說蘇東坡“是一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這種無拘無束的天性也表現在他對詩詞藝術的“任性”上,行云流水,隨物賦形。
當時宋詞的缺陷被世人詬病已久,但“心有余”的詞人缺乏足夠的藝術功力和創新魄力, 未能開拓出一條新路。一向反對俯首前人腳下的蘇軾來了,他才華橫溢、藝高膽大,豈能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他居高臨下、不拘一格,別出心裁、融會貫通,最終以雄厚的創作實力和享譽神州的優秀作品讓世人深深折服, 繼而掀起革新浪潮,讓北宋詞壇煥然一新。如今談及蘇軾的藝術成就是毋庸多語的,有人說蘇軾開創了豪放詞的派別,一改宋詞的“靡靡之音”;也有人說蘇軾“以詩為詞”,突破了傳統詞作的創作局限。在筆者看來,蘇軾在詩詞藝術創作上的貢獻,同樣可以從追求自由的角度來解讀。詩言志,詞言情。言情,是詞的傳統題材。蘇軾“以詩為詞”是對傳統題材的開拓與創新,即使言情詞的范圍,也從傳統的男女之情擴大到手足之情、師友之情。“以詩為詞”在今天看來是對蘇軾的贊美,但在蘇軾所生活的年代,也招致了批評。曾有人說蘇軾的“以詩為詞”改變了詞作的方法,不得詞作的精要所在。不過也有不少文人為蘇軾辯解,“以詩為詞”是一種文學創新的手法,突破了傳統詞作的限制,包括題材、風格和語言文字上的突破,是對傳統詞作的革新,是要爭取更多的創作自由。
蘇軾的詞不僅可以以詩為詞,還可以以文為詞。雖然宋代的詩創作已經有議論化的傾向, 但蘇軾的詞的議論化也是一種詞創作革新的表現, 而且蘇軾還發展了小序。當時有不少文人在宋詞創作中,喜歡以一段序言來交代寫作的背景,稱為小序。在蘇軾之前,柳永、范仲淹、 歐陽修等人都寫過小序, 小序一般不超過十個字。在蘇軾的筆下,小序的字數并無限制,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有的小序字數甚至超過了詞作字數的一半,有的也就寥寥數字。蘇軾常常把創作的背景和心態通過小序的形式展現出來,形同一篇短小散文,讓讀者更準確、深刻地體會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這種自由的創作形式讓蘇軾的詞作別具一格、大放光彩。
除此之外, 蘇軾還常常把神話以及民間小說的內容融入詞創作之中,使得詞的內容更加精彩豐富。
3 結語
蘇軾是自由的。蘇軾奔波于官場,卻堅持獨立的政治操守,不愿投機鉆營或同流合污;蘇軾向往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卻不忘政治抱負、家國情懷;蘇軾推崇儒家,但不被儒家思想所局限;蘇軾接受佛老,但又有自己的分析和選擇;蘇軾文學風格獨特,自成一派,卻沒有以自我為法,“強令門人師范”。蘇軾的倔強、獨立與包容決定了他與眾不同的人生際遇。而他的創作思想表現出更為解放、更為自由的特點,既不同于當時的道學家,又不同于歐陽修等詩文革新派,在北宋文壇獨樹一幟。這些綜合因素使得蘇軾的詞充滿了自由灑脫的氣息,讓自由成為蘇軾詞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