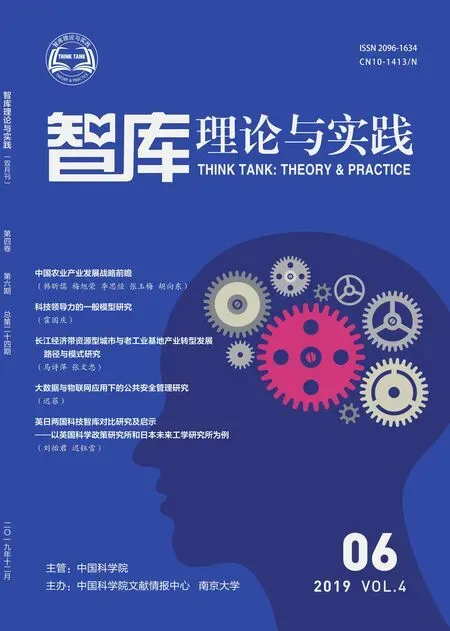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 李佳洺
1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城市與區域發展戰略專業委員會 北京 100101
2015年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綱要》和2017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都將疏解非首都功能作為北京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功能對人流、物流等有強大的吸引力,成為“大城市病”的重要成因,因此作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點。產業功能的疏解將引起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盡管已有的相關理論明確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發展的重點將由制造業逐步轉向服務業,但是并沒有就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給出一個明確的量化關系。而產業結構作為政府進行宏觀決策的重要指標,對未來產業調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對北京產業結構特征的剖析和未來發展趨勢的研判,將為城市發展提供科學的決策支持,并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
1 北京產業結構特征與面臨的調整壓力
1.1 北京產業結構變化過程與特征
北京先后經歷了消費型城市、生產型城市和服務型城市轉變的過程,第三產業比重也隨之呈現先降低再上升的變化趨勢。建國初期,北京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型城市,城市經濟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到1952年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略低于第三產業[1]。1953年,北京第一次城市總體規劃指出,北京不僅是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還是工業中心。到改革開放前,北京仍在積極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1978年,北京第二產業比重達到70.96%,是服務業的3倍以上。改革開放后,政府對北京的職能有了新的認識,并反思了工業優先的發展思路。1982年城市總體規劃明確將北京定位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并要求嚴格限制工業發展[2]。此后的1992年城市總體規劃又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服務業,這使得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間,服務業占比以平均每年近兩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3-4]。進入21世紀,服務業比重依然持續提高,2017年北京市服務業增加值達到22,569.3億元,在三次產業中的占比為80.6%(圖1)。事實上,自1994年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后,服務業就開始主導北京的經濟發展。

圖1 北京產業結構變化趨勢Figure 1 Changes in Beiji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1.2 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外部壓力
1.2.1 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雄安新區建設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著力加快推進產業對接協作,理順三地產業發展鏈條,形成區域間產業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聯動機制,對接產業規劃,不搞同構性、同質化發展”。為了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重大國家戰略,解決地區長期以來面臨的產業體系難以銜接、經濟發展差距明顯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然要求北京對城市經濟體系和產業結構做出調整,以適應地區協同發展的新局面。
此外,雄安新區的建設也會對北京產業未來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雄安新區作為未來與廣東深圳和上海浦東比肩的先行示范區,將成為北京一些高端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主要承載區,從而促進北京大量高端經濟和產業功能外遷。除大型央企和國有企業紛紛宣布將總部遷移至雄安新區外,北京也大力促進中關村科技園等在雄安新區落地,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
1.2.2 “四個中心”的城市定位與非首都功能疏解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北京時提出,北京要堅持和強化首都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并強調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因此,自2014年起,北京就開始對區域性批發市場、一般性制造企業等進行疏解。到2015年底,北京疏解了220個區域性批發市場,79家工業企業。
同時,2017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進一步強調了北京“四個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并明確“堅決退出一般性產業,嚴禁再發展高端制造業的生產加工環節”。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必將促使北京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
1.3 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
1.3.1 城市邁入高收入發展階段 2012年北京人均GDP就超過了1.2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1.26萬美元以上就成為高收入國家,因此北京自2012年起就逐步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標準。2017年,北京人均GDP超過2.05萬美元,盡管距英國、德國、日本等老牌發達國家人均GDP 3萬~4萬美元左右的水平還有一定差距,但毫無疑問北京已經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城市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以前快速的發展過程中,北京吸引和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資金等優質發展要素,人們更多注重收入水平的增長而忽略了生活質量。當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后,城市居民也開始關注生活品質,城市社會、經濟、產業等方面都面臨轉型。
1.3.2 北京“大城市病”十分突出 近年來,空氣污染已經成為北京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如2013年北京空氣質量優良的天數為176 d,即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不足全年的一半,但重污染累計達到58 d,即平均每周都會出現一天重污染的情況。交通擁堵也是北京發展的主要瓶頸,來自高德的數據顯示,北京在2014和2015年連續兩年成為全國最為擁堵的城市,2016和2017年也分別位于第3和第2位。盡管北京高峰擁堵延遲指數已經從2015年的2.06下降到2017年的2.03,但是相對于上海、廣州等同為人口眾多的一線城市來說,北京擁堵程度依然很高。除此之外,不斷高企的房價、擁擠的醫院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等都迫使北京需要對產業經濟等進行疏解和調整[5]。
2 產業結構調整面臨的困境
從北京產業結構變化的趨勢來看,服務業比重持續提高,盡管增速有所放緩;從城市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來看,隨著制造業的外遷和疏解,未來服務業在北京城市經濟中的比重很可能會進一步提高。
但是與國內同級別城市相比,北京服務業比重已經處于較高水平。北京服務業比重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超過廣州后,就一直顯著高于上海和廣州。2008年北京服務業比重比上海高出20個百分點以上,比廣州也高出17個百分點。此后差距雖然收窄,但到2017年為止,北京服務業比重依然比上海和廣州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圖2)。然而,在北京市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GDP和人均GDP等表征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并沒有明顯高于上海和廣州。同時,就北京自身而言,服務業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已經低于制造業,因此從經濟發展水平的角度來看,北京進一步大幅提高服務業比重的理由并不充分。

圖2 北京、上海、廣州第三產業比重變化趨勢Figure 2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Beijing,Shanghai,and Guangzhou
總體上,北京產業結構調整似乎出現了兩難的困境。從產業結構調整趨勢和城市發展內外部環境來看,北京服務業比重仍將進一步提高,但是從橫向比較以及自身發展特點來看,服務業比重已經處于較高水平,進一步提升的理由并不充分。而盡管“配第-克拉克”定律等經典理論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從業人員不斷向第三產業轉移,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也不斷提升,但是這些理論和已有的實證研究都沒有給出一個量化的對應關系。因此,未來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進一步提高服務業比重,直至成為城市唯一的經濟活動,還是保持一定的制造業比例,將服務業維持著一個合理的區間,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此外,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僅要有利于自身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要考慮對京津冀地區發展的影響。即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否有利于京津冀地區縮小地區發展的差距,緩解北京的虹吸效應,扭轉核心城市周邊長期存在“集聚陰影”(agglomeration shadow)的局面,實現區域更加均衡的發展[6]。因此,對北京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剖析將不僅有助于北京產業功能的疏解和自身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且將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產生重要影響。
3 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總結和理論剖析
3.1 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總結
發展經濟學相關理論和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有很強的相關性。由于人均GDP是經濟發展水平很好的表征變量,因此選取人均GDP和制造業和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進行總結,對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借鑒意義。
3.1.1 就國家尺度而言,發展處于較高水平時,服務業比重大致維持在75%的水平 采用局部多項式回歸(Loess函數)等非參數估計的方法,對“人均GDP”與“制造業比重”及“服務業比重”的相關關系進行擬合分析。從各國人均GDP與產業結構的對應關系來看,隨著人均GDP水平的不斷提高,制造業比重呈現不斷降低的趨勢,而服務業比重則是不斷增加。而且當人均GDP達到6萬美元后,制造業比重會快速下降到接近于0,而服務業比重則接近100%(圖3(a)所示)。
但是出現制造業趨近于0這一極端狀況主要是由于新加坡、中國香港和澳門等規模很小的國家和地區造成的,從圖3(a)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趨勢出現明顯差異的拐點。去除這些規模較小的國家和地區后,發現:當制造業比重降至25%左右后基本趨于穩定,而服務業比重上升至75%左右將趨于穩定,并不會隨人均GDP的增加而不斷下降(圖3(b)所示)。

圖3 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主要國家/地區產業結構與人均GDP關系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major countries/ regions with GDP per capita exceeding USD 20,000
3.1.2 就省(州)尺度而言,發展處于較高水平時,服務業比重大致維持在80%左右 用Loess局部加權回歸的方法,對美國各州的“制造業比重”或“服務業比重”與“人均GDP”的相互關系進行擬合分析。結果表明:隨著人均GDP的走高,制造業比重將無限趨向于0,服務業比重則趨于100%。但是這一狀況同樣是由于華盛頓特區規模較小①華盛頓特區2012年人口僅64.6萬,位列各州中的第49位,面積也僅177 km2造成的。
去除華盛頓特區這一特例,重新進行回歸擬合得到圖4。由圖可見,在美國各州,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制造業比重將不斷下降,在下降至18%左右后,不同參數的擬合曲線走勢出現一定分化,但總體來看,制造業比重將基本穩定在18%左右,不會隨人均GDP增加而無限降低(圖4(a))。對于服務業而言,隨著人均GDP的上升,服務業的比重將不斷上升,上升至80%左右時,不同參數的擬合曲線走勢再次出現明顯分化,當模型參數span值越小,即更多考慮高人均GDP的局部變化規律而非整體變化規律時,擬合曲線的走向趨向于穩定在80%左右。因此,隨著人均GDP增加,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至80%左右時,各州基本趨勢保持一致,當超過這一數值后,各州的發展趨勢就出現明顯的分化,總體上服務業比重更趨于保持在80%左右的水平上(圖4(b))。

圖4 美國各州產業結構與人均GDP的關系(除華盛頓特區)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U.S.states (excluding Washington D.C.)
3.1.3 對于城市而言,不同職能類型城市產業結構有較大差異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發達經濟體之一,其首都東京不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是東京灣地區經濟增長的核心。按美金當年價格計算,東京都的人均GDP在1986年突破了2萬美元。隨著人均GDP的上漲,制造業比重不斷降低,在下降到15%左右后,下降速度明顯放緩,制造業比重趨于保持穩定(圖5(a));服務業比重隨人均GDP上漲而不斷提高,上漲到85%左右時,上漲速度明顯放緩,服務業比重開始趨于穩定(圖5(b))。
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均GDP從5萬美金提高到7萬美金時,東京都的制造業比重才由30%左右快速下降到15%左右,而相應的服務業比重則快速上升到85%左右。而在人均GDP達到5元美元之前,制造業比重是較為平穩地緩慢地由40%左右下降到30%,而服務業比重上升也較為平緩。

圖5 日本東京都產業結構與人均GDP的關系Figur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per capita in Tokyo
與日本東京都不同,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和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業比重都在90%以上,尤其是美國華盛頓特區,服務業比重更是接近98%。華盛頓特區2016年人均GDP高達9.76萬美元,位列全美第1。其作為美國的政治中心,是大多數聯邦政府機構、各國大使館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產業結構較為特殊,服務業比重高達98%(如圖6)。盡管從這3個城市的發展趨勢來看,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服務業幾乎成為城市唯一的經濟活動,但是這類城市職能較為特殊,并非傳統意義上職能較為綜合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圖6 華盛頓特區“服務業比重-人均GDP”Loess回歸Figure 6 Loess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share of service and GDP per capita in Washington D.C.
3.1.4 區域尺度越大服務業比重越低,城市職能越綜合服務業比重也越低 從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各州以及東京都等城市發展過程來看,盡管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制造業在經濟活動中的比重將快速下降,而服務業則快速增加,但是在人均GDP達到一定數值后產業結構就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當然,這一相對穩定的產業結構隨著空間單元等級的降低而有所變化。
通常來說,空間單元等級越高,制造業穩定狀態的比重也越大,而穩定狀態對應的人均GDP也越低。穩定狀態下,隨著從國家級、州(省)級到城市級空間單元不斷縮小,制造業比重逐步降低。而就城市級空間單元而言,具有特殊職能的城市的制造業比重要明顯低于綜合性的區域中心城市,見表1。

表1 不同空間尺度下人均GDP與產業結構特征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per capita GDP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3.2 不同類型城市產業結構差異的理論剖析
綜合職能城市與特殊職能城市在產業結構方面的差異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不同類型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綜合職能城市一般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對于周邊城市有很明顯的帶動作用,如東京作為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時也是東京灣地區經濟發展的核心,其發展帶動周邊的埼玉、千葉、神奈川,形成東京首都圈,并與川崎、橫濱等一起將東京灣發展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經濟區;而特殊職能城市通常偏重于某一特定職能,通常區域經濟并不是圍繞此類城市展開,如香港作為亞太甚至全球的貿易中心,雖然與珠三角地區有很強的經濟聯系,但是珠三角地區依然是圍繞著廣州和深圳發展,華盛頓和澳門分別以政治文化和博彩業為主要職能,更與周邊區域經濟產業有明顯差異。換句話說,仍保持一定比例制造業的綜合型城市對周邊區域經濟增長有較好地帶動作用,而服務業比重趨近于100%的特殊職能城市與周邊區域的經濟聯系相對較弱。
這樣的差異一定程度上是由服務業和制造業在空間中的集聚與擴散特征造成的。服務業在空間中呈現點狀集聚的特征,產業發展以等級擴散為主,即核心城市服務業更傾向于向下一個等級的城市擴散,而不是核心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而制造業在空間中則呈現面狀集聚的特征,產業以接觸擴散為主,即核心城市制造業更傾向于向距離較近的周邊城市轉移和擴散。這與兩類產業產品的傳輸和運輸成本有關。服務業生產的產品以知識和信息為主,除在較小空間范圍內進行面對面交流外,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傳輸標準化的知識產品,對于周邊城市還是較遠的城市成本幾乎一樣,同時由于服務業產品需要較大的市場空間,因此產業更傾向于向距離核心城市較遠,但市場規模較大的較高等級城市擴散,而非距離較近但規模較小的城市;而制造業產品是實體貨物,運輸成本與空間距離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制造業的轉移擴散和產業配套更傾向于在距離核心城市較近的中小城市,同時中小城市也有充足且廉價的土地,有利于制造業的發展。因此,保持一定比例制造業的核心城市更可能通過產業鏈的聯系,與周邊區域的生產網絡進行對接,從而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而以服務業為單一經濟活動的核心城市更傾向于與距離較遠但規模等級較高的城市聯系互動,由于與周邊城市缺乏較強的產業聯系,所以對周邊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較為有限。
事實上,一些研究已經表明服務業的發展對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呈現負向影響[7-8]。而且隨著發達國家制造業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核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明顯下降,如Loannides和Overman對美國城市發展的研究表明,距離大城市較近而擁有較高市場潛力的城市發展并沒有顯著快于距離較遠的城市[9];Partridge的研究也表明,美國大城市對于小于25萬人的城市有一定帶動作用,而對中等規模城市的發展則是顯著的負向影響[10];Tervo對1880—2004年芬蘭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表明,自1950年后隨著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富裕地區對落后地區的帶動作用消失了[11]。
4 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考與建議
盡管國家已經明確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四個中心”定位,但是,北京作為一個人口超過2,000萬的超大城市,顯然不能簡單“去經濟化”,不是放棄經濟發展,而是放棄發展大而全的經濟體系,構建符合首都特點的高精尖產業結構。而且,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需要權衡北京在京津冀地區以及全國層面的作用和職能。
北京長期以來既是我國的首都,承擔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職能,也作為我國三大增長極之一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核心,但是隨著城市副中心的建設,一定程度上造成首都政治文化等職能與城市經濟社會職能分離的局面。因此,從遠期來看,北京繼續承擔全國政治中心和區域發展核心雙重職能,或者逐步弱化城市社會經濟職能,主要承擔首都政治文化職能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但是就近中期來看,基于北京自身以及京津冀地區的現實情況,北京仍然應該保持國家首都和區域經濟中心并重的雙重職能,因此產業結構調整空間較小。與東京類似,北京未來既作為我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承擔帶動周邊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從城市職能來看,北京應該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區域中心城市。一方面,從此類城市的規律特征來看,城市應該適度保持一定的制造業;另一方面,與東京等世界城市相比,北京超過80%的服務業已經與東京產業結構相差不大,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同時與上海和廣州等國內發展水平相當的城市相比,北京服務業比重已經處于較高水平,因此,從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來看,產業結構并不是其主要限制因素。從京津冀區域層面來看,與服務業相比,制造業對周邊區域更強的外溢性也有利于區域協同發展的推進。總體上,無論從北京自身發展還是京津冀區域協同來看,北京制造業比重并不高,不應簡單地推動制造業向外疏解,而應該注重制造業內部的提升和調整,部分高端制造的發展和試制環節的保留有利于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事實上東京依然將“享譽世界的東京的制造產業”作為城市的一個重要名片。
遠期,如果定位于國家首都,則北京產業結構有較大調整空間。與華盛頓類似,作為特殊職能城市,北京只是承擔國家首都職能,主要為全國提供政治、文化、科技等服務,并作為國際交往的舞臺,提升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則可以進一步加大對制造業的疏解力度。但是近中期并不適宜,因為高端服務業的發展雖然能夠大幅提高北京自身的發展水平,但是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并不強,不能有效縮小北京與周邊城市發展的差距,甚至可能進一步擴大與周邊區域產業梯度。尤其是目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生產網絡并不發達的狀況下,北京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能有效促進河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地區經濟的發展。
此外,河北要加強與天津的對接,逐步形成完善的制造業生產網絡,以促進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從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角度來看,地區經濟的協同顯然不應只是北京單方面的調整,京津冀地區長期割裂問題也需要天津和河北的積極應對。除去體制機制問題外,京津冀三地產業體系難以有效銜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北京與周邊城市存在顯著的產業梯度差,而且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特征又使其對周邊區域帶動作用有限。因此,河北不應僅僅盯住北京,舉全省之力推進環首都經濟圈等戰略,而應利用現有的制造業基礎,加強與天津先進裝備制造業等的對接合作,逐步建立完善的制造業生產網絡,從而與北京和天津的科技研發、金融服務等進行對接,推動京津冀產業體系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