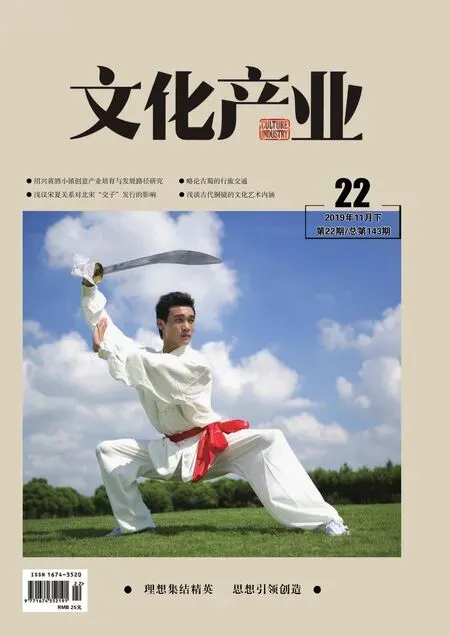略論古蜀的行旅交通
◎尉艷芝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2)
古蜀時期,人們在狹小的范圍內從事生產勞動和生活,為了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需要不斷地奔波行走,足跡所到之處就形成了道路。古蜀人以大無畏的精神開辟了棧道,加強了同關中以及其他地區的聯系。他們從成都出發,不辭辛勞,風餐露宿,長途跋涉,經過商販的接力傳遞,在原始的南方叢林中,走出了一條對外開放之路,即南方絲綢之路。盡管四川地處內陸,古蜀先民們的水上交通依然占據重要地位,他們的造船技術先進,并且還發明了索橋,這種造橋原理至今沿用。
一、開辟“空中走廊”
中國西南地區自古交通閉塞。四川盆地被眾多的高山峽谷環抱,關中與漢中、四川盆地之間,橫隔著巍峨的秦嶺和巴山兩大山脈,山勢高峻陡峭,地形復雜。在生產力較低下的古人,尤其是鐵器工具出現以前的人看來,這是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
關中,自古以來是帝王之都,經濟文化發達,對其他地區的人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作為國都,關中地區的人口快速增長,生產生活資料供不應求,而四川盆地物產豐富,因此兩地的溝通和交換勢在必行。蜀地的人們要穿越米倉山、大巴山,再穿越秦嶺,才能到達關中地區[1]。
秦時,西部的青海、新疆、西藏還尚未納入中央王朝版圖,秦嶺就是華夏諸國中的最高山峰。在這樣的崇山峻嶺中開辟道路,無疑困難重重。唐代詩人李白用“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來形容蜀道的險峻和出入四川的艱難,在李白的詩里,連白鶴都飛不過秦嶺,蜀道的崎嶇難行就可想而知。那么古蜀時期的人們,怎樣穿越高山險谷到達關中地區呢?
古蜀先民,曾經為了生存,沿著溫潤平緩、植被茂密的河谷,輾轉遷徙,經過長期探索,他們發現隔絕中原與大西南的秦嶺中有河谷走道,為減少翻山越嶺之苦,先民們利用河谷的峭巖,鑿石架木,修筑棧道。先秦蜀民披荊斬棘,開山劈崖,架木為橋,在崇山峻嶺、高山峽谷中開鑿了一條溝通川內外的大通道——棧道。在棧道靠河流的那邊及拐彎處,有的還裝有欄桿,以防人馬墜入河中。棧道險要無比,遠看就像一條空中走廊[2]。
古棧道十分險要,在懸崖峭壁的棧道上通行艱難,有的地方很窄,只能容納一人通過,想象一下,古蜀人背著背簍,攀欄前進,腳底下萬丈深淵。實際上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巴蜀的軍隊參加武王伐紂,就已經開辟了可通兵馬的道路,這是關于蜀道的最早記錄。道路的修成并非一蹴而就,一代又一代蜀人的努力修整,才終于使得道路越來越暢通。春秋戰國時期,棧道千里,通于蜀漢,蜀道的開通加強了兩地之間的聯系,促進兩地間的物資交流和貨物往來,方便了人們的生活。
先秦蜀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鑿山而行、架橋為路,創造了一個偉大的交通奇跡,它比西方的羅馬大道還早,可與大運河、長城相媲美。古蜀人沿河谷選修道路,近捷便利,這種方法至今仍被采用,今天許多鐵路、公路都沿著河谷修筑,被稱為“沿溪線”,我們不得不嘆服古蜀人的智慧。
二、對外開放的南方絲綢之路
三星堆時期,青銅鑄造、各類手工加工以及絲綢和蜀布的紡織加工,都已十分昌盛,這也為古代蜀人進行遠程貿易活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蜀國早就與周邊地區如秦國、楚國、滇和夜郎古國有著貿易聯系,其中有官方貿易,也有民間通商[3]。商周時期,蜀國青銅器的大部分銅料,就有可能從富產銅的楚國貿易得來;青銅器所含的鉛,就是來自云南。經過蜀國商人的販運,夜郎國的人也能吃到蜀國的特產枸醬,蜀的丹砂和空青作為馳名商品,被蜀國商人運往中原和東方各地,這些名貴商品受到當地達官貴人們的喜愛。
早在商朝中晚期,古蜀先民就在崇山峻嶺中,開辟了一條以成都為起點,向西南出發,由東、西兩道匯聚于大理,在楚雄匯為一道,繼續向西,由騰沖、瑞麗、畹町出境入緬甸,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孟加拉國等國的道路,這條路線被稱為“蜀身毒道”或“南方絲綢之路”,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之路。古人僅憑著驢或者騾等交通工具,甚至步行,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在外奔走,其中的艱辛難以想象。
奔走在這條路上的蜀商,都是精明能干的跨國商人,是國際交流的使者。在他們的馬隊背上,裝載了大量蜀地產的馳名商品,這些商品,不僅暢銷國內,也深受國外人們的喜愛,不僅有美麗的絲織品,還有漆器、茶葉、瓷器、竹器、鹽巴、丹砂、生絲、銅鐵器、金銀制品等,然后又換回了象牙、翠玉、紅藍寶石、犀角、珠璣等具有西域風情的特產。廣漢三星堆出土的海貝,產于印度洋北部地區。東周時期,蜀國的王公貴族流行佩戴的一種稱為“瑟瑟”的寶石串飾,這種寶石產于印度和西亞,顯然是商人們從異國販運而來[4]。
商周時期,蜀地的絲綢業已有相當發展。絲綢是蜀商們經營的一項重要商品,暢銷國內外。西方考古資料也說明,中國絲綢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傳至歐洲,希臘雅典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里發現了中國絲織品,而中國絲綢早在商周時期就已傳至埃及。到公元前4-5世紀時,中國絲綢已在歐洲流行,是歐洲上層貴族們十分喜愛的高檔時尚的服裝面料。
先秦時期的跨國商人們進行的長途販運活動,把中國的特色產品輸出到異國他鄉,把異域風情的商品引入國內,極大地豐富了古道沿線各族人民的社會生活,經商豐厚的利潤,也提升了古蜀商人的生活水平。
3000年前,古蜀人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從成都出發,不辭辛勞,風餐露宿,長途跋涉,經過商販的接力傳遞,在原始的南方叢林中走出了一條對外開放之路,顯示了古蜀人強烈的開放意識和勇于冒險的進取精神,先秦和秦漢時期蜀地的富裕,也同古蜀人的對外開放息息相關。
三、先進的造船技術
先秦時期的四川盆地,江河湖泊眾多,遠古先民很早就開始想辦法跨越江河,到達不同的地方。人們最初的渡河工具可能是葫蘆,把它系在身上增加浮力以渡水。后來人們開始造船,獨木舟可能是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
蜀國人很早就習慣水性,善于駕駛船只,戰國時蜀人和巴人一樣,死后多用船棺,也反映出他們便利的水上交通。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利用生存環境中的水道和內陸湖泊所提供的便利條件,用船作短途運輸,運送貨物。
春秋戰國時期,造船水平有很大進步。南方的楚國、吳國、越國等國已將各種船只組成水軍用于戰爭。戰國時期,蜀國的人們已經可以制造樓船,通過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戰國銅壺的紋飾,可以看到當時樓船的樣式,當時的樓船分為上下兩層,船體比較窄。下層船艙內有三四個佩戴短劍的士兵。這些人身體前弓,奮力劃槳。戰船的上層站有四五名士兵,他們有人在擊鼓助陣,有人拿起箭準備射擊,還有武士拿著劍正在和敵人搏斗。這個戰艦只能容納7-9人,是一種小型的樓船。
古代蜀人的造船水平技術較高,和當時以造船著稱的越國不相上下。戰國時期,除了樓船之外,古蜀先民還制造了舫船,這是一種大型船只,是兩艘船并排綁在一起,這樣既能保持船的平穩,又能增加載重,可謂一舉兩得。蜀地造船工業的規模很大,公元前308年,秦國將領司馬錯討伐楚國的時候,就在蜀國制造了上萬艘大船[5]。
先秦時期,四川盆地河流眾多,大部分可以通航。當時岷江至長江的航路,橫貫四川盆地,是從四川西北高原出發,經過四川,最后到達楚國、吳國、越國的水上航線,是東西交通大動脈。沱江、嘉陵江都能通航,是聯系蜀地南北的交通動脈。《戰國策·燕策》記載,蜀國的軍隊,從汶山出發乘船順江而下,五天就能到達郢地。《楚策一》記載,秦國西邊的蜀國,距離楚國三千多里,大船上裝滿了小米,舫船上還有很多士兵,一個舫能夠裝載五十人和三個月的糧食,到了水里就浮起來了……雖然負重前行,但是速度很快,不到十天就能到達捍關。十天,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時間也許太長了,我們的郵輪可能用不到兩天就能到達,但是在兩千多年前,蜀國的船只已經非常快了[6]。
古蜀時期的人們利用大自然賜予的木料來制造船只,又充分利用四川的江河湖泊,把原本是交通障礙的大江大河變成了水上航行通道,把東西南北地區都串聯起來,加強蜀國同外地間的物資交流,方便了人們的生活,開拓了人們的視野。
四、驚險刺激的水上索橋
四川西部山區多高山峽谷,松潘茂州地區,江水湍急,波濤洶涌,人們根本無法乘船渡過。古代生產力低下,古蜀人手中只有簡單原始的工具,建橋相當的困難。這些江河阻隔了他們的道路,怎樣才能到達彼岸呢?面對滾滾江流,當地的人們沒有退卻,想出了一個絕招,發明了索橋,由于四川古代造索橋是用竹索,所以也稱為笮橋。笮橋最初可能是由蜀地的少數民族發明的,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里的人們用索橋來渡水。
索橋可分溜筒和繩橋兩種,溜筒更原始,是四川地區的羌族、藏族、彝族少數民族經常采用的一種交通設施[7]。溜筒的使用方法是:人們用竹篾或者藤皮編織成大纜索,分別系在兩岸的石柱上,此岸的纜索系在高處,對岸的纜索放在低處,過河時,人們用繩索把自身綁在溜筒上,人是懸在半空中的,利用從高處往低處滑的慣性,并借助手攀腳蹬的助力,溜到對岸。人們不但可以空手渡過,還可以運送牲畜和物資。溜筒下面就是滔滔江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命喪江中,場面相當驚險。過橋如此艱難,那么修橋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氣,付出更艱巨的勞動。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勇氣和智慧。
兩千多年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在溜筒的基礎上建造了繩索橋,以方便人們通行。繩索橋就是用幾條大型繩索跨河排列,兩端固定在木樁上,上面拴著竹笆加固,橋的兩側稍高點的地方用巨索為欄桿,過橋的人可以手扶著。笮橋的原理,至今仍廣泛使用在現代橋梁建設和建筑結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