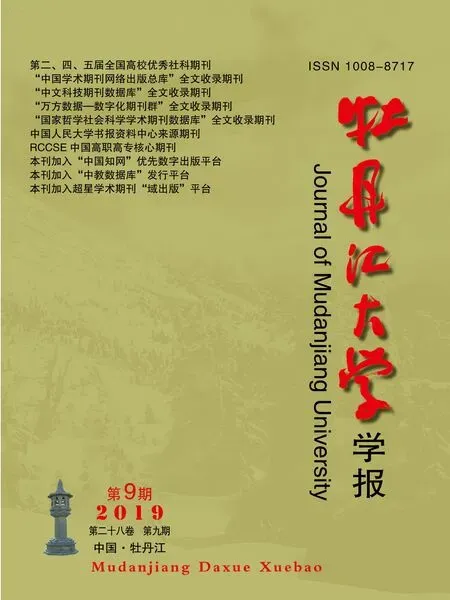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消費者”概念的反思與重構
——以懲罰性賠償條款的解釋適用為中心
雷 琳
(四川大學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問題的提出
懲罰性賠償,也稱示范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是指法院作出的賠償數額判決超出被侵權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其是在具有損害填平功能的補償性損害賠償之外,出于通過對行使不法行為的被告施加懲罰、以使被告與將來他人不敢再為相類似行為的考量,以期達到“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能的法律制度。從懲罰性賠償制度產生至今,便具有了“抑制不法行為與管制損害事件發生”[1]之制度功能。
自懲罰性賠償條款規定以來,其一方面起到了凈化市場、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積極效用,另一方面卻出現了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王海現象”①。必須承認的是,自《消法》頒布至今我國各級、各地法院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時多有差異,由于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此規定認識不一以及受社會輿論壓力等因素的影響,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與司法裁判的統一性要求常有不符。《消法》第55條第1款仍沒有對“知假買假”“消費者”等行為或概念作出明確界定,而司法實踐中消費者訴訟以及“王海們”的數量只有增無減,故而有必要重新對《消法》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之構成要件進行分析,按照目的解釋、功能解釋的方法挖掘“消費者”概念應當具有的內涵與外延,對理論紛爭與司法實踐進行必要的批判和修正,力圖為該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做到統一的厘清及界定。
二、理論紛爭
綜觀國內學界關于“懲罰性賠償”的學術研究,其爭議焦點可歸結為一點,即關于“知假買假者”能否受到《消法》保護的問題,針對于此,學術理論關于其支持與否的觀點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勢。
(一)反對保護“知假買假”的觀點
關于知假買假行為應否受到《消法》保護的問題,學者們從民事法律基本原則到《消法》立法意圖都對此問題進行了闡述。郭明瑞教授直接從民法的基本原則角度否定了知假買假行為的合法性,其認為知假買假此種不符合民法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屬于“不依市場化運營方式運作的關系,不應受到消法的保護”。[2]梁慧星教授則認為用懲罰性賠償條款來保護“知假買假”者明顯違背了《消法》規定的立法意圖,“該條規定的本意是消費者必須為了‘生活消費’而購買商品”。[3]在此基礎之上,楊立新教授還對知假買假行為可能承擔的侵權責任進行了論述,其認為知假買假行為不僅法律不能對其予以保護,甚至還應當追究消費者欺詐或惡意訴訟的侵權責任。[4]
概括以言,學界不支持知假買假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主要基于以下幾種理由:第一,知假買假者不具有“生活消費”的目的。其認為一般而言,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消費者不會在一段時間內集中購買或多次大量購買數個相同商品;第二,知假買假過程中本人并未受到“欺詐”的不當影響;第三,知假買假者沒有實際損失,不應依據《消法》獲賠,概因知假買假者對所購商品的使用價值無任何期待利益,其僅欲通過買假索取賠償,是純粹的以盈利為目的之行為;第四,“知假買假”行為有違社會道德,是投機者利用法律的歧義和漏洞以牟取私利,并非《消法》的立法宗旨所提倡,不應得到法律的保護。
(二)贊成對“知假買假”進行保護的觀點
認為對“知假買假”行為有必要進行法律保護的學者一般從“消費者”整體的利益出發,意圖通過對“知假買假”行為進行合法性認定以達到凈化市場之效用,其主要持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李有根教授直接從語言邏輯上否定了反對保護知假買假論者的觀點,其提出了一個有關保護知假買假的“悖論補充法”,即“如果不承認他們是消費者,他們就必須自己來消費這些商品,也就必然成了真正的消費者”,[5]從而以邏輯建構的方法肯定知假買假者的法律保護。
第二,從法律規定的概念闡述出發肯定知假買假者的法律保護。王利明教授認為不應以購買者的動機與目的來識別是否為“生活消費”的標準,即其認為從消費目的的本質來看,知假買假者與普通消費者都是為了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且在司法實踐中很難具體確定購買者的主觀意圖為何,故而不論知假買假者的主觀意圖為何,只要其在客觀上購買了經營者出售的偽劣產品,經營者即構成了欺詐。[6]
第三,在前述結論的基礎之上,應飛虎教授運用社會學與統計學的方法,對廣東、浙江、四川等地的消費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并結合“我國假冒偽劣產品價值”“國民人均收入”等數據,首先分析了消費者意欲尋求懲罰性賠償的邊際成本,其次進行了“專業打假團隊”運用懲罰性賠償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即其具有“私力執行成本更低、激勵更大、效率更高、負面影響更小”的優勢,在此基礎上,其認為“不能為維護某種思想‘純潔性’或邏輯上的統一性而排斥一種特殊的、有效的制度。”[7]
三、“知假買假者”應屬“消費者”的概念范疇
(一)《消法》中懲罰性賠償的法理基礎
在進行懲罰性賠償條款是否對知假買假者予以法律保護的闡釋當中,必然涉及到對其背后的法理基礎進行分析。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基本法,《消法》有其特殊的法理所在,同時作為消費者保護與懲罰性規制雙重效用共性的糅合,《消法》中懲罰性賠償條款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作為其制度設計的法理基礎。
1.社會正義觀的轉變
法律是一個與正義關系密切且隨著正義觀的進步而不斷完善和擴張的制度體系,任何法律只有從正義方面獲得合理解釋才具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羅爾斯將正義分為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按其觀點,形式正義是按照絕對平等和自由的原則分配權利和義務,而實質正義則是依據主體身份特征進行傾斜式分配。形式正義的核心是期望相同的案件將得到平等的對待,而實質正義則要求一切法律事務和社會關系中,要貫徹和體現合理、合法與正當性的原則。[8]
20世紀前的民商法貫徹形式平等的理念,這種啟蒙的正義觀以假設社會大眾在能力與經濟地位上的平等為前提,并且認為所有民事主體均應得到平等的對待,因而是一種抽象的形式平等。但是自進入20世紀以來,商品經濟的極大發展帶來多元化的交易形式,市場主體的地位有了明顯差別,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地位、能力差別亦被不斷拉大,原本民事主體間平等性與互換性的條件亦逐漸減弱。這種情況促使民商法理念從過去的形式主義轉向實質主義,給予弱勢的一方以特殊保護成為了法律的一項重要任務。《消法》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基本法,其主要目的即在于糾偏經營者利用形式正義帶來的不公問題,通過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以實現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利益的平衡與交易活動的公正,消弭因兩者之間能力與地位不平等而帶來的對公平交易的不當影響,以求實現實質公平。可以說,《消法》是實質公平理念的一個集中反映和體現,同時亦擴大了民商法中實質正義的存在空間。作為傾斜保護消費者理念的一個集中反映——懲罰性賠償,也應該以實質正義觀為基礎,制度確立與規則設計必定以實質正義為引導。
2.國家干預市場經濟
懲罰性賠償的另一法理依據即為國家干預。所謂國家干預,是指國家機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總體的、適度的管理、調控與指導。在市場經濟中,經營者為追求更多的經濟效益,在進行不法行為前往往將不法行為所獲利益與守法成本進行比較,在違法成本較低的情況下,不法行為人往往自擔風險,制造或者銷售偽劣產品,提供欺詐性服務,牟取不法利益。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市場經濟尚處于起步階段,法律制度的缺陷給不法行為人制造偽劣商品、提供欺詐性服務以巨大的可乘之機,如若國家不對市場進行適度的干預,那么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將無從保障。在此背景之下,可借懲罰性賠償制度實現國家對民商事活動進行適度干預,即通過賦予消費者一定的“獲益”,從側面鼓勵消費者與制假販假行為作斗爭,一定程度上作為國家對市場環境進行監督與把控的補充,間接實現國家對市場交易、市場環境的干預。同時,消費者運動的極大發展也呼吁國家干預對處于弱勢的消費者給予傾斜性保護,實現社會正義。
3.“私人執法”理念
一般認為,所謂執法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執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運用法律管理社會活動的行為,但廣義的執法又可分為公共執法和私人執法兩個范疇,其中私人執法則是指:“個人或社會組織依據國家法律、政策或民間習慣法對違法或違規行為進行私人監控、調查,并據此對該違法或違規行為進行威懾、懲罰或提起訴訟的行為。”[9]在匿名社會中,公共執法的信息收集成本較大,且許多類似道德義務的行為用公共權力進行糾正沒有必要且難以調整,私人執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公共執法信息收集不足的弊端,并且可以減少執法成本、有簡便快捷之優點。在具體實施上,允許私人執法者因此而獲利作為獎勵執法者的成功來對私人執法者實現激勵,《消法》懲罰性賠償條款的設立便是私人執法理念的重要體現。
(二)“知假買假”不失消費者資格
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被告對知假買假者進行抗辯的一項重要理由即為原告曾有過另案訴訟,以原告曾多次進行消費者訴訟為牟利目的進行抗辯,除此之外,被告還會以對原告購買商品、服務的數量、次數過多為由提出對消費者知假買假的質疑。必須承認的是,在不同領域、不同產品當中,法律無法對超過如何的購買數量或次數可以認定為“明顯超出生活消費需要的惡意購買”做出明確規定,這種法律規定的局限性造成了司法適用的不確定性。針對于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按照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一次購買、使用一部手機足矣,如果某人一次購買六七部手機而硬說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10],但僅以一般社會經驗作為判斷仍具有其局限性,譬如“張勇進訴江蘇時代超市有限公司如皋店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原告購買的用于捐贈給慈善機構及職員福利待遇的1187條羊毛褲雖然不屬于為自己生活消費而購買,但其購買并不是為了經營性目的,雖然最終直接使用商品的個人不是合同的當事人,但也被法院認定為了消費者。故而不能僅憑借數量、購買次數的因素而斷定購買者是惡意購買不受懲罰性賠償條款的保護,應當在其基礎之上參考其他因素。具體而言,消費者對商品的消費方式包括消費者購買商品供自己生活消費(購買并使用),也包括使用他人購買的商品的生活消費(使用),同時包括購買商品給他人使用的生活消費(購買),購買數量不應該受限制。
從經營者的角度出發,經營者如若進行抗辯,需要證明提出索賠的購買人為“惡意購買人”,認定惡意購買人可通過證明購買人購買商品是出于銷售經營的目的,只要其在購買時是為這一目的即為己足;或者提出索賠的商品或服務是經過之前的訴訟中處理過的,可以說這是“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變式。而針對其他未被《消法》第55條第1款處理過的商品或服務的處理則不在此列,也就是說購買者針對其他產品的另案訴訟,不能成為在此案中認定其為惡意購買人的理由。
基于以上闡述,管見以為,在認定“消費者”的司法實踐中需要明確以下幾點:第一,不能以購買者購買的數量、消費標的的大小、消費者是否系購買者本身、消費者是否以前提起過相似案件的訴訟等作為判定其是否為消費者的標準。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瑕疵而購買的民商事主體,只要其購買商品不是為了銷售,或為了再次將其投入市場交易,就不應當否認其為消費者。“‘勿為不法’固然可嘉,‘勿寬容不法’尤為可貴”[11],經營者不法的欺詐騙局并不會因為被消費者識破而變為合法,換言之,對于“知假買假”者只要其不是為商品的再交易而購買之人,就應當認定為消費者,其購買的動機和目的不屬于法律調整的范疇。第二,不論該商品屬自用、他用,是否知假買假等,只要是在貨價上明碼標價陳列,均視同商品,可成為消費者購買對象。
四、結語
“王海現象”的出現引發了學界關于“消費者”概念的理論爭議,綜而觀之,其核心爭議點在于知假買假者能否認定為消費者的理論紛爭。以懲罰性賠償條款的解釋適用為論證中心,通過對知假買假行為中“生活消費”與“受到欺詐”兩個核心構成要件進行理論闡述,提出對知假買假行為法律性質的反思。在遵循前述思路的基礎上,加之以懲罰性賠償條款設立的法理作為理論支撐,能夠得出知假買假亦應當受到懲罰性賠償條款保護之結論,從而為“消費者”概念的內涵進行一個理論重構。以明晰其概念的內涵為基礎,希冀于為我國司法實踐中統一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
注釋:
①1995年,22歲的山東無業青年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購買了12副假冒索尼耳機,然后徑直向東城區工商局投訴,依據原《消法》第49條,向隆福大廈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這讓王海聲名鵲起,伴隨聲譽而來的還有打假巨額賠償。時隔不久,王海籌資20余萬元購買了假冒品牌電池,成功索賠40余萬元。此后他四處購買假貨然后向商家索取雙倍賠償。由于他的打假行為帶著鮮明的牟利動機,一時間在社會上引發熱烈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