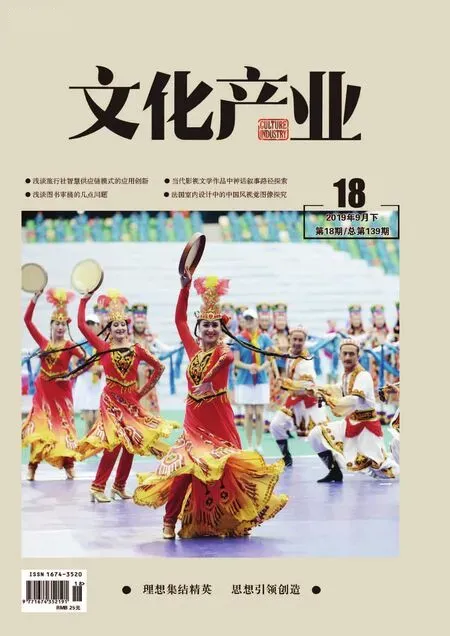樂山邊河號子的藝術特色與傳承現狀
◎雷海燕
(樂山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 樂山 614000)
四川省地形西高東低,河流眾多,其中金沙江、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等河流,長度皆超過500公里。在這些水系上,航運發達,貿易往來眾多,當枯水期無法正常航運時,船工這一職業便應運而生,與船工活動密切相關的號子也隨之產生。金沙江號子、岷江號子、沱江號子、涪江號子……幾乎四川所有江河中都有號子的影子。
號子的產生與船工的工作密切相關,船工也稱纖夫,纖夫是當船遇到險灘惡水或擱淺時,以纖繩幫忙拉船的人①。號子就是纖夫們在拉船時哼唱的歌謠,其目的是協調全船船工的步伐,鼓舞眾人的情緒,把力氣用到同一個節奏上,以眾人身體的力量拖動船前行。也就是說,號子對于拉纖起著巨大的協調作用。
樂山市是一個水系發達的地區,孕育出犍為縣的岷江號子、沙灣區的銅河號子、馬邊縣的邊河號子等。其中岷江號子和銅河號子較為出名,邊河號子受到的關注較少,但是又獨具特色。
一、邊河號子的形成環境
邊河號子產生于馬邊河流域。馬邊河源于馬邊彝族自治縣,于犍為縣匯入岷江。共流經馬邊、沐川、犍為三縣,來源于深山,流過草地,從山谷沖出,河水清澈,像一條碧綠的玉帶環繞著群山,被稱為“清水溪”。唐朝詩人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清溪”,所說的就是馬邊河②。
邊河號子的形成與其復雜的地理環境有關。馬邊河流域河床狹窄、彎多、灘陡、水流湍急、明礁林立、暗礁密布,行船難度大,時有事故發生。地勢最危險處便在火谷,船筏順流而下進入火谷境內,首先是經過長約500米的橋墩溝灘,前面河心又是一塊兀立的巨大老鴉石,繞過此石,船還未打正,就到了九龍灘,此灘由苗兒腔處的險峻高山上滾落的巨石形成,不諳水道者行船必出事無疑。如果在夏天,山上滾落巨石,一不當心就會船破筏散。馬邊河最慘重的一次行船事故發生在1946年黃丹下渡口狗腳三灣灘,這個灘因連續三灣三灘而得名。一天之內竟因水急灘險打爛三艘木船,損失煤炭70多噸③。跋山涉水、日曬雨淋,雖然艱苦,但也遠遠沒有翻船讓纖夫們這般恐懼。船只一旦翻掉,纖夫往往非死即傷。
二、邊河號子的音樂藝術特色
(一)大量采用虛詞,幾乎沒有實詞
與同屬樂山地區的岷江號子和銅河號子不同,邊河號子收錄的歌曲中沒有具體的內容。岷江號子和銅河號子唱詞內容豐富,有描寫歷史故事的,也有描寫神話傳說的,甚至有日常生活中的黃段子。而邊河號子通篇的歌詞多用單音節或短語,很少用句子。有拉纖時的動作行為,如大量重復“走”“來”等字;也有表示對答的,如《滕耳》里面的“江嘞”“蹬嘞”和“陡陡起”“穩嘞”等。
除此之外,虛詞占大量篇幅,主要的作用就是協調步伐,用虛詞呼喊統一的口號來保持動作一致,包括“將嗨嗨”“咗嗬咗”“嗬嗬”等都是開口音,使用這些開口音有利于振奮船工們的精神,使船工們的情緒得到調節,起到消除疲勞的效果。盡管這些唱詞只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襯詞,但它使船工們配合默契,使號子的實用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它不僅把船工們的喜怒哀樂融入其中,還包含著船工們對自然的思考,以最適合的姿態面對著不可控的滾滾河水。
(二)“一唱眾合”,回聲效果突出
川江號子的演唱形式多種多樣,有獨唱、對唱、齊唱、一唱眾合等演唱方式,其中“一唱眾合”是眾多號子中最常見、最基本的演唱方式④。作為川江號子當中的一種,邊河號子的演唱也多是采用一唱眾合的方式,領江領唱,眾人齊唱。領江是整個船工隊伍中的領導者,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他在演唱中起的是一個帶頭作用,在整個號子的演唱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據采訪,沒有了領江領唱,整個號子將無法進行。眾人合唱的部分音樂變化少,唱詞多是以重復詞、襯詞為主,領唱開唱,幫腔也隨之而來并總是后于領唱,形成兩個聲部,采取遲緩半拍、強調重音、減弱尾音的方法,使演唱具有強烈的回聲效果⑤。這樣的回聲效果也與馬邊河流域的地形息息相關,馬邊河地區群山環繞,多為峽谷,號子一喊,號子聲便在山澗之間回蕩,空谷傳響。
三、邊河號子逐漸失傳的原因
邊河號子在音樂領域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可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邊河號子當下的生存環境并不樂觀。
1961年后,隨著沐馬公路、沐黃公路相繼通車,貨車轉向公路,汽車運輸較水運更方便快捷,木船的使用慢慢退出歷史的舞臺。1995年黃丹電站建成投運,馬邊河的水量由大變小,以往充滿著暗礁險灘,波濤洶涌的馬邊河不復存在,木船的生存空間更加狹小。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交通方式出現在人們生活中,木船的使用漸漸成為歷史。原來拉纖的船工再也沒有了工作崗位,紛紛尋找新的工作,號子的發展也就止步于此。
邊河號子沿襲了我國民間音樂的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曲調大多數是船工們根據行船途中所遇到的具體情況編制而成,基本上都是現場編唱,即興作詞,在用詞造句上沒有嚴格規定,比較自由和隨意。這種演唱方式也不利于后期的收錄和匯編。同時,傳承方式封閉,只是在船工之間傳唱,為后期傳承也增加了難度。如今,當年在馬邊河上拉纖的船工都已經上了年紀或已去世,目前并未發現有視頻、錄音資料,遺留的僅僅只是部分書面唱詞,而當今絕大多數人都沒聽過甚至不知道這類號子。
邊河號子的曲譜只留存了三篇,被收錄在《四川民間歌謠集》,而馬邊、沐川、犍為三地幾乎沒有其他的資料可供后人參考,作為地方特色的音樂形式并沒有得到如岷江號子、銅河號子一樣的重視,關于邊河號子的記載只有個別論文上的寥寥幾筆以及收錄的三篇曲譜。邊河號子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困境,古老的民間藝術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
四、邊河號子的精神內涵
船工要靠自身力量拉動千鈞重的大船,就必須依靠于彼此之間的團隊協作,邊河號子的作用就在于此。眾人步調一致,高喊出邊河號子,共同面對路上的風風雨雨,擁有無堅不摧的力量。船工靠人體力量拉動著數噸重的大船,走過崎嶇的道路,渡過無數激流與險灘,從未因道路艱難而止步。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們能用號子來調節情緒,集合力量,更是體現出了船工們的智慧,這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值得我們傳承和弘揚。
邊河號子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民群眾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文化遺產。它根植于樂山的山水之中,融于樂山文化之中,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社會學價值不可估量。對它的保護研究與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纖夫百度百科。
②《犍為縣志》(1818年版):“清水溪,亦名清溪,縣南二十里,發源馬邊廳煙草峰,經屏山縣界,合峽溪、龍盤溪、楊溪、漏眼溪諸水至縣界孝女渡,入大江,是名清溪口。”
③段遠洪:《馬邊河的“坎坷”航運》,海棠社區論壇http://bbs.leshan.cn/forum.php?mobile=2&mod=viewt hread&tid=663656。
④楊浩然:《民間歌謠之勞動歌》《青年社會》,2015年,3月上第7期總第589期,第182頁。
⑤楊羽健:《關于川江船工號子(下)》《四川音樂》,1984年,第5期,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