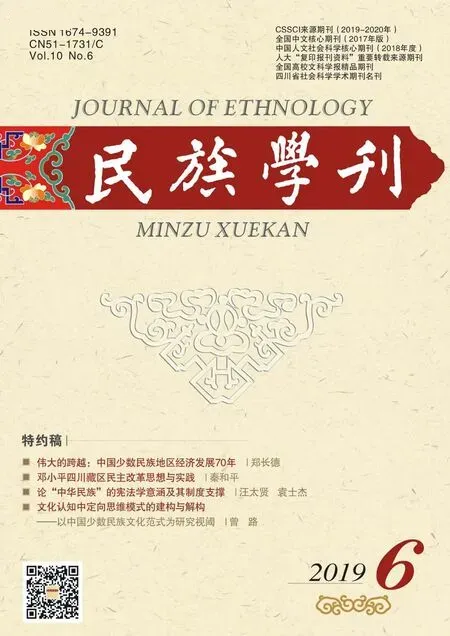白壽彝先生的民俗學實踐與理論
白壽彝是我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領域廣泛,涉獵中國通史、民族史、回族史、史學史等諸多領域,白壽彝的具體研究成果為世所重,其中相當一部分反復被前人申述,前賢時彥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1]白壽彝歷史研究的特點之一是關注社會下層和民風民俗,但專門從民俗學角度來研究其學術和思想的似乎尚不多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俗學研究蔚然興起,顧頡剛先生等當時民俗學研究的代表學者,意圖通過民俗研究改造社會下層,喚起民間的力量,救亡圖存。白壽彝作為顧頡剛先生的學生,深受其影響。一方面向下看社會下層歷史,一方面把民俗學與古史研究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與風格。
白壽彝就學于顧頡剛先生等民俗學界的老一輩學者多年,因而在其早年的學術生涯中,民俗學是其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方面白壽彝的成果雖然是吉光片羽,但是在民俗學研究方面,白壽彝卻依然持之以恒,新中國成立以后直到晚年仍持續關注,發表若干論文。其民俗學研究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白壽彝的民俗學的實踐,一個方面是白壽彝的民俗學理論研究。前者又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收集歌謠,二是撰寫論文;后者白壽彝具體探討了民俗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從實踐到理論是白壽彝民俗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特點也包含在白壽彝的其他學科的研究當中。
瞿林東先生曾經將白壽彝的史學理論風格凝練為“白壽彝史學”,[2]這一概括能夠反映白壽彝的史學實踐與史學理論,就民俗學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講,白壽彝也是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來看待民俗學研究民俗學的。白壽彝的民俗學研究應該納入到“白壽彝史學”的體系當中。對白壽彝的民俗學研究作一梳理具有一定的學理意義。
一、白壽彝收集的《開封歌謠集》
《開封歌謠集》是白壽彝在河南開封進行民俗學田野調查的實踐成果,這與白壽彝的民俗學理論性研究成果有較大區別,是二十世紀20、30年代收集地方歌謠集的代表性作品。這本書耗費了白壽彝不少時間,其間曾經散落一次,在朋友的鼓勵下,重新收拾,再起爐灶,重新編纂了這本小書。
這本書由廣州中山大學1929年出版。其中收錄了兒歌47首,婦女的歌15首,車夫的歌4首,囚徒的歌1首,游戲歌1首,儀式歌2首,矜智歌2首。正如白壽彝所說:“歌謠中所反映的事物,今昔已大不相同。時代為這些歌謠增加了地方性社會歷史的信史光彩”。[3]835積極地發掘地方史料,為地方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是白壽彝那代學者認為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目的就在于改造社會,喚起民間的力量。《開封歌謠集》是研究開封當時民俗民風的重要資料,同時也可以從白壽彝對資料的擇取觀察其學術思想。以下僅以此書為中心,略作一番分析考察。
(一)兒歌。兒歌第7首原文自錄如下:“小雞兒,要吃黃瓜;黃瓜辣嘴,要吃牛腿;牛腿有毛,要吃仙桃;仙桃有胡,要吃牛犢;牛犢撒歡兒,撒到天邊兒;天邊兒有個小井兒,撲騰掉里沒有影兒”。[3]838
這首兒歌不僅押韻,而且體現了兒童純正的童真。反映了當時開封地區兒童的生活的歷史鏡像。
又如第40首,寫過大年的情形,是很可以反映開封當時的基本情況的:“二十三打發灶爺上老天,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拐豆腐,二十六割塊肉,二十七殺個雞,二十八殺個鴨,二十九蒸饅頭,三是挑旗兒,大年初一兒,撅屁股亂作揖兒”。[3]856不僅僅描寫了當時的開封過大年的基本風俗,更體現了當時開封的兒童在過年時候的喜悅之情,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的開封民俗的具體情況。
仔細分析這些兒童歌謠,還可以有如下認識。在這一系列的兒歌當中都有孩子們熟悉的動物,熟悉的瓜果蔬菜等豐富的內容。這些小動物有貓、有小蛐蛐、有馬、有雞、有烏鴉、有牛、有狗、有鸚鵡、有蒼蠅、有猴子、有蛤蟆、有鴨子、有蜈蚣,有蜜蜂、有大雕。這些動物都是孩子們經常可以見到的動物,進入到民俗中的歌謠當中,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孩子們接觸到的常見生活中的動物,是孩子們動物情趣的體現。也是孩子們開始初步認識世界,認識生活的重要源頭之一,兒童的認識從最切近身邊的事物開始。
這些兒歌里面有很多常見的瓜果蔬菜花草植物。如黃瓜、桃子、花生、大蒜、茄子、瓜子、西瓜、菠菜、小蔥等;植物有牡丹花、迎春花、海棠花、棗花、棉花、菊花、丁香花、石榴花等。這些事物都是兒童經常接觸的,之所以能夠流傳在歌謠當中,這說明這些是兒童們經常接觸經常遇到的,所以別有一番情趣蘊含其中。可以說現實的生活是觸發兒歌產生的原因,兒童們通過這些歌謠獲取自己必備的知識。
這些兒歌里面除了上文提到的春節,還有臘八節,可見白壽彝對于節日民俗是相當重視的,有意識的從兒歌當中收集與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的民俗歌謠。民間歲時節日通過歌謠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關于歲時節日的發展與流變,鐘敬文先生主編的《民俗學概論》有專章討論,這里不一一贅述了。[4]
在這些兒歌里面還提到了一些社會現象,比如繼母現象,體現了小女孩失去親生母親,父親取了繼母之后的悲慘遭遇。這里就特別體現出來了民俗學工作者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來改造社會的意圖,傾向性非常明顯,下文還要繼續討論。還有關于師生之間關系的幽默歌謠,如第44首,就反映了這樣的內容。還有關于兒童家庭生活的歌謠,比如一家十個閨女的女婿的職業情況,這在第37首里面反映得特別突出。
這些兒歌從生活的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開封兒童的民俗情況,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對于了解當時的人情風貌、地方習俗、社會環境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今天看來,也頗為有趣。
(二)婦女的歌。婦女歌里面收集了沒有出嫁的小姑娘,收集了在夢里想著遠嫁的新娘,收集了在尼姑廟里面有相思之苦的小尼姑,收集了年老體邁的母親的無助等。其中尤其以待嫁閨中的新媳婦和大姑娘的歌謠為多。
如第54首:“新媳婦兒,心腸窄;小兄弟兒,來請姐:搬個板凳兒你坐下。掀開門簾兒去打扮:梳油頭,擦粉面,頭上戴那九鳳冠;紅軸小襖套藍衫,藍衫上頭套云肩;紅綢褲兒,五色帶兒,小金蓮兒賽似藕牙兒尖;想戴鐲兒,嘩啦響,滿把戒指兒翠發藍。叫丫環鋪紅氈,拜上婆婆住幾天!天又短,路又遠,那宗閑事我不管。好咧,住半月,不好,住十天。”[3]868-869
把一個心地不那么寬敞的小媳婦的形象活脫脫地寫在了紙張上。在關于婦女的歌謠里面,關于婆媳關系的歌謠占了相當的部分,從歌謠的形式來看,當時的社會婆媳關系也是不好處理的,當然,復雜程度比今天還是要略微低些。白壽彝收集的這些資料為我們考察當時的家庭內部關系提供了很好的民俗材料。
其他如尼姑身在佛門的相思苦,經過白壽彝的整理也躍然紙上,即第51首,把一個小尼姑身在佛門卻心在人間的細膩心理描繪得非常入微。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舊的禮教對于婦女們的精神摧殘,同樣也是不可多得的社會史資料,而通過歌謠的形式反映了出來。
又如養老問題,在今天是一個社會問題,在當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中國傳統社會“養兒防老”的思想非常濃重,但是置老人于不顧的現象也比比皆是。婦女的歌謠第61首表現了這一困窘的情形。
原文如下:“拐棍兒一,拐棍兒一,兒哩飯好難吃!拐棍兒兩,拐棍兒兩,拐棍兒倒比兒還強!拐棍兒三,拐棍兒三,兒哩衣好難穿!拐棍兒四,拐棍兒四,婆子是媳婦眼里一根刺。拐棍兒五,拐棍兒五,為兒不知當年娘受苦。拐棍兒六,拐棍兒六,臨死落個干饅頭!拐棍兒七,拐棍兒七,萬貫家業娘治哩。拐棍兒八,拐棍兒八,萬貫家業不當家。拐棍兒九,拐棍兒九,莊田地土帶不走。拐棍兒十,拐棍兒十,送到南北坑兒里沒人提。”。[3]875-876把一個母親對兒子的無奈表現得淋漓盡致,把婆媳關系演繹得形象生動,把作為母親對兒子的愛和無奈交融在一起。這是歷史的民俗,也是現實的民俗,如何破解這樣的難題,不僅是當時人的問題,也是我們現代的問題。從這則歌謠結合我們當今現實來看,隱喻中包含著巨大的反諷。社會進步了,思想觀念沒有更新;社會進步了,人情冷暖卻沒有得到改善。現代社會的有“現代病”,現代社會也有“傳統病”,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如上所論,對于改造社會,改變社會風氣,喚起民間的力量是有指導作用的,放在當時如此,放在當下也可借鑒。
(三)車夫的歌。如65首,原文如下:“手拿洋車桿,出門做了難,拉夠半價沒面錢”。[3]878體現了白壽彝對于下層的注意。我們傳統社會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王侯將相的歷史,都是英雄的歷史。廣大的勞動人民被淹沒在英雄的歷史當中。傳統社會的文人士大夫很少注意下層的歷史,民俗學引導著白壽彝這代學者,不僅具備向上看歷史的意識,同時具備向下看歷史的情懷。這里對于車夫的關注,就很好的體現了白壽彝收集資料的用心。
在歷史的創造者的問題上,王侯將相是歷史的創造者,普通的販夫走卒同樣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推動著我們的歷史不斷向前進。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歷史也是人民創造的,英雄和人民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推動著歷史的車輪不斷前進。[5]白壽彝從一個愛國主義史學家走向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前期尊重人民的愛國主義史學家的特點,從后期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民俗學的理論分析更可以看出他的這種不俗的理論修養。這里將在下文繼續討論。
又如對囚徒的歌,也表現了上述的向下看歷史的這種意識。原文過長,僅錄幾句:“二月哩,龍抬頭,酒肉哩朋友結下冤仇”;“六月里,熱難熬,手把監門兒往外瞧;穿靴戴帽有多少,沒有一人來瞧瞧”;“十三月,一年多,大老爺堂前領酒喝,好酒喝哥叮叮醉,到了西關把頭割”。[3]879-881這種向下看底層的歷史,從二十世紀20年代、30年代就有了這種強烈的意識,而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是當時學人學界的風氣使然,是當時學人學界希望通過對社會底層的發掘與再造,進行國民性的改造的認識,是對民族的一種負責精神的體現。從白壽彝收集的歌謠就可以看出來一些表征。
以上我們擇取白壽彝《開封歌謠集》中的一些歌謠進行了不成熟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壽彝的民俗學實踐的一些特點。一是關注現實生活;二是關注社會問題;三是符合民間文化的特點;四是有一種較強的關注底層的意識。對于歌謠集中的其他部分,同志們也可以做類似的爬梳,得出相關的結論。
二、白壽彝的古代民俗研究
白壽彝作為一位歷史學家,雖然民俗學成果不多,但他的作品可視為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果說《開封歌謠集》是白壽彝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對民俗學的具體實踐。那么白壽彝為數不多的研究類文章則可以看作他將這種實踐內化為理論的研究。白壽彝早年的民俗學研究的代表作品《五行家的歌謠觀》體現了他民俗學研究的興趣。
(一)《五行家的歌謠觀》
《五行家的歌謠觀》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白壽彝的民俗學力作。[6]二十世紀20、30年代中國形成了一股整理研究民俗的高潮。僅出版的刊物就有《歌謠周刊》《北大國學門周刊》《北大國學門月刊》《民間文藝》《民俗》等。出版的歌謠集也在10鐘以上之多。
白壽彝認為五行家的歌謠觀的重要之處在于能夠預測將來的事,尤其是能夠預測將來能夠發生的災害的事情,這與五行家能夠成家的本質特點是一致的。如五行家能夠預測到個人的不幸,能夠預測到社會的騷動,能夠預測到軍事的失敗,能夠預測到政治的變亂。
白壽彝引用《漢書·五行志》歌謠說明了趙飛燕的命運;引用《晉書·五行志》歌謠說明了諸葛恪的命運;引用《后漢書·五行志》說明當時社會騷動的情形,同時引用該書說明更始軍事上的失敗;引用《明史·五行志》歌謠說明代政治上的變亂。
在反復爬梳這些資料的基礎上,白壽彝還從古代歌謠里面還得出了歌謠能預示一個人發生不幸的地點和時間的結論。對于這些古代五行家的歌謠,有一個別名,叫“詩妖”,相信這些歌謠的人認為這些歌謠是有一定的預示意義的。白壽彝認為這種對歌謠的預示功能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而不見得就是為了采風問俗,而是具備一定的政治意義的。這無疑是一種破的之見,這和當時的古代民俗學觀點不完全一致,即民俗學功能的政治化,而不僅僅是文化意義上的。這也是利用歌謠進行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后文還將繼續討論到。
對于歌謠觀念的理由,白壽彝通過對正史的仔細爬梳,得出了三個觀點:一是誹謗說;二是熒惑說;三是感應說。對于誹謗說,白壽彝認為是人們相信了歌謠的神秘力量;對于熒惑說,白壽彝認為是由于天上的神意所教授,傳給兒童唱的;對于感應說,白壽彝認為是歌謠為感,災禍為應,或者是災禍為感,歌謠為應。
在上述三種分析中,以誹謗說影響最大,自漢以來尤甚;感應說取宋儒的思想;而熒惑說最少為五行家所取。所以說歌謠形成觀點也是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變化的。
這篇民俗學的論文不長,但是白壽彝能運用正史資料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文獻功底扎實,對于正史相當熟悉。第二:邏輯分析能力很強,與白壽彝早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有極大關系。第三:具備一定的田野意識,能夠結合古代與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判斷歌謠的性質。這是白壽彝在這個階段民俗學研究的基本特點。
(二)《殷周的傳說、記錄和氏族神》
到了二十世紀60年代,白壽彝的民俗學研究顯示出了較為恢廓的姿態。時代的腳步總是推動著學者們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研究視角、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也發生著相對的變換。史學工作者不可能不受到時代的影響,史學工作者的作品也對時代產生著作用。
二十世紀60年代,白壽彝的民俗學作品屈指可數,但是體現出了如下若干特點。第一,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傳統史學加以重新分析,重新對某些古史進行有探索性的研究與嘗試。第二,能夠利用當代學者(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成果與自己的研究心得較好地結合在一起。第三,能夠對原來的不被人重視的歷史資料給予新的闡釋。第四,從某種程度上講,適當的擴大了歷史學與民俗學的交集。第五,傳統史學方法的運用依然體現在了白壽彝的具體研究當中,一是扎實的文獻功夫,二是“以文見史”方法的運用;對經典文獻的選擇、處理和使用精準恰當。這些都體現了白壽彝的文獻功底。第六,對學術研究中的不當觀點給予批判。第七,能夠運用民俗學發現古史研究中的新問題,并做出新結論。
最能夠體現白壽彝上述七點內容的就是白壽彝的將歷史學與民俗學結合的力作《殷周的傳說、記錄和氏族神》。[7]從這篇論文我們可以看出上述七個方面的特點。可以說這篇論文是白壽彝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后,結合民俗學結合歷史學對古史研究進行的新的嘗試與拓新。
這篇論文白壽彝結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反杜林論》等經典作家的論述,探討了殷周時代的傳說中記載的神話故事與現實的情況。通過對文獻的分析,結合理論的指導,具體的探討了殷周時代的著名人物,有夏朝的大禹;殷朝的契;周代的后稷。
在這篇論文中,白壽彝指出,當時的社會已經處于奴隸制社會,但是對于這樣的文字記錄卻是缺乏的,只能從后來的文獻中給予發掘和考察。而這一時期的氏族神也只能是神話或者故事,氏族神在這些記錄中占據了相當的份額。傳說與神話不是民俗學所獨有的觀察視角,同時也是歷史學觀察歷史的源頭的重要視角。雖然傳說與神話不具備嚴格意義的“信史”作用,但是傳說與神話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繼承性與延續性,蘊含先民的歷史意識。[8]
對于大禹的分析,白壽彝分析了大禹作為夏后氏的始祖,具備很多的能力,比如他的力量能夠達到四方,又如他的能力具備平定水土,同時大禹還能夠奠定山川,而這些能力的具備都是上帝賜予的,大禹在這里就是上天的兒子,代替上天執行天上的神在人間的旨意,因此大禹既具備天上神的資格,也是地上神的代表。通過對資料進行排比,白壽彝肯定了記載大禹的舊時代傳說的主要事跡。
在論證大禹的時候,白壽彝采用了《書》、《詩》、《國語》、《楚辭》等基本資料,對于《書》、《詩》、《國語》,白壽彝仔細排比材料,對于《楚辭·天問》則給予了高度關注,這顯然是利用文學資料來證明歷史問題或者民俗問題,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白壽彝對于材料的選擇是謹慎的,他認為《楚辭》作為戰國晚期的作品,記載大禹的事跡不是原來的模樣,(這應該是受到了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的影響)但應該保存了那個時代或更早時期的傳說的內容。這是因為作為文學作品的《楚辭》沒有像專門從事歷史的工作者那樣去構建一個較為系統的古史譜系,既不存在改造古史,也不存在拼湊古史。從內容上看,大禹的事跡沒有超越《書》、《詩》的范圍,在內容上與這些歷史史料具有一致性。對于《楚辭》的記錄,白壽彝不是一概而論,他結合王逸的見解,認為同時這些記載的大禹的材料從壁畫的角度看,更有接近原始的大禹更多的地方,而《楚辭》可能有附加的成分在里面。而這也是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的。
這樣大禹在他所處時代的基本情形就被勾勒了出來,歷史材料和文學材料的并用使得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認識到一個遠古時代的大禹的形象,大禹的氏族神的形象被勾勒了出來,這是白壽彝的重要貢獻。
在后面分析契和后稷的時候,白壽彝同樣體現了深厚的文獻功底。關于白壽彝的文獻學功底,白壽彝自己有一段回憶:“我在燕京的學習生活雖然只有三年,但對我日后所從事的各項學術研究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工作,實際上使我在歷史文獻學方面也得到很好的鍛煉。”[9]早年對于朱熹的研究工作,為白壽彝打下了較好的歷史文獻學功底,這些都成為他日后源源不絕的學術提升的活水。
對于契的分析,白壽彝引用了《孟子》、《荀子》的材料,但是白壽彝認為這些儒家的正宗學派的學者是按照儒家的思維說了一些空話,沒有實質性的討論。更早的資料還是要從《詩》入手,而白壽彝正是這樣做的。分析了《詩》對契的記載。
當然對于具體的文學資料,白壽彝的分析是文學資料的可信度還是較歷史資料的可信度略低,通過對文學資料之間的排比,有的文學資料可信度高,更可以作為史學資料進行運用。整體上看,文學資料可以作為旁證,不可作為實證。于細微之處觀察歷史,如《商頌》中有一句:“帝立子生商”,白壽彝認為這個“立”字在這里下得很重,資料的仔細爬梳,對于一個字在全文中的分量,白壽彝都是沒有放過的。
白壽彝認為契跟大禹不一樣,通過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是天上的神,但是不一定看作是地上的神。對于后稷,在生前,白壽彝通過資料分析,還不能算是神,但是到了死后,才具備了神的資格,而后稷在死后被看作是上帝的子女,成為地上活動的神。
大禹既是天上的神,又是地上的神;契是天上的神;后稷是地上的神。這是白壽彝通過分析甲骨金文、《易》、《書》、《詩》、《左傳》、《楚辭》、《山海經》、《孟子》、《荀子》、《墨子》、《呂氏春秋》等傳統文獻作為自己的立論支持,這些材料是研究上古時代的典型材料。
同時白壽彝又結合經典作家的研究對當時的群婚現象、母系社會、父系社會給予了剖析,與此同時,對于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白壽彝也給予積極地吸收,如對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對郭沫若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對侯外廬先生的研究成果,盡力給予吸收。這體現了白壽彝善于利用當代人的成果為自己所要討論的問題進行針對性思考。對當代人關于這一時期的研究結論不當,白壽彝也給予批評,如對李玄伯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就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白壽彝最終得出了這些氏族神的“天下化”和“地域化”的特征,并且進一步指出:“殷周時期關于氏族神的傳說和記錄,曾經長期地被學者們簡單地看作神話和迷信。至于它們是中國歷史記載的萌芽,它們本身也有自己的發展階段并反映不同階段的歷史內容,這是很少被注意的。這是我們應該予以發掘的”。[7]
白壽彝這一階段的民俗學研究明顯帶有他所處時代的烙印,如對神的討論,如對群婚制的討論,如對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的討論,如對氏族圖騰的討論,如對這些氏族神如何轉變為政治寡頭的討論,都反映出了他那個時代學術研究的風氣和學術研究的熱點,時代反映史學,史學反映時代,這是一個互相作用的過程。
如果仔細比較新中國成立前后的這兩篇白壽彝的代表性論文,我們不難看出,新中國成立前,白壽彝的民俗學研究特點重點在于開啟民智,破除迷信思想;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的民俗學研究特點重點在于如何將歷史學與民俗學結合,研究中華民族的古史問題,而這一問題涉及先民的族源問題,是在為我們尋找中華民族的根,而這點,在今天看來,對于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還有一定的學理價值與實踐價值,至少為我們廓清古史的迷霧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白壽彝晚年的民俗學研究及其理論啟示
白壽彝在二十世紀20、30年代對民俗學進行了一定的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也進行了一定的相關研究工作。這些工作的成就取得,來自于白壽彝的高深學養。也來自于他的老師們對他的啟發和影響。
中國民俗學在二十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改革開放以后,再次繁榮起來。白壽彝在這個時候提出,要建立屬于中國的民俗學,要編著中國人的民俗學史。瞿林東先生曾經回憶到白壽彝和鐘敬文先生多次交流,白壽彝與鐘敬文先生提出要寫出厚重的中國民俗學史。[10]這是老一輩民俗學工作者的歷史貢獻。
關于歷史學與民俗學的關系,白壽彝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一篇論文當中較好的闡釋了他對歷史學與民俗學的基本看法,可以視為白壽彝對歷史學與民俗學看法的一個基本理論定位。白壽彝認為:“研究歷史,不能完全擺脫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歷史的解釋”。[11]這就是對歷史學與民俗學兩個學科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概括。我們可以這么認為,白壽彝這時候已經把自己對民俗學的實踐,對民俗學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個理論的層面:認為要建立屬于有中國特色的歷史民俗學。與此同時,認為歷史學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是一種互相支援的學科,體現了白壽彝的學科交叉意識的理論興趣。而在白壽彝涉及的相關領域,白壽彝通過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扎實的理論分析,都能夠將某一領域的研究上升到一個理論的層次,對民俗學而言也可做如是觀。這正是“白壽彝史學”的風格與特點所在,①也是民俗學的風格與魅力所在。民俗學與歷史學作為姐妹學科,應該要有這樣一種學科交叉意識。白壽彝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較好的示范效應,老一輩民俗學工作者和歷史學工作者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示范和榜樣,我們有理由把他們作為標桿,推動和進行我們的研究。
結合上面的具體論述,從白壽彝的具體民俗學實踐與研究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以下若干應該可以成立的結論:第一,民俗學與歷史學有交叉的學科研究視域,兩個學科之間有交相互補之處,歷史學者應該關注民俗學研究,民俗學研究也應該借鑒歷史學研究成果;第二,民俗學需要研究者俯下身體向下看,要有充分的實踐性,充分發揮民俗學接地氣的學科優勢,真正開啟民智;第三,民俗學要有一定的理論作為指導,這主要表現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體學術范式指導;第四,民俗學要充分地將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互結合應證,才有可能得出堅實可信的結論,民俗學應該重視考古成果和相關學科成果;第五:民俗學的存在是歷史的發生過程,在這個發生過程中,需要民俗學研究者和歷史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尋找屬于學科之間的“類本質”的共同點,尋求“類本質”的共同點,是為了構建學術共同體的研究范式,同時,也要看到民俗學與歷史學及其它學科確實存在學科分野的實際情況,進而推動民俗學研究,充分注意到民俗學的獨立性和與其它學科的學科交叉性。
我們可以這么認為,白壽彝為我們留下的是民俗學的實踐、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民俗學的理論,這三個層次是一步步向前推進的,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進程。這也正是我們今天需要的一種踏踏實實的進行學術工作的態度,白壽彝通過他的民俗學研究為我們展示了這樣生動的一課,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白壽彝留下了他對民俗學的理解,留下了他對民俗學的實踐性認識和理論性認識,對我們今天的民俗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與借鑒價值,從學科交插與融合的角度來看,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筆者后學,只能就所掌握的材料對白壽彝的民俗學實踐與理論作出這樣一種勾連,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以作引玉之磚,不當處愿聞學界前賢時彥宏論。尚祈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注釋:
①在筆者閱讀這篇文章和相關文章的時候,發現至少有七篇文章直接參考了白壽彝的這篇文章中的思想和內容來豐富各自不同的民俗學研究觀點。這七篇文章茲錄如下。烏云娜《艾伊絲蒙古族風格打擊樂團的傳承與變遷》,《當代音樂》2016年第3期。陳金文《論中國民俗學研究本體的構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朱新屋《閩北走廊與物的流動——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蕭放《中國歷史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論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王曉麗《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討論民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4期。張文生《歷史學與民俗學關系析論》,《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陳福康《論鄭振鐸的文學遺產思想》,《學術月刊》1987年第12期。在這七篇文章中,有一篇對白壽彝的文章的材料略作修飾,直接使用,這里筆者不想對該作者的行為有什么評價,只想通過這一事例說明白壽彝在民俗學資料的選材上確實有后人無法繞過的地方,故而后學只能依據白壽彝成熟的民俗學研究成果為自己的文章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