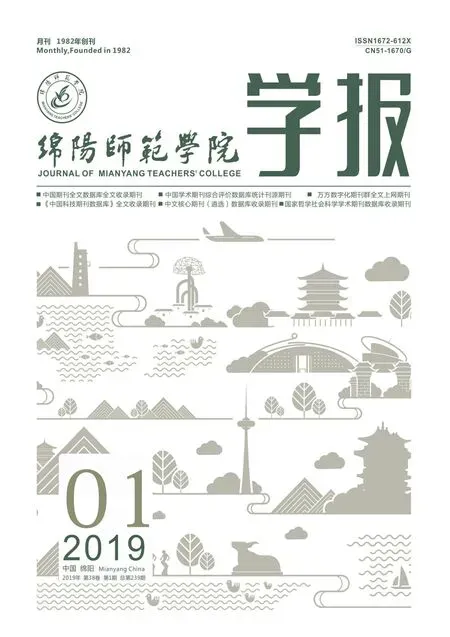從加繆的“荒謬”看救贖何以可能
何剛剛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 250100)
一、荒謬哲學之“荒謬”及其“救贖”
(一)“荒謬”的歷史流變
“荒謬”一詞來自于拉丁文,意思是“不合乎曲調,無意義的”。“absurds”其前綴“ab”作用是加強語氣,后綴“surds”意思是“聾”或“被蒙住”。由此推斷,“荒謬”是人感覺的一種判斷,主要是指一種直觀感受,而且在主體看來這種直觀感受是非理性甚至無意義的。從西方哲學來看“荒謬”具有深遠的歷史背景。基督教哲學家德爾圖良就曾說過“因為荒謬,所以相信”。在德爾圖良這里“荒謬”一詞已經不同于日常用語,而是帶有哲學意味。但是這也并未上升到概念層次,它僅僅是指一種與理性精神性相沖突之后產生的感覺。
在德爾圖良之后,“荒謬”在西方哲學中一直存在,但是由于近代理性精神的興起壓制了這種非理性因素,直到克爾凱戈爾又將“荒謬”一詞重提。然而在克氏那里,荒謬仍是被視作一種情感性的詞語。在克氏之后舍斯托夫開始公開地反抗黑格爾主義。他認為人的生存就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深淵,人要么求助理性及其形而上學,要么聽從于上帝的呼告。然而恰恰是這樣一種關心活著的人的真理,卻被人們認為是荒謬和不可能的。舍斯托夫的荒謬基于他對必然性的駁斥。尊重必然性,崇拜理性,這是西方哲學的一貫傳統,特別是笛卡爾之后理性之墻就更加牢固。然而面對這樣一堵墻,舍斯托夫提出了“以頭撞墻”的理論。他認為必然性才是最大的荒謬,必然性不過是為了讓人們更加順從而已。“這種對于必然性的承認與順從,使得人們的心靈在失去自由的時候得到補償。全部哲學教導他們同樣違背人的意愿,而我們需要在荒謬之中依靠信仰去撞理性之墻。”[1]118在意識到荒謬的事實之后,幾乎每個哲學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從克爾凱戈爾到舍斯托夫,隨著對于荒謬認識的深化,救贖方式也在發生改變。
(二)“荒謬”視野下的“救贖”
克氏用為上帝獻子的亞伯拉罕來說明當信仰與理性出現悖論,個體產生一種荒謬感的時候,人應該如何去實現救贖。克氏給出的答案是人應該去委身于信仰,依靠激情的力量來實現救贖。亞伯拉罕之所以如此堅定,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自己也可以拒絕獻上以撒,同樣可以去熱愛上帝,但是由此而言,他卻沒有了信仰。因為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若是熱愛上帝,那實際上只是在反映自己而已[2]32。其次,作為一個虔誠的信仰者來說,那種充滿恐懼與顫栗之路本身就是通往信仰之路。克氏認為上帝對于個體的考驗是一個過程,而且必須獨自去承受。對于亞伯拉罕而言真正的考驗絕非獻上兒子那件事本身,而是整個事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巨大的荒謬,而最后委身于信仰實現救贖。克氏顯然是將信仰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層面,這對一般受眾來說根本難以達到的高度。而舍斯托夫相信上帝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在上帝那里沒有不可能的事情。哲學的使命就在于把自己從理性精神中解放出來,去尋找荒謬與悖論。他認為哲學就是依靠信仰去將不可能的東西變成可能的東西,并依靠勇氣在無盡的荒謬中尋找真理”。雖然舍斯托夫與克氏的救贖觀點有所不同,但是舍斯托夫認為,依靠信仰就能獲得救贖的觀點與克爾凱戈爾很是相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僅僅從信仰的角度出發,這就把那些無信仰的人就排除了。當舍斯托夫提出“以頭撞墻”時,他們的意思是“信仰依靠荒謬支撐,任何人都不會對這種論斷產生懷疑”。荒謬是實現信仰的前提,究竟人是為了救贖還是為了信仰,這是一個問題。德爾圖良和克爾凱戈爾堅決聲稱,“因為荒謬才可信,正因為不可能才肯定,爭取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乃是一場瘋狂的斗爭,都是一場瘋狂的斗爭,是以眼淚、呻吟和詛咒為代價的斗爭”。然而這種斗爭似乎只有少數信仰者才可以完成,可是對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又何以救贖,這是他們所沒有解決的。
二、加繆之“荒謬”及其“救贖”
(一)加繆之“荒謬”
在西方思想史中真正將“荒謬”上升到哲學概念高度的人應是加繆。他對于荒謬的論述最為深刻。西西弗斯的荒謬的思想來源建立在尼采提出的“永恒輪回”的基礎上。尼采將傳統西方時間觀從直線型變成了圓周式的“永恒輪回”。他說:“你現在和過去的生活也就是你以后的生活,并且再過無數遍,其間將沒有任何新東西,而只有每一種痛苦與快樂,每一思想和每一聲嘆息包括這個蜘蛛與樹間的月影,也將一再重復。”[3]317尼采以“永恒輪回”對傳統基督教與西方哲學單一維度下所最終追求的目的論進行了激烈的駁斥。永恒輪回保證了生命永恒的同時,也使得生命的神圣性消失,荒謬由此而出現。加繆正是在這一點上進行了分析。加繆對于“荒謬”的論述是從人的存在狀態切入的。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人生值得存在與否就是在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維的,精神是否有九個或者十二個等級都在其次。”[4]624他從對自殺的探討中推論出荒謬,探討荒謬。他認為荒謬是人的自殺的情感來源。人的存在的意義,不過是出于一種自我慰藉。有一天當人突然被剝奪了幻覺之后,意識到自己在世上不過是一個局外人,這種放逐便是荒謬感。
加繆對于荒謬的論述更多的是側重于每一個個體的感受,而非嚴格的理性證明。我們的日常生活——起床、吃飯、電車、下班——這些不過是程序化的事情。但是當人在循環之中如果追問到“意義”之時,就會對自己所在的世界以及所做的事情產生質疑。西西弗斯如果能夠一直推石頭,始終不去思考“為什么”的問題的話,那么天神的懲罰本身也就沒有太多的威懾力。然而已經身處在程序化之中卻依然看清了這種虛無性,那么荒謬感也就由此產生了。
在《局外人》中加繆將這種荒謬感表現得淋漓盡致。主人公默爾索已經意識到了荒謬,而且力圖為生命尋找另外一種可能性。姑且先拋開他的“反抗”不談,僅僅就其對于荒誕的體會來說也是深刻至極的。默爾索在母親去世后并沒有異常的痛苦,而是依舊以局外人的姿態來審視這個世界。在給母親送葬途中,默爾索看到風景那一刻覺得“這片土地上將最絕望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了。而面對著這種絕望由此而來的荒謬感,默爾索認為出路是沒有的”[5]11。這些都是對于荒謬的具體感受。至于荒謬的體會如何成就荒謬的概念,在更深層次上而言,是由于人所生存的無根基性所致。
默爾索曾說:“我曾以某種方式來生活過,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生活。我做過這件事,沒有做過那件事,什么都毫無意義。我很明白這是為什么。”[6]126默爾索的這段話表達了他對人類生存信念的質疑。他認為人們所過的生活和所做的選擇也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來世與救贖本身也沒有意義。上面可以看出,在加繆這里“荒謬”不再是一種情感性的個體體驗,而是作為哲學概念出現的。
(二)從“局外人”到“西西弗斯”式的救贖觀
加繆對“荒謬”與“救贖”的論述是同時展開的。《局外人》中的默爾索,生活方面與常人并沒有什么不同,唯一有區別的是默爾索的生活得過且過,而且異常敏感。他尤其注重那些被別人忽視的細節。這兩個特點,前者最能表現一種“局外人”的狀態,而后者則引起“荒謬感”。在開篇中得知母親死后,默爾索依然在意的是日期,而非母親去世的這一事實;給母親守靈時他所關注的依然是別人的衣著和神態;最后在送葬的路上,默爾索甚至欣賞起風景來。整個事件中,他似乎沒有表露出任何悲傷,但是直至法庭對他進行“審判”時,默爾索對于荒謬的認識才展露無余。
阿爾及利亞刑事審判系統的官員們把先前出現的所有偶然事件以及默爾索被動的反應聯系在一起,企圖把他描繪成一個怪物。這種看似合乎理性與邏輯的審判系統本身就有許多荒謬之處,因為他們盡可能去證明一個已經接受了的前提,即默爾索是有罪的。加繆試圖從對默爾索的審判來批判整個刑事審判系統的荒謬性。以刑事審判系統為代表的國家機器,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毀滅默爾索,是因為默爾索實際上在以一種極端的荒謬來反抗荒謬。“默爾索在荒謬中代表的是一種真正的威脅。他恐怖之處不是他犯罪或者作惡的傾向,而是他對于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希望、信念和理想的漠不關心。默爾索由此變成了一個極度危險的人。”[7]54這個“危險的人”一詞是針對法庭而言的,但是如果站在法庭的對立面而言的話,默爾索卻是一個反抗英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冷眼旁觀和隨遇而安與中國道家哲學中的“順其自然”不同。后者是一種順從的哲學,而前者則代表著反抗。
在加繆看來不僅現存的東西需要反抗,而且連上帝和彼岸都是如此。在默爾索與神父的交流中,他認為自己至少能把握現在,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著而沒有別的指引。死亡在他眼里更加無所謂,因為所有人都要死,殊途同歸而已。而代表著基督教的神父在他看來還不及女人的一根頭發。這點充分表現了加繆的反神論傾向,高揚了人道主義。
這樣說來,局外人的出現是因為個體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謬,以一種反觀荒謬的視角來擺脫荒謬。可以說默爾索的反抗是極其深刻的,但是這種反抗本身卻成了最大的荒謬。而且反抗竟然以生命作為代價,而這種形式的反抗究竟值得與否,這正是《西西弗斯神話》中加繆所要探討的話題。加繆在文中提出:“認識到世界是荒誕時是否就意味著生活不值得過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認識到荒謬之后依然可以有尊嚴地去生活。除此之外,加繆認為荒謬的結果應該是激情,西西弗斯知道自己的未來永如今日,自己只有改變自己來與命運抗爭。這樣他就比懲罰他的諸神更加堅強。他用執拗的熱情拒絕悲哀來擁抱自己的勞動,以此來嘲笑諸神,并且聲稱 “不存在任何嘲笑所無法改變的命運”。而西西弗斯拒絕去順從神明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成為了自己的主宰。純粹的幸福也就在這一主宰之中,因此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在一定意義上來說,西西弗斯在加繆那里已經成為了全人類命運抗爭的代言人。在這點上《鼠疫》表達得更為清楚。加繆給里厄醫生設置了更為荒謬的生活場景,但是里厄與默爾索的不同在于他關注別人的幸福。他對別人的痛苦以及自己的職業道德有著清醒的認識。作為醫生,他的使命就是與痛苦死亡來戰斗。盡管他也知道鼠疫對于他來說不過是一場無休止的失敗。這點可以說是對于西西弗斯精神的繼承,但是與西西弗斯不同之處在于里厄除了嘲笑天神和勇敢前行之外,他還有一層道德意義上的崇高。因為他始終在盡自己的可能去保護他人享有更加美好和長久的未來。而且,里厄認為這些付出都是理所當然的,因此這就將西西弗斯精神從自我救贖提高到了全人類救贖的高度。
三、加繆的救贖觀何以可能
走筆至此,加繆似乎完成了從荒謬到救贖的指引。但是,加繆的救贖方式依然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是人何以認識到荒謬的事實。從加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反抗的前提正是建立在認識到荒謬的基礎之上。但是如果對于局中人而言,依然躲在理性之墻下企圖尋找到慰藉。那么對于這些人來說救贖是否是可能的?第二個問題是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所推的是石頭。可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荒謬的具體事物是不斷變化的。如果石頭變成了其他東西,那么同樣的救贖方式能否依然適用?最后一個問題是反抗本身并不是目的,所有人都應該在反抗中得到幸福與尊嚴,因此反抗的限度何在?
綜上所述,從第一個問題談起。對于那些不認為世界是荒謬的人能否實現救贖。從古至今的任何一種宗教必須建立在“信”的基礎上,似乎得救者必須信仰,對于那些不信教的人而言似乎只能墮入黑暗。倘若加繆的哲學也是如此,那么也就沒有存在下去的意義。因為僅就加繆所批判的基督教而言,也比加繆的救贖理論要精致得多。加繆的哲學之所以能被奉為時代的良心,就在于它能夠使得人類實現一種普遍性的救贖。
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他的生存方式與人類大不相同。加繆認為人類終生都在做同樣的工作,這種命運同樣也是荒誕的。但是與西西弗斯相比,人類卻更容易得到幸福,因為平凡的生活可能更有意義。盡管工作單調重復,但是人通常也盼望著完成手頭的工作。對于工人來說,不論他認識到他自己的整體命運與其他人是否有相似之處,這不是十分重要。因為他生活著,他裝一個零件,完成一件工作,其實就是在反抗。每完成一個目標,實際上都是在追求幸福。這種對于幸福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救贖,因為天神以荒謬的形式來懲罰西西弗斯就是讓其陷入絕望與痛苦。但是縱使沒有意識到這種荒謬感的人,他們也是在追求一種拯救。如果說已經意識到天神在懲罰他的西西弗斯樂此不疲地推石頭是一種崇高,那么在根源上能用人類固有的對于幸福的追求的動力去溶解掉荒謬本身,就更使得天神的做法顯得幼稚而無意義。因此在加繆這里,即便是對于那些毫無信仰,對于彼岸世界沒有依戀的人也能獲得救贖。
其次,需要討論的是西西弗斯手中的石頭如果變成了其他東西,那么這種反抗是否依然適用。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說《砂女》中將西西弗斯手中的“石頭”變成了柔軟的“沙粒”。一片荒漠之上的孤獨感和村中日復一日的挖沙的行為交織在一起,使得追求自由的人最終深陷于松軟的沙粒之中無力反抗。西西弗斯所推的石頭,這堅硬無比的東西具有一種天生的反抗感,當客體與主體一致時必須變得同樣堅硬。而沙子不同,它代表的是一種柔軟與流變。因此安部公房說:“確實,沙子不適合生存,但是固定不變對于生存是否就不可或缺呢?正因為人們執著于固定與不變,所以才會出現厭惡。假如一切如沙子般流動,那么這種感覺就會消失。”[8]5當個體處在松軟的沙粒之中得到快樂的同時也喪失了反抗的勇氣。現代人承擔的荒謬感前所未有,而且這種荒謬是一種無定型的瑣碎的東西。如果說,對于西西弗斯手中那個巨大無比的石頭的反抗需要勇氣,那么反抗現代性的沙子般的荒謬則需要耐心。加繆在書中多次提到了地中海的陽光和沙灘。因此不能只看到西西弗斯的悲壯,還要看到當默爾索躺在地中海岸邊沙灘上的愜意。即使默爾索身處在監獄之中,還似乎想起了泥土的香味和海水的味道。反抗與享受,苦難與陽光,這些看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也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不忘記反抗,也不忘記生命的樂趣所在。當沙子流下的時候可以與陽光作伴,而當其威脅到生存時就盡力去反抗。從這一點上而言,只要有足夠的擁抱苦難與追求陽光的勇氣和耐心,個體就能最終得到救贖。
第三,反抗的限度。加繆提倡反抗荒謬,但是他始終認為反抗應該有一個限度。他認為反抗不應該局限于個體的利益,而且也要為別人的價值考慮。那種以反抗為名義去進行暴力和掠奪的行為毫無意義。因此加繆一生反對暴政和蘇聯的極權主義。加繆指出,每個人都渴望自由、尊嚴和美麗,渴望賦予自己存在的統一性。他認為,對于人性而言,存在調整、限制、適度的根本原則。如他所說:“反抗在歷史上也是一個無規律的擺鐘,在不確定的弧形上不停擺動,不斷追尋自己最完美、最深刻的節奏。但是,這種不規則不是絕對的,他始終圍繞一個中軸,有自己的調整與限度。”[9]294因此任何暴力學說本身都是與加繆救贖理論背道而馳的,反抗本身是為了追求陽光。這里體現了一種強烈的人道主義。也只有給予反抗以限度,才能讓加繆哲學中的反抗成為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最終給予身處在孤獨與荒謬之中的全人類以救贖。
四、結語
加繆繼承了傳統西方哲學關于“荒謬”的探討,并提出了他獨特的救贖觀。加繆身上獨特的地中海氣質使得他像一個游離在邊界的游俠,在歷史盲目的潮流中固守著理性與激情的平衡。可以說,他的思想是在生命與愛的前提下,用節制與平衡以及古希臘智慧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面對荒謬,他主張的反抗也是建立在博愛和人道主義基礎之上的。加繆對于人類生存的無根性以及荒謬感的論述獨樹一幟,但是,他又能入于荒謬而出于救贖。這種救贖不同于以往依靠彼岸或者上帝。加繆認為荒謬是不可逃避的事實,但是,他認為正是因為荒謬,所以才要反抗。這種反抗從心理上到實際行動上再到集體反抗,每一次反抗都是在靠近幸福。作為個體的人只能依靠自己來獲得尊嚴。所以加繆哲學根本不是大眾所理解的那種虛無主義。相反,加繆對于人性尊嚴的認可以及對光明的追求很是強烈。在他的反抗哲學中,依稀可以看到那個出身于阿爾及利亞貧民窟的孤兒。不論一生多么艱難坎坷,他都始終沒有忘記對于地中海陽光的追求。正如諾貝爾獎給予加繆的評價一樣,他的哲學冷靜而熱情地闡明了人類的良知以及向往,這些也許就是他畢生所追求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