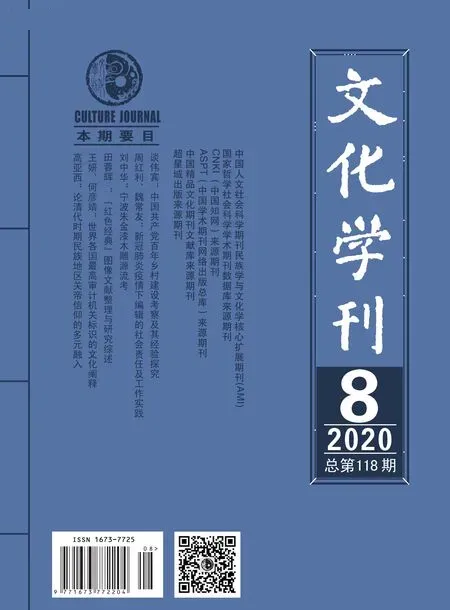語用順應論視角下《飛鳥集》漢譯對比研究
——以鄭振鐸和馮唐譯本為例
周逸帆 劉風光
《飛鳥集》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Tagore)享譽國際、最負盛名的著作。325首清新雋永的無題小詩在歌詠人與自然和諧之美的同時又富有靈動的哲思,語句受日式短歌俳句影響流暢簡潔。國內(nèi)《飛鳥集》翻譯自鄭振鐸(1922)開始,后有陸晉德、徐翰林、白開元等人的譯本,但鄭譯本被公認是國內(nèi)最經(jīng)典的譯本[1]。2015年,馮唐區(qū)別于傳統(tǒng)翻譯的全新譯本問世后評價分化達到極端。
學界也通過不同視角對《飛鳥集》鄭譯本和馮譯本進行對比分析。其中包括在忠實原則視角下選取合適的語料庫探究譯本的風格變異問題[2];以文化取向為出發(fā)點,對比分析翻譯策略差異[3];從譯者主體性角度探究譯者顯形和詩學重構(gòu)現(xiàn)象[4],探究兩位譯者詩學觀差異及其對譯文的影響[5];結(jié)合喬治·斯坦納的闡釋學四步驟分析二者分別如何發(fā)揮譯者主體性地位[6]。目前并沒有學者從語用順應論視角進行對比分析、探究二者差異和影響的。
本文選取《飛鳥集》鄭振鐸譯本和馮唐譯本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原文及譯文為研究對象,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其一,兩位譯者在順應意識程度上是否存在差異?其二,從語境關系順應和語言結(jié)構(gòu)順應角度來看,兩個譯本存在哪些差異?其三,如果差異存在,對詩歌交際效果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
一、語用順應理論框架
20世紀80年代后期,Jef Verschueren提出了以達爾文進化論為思想基礎的語言綜觀論,順應論是這一思想的核心。考慮到語言使用是一種受到認知、社會和文化多層面影響制約的語用交際行為,Verschueren希望用一以貫之的較為宏觀的理論框架解釋闡述語言現(xiàn)象。他認為,語言的使用是在不同交際需要的驅(qū)動下,受或高或低的意識程度支配的一系列選擇行為。語言選擇基于語言的三種特性,即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其中順應性居于核心地位[7]。順應論從四個維度——語境關系順應、語言結(jié)構(gòu)順應、順應的動態(tài)性和順應意識突顯程度,對語言選擇行為進行解釋。語境關系包括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前者為語篇內(nèi)上下文,后者涵蓋交際對象雙方、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順應語言結(jié)構(gòu)則體現(xiàn)在語音、語體、語碼、詞素、詞匯、句式和句法等多個層面的語言選擇。順應過程中每種選擇都不是割裂的、固定的、機械的,相反是聯(lián)系的、變化的、靈活的。語言使用者在交際過程中的認知心理狀態(tài)和能動性,也會影響語言的選擇,進而影響交際效果。
語用學和翻譯都注重對交際信息的正確理解和恰當使用、傳遞,所以二者聯(lián)系十分緊密[8]。在翻譯實踐中,沒有任何方法能夠使原語和譯語的字句一一對應[9]。翻譯是一個受多方面因素制約,需要不斷調(diào)整、做出合適選擇的動態(tài)順應過程。而詩歌文本形式短小精悍,語言高度凝練,其闡釋空間區(qū)別于其他文學文本。詩歌意象和語境的不確定性,表達形式和語言使用的特殊性都決定了詩歌翻譯的復雜性[10]。因此,譯者需要格外注意詩歌翻譯的動態(tài)順應,以期減少經(jīng)典詩歌文本語用等效和交際價值的損失。
二、順應過程的意識程度
翻譯的選擇體現(xiàn)在各個維度上,確定當譯之本更是首要選擇[11]。鄭振鐸(1898—1958)在其譯本的序言中明確表達了他的“選擇”主張:源語和譯語的差異導致散文詩中部分特用的文詞和隱喻暗示性強的句法具有不可譯性。直譯不可達意,稍加詮釋則致原文風韻和含蓄喪失。因此,鄭振鐸主張詩集的翻譯應當在可能的范圍選擇,受譯者的興趣與能力制約[12]。同時,作為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壇主力軍,鄭振鐸大力倡導新文化運動,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翻譯理念。在譯本序言末尾,鄭振鐸表明:“我的譯文自信是很忠實的。”[13]而當代著名作家馮唐翻譯的《飛鳥集》遵循自己獨到的翻譯理念和個人典型風格。在其譯本末尾的自述中表示,自己“固執(zhí)地認為詩應該押韻”,甚至于“翻譯中一半的時間是在尋找最佳的押韻”,承認自己“沒百分之百尊重原文”,認為詩歌翻譯需要更加“有我”[14]。
意識程度在順應論四個維度中占據(jù)主導地位。語言使用者個體心理和經(jīng)歷的差異及時代差異會導致順應意識突顯程度有所不同,受其支配的語言表現(xiàn)也有所不同。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鄭振鐸和馮唐的順應意識突顯程度具有明顯差異。下文筆者將深入對比分析在不同順應意識程度支配下二者譯文的具體差異。
三、《飛鳥集》鄭譯本和馮譯本對比
(一)語境關系順應
語境涵蓋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交際對象雙方、社交、物理和心理四個維度互相影響,共同構(gòu)建有機統(tǒng)一的交際語境。社交層面涉及社會場合、情境、規(guī)范和原則等;物理層面包括時空的構(gòu)建和指稱;心理層面則包含情感、個性、信念和意愿等認知心理因素。
例(1):
原文:In my solitude of heart I feel the sigh of this widowed evening veiled/ with mist and rain.(1)文中泰戈爾英文詩歌原文均出自:[印]泰戈爾.馮唐譯.飛鳥集[M].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鄭譯文:這寡獨的黃昏,幕著霧與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里,感覺到它的嘆息。
馮譯文:在我心的苦寂中/我聽到夜的嘆息/霧/雨。
原文的with介詞結(jié)構(gòu)表明“霧”和“雨”都是與前面“孤獨的黃昏”相伴相融的意象,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在霧雨朦朧的黃昏之際“我”內(nèi)心的孤寂和憂傷。鄭振鐸譯成“寡獨的黃昏,幕著霧和雨”,渲染呼應下文“我”的內(nèi)心感覺。其散文體譯文能較好地將這一物理場景完整連貫地描繪出來,充實了語言語境,通過環(huán)境營造、氣氛烘托,使得情感曉暢地傳遞到讀者心中,引起共鳴。而馮譯文追求詩歌的形式簡潔,丟棄了對“夜”的修飾成分的翻譯,沒有將“widowed”(寡獨的)詞意和with結(jié)構(gòu)的邏輯譯出,而是將“霧”和“雨”獨立出來,單獨并列置于句末,且前文末尾是與之并無關聯(lián)的“嘆息”。這種字句安排使得場景缺少融合感和邏輯感,沒能與語境的物理世界較好地順應,也不便于讀者理解。
例(2):
原文: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 the silent trees.
鄭譯文:憂思在我的心里平靜下去,正如暮色降臨在寂靜的山林中。
馮譯文:痛在我心里漸漸平和/夜在樹林里一字不說。
原詩旨在用籠罩山林的無聲夜色渲染類比在“我”心中逐漸沉淀的憂思,表明哀傷之感可以淡化卻不可完全消除和擺脫。筆者認為,在此句詩中,“l(fā)ike”至關重要,因為它應和了前后兩種動態(tài)的變化過程,也是提示比喻修辭的詞眼。“憂思平息”和“暮色降臨”都是動態(tài)的,鄭振鐸一個“正如”串聯(lián)了兩個變化,順應了語言語境,也讓讀者的心理過程自然過渡,情感得以流暢傳遞。而馮譯文割裂了語句的邏輯,犧牲了連接兩個狀態(tài)描寫的關鍵詞“l(fā)ike”的翻譯,用兩個獨立的句式分說“痛的漸漸平和”與“夜的一字不說”,沒有恰當體現(xiàn)該句修辭,且聯(lián)系缺失,有破碎孤立之感,影響詩歌傳情效果。
(二)語言結(jié)構(gòu)順應
對語言結(jié)構(gòu)的順應涉及具體的語音結(jié)構(gòu)、語體語碼、詞素詞匯、分句命題等的選擇。本文主要分析兩個譯本在語句長度和語音形式方面體現(xiàn)的語言結(jié)構(gòu)順應情況。
例(3)
原文:Shadow, with her veil drawn, follows Light in secret meekness, / with her silent steps of love.
鄭譯文:帶著面紗的影子/隨著光的步子/愛戀/柔軟。
馮譯文:陰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溫順地,用她的沉默的愛的腳步,跟在“光”后邊。
鄭譯文中的“陰影”有娓娓道來之感:戴上面紗,腳步沉默而充滿愛意,秘密而溫順地跟隨著“光”。其擅長以散文體保留詩句的神韻和詩意,與原語成分結(jié)構(gòu)相似,長度相似,表意清晰完整,音韻和諧動人。馮唐則追求形式,崇尚至簡,寥寥數(shù)字描繪了“影子”,并且省略了原文兩次出現(xiàn)的第三人稱指示語“her”,省略了“secret”和“silent”。馮譯文中“l(fā)ove”和“meekness”被譯為“愛戀”和“柔軟”,僅以詞語形式單獨置后并列,表義較為孤立。原文中詩人塑造了一個溫柔羞怯甚至有些隱忍卑微的“影子”形象。馮譯本打破了原文的形式結(jié)構(gòu),過分追求語言的凝練和對等,刻意遺漏細節(jié)信息的翻譯,因此沒有很好地順應原文的語言結(jié)構(gòu),不能生動體現(xiàn)出原詩“影子”的特點,有失原文意境。
例(4):
原文:Bees sip honey from flowers and hum their thanks when they leave.
The gaudy butterfly is sure that the flowers owe thanks to him.
鄭譯文:蜜蜂從花中啜蜜,離開時盈盈道謝。浮華的蝴蝶——卻相信花是應該向它道謝的。
馮譯文:蜜蜂采蜜/道謝辭花/浪蝶覺得花應該謝謝他。
通過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鄭譯文的散文形式簡單平實但表意準確;而馮譯文則過分追求形式,以形害意,生硬的對稱結(jié)構(gòu)和押韻沒有順應原文句式和語音形式,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在對原句字詞“gaudy”(華而不實的,俗麗的)的處理上也出現(xiàn)了錯譯,沒有很好地順應經(jīng)典詩歌文學的格調(diào),引起很多讀者反感甚至抵觸。原詩意在表達謙卑者比高傲者更懂得感恩的內(nèi)涵,馮唐“喧賓奪主”的結(jié)構(gòu)形式和詞匯選擇干擾了讀者的注意力,有礙讀者品味原詩的哲思。
總體而言,鄭譯文雖平實,但更加忠實于原文的表意、結(jié)構(gòu)和情感意境,能較為恰當?shù)仨槕牡亩嗑S語境和散文詩體,體現(xiàn)原作語言的經(jīng)典風格和深刻內(nèi)涵。而馮譯文并未完全順應原文語意和語言結(jié)構(gòu),過分關注押韻,存在漏譯、錯譯,有損部分原詩的文學及審美價值,有礙經(jīng)典詩歌文本教化怡情的社會功能。
四、結(jié)語
本文從順應論視角對比分析鄭振鐸和馮唐二者順應意識程度的差異和譯本在語義表達、結(jié)構(gòu)轉(zhuǎn)化、意象處理、意境傳遞等詩學要素處理方面的差異。通過分析筆者發(fā)現(xiàn):鄭譯本對原詩語義、結(jié)構(gòu)、意象、意境等詩學要素方面的順應較為全面,適當?shù)剡M行語境補缺和語用充實;而馮譯本個人風格過于突顯,未能較好地順應原作和讀者,因此二者譯作的語用交際功能、文學審美價值和大眾接受程度也有所差異。詩歌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跨文化、跨語言的語用交際,原作、譯作、讀者之間構(gòu)建的語言語境順應與否,順應程度的差別,都會直接影響詩歌翻譯的交際效果。順應論對經(jīng)典詩歌文本翻譯具有一定指導意義。動態(tài)順應要求譯者在原作的合理制約下充分發(fā)揮主體性和能動性[15],在翻譯實踐中要強調(diào)順應的動態(tài)性,保持順應的意識性。譯者應在宏觀上把握順應,考慮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寫作風格,讀者的接受能力和審美期待,雙方所處時代語境和文化背景信息等,做到順應交際雙方的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同時要在微觀上把握順應,關注語音詞句、語義連貫等語言結(jié)構(gòu)。不能“顧此失彼”,要進行綜合視角下的選擇平衡,以期實現(xiàn)原語和譯語多層面上的語用等效,通過最佳順應最大限度地去“獲得譯文與原文之間的語用等值”[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