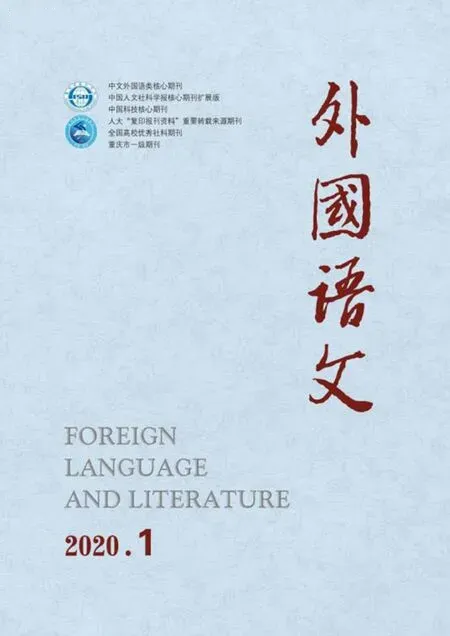情緒智力與口譯研究
——以幾個特殊領域的口譯為例
邱進 廖雪汝
(重慶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重慶.02160 )
0 引言
多年來,認知取向的翻譯研究在國內外翻譯學界一直是一大熱點,國內對翻譯的認知研究尤為偏愛。2017年召開的認知取向的翻譯研究全國性學術會議有四個,即首屆全國翻譯傳譯認知高層論壇暨中國翻譯認知研究會委員會成立會議(2017年5月5—7日)、首屆中國生態翻譯與認知翻譯研討會(2017年8月4—6日)、第四屆翻譯認知國際研討會(2017年11月3—4日)、“一帶一路”背景下翻譯傳譯認知國際研討會暨中國翻譯認知研究會第二屆大會(2017年11月10—12日)等。以翻譯認知為研究重心的全國性學術組織有兩個,即中國翻譯認知研究會和中國生態翻譯與認知翻譯學會。翻譯的認知研究已成為國內翻譯學界的一大主流,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與此相反,翻譯的非認知研究卻長期被嚴重忽視,不僅尚未召開過以翻譯的非認知研究為主題的全國性學術會議,也未成立以翻譯的非認知研究為重心的全國性學術組織,非認知研究的成果更是鳳毛麟角。認知因素與非認知因素都能對人的活動產生影響,而且非認知因素普遍存在于認知過程之中,兩者常常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認知結果,甚至有時非認知因素能獨立地影響認知結果。作為翻譯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的口譯研究,當下主流是重視認知層面的研究,而對情緒智力等非認知因素的研究尚待起步。
情緒是主要的非認知因素之一,是影響口譯的一個重要因素,有可能顯著影響口譯活動。相比筆譯人員,口譯員面臨的壓力更大,情緒等非認知因素對口譯活動的影響可能更甚。為什么兩個專業背景、年齡和性別一樣的口譯員在從事同一性質的口譯工作時,其口譯質量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在試圖解答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翻譯學界逐漸認識到了某些非認知因素的價值,認為情緒、性格等非認知因素可能有助于解答此問題(謝柯 等,2017),一些翻譯研究者已從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視角對翻譯展開了初步的研究。情緒智力這一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Salovey等(1990)提出,引起心理學界極大關注,現已成為心理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而且情緒智力理論及基于此的測評工具被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如企業管理、教育、醫療、法律等。當前國內外基于情緒智力的翻譯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研究成果還很少,但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情緒智力中的情緒知覺與表達、移情、壓力管理、自我激勵、適應性等與翻譯實踐關系密切,情緒智力能為翻譯學的諸多議題提供一個全新的研究路徑和框架(Hubscher-Davidson,2013;謝柯 等,2017)。由于口譯的性質和特點,情緒智力對口譯實踐的影響可能要大于筆譯實踐,但目前基于情緒智力的口譯研究還十分缺乏。本文將簡述情緒智力的一些重要方面,分析其與口譯的關系,著重論述情緒智力在幾個特殊領域口譯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具體的研究路徑。
1 情緒智力的模型及預測效度
1.1 情緒智力的模型
美國心理學家Salovey等(1990)提出了系統的情緒智力理論,并分別在1997、1999和2000年對情緒智力的定義進行了三次修正,2000年的修正版情緒智力定義沿用至今,即情緒智力能力模型。Salovey等的情緒智力能力模型由四個不斷遞進的維度構成,后一種能力以前一種能力為基礎。第一個維度即情緒智力的最基本能力是情緒感知和表達能力,即從自己的生理狀態、情感體驗、思想及他人、語言、藝術活動中辨認和表達情緒的能力,此能力為其他能力提供基礎。第二個維度是情緒促進思維的能力。Salovey等在2000年修正情緒智力能力模型時,特別強調情緒智力是一種與認知運作有關的心理能力,作為非認知因素的情緒與認知因素具有密切關聯。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情緒在知覺、注意、記憶、執行控制和決策中起關鍵作用,情緒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果(Tipples,2008)。第三個維度是情緒理解能力。此層次的能力能使個體理解情緒所傳達的意義,并能將情緒體驗與語言表達聯系起來,是一種能理解復雜心情、認識情緒轉換的可能性及原因的能力。此能力在四層次能力中認知意味最強,是Salovey等最早提出的情緒智力三因素模型中沒有的。第四個維度是情緒管理能力。這是最高層次的能力,主要是指個體能根據所獲得的信息恰當地進入或脫離某種情緒、調節自己和他人情緒的能力。個體能利用和調節所產生的情緒是情緒管理能力的最佳表現形式。Salovey等提出的情緒智力能力模型是在心理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情緒智力模型,簡單來說,其本質是辨認不同情緒的意義及其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推理和解決問題,及利用情緒改善認知活動的能力(彭正敏 等,2004)。
除了情緒智力的能力模型,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其他的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情緒智力模型還有三個,即Bar-On的混合模型、Goleman的勝任特征模型和Petrides、Furnham的特質模型(謝柯 等,2017)。這些模型與Salovey等提出的能力模型的最大區別在于其不僅包含心理能力,還包含了其他人格特征。Bar-On提出的情緒智力混合模型由個體內部成分、人際成分、適應性成分、壓力管理成分和一般心境成分五個維度構成。Bar-On提出的模型已涉及某些人格特質,如人際成分。Goleman的勝任特征模型包含五個因素,即自我意識、自我調節、動機、情感移入和社會技能。雖然Goleman也認為情緒智力是能力,但他描述的一些特點,如為委托人和客戶服務及對組織承擔義務等,不能簡單地歸為能力因素。Goleman對情緒智力的定義比較寬泛,將人格因素也納入了情緒智力,不像Salovey等將情緒智力嚴格界定為非認知心理能力。與能力模型差異最大的是特質模型,特質模型反對將情緒智力看作是一種能力,而是主張將其納入人格特質的范疇。Petrides等(2001)提出的情緒智力特質模型包含情感性、社會性、自我控制和幸福感四個維度,他們認為情緒智力包含人格領域的諸多傾向。Bar-On的混合模型、Goleman的勝任特征模型和Petrides等的特質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屬于情緒智力的特質模型,只是人格特質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同。
雖然情緒智力有諸多不同的模型,但這些模型并非水火不容。情緒智力的這些模型都包含一個共同要素,即對情緒的感知、理解和運用,而這一點正是情緒智力的核心。在研究情緒智力和將其應用到實踐領域時,科學的做法是依據特定的目的、對象等選擇特定的情緒智力模型,甚至整合相關模型。情緒智力還處于不斷發展之中,沒有哪一種模型是完美的,不同的模型各有優劣,不同模型之間應是互補的關系。近年來,心理學界出現了情緒智力理論整合的傾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無疑能促進情緒智力的發展并優化其應用。
1.2 情緒智力的預測效度
Goleman的暢銷書EmotionalIntelligence:WhyItCanMatterMoreThanIQ使情緒智力的概念在全球廣為傳播,很多領域看到了情緒智力的應用價值,一些企業、組織和學校甚至將情緒智力作為選拔人才和進行企業與教學改革的重要依據之一。根據不同的情緒智力理論模型,大量的情緒智力測驗工具被開發出來。情緒智力測驗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基于Mayer等的情緒智力能力模型開發出來的測驗工具,即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MSCEIT);二是基于Mayer等的情緒智力能力模型開發出來的自陳或他評測驗,如Workshop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rofile(WEIP)、Swinburne Univers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SUEIT);三是基于Bar-On、Goleman、Boyatzis和Petrides等人的情緒智力特質模型開發出來的自陳或他評測驗,如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ventory(EQ-i)、Emotional Competence Inventory 360(ECI-360)、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TEIQue)。這些情緒智力測驗工具紛紛被運用到不同實際工作領域和研究領域,特別是被用來探究情緒智力與工作績效、事業成功、學業表現等方面的關系。大量研究表明,情緒智力與工作績效密切相關(Mills,2009)。這些研究也得出情緒智力的諸多方面與事業成功和學業表現有顯著相關性的結論,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事業和學業的走向(Di Fabio et al.,2014)。情緒智力研究的時間還不長,還存在一些理論問題需要解決,但大多數的研究都表明,情緒智力與社會適應能力、工作績效、生活或工作滿意度、學業表現、學習或學術能力等方面的許多指標存在正相關關系,情緒智力對這些方面具有較強的預測力。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無論是基于能力模型還是特質模型的情緒智力測驗都具有較高的預測效度,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化,將會出現具有更高預測效度的修訂版甚至全新的情緒智力測驗工具。
2 情緒智力與口譯
韓子滿(2017)指出,當前國內翻譯研究的一大癥結是過于迷戀理論和研究方法創新,輕視研究對象,許多值得研究的翻譯現象無人研究或研究不深入。雖然此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但是一些有潛在價值的議題確實沒有引起翻譯學界的關注,其中研究嚴重不足的一大方向就是口譯的非認知研究。近年來,口譯認知研究發展迅猛,已成為翻譯研究的熱點,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口譯研究領域。與口譯的認知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口譯的非認知研究卻乏人問津,出現了“一冷一熱”的現象。任何活動都不可能只涉及認知因素,非認知因素必然會或多或少地牽涉其中。非認知因素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對人類活動產生影響,還常常和認知能力產生交互作用,共同對人類活動產生影響,高度復雜的口譯活動更是如此。對口譯非認知研究的嚴重不足導致的結果就猶如一個人缺了“一條腿”,至少是像一個“跛腳”之人。沒有非認知因素的參照,對口譯認知因素作用及運行機制的認識也可能會比較片面,研究結論的科學性也會損減。
情緒智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非認知能力,在口譯實踐中能產生不可忽略的作用。由于要求口譯員要瞬時翻譯出講話人的信息,還要保證較高的正確性和流暢性,這很可能會使口譯員產生較大的時間壓力和誤譯壓力。除了這兩類常見的壓力,口譯員還可能產生其他壓力,如庭審口譯員可能面臨道德壓力,沖突地區的口譯員可能面臨危險壓力等。口譯員在壓力下進行口譯任務會產生焦慮、緊張、恐懼等負性情緒,影響口譯質量。抗壓能力差的口譯員不僅會影響工作績效還會影響自身的職業滿意度,既影響口譯工作的客戶滿意度又不利于口譯職業的發展。無論是哪一種情緒智力模型,都涉及抗壓。Salovey等的能力模型的第四維度是情緒管理能力,其中就涉及調節自身情緒以應對壓力。Bar-On的混合模型其中的一個維度是壓力管理成分,與抗壓直接相關。Goleman的勝任特征模型中的一個因素是自我調節,與抗壓高度相關。Petrides等的特質模型中的自我控制維度也與抗壓具有相關性。口譯員與筆譯者的一大區別是口譯員要與不同類型和領域的人打交道,口譯工作對口譯員的社交性和適應性有明確要求,口譯工作的績效與此相關。英國的The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發布的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 in Translation明確指出,適應不同工作環境的人際交往能力是合格職業譯者的核心能力之一(The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2007)。歐盟委員會的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也指出,合格的譯者需具備適應不同情境和與不同團體互動的能力(EMT Expert Group,2009)。而情緒智力四大主流模型中,除Salovey等的能力模型沒有強調社交能力和適應能力外,Bar-On的混合模型(其中的人際成分和適應性成分維度)、Goleman的勝任特征模型(其中的社會技能因素)及Petrides等的特質模型(其中的社會性維度)都凸顯了這兩種能力。情緒智力與口譯還有一大關聯,即對情緒信息的識別、理解和表達,情緒智力的任何一種模型都對此進行了強調,是情緒智力理論的核心。文化交流、經貿、科學技術等一般領域的口譯涉及的情緒信息可能不顯著,但法律、醫療、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口譯實踐常常需要口譯員能辨識并理解講話人的情緒,并以能促進預期目標實現的方式進行情緒表達。不僅如此,這些特殊領域的口譯任務對口譯員的抗壓能力、社交能力、適應能力等有更高的要求。大量的口譯認知研究表明,口譯是一種高級的認知活動,涉及知覺、注意、記憶、思維、理解、概括、推理等諸多認知能力(許明,2008)。既然心理學界已經公認,情緒等非認知因素與認知因素能產生交互作用,情緒等非認知因素能獨立或與認知因素共同對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果產生影響,那么情緒很有可能也會影響口譯的認知過程和結果。也就是說,口譯員的情緒智力與認知能力可能存在相關性,可能會影響口譯認知過程的信息加工,影響口譯質量。
3 情緒智力與幾個特殊領域的口譯
當前國內外基于情緒智力的口譯研究成果還非常少,少數學者的研究多屬間接性研究。Nicholson(2005)的研究證明,情感性強的口譯學員的口譯能力比情感性低的口譯學員強。有研究表明,手語口譯涉及某些性格要素,情感因素與口譯表現存在關聯。情感等性格要素與口譯員的工作能力也存在相關性。Singureanu(2016)的研究發現,情緒智力高的口譯員的適應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更強,其工作績效和職業滿意度也更高。國內的康志峰(2016)指出,元情緒對口譯員的工作表現能產生影響,其教學實驗也證明元情緒能影響學生譯員的口譯行為和口譯效果。當前基于情緒智力的口譯專門研究還極少,零星的研究成果僅是考察口譯的一般情況,個別學者還考察了手語口譯,但其他具有現實意義且能凸顯情緒智力重要性的口譯領域則無人問津。下文將聚焦幾個特殊口譯領域,論述情緒智力在這些口譯實踐中的重要價值,并提出具體的研究方向。
3.1 情緒智力與國家安全事務口譯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開始研究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外語能力和教育問題,認為在國家外語教育中應將國家安全作為重要參數,構建更強的國家安全性(文秋芳 等,2013)。國家安全導向的外語教育不僅涉及語種建設,作為外語能力重要組成部分的翻譯能力也應成為其中一部分。而且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口譯教育不能僅側重于雙語轉換能力,其他能力和特質也應重視,如保密意識、職業倫理、性格特質、社交能力、情緒智力等,甚至應成為選拔從事國家安全領域口譯工作人員的前提條件,也應在培養國家安全領域專業譯員過程中特別予以強調。
進入21世紀后,世界主要國家都致力于發展經濟,世界和平指數也顯著提高。但和平外衣下卻時常涌動威脅國家安全的暗流,以ISIS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對世界和平構成了重大威脅,局部戰爭或沖突頻發,間諜活動也比較活躍。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員成為特殊的口譯員群體,雖然數量遠少于一般領域的口譯員,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員的主要工作是,在審訊或面試恐怖分子和涉嫌恐怖主義人士、間諜和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人士、戰爭或沖突牽涉人員、申請移民和避難人員時,充當審訊官或面試官的口譯員。前三類屬典型的國家安全事務,移民和避難等也可能涉及國家安全,這些領域常常被忽略。鑒于以往發生過移民或難民實施恐怖襲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內相繼出現了一種聲音,那就是擔心移民和難民會增加其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應加強對移民和難民的管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謹慎處理此類問題是合理的。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工作關乎國家與人民的安全,若是處于戰爭場域,口譯員會面臨安全壓力,其情緒更易受到影響。情緒智力能力模型的其中一個維度就是情緒能促進思維的能力,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境下,口譯員的口譯認知能力,如雙語口頭轉換能力和工作記憶等,很可能會受情緒的影響。此外,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工作要求口譯員具備更強的情緒感知和理解能力,情緒管理能力與壓力管理能力也比一般場合的口譯員要求更高。在口譯水平相當的情況下,應優先選聘情緒智力高的口譯員從事國家安全領域口譯工作。口譯員并非完全隱身的,口譯員常常是口譯活動的參與者,對談話結果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口譯員在現實口譯活動中展現出了不同的角色,不僅僅是“傳聲筒”。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員更是如此,不可能僅扮演語言轉換者的角色。口譯員與涉及國家安全的被審訊者或被面試者說同一門語言,且了解其文化,有可能口譯員對被審訊者和被面試者的獨特語言風格、隱藏在語言和副語言中的信息有更敏銳的洞察力,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口譯員和被審訊者及被面試者才是更直接的對話者。口譯員應成為審訊者或面試者的協助者,充當助理審訊官或助理面試官的角色,審訊者或面試者與口譯員共同協作,挖掘重要信息,維護國家安全。在審訊者或面試者主導的基礎上,口譯員應能準確辨識被審訊者或被面試者隱藏在語言和副語言(如表情、語氣、動作等)中的情緒和態度,深刻理解特定情緒的意義,并對被審訊者或被面試者的情緒進行準確的表達。國家安全事務口譯員還會和相關領域的官員和專家打交道,其社交能力是促進工作順利完成的重要保證。還有一點不可忽視: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場合往往會給口譯員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其情緒還可能在審訊或面試過程中受到影響,口譯員若不能準確辨識和理解自身及他人情緒,管理情緒,產生的負面情緒必定會影響口譯質量,影響口譯員的工作績效和職業滿意度,還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危險。也就是說,從事國家安全事務的口譯員的情緒智力需涵蓋能力模型和特質模型中的相關要素,能力模型中的情緒促進思維的能力要素與口譯基本質量密切相關,能力模型中的情緒感知、理解與管理能力及其特質模型中的人際、適應、社交與壓力管理等要素與口譯質量也有較強的關聯,而且情緒智力的這些要素還關乎口譯員作為助理審訊官、助理面試官等角色的扮演程度問題,對促進國家安全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一般場合的口譯員可能不需要較高的情緒智力,但專門從事國家安全事務的口譯員,情緒智力應當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之一。
基于情緒智力的國家安全領域的口譯研究可主要從以下三個方向展開:(1)深入探究情緒智力及其要素與國家安全事務口譯的關系,如探究其與國家安全背景下的口譯行為、口譯認知、口譯質量、工作績效、職業滿意度、獨特角色發揮等的關系;(2)從情緒智力視角對從事國家安全事務口譯工作的口譯員進行系統研究,可依據不同參數進行對比研究,探究此領域不同類型口譯員的異同,甚至探究他們與其他領域口譯員的異同;(3)研究情緒智力對國家安全事務口譯員培訓和專門人才培養的啟示,構建特色人才培養模式和培訓機制。
3.2 情緒智力與醫療口譯
隨著國際交往的深化,在我國生活的外國人士數量顯著增加。2006年僅在中國珠三角生活的外國人就已經達到30萬,而且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中國工作和旅游的外國人數量將會不斷增加。一旦有醫療需求時,大多數外國人則選擇回國或赴香港治療,出現了外國人士舍近求遠尋求醫療救助的現象。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溝通環節的欠缺嚴重影響了外國人士對中國醫院和醫生的信任度。2009年美國國家醫療口譯認證會(The National Board of Certification for Medical Interpreters)和美國醫療口譯認證委員會(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成立,并于2010年組織實施了醫療口譯員資格認證考試。此資格認證考試除了涉及譯前準備、醫學知識、語言轉換能力外,還涉及與醫療人員的交際、臨床表現、文化意識等方面的內容。一般場合的口譯,如會議口譯、商貿交流口譯等,更多的是要求口譯員能快速準確地傳達講話人的信息,扮演語言與文化橋梁的角色。而醫療口譯卻比一般口譯更具挑戰性。患者的健康擔憂、受疾病折磨、疾病傳染風險等情形可能會給醫療口譯員帶來情感上的壓力,醫療口譯員需具備異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外,在醫療口譯實踐中,醫療口譯員扮演的角色比一般口譯員多,除了語言轉換者的角色外,醫療口譯員還具有患者代言人、共同醫生、醫患關系協調者等多個角色(蘇偉,2010:87),這些角色需要口譯員具備更強的社交、適應和壓力管理能力,即特質模型中的核心成分。醫療口譯員還需具備較強的情緒智力模型中的相關能力,他們需辨識和理解自身情緒,管理情緒,有效抵抗壓力,保證高工作績效;醫療口譯員需正確辨識并理解患者、醫生、醫護人員等的情緒,從中協調各方關系,協助各方實現利益最大化。醫療口譯屬于社區口譯,社區口譯區別于一般口譯的是,前者不是一種簡單的信息傳遞,而是一種社會交際行為和權益平衡過程。社區口譯員往往扮演多重角色,其語言轉換能力甚至只具從屬性,而其社會交際能力、權利關系的協調與平衡意識、危機與困難處理能力等才更為重要(張威,2016:24)。顯然,除了雙語口頭轉換能力外,合格的醫療口譯員還需具備較強的社交能力、適應性、抗壓能力、情緒識別、情緒理解與表達、情緒管理等能力,這些能力正是情緒智力的重要因素。情緒智力的多個要素與職業醫療口譯員需具備的特質具有相關性,情緒智力可能對醫療口譯員的工作績效、職業滿意度等產生影響。醫療口譯員和國家安全事務口譯員一樣,需具備情緒智力兩大模型的能力與人格特質。
情緒智力可為醫療口譯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切入點,其研究可主要從以下四個方向展開:(1)可以考察情緒智力是否能促進醫療口譯員不同角色的發揮及其促進程度;(2)探究情緒智力及各要素與醫療口譯的關系,探究其對醫療口譯質量、譯員工作績效、客戶滿意度等方面的影響;(3)對醫療口譯員與其他領域口譯員的情緒智力展開對比研究;(4)探究情緒智力對職業醫療口譯員培養的啟示。
3.3 情緒智力與法庭口譯
法庭是一種易引發情緒和內心沖突的情境,與一般場合口譯員相比,法庭口譯員更易遭受諸多壓力和內心失衡。無論是民事審判還是刑事審判,對當事人的影響都極大,特別是涉嫌重罪的審判。若溝通出現問題,法庭口譯員常常是被指責的對象之一,再加上事關重大,法庭口譯常常會給譯員帶來心理壓力。此外,可能遭遇的語言困境、法律困境和道德困境也讓法庭口譯員備感壓力(余蕾,2015)。溝通雙方的語言水平可能嚴重不平衡,這會使法庭口譯員深陷語言困境。由于法庭口譯制度還不完善,如我國對法庭口譯人員的資格、操作流程、質量認定等重要問題沒有提及,這使得法庭口譯員可能陷入程序性困境。由于被告的語言表達可能出現不規范和邏輯不清等問題,處于一種令人同情的狀態,法庭口譯員在口譯策略采用上可能會面臨兩難選擇,有可能會出現越過職業道德的行為。庭審過程中口譯員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可能會使其產生道德情緒,而情緒可能影響道德判斷(謝熹瑤 等,2009;伍如昕,2015)。“Camayd-Freixas聲明”是美國法庭口譯界著名的案例,能讓我們管窺法庭口譯員面臨的困境。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在2008年5月逮捕了肉類加工廠Agriprocessors近400名以危地馬拉人為主的西裔外來工人,其中297人被控“惡性身份盜竊”或“社會保險欺詐”。佛羅里達國際大學西班牙語教授兼美國聯邦法院英語/西班牙語資深口譯員Erik Camayd-Freixas也曾表明,他在擔任此案件的法庭口譯員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是他23年職業生涯中第一次產生退出的想法。他在“聲明”中指出,案件的庭審讓口譯員無法保持中立,庭審程序存在諸多不規范,產生了令人痛心的后果(Camayd-Freixas,2008)。角色沖突和權利的失衡讓資深法庭口譯員都萌生退意,可見庭審對口譯員的影響。還有一種常見的情形:法庭口譯員在遇到強奸、謀殺、兒童傷害等案件時,有可能會產生不利于中立性和專業表現的情緒。法庭口譯員的抗壓能力、管理情緒的能力等對其保持中立、保證高工作績效等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法庭口譯員需正確辨識和理解相關各方的情緒,并作出恰當表達。如代表控方的法庭口譯員有必要發揮責任者角色,辨識和理解被告可能在語言和副語言中隱藏的重要信息或態度。情緒表達能力也是法庭口譯員需具備的重要技能。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法庭口譯員是聯系雙方的焦點,更具交流的直接性。如在盤問或抗辯時,口譯員除了傳遞代表方的語言信息外,還需保存副語言元素和保持語域(趙軍峰 等,2011:26-27),口譯員需準確傳遞代表方的情緒狀態和話語風格。法庭口譯員需在正確辨識和理解代表方情緒狀態及話語風格的基礎上,準確地進行情緒和風格表達。還有一點也不可忽視,即法庭口譯員是連接案件各方的紐帶,常常需要與警察、法官、律師、當事人及其他相關人士交流和溝通,社交能力也是法庭口譯員必不可少的。從以上論述可知,法庭口譯員需具備的情緒智力成分也涉及能力模型和特質模型兩大模型中的幾乎所有要素,法庭場域易引發情緒變化和內心沖突,能力模型中的情緒促進思維、情緒管理與表達等能力及特質模型中的壓力管理成分等就顯得十分重要;由于法庭口譯員需扮演多重角色,其具備特質模型中的社交能力及能力模型中的情緒感知與理解等能力也不可或缺。
從情緒智力視角進行法庭口譯研究是一個全新的方向,研究者可以探究情緒智力及各要素對法庭口譯員口譯質量、工作績效、職業滿意度等的影響;還可探究情緒智力與司法公正、法庭口譯員職業道德、角色沖突等的關系;還可研究情緒智力對職業法庭口譯員培養、法庭口譯制度等的啟示。
除了上述三個領域,情緒智力還可能對手語口譯、警務口譯等其他特殊領域的口譯產生重要影響。手語口譯員需充分理解雙方的文化差異,能準確辨識和理解各種手勢、表情、動作等,能正確表達出對方的情緒狀態,積極參與雙方的交流,扮演文化調解員的角色。警務口譯主要是指對犯罪嫌疑人錄口供、審問犯罪嫌疑人、詢問目擊證人等工作進行口譯。警務口譯員既要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又要維護司法公正,這可能會使口譯員產生心理沖突,影響其情緒狀態。警務口譯員的情緒對其職業倫理能產生影響(Mulayim et al.,2017:124),工作的難度、重要性和危險性等可能使警務口譯員產生諸多壓力,影響其工作績效。職業警務口譯員不僅需具備較強的情緒管理能力、抗壓能力,還需具備社會交往技能和知識(Mulayim et al.,2017:133)。此外,代表警方的口譯員往往需扮演助理審訊人員的角色,需通過語言和副語言等判斷犯罪嫌疑人可能刻意隱瞞的信息和態度,這就需要警務口譯員具備很強的情緒識別和理解能力。有時甚至需要警務口譯員能對犯罪嫌疑人和目擊證人等的微表情和微動作等進行識別和理解,判斷其是否撒謊。顯然,情緒智力的多個要素與手語口譯員和警務口譯員需具備的特質具有相關性,能為相關研究帶來新的認識。
上述特殊領域口譯與一般場合口譯的共同點是,口譯員必須在數秒內準確傳譯出講話人的信息,因此面臨較大的時間壓力和誤譯壓力,也存在一定的社交壓力。其不同點在于,一般場合的口譯員更多的是將焦點放在雙語轉換上,扮演的角色相對比較單一,即語言與文化的橋梁;而特殊領域口譯的敏感性比一般場合口譯高得多,帶給口譯員的壓力更大。國家安全口譯關系國家和人民的安全,事關重大,不容有失;醫療口譯關乎患者的生命與健康、和諧的醫患關系、個人福祉與社會和諧;法庭口譯關系到一個人的聲譽和法律公正,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極大。從事這些特殊領域口譯工作的譯員面臨的壓力類型更多,強度更大,口譯員需扮演的角色更多元化,這些特殊性要求口譯員具備更強的情緒處理能力,還需展現較強的能力模型中的諸多人格特質。這些特殊領域的口譯員需具備更強的情緒感知、理解、表達、管理等能力,較強的適應和社交能力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4 結語
當前的口譯研究聚焦于與口譯相關的認知層面,產生了許多能提升口譯能力和口譯教學質量的研究成果。但情緒不能剝離思維,情緒智力等非認知要素與認知要素產生交互作用,并對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果產生影響。情緒智力能力模型中的情緒與思維交互要素與口譯的認知能力有強相關性,口譯的瞬時性特征常常使口譯員面臨較大的時間壓力和誤譯壓力,對這些壓力處理不當會影響口譯員的理解、工作記憶、思維、推斷、表達等口譯認知能力,影響口譯工作績效和職業滿意度。
國家安全口譯、醫療口譯、法庭口譯、警務口譯等情況更復雜,更易引發口譯員情緒和心理的變化,其面臨壓力的類型更多,程度更大,非認知因素對上述特殊領域的口譯員工作績效及職業滿意度的影響更顯著。此外,這些特殊場合的口譯工作需要口譯員承擔除語言文化橋梁之外的其他角色,如助理審訊官、助理面試官、醫患關系協調者、庭審責任者等,這就要求口譯員具備情緒智力的能力模型和特質模型中更多的能力要素,如情緒感知、情緒理解、情緒管理、情緒表達能力及適應能力、社交能力與壓力調控能力等。情緒智力在這些特殊領域的重要性不亞于認知能力,研究的有效性突出。與筆譯相比,一般場合的口譯需要口譯員具備比筆譯人員更高的情緒智力;而由于國家安全、醫療、法庭、警務等領域的顯著特殊性,要求從事這些領域口譯工作的譯員具備比一般場合口譯員更高的情緒智力。
雖然情緒智力對口譯研究和實踐有重要價值,但當前國內口譯研究界對情緒智力等非認知能力的研究嚴重不足。目前國內尚未出現基于情緒智力的口譯專門研究,國家安全、醫療、法庭等領域的口譯相關研究更是空白。情緒智力與口譯關系密切,將情緒智力引入口譯研究是十分有價值的,特別是在當前口譯研究“重認知”的背景下,此類研究更顯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