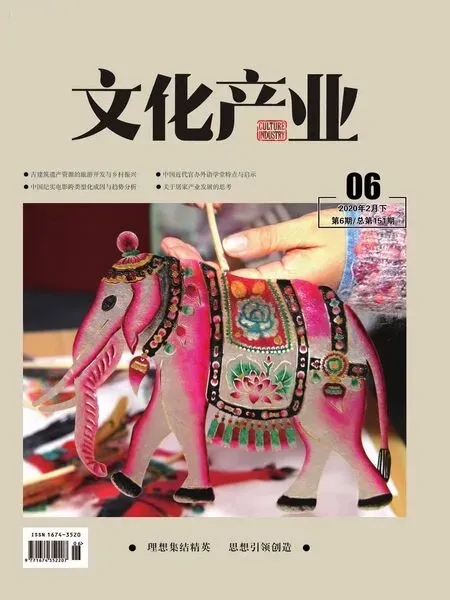淺談《論語》中“學”之內涵及其現代延伸
◎沈偉濱
(南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南通 226019)
“學”在《論語》中之地位尤其重要,其貫穿人修養發展過程之始終,是成就理想人格、實現人生價值的必由之路。“學”有豐富的內涵,不局限于其本身,亦講求與之相關的聯系。然而“學”之本義為何,“學”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學者當如何治學,“學”之于當世有何啟發?本文通過闡釋“學”之基本內涵,分析其目的及其影響,討論為學之態度和方法,總結出“學”的現實意義,以期能理清其脈絡,增進對《論語》中“學”之思想的理解。
一、《論語》中“學”之基本內涵
通觀《論語》中“學”之一字,凡出現六十五次,其大略有兩種含義,一為學習、效法,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學而不厭”(《述而》);二為學識、學問,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政》),等等。論語開篇即道盡學之要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學習六藝并且能在適當的時候踐行之,不也感到很歡欣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遠來拜訪我,不也感到很快樂嗎?他人不了解卻不感到憂郁憤怒,這不正是君子的表現嗎?
邢昺引《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①此處之覺悟者,當是指認識,即由啟發而得感性認識。“學”之古文字形主體部分從子從爻,可會意為學習計算,而朱子謂學為效,認為覺有先后,后覺習效先覺為學,故“學”即學習、仿效之義②。《說文·卷六·教部》:“斆(學),覺悟也。從教從冖。”“冖”是幕布,覆蓋義,喻兒童心智未開,懵懂無知,故須由老師傳授知識,蒙童受教而得以啟迪智慧、擺脫蒙昧。教與學密切相關。《說文》訓:“敎,上所施,下所效也。”“教”是長者引導晚輩模仿學習其言行。《禮記·學記》引“《兌命》曰:學(斅)學半”,“教”占“學”的一半,教學相長,相互促進。學能知己身之不足,教人而知何處困頓不通,然后可以自省自正。善教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而學者陶然醉乎其中。先時“學”“斅”并用,“學”中即含有學習、教授二義,而“學”之本義則可理解為教授學子知識且學子主動學習而漸覺悟,“學”是經驗的傳遞和思想的交相感通。春秋時在“學”旁加一“攴”為“斅(教)”,“斆”之右側為手執鞭撲之形,意為督促學子學習,“斅”與“學”二者之字義遂區分開來。秦以后又去“攴”作“學”,為主自覺,使學者自覺學習而得以開悟。以此觀之,“教”是自上而下傳達經驗,“學”是自下而上主動求知。蓋教在人,學在己,善教不善學,無可奈何也。
今人常將“學”“習”連稱,可見“學”與“習”間當有內在聯系。《說文》曰:“習,數飛也。”“數”有屢次、經常之意,朱子注:“學之不已,如鳥數飛。”③因而“習”之本義可理解為鳥雀在晨間反復張開翅膀練習飛行。曾子三省其身而有“傳不習”之虞,此處之“傳習”,或謂反復學習師長所授知識道理而熟之于心,或謂自己所授之業已然躬行體驗,因而“習”有復習、實踐之意,蓋從上處引申而出。上文之“學而時習”,有學者便釋“習”為復習、溫習之意,謂學當經常溫習之而能得其樂,固有其所循之理。以愚愚見,其依據在于教人“溫故而知新”,反復玩味之而常有新的見解和心得,故而內心得滿足充實,精神為之一振,欣喜便油然而生。此或為勉勵學者勤學不廢也。然常學而能常新者終是少數,對常人來說,重復式的學習難免煩瑣枯燥,又怎會樂在其中呢?故而要滲入現實情境來轉化其所學,即踐行、實踐之,方能增強“學”之幸福體驗。學要能行,知行要合一,不行不如不學也。唯我深得于學,了然于心,始能隨時施用,因時從宜。
“學”與“思”間關系亦非淺,“學”之本身便是一個抽象思辨的過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只學習而不思考則疑惑不解,光思考而不學習則其業荒廢。學習過程中若存在些許疑問,當先自己努力求索,再比較前人觀點深加探究,形成自己的見解,并以此為出發點向外發散而不斷調整、完善,最終合成一新體系。此見解未必是創見,亦確實不必過分追求標新立異,事事求新解,但一定不能是頑固不化之成見,否則必無大的影響力。頑固者或劃地自限,囿于孤室,自囚于思想牢籠之中不可自拔,或一味向書上用工而不入實景體驗,因而思維日益狹隘化,治學氣度日漸短淺。其未嘗不窮思冥索力求突破,卻難逃偏枯。故學不可固陋,固陋則不能變通,此乃為學之最下乘。
“學”源自社會生活實踐并作用于社會生活領域。學習之內容,就當時語境背景下,不僅指抽象的知識經驗,還有禮、樂、射、御、書、數(即六藝)等行為規范和社會生活技能。《述而》中說孔子教學之條目:“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即要求學“道”“德”“仁”“義”四類。“道”為終身奉行之信仰與守則,德為汲汲以求之目標,仁為人與人相處之原理,六藝為生活所必須掌握之技能。然其又說孔子以“文、行、忠、信”為主要內容,蓋自上推出,而孔門學者自當以此四者為學。孔子又重詩教和禮樂之化,于是學“詩”“禮”“樂”三者。詩以言志,表達性情;禮以規范,立身處世;樂以怡養,和順自然。由是可見“學”之內容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亦即包括了感性經驗與實踐經驗。
二、“學”之依歸
“學”合外內之道,是自我德性的內在修持與個體行為外化調整的有機統一。其必有所依歸的準則和瞻望的方向,我們因之得以自我完善、充盈生命的格局,化理想之本然或應然為現實存在之實然。揚雄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④”儒家學者皆追求“君子”這一理想人格,而唯有“學”這一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自修過程才能達成其憧憬。“學”何以有可能呢?
首先,學能成道。孔子之道,平易近人,人間道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各行業工作者在其工作地點完成相應的工作,君子(亦即道德之先行者)通過學習來完成他們的使命。此處之“道”,錢穆先生解作“人道”,即人所由之道路、途徑,人應終身學習以致之;李澤厚先生則譯之為事業,亦云須努力學習以完成之⑤。蓋二者所言大略相同也。竊以為,“道”即是我們所秉持的原則和生命的終極追求,一以貫之謂之道。其屬命定之必然,人人皆具有而不可不踐履,踐履謂之“行道”。既行得此道,便須篤實前進并極力拓展、推行之,令其發揚光大,顯達于世,此即“弘道”。惟當我矢志成全此道使臻于完善,方可實現自我之價值,而“成道”在于“為學”,“非學無以明道,亦無以盡道之蘊而通其變化”。“人不學,不知道”(《禮記·學記》)人若不學習便無從知曉道理。學以知道,明白有此道之存在;知道然后能信道,相信此道我有之且我能行之;我堅定實行而后能“致道”,即完成之使之圓滿。而此道之存在亦使為學有了明確的方向而更能堅持下來。道之所得本于學,學之所求即在道⑥。“道”“學”不相離,道大則學益進,學高則道益廣,“道”以成“學”,“學”以致“道”,即如是也。
其次,學以求知。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季氏》)學而知之,乃自覺自為之學,強調人之主動性;待困惑而將以學之,則帶有目的性;心存疑竇不消而不求解,便最是下乘。學然后能明白事理,于世間事物無不通透洞達,便不易為外物所屈抑和迷惑。孟子之“不動心”與荀子之“解蔽”即是為此。所知者為何?曰命,曰禮,曰言。命為人力所不可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列子·力命》)我因命行此道,道本于心,既順從本心,則知其不可而為之,此為我誓所必行也。禮既行事之準則、行為之規范,不知禮則無所措手足,無得恭儉莊敬以自立于世。言即思維活動、心理活動的表達,知言而能分辨是非得失。
再次,學以為己。“為己”是為專注自己道德學問的提升并以此周全、充實、成就自身,而非炫智于外,做表面文章,如此才能感通他人。“學”是為己之學,為己以成己,學以美其身。換言之,學習是為了成就自我之德性,不斷改進、完善自己,非為取悅于眾人也。“人不知而不慍”(《學而》),人不盡知我而不懷忿恚之心,則一來能顯我之寬容,不求全責備于人,二來修行自家事也,縱有不知我者,又何怨之有,自尋煩惱罷了。學之進退全在于我,故要自強不息。學雖為成己,卻不是說僅僅是自己之“私學”,局限于自我狹隘閾境便滿足了。儒家學者在致力于個人成長的同時不忘關注社會現實:“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當自我修養成熟時便能使周圍人信服,進而使天下人安樂,我有此愿望且有能力成就之,這體現出了高度的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亦是學者為學的最高追求和對整體生命的終極關懷。故為己以成己,成己以成人。學以成人,成人即能行仁,能盡人之道,處理好人與人間的關系,使人人相親。仁有“恭、寬、信、敏、惠”五項條目,以近取譬,則為仁在己,求仁而得仁。好學深求究其實,乃能成其仁。故“成己”是“成人”的基礎,“成人”是“成己”的延伸,“學”是為己與為人、成己與成人的內質性統一。
最后,學以成德。德猶得也,行道有得于心為德。德乃人與生俱來之質性的發揚,由先賦而后致,漸成長為良好的人格品質。“德”有知、仁、勇三者,一以分明,一以自持,一以踐行。知者明道達義,心不惑亂;仁者心懷天下,坦蕩無私;勇者心無恐懼,直道前行。其中“知”為起始,然后能達“仁”“勇”之境,而成知必始于學。無以文滅質,矯飾天性稟賦;亦無使質勝文,令其流于粗野。儒家要求君子德才兼備,品學兼優,而德育向來重于智育。為學以輔德、成德。學乃成德之修,德重于學。縱使人才力超絕,然其不講究操行,則不可謂盡善盡美。若其心懷不軌,走向歧途,則學愈高遺害愈大,終是戕賊于世。
綜上所述,“學”以“成道”“求知”“為己”“成德”而俟乎君子,“學”是經驗的表達和知識的踐履,其借由個體的內在努力達到自我與外界認同,突顯了人的主體能動性,推動理想人格與現實人格的和諧融合而止于至善。
三、“學”之思維理路
(一)“學”之態度:何以“為學”
其一,求學須敬,學主謙敬。“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而》)不敬則學不固。當知學問無窮,人之于學不過浩渺星海一孤舟,當常懷敬畏之心,莊敬肅正,孜孜以求之。而或學問有所得,則知我所不知者甚眾,而日益虛心向學。
其二,問學須誠,學貴乎誠。當自誠于己,克念克敬,使思慮純正,澄澈光明。不為貧富死生易其志,安貧樂道,守死善道。為學不可自欺,不茍其言,知則知矣,不知則不知矣,而不可蒙蔽自心。
其三,治學須精,學貴精一。心致志,用功于一處,方能勇猛精進。
其四,為學須謹。應嚴于律己,嚴格自我學習、自我教育。學習過程中一不可妄加臆測,逾越本位,胡思亂想;二不可自慊自是,驕吝自滿者將不得寸進;三不可執滯于物,不知變通,要有辯證、綜合思維,能夠適時達變。
其五,好樂其學。“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應好學、樂學,好學者以學為目的和歸宿而非工具手段,樂學者學之能有愉悅生發,則可長久堅持而不倦。
其六,學貴有恒,欲速則不達。一曝十寒不可取,躐等而求不可能,半途而廢則前功盡棄。真積力久才能畢其功。
(二)“學”之方法:何以“成學”
第一,以“時”學。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⑦”即學習要有規律性,在適當的時候學習,就身心發育、季節變化和晝夜交替不同的階段安排不同的內容進度。進學有次第,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學莫貴乎立志。為學之要正在于立志,即要“志于學”。朱子曰:“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⑧故立志須高遠,高遠則心氣挺拔而不狹隘自慊,知學無止境而不畏葸,反有終身學習之心;立志又要篤實,不可虛無縹緲,過分理想化,所謂“望山跑死馬”,要能看到可行性,如此才有繼續前進的動力。向學之心堅定則力學以立身,立身兼立道與立業為一,道既立則目標明確而不為外物亂其心,由此上達而知天命,亦即我所必然之擔當,隨年漸長學漸進內心始覺通達,能聽得異議并知曉其理所在而服之,終至于言行舉止莫不任意施行而合于規矩之內,得內心無限自在之體驗。斯六者環環相扣,銜接致密,不可一蹴而就。此為進學之階段,亦為進德之順序。
第二,學“經驗”,即師法前人。“人必學于人,尤必學于古之人,始獲知道。”⑨須沿先行者腳步行進,與前人智慧相交涉,汲取其已摸索出來的經驗加以借鑒,裨益自身。縱有良材美質可不依循成法而為善,若不學亦不能登堂入室。
第三,“一”其學。博學而能“一”以貫之,即求有貫通諸學之道。學習應有重點,盲無目的地學便會導致雜亂無章。應培養核心思維能力,結合自身規律凝聚自己的思維核心并以此發展出自己的學習體系,理清脈絡,學習便事半功倍。
第四,能近取譬,見善則遷。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多人共處則其中必有優于我者,其或在某一領域有專長,或在某種程度上某些品質較我更突出,皆值得我取法。學無常師,達者為師,我們應見賢思齊,擇善而從,敢于求教,既能問道于才高者而不怯,又能求教下問而不以為恥,虛心向身邊人學習。
第五,為學須重微,即要積累,積學以窺圣境。“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淺處更見其真義。惟有精微之至,始是廣大之由。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為學須從細處做起,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積少成多,逐漸養成至大成的境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亦當知學無止境,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而能有極高造詣。
第六,為學須內省,即要省察克治,查漏補缺,獨立思考。如孔子言“九思”而求明、聰、溫、恭、忠、敬、問、難、義,極盡省察之功。內省在于改過:一要自省其身,知錯認錯,自知錯在己身而能坦然承認;二要敢于改正,知其不善而速改以從善,而不能一味畏難不愿補救,否則便可能會使錯誤擴大化,積重難返;三要做到“不貳過”,切不可重蹈覆轍,一錯再錯。
第七,注重“群學”。“學”在群己之間,既須慎獨自律,又須樂群敬學。“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久。”⑩人生而群居而非隔絕于世,故學須取之于群體生活之中。要注重“群學”,即要重視環境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好的學術氛圍能改善集體學習風氣,如眾向善而我亦向善,眾好學而我亦好學。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所受局限畢竟較大,而置身群體中則有可能尋得三兩學術道友,彼此交流、借鑒,取長補短,相得益彰,相與輔德進道,大道同行。敬學樂群須戒慎乎群居而不學善道,思非其位,言不及義而好賣弄聰明、欺惑愚眾。
四、“學”之精神的現代延伸
《論語》中“學”之思想對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其一,就個人成長而言,“學”有助于擺脫自我偏見,強化其主體性認同社會感覺能力,促使其與現實社會發生聯系,深化其對社會活動的理解,培養人的親社會意識趨向并激發行為,防止人格異化。其二,化道德之應然為現實之實然,實現人生價值。“學”之一字貫穿人們修養發展過程之始終,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通過自我教育和熏陶提升內在涵養,賦予個體以精神超越的力量。其三,引領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增強其判別是非的能力和抗誘惑能力,以在競爭激烈、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應對各種復雜的挑戰和考驗。
同時,“學”之思想還有助于維持社會的穩定、生存和延續。學以成人,促進人的社會化進程,將其培養成為社會所需之人才。“學”之思想還對當代教育理念的改革、教學方法的創新以及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構建亦頗具啟迪作用。其重視樂感教育,教人樂于學習,學以為樂,享受學習過程而得到內在精神滿足和升華。再如,啟發人博學返約,致廣博而不駁雜。當今之世重實學,強調學以致用,然而學習不可只關注于政治、經濟等實用性之學,亦須了解其他各類學問。筆者認為,世無無用之學,只有無用之人,應以開放的襟懷包容人類世界所產生的各種思想、學問,善加甄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予以適當的“揚棄”,批判并有選擇地繼承之、發展之、匯通之,結合時代精神賦予的新內涵、新詮釋,最終道以成人文,“學”止于至善。
新時代學習觀與《論語》中“學”之思想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繼承了重視學習的優良傳統。習近平學習觀指明了當代社會的學習導向,是傳統“學”之思想的價值表達和精神凝結。學習習近平學習觀,領悟其中“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學”之思想,有助于學者認清學習理想與實際需求之張力,防止功利主義學習傾向。引導當代學者樹立正確的學習思想,培養學習的使命意識,既迎合現實需要,又呼應時代要求;既立足當下實際,又著眼未來發展。譬如,傳統“學”之思想提倡學思并重,而習總書記亦認為“讀書學習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思考認知的過程”?。再如孔子曾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而習總書記亦強調學習應有緊迫感,當發憤忘我,迎頭趕上,不可有懈怠之意。
當代國際競爭的實質乃在綜合國力的較量,學習在這種角逐中起先導性作用。不學則無以應對劇烈的社會變革,更無以在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穩步前行。“我們的民族要上進,就必須大興學習之風,堅持學習、學習、再學習,堅持實踐、實踐、再實踐。”?學習是獲取進步、完善自我、實現超越的源頭活水。我們應持向學之心、立深學之志、具真學之力、明善學之道、修勤學之功,自覺以習近平學習觀為引領,通過學習以汲取先進經驗,優化知識結構,拓寬認知渠道,拔高思想境界,突破理論視野,鑄就世界格局。應在學習過程中掌握社會運行之客觀規律,學會協調人際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努力成為社會所需之通才,并由之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養,增強社會創造力,為社會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在探究“學”之思想含蘊過程中貫徹學習實踐,此即“學”之精神的現代延伸。
【注釋】
①⑦(三國)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1頁。
②(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中華書局,2011年,第49頁。
③(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中華書局,2011年,第49頁。
④(漢)揚雄撰《法言注·學行卷第一》,中華書局,1992年,第15頁。
⑤參見錢穆《論語新解·子張篇第十九》和李澤厚《論語今讀·子張》。
⑥錢穆:《論語新解》,三聯書店,2012年,第359頁。
⑧(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中華書局,2011年,第54頁。
⑨錢穆:《論語新解》,三聯書店,2012年,第376頁。
⑩錢穆:《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頁。
?習 近平:《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推動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建設》,2009年《學習時報》。
?顧俊:《習近平學習觀的豐富內涵和核心要義》,2016年《唯實·理論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