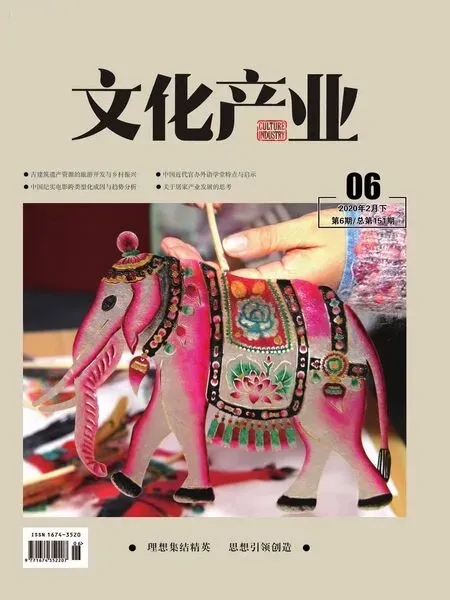淺析徽縣民歌
◎成子恒
(甘肅省徽縣文化館 甘肅 隴南 742399)
徽縣位于甘肅東南部,隴南市東北部的徽成盆地,自古是秦隴文化、巴蜀文化交匯地帶。徽縣自明代洪武7年知州金堅創辦學宮,首開辦學之先河,嘉靖13年全縣已有三元書院、風山書院、風鹿義學、峽門私塾等義學私塾90余所。至民國4年全縣興辦初級小學39所,還建立了吳山女子小學。歷代文化教育的發展,為徽縣傳統民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民歌歌詞的創作、記載、傳播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歷代文人在徽縣的足跡
漢唐以來,名人吟詠徽縣境內山水勝跡的詩詞、文賦達200余篇(首),詩仙李白曾贊嘆蜀道名山青泥嶺,寫有名篇《蜀道難》;詩圣杜甫經徽縣南奔入蜀時,在徽縣境內留下了《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等紀行詩和“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的哲理名言。柳宗元、陸游、韋應物、武元衡、趙忭等文人雅士亦分別留下了鴻詞佳句。
南宋時期,宋金交戰,川陜宣撫(指揮部)設于此地。抗金名將吳玠三兄弟,憑仙人關及鐵山棧道抗金數十年,在境內仙人關以三萬人一舉擊敗金兵十萬之眾,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明代,徽縣經濟繁榮,文人薈萃,英才輩出。洪武22年,名道士張三豐在徽縣(州)境內停留10余年,不僅賦詩作畫,還在侯家酒店編歌舞蹈,以贊佳釀;徽籍進士高斗南、郭從道、郭莊等異地為官,清正廉潔,惠政多方,嚴懲邪惡,無私為民。另據民間相傳,朱元璋之女安慶公主曾在徽縣境內出家修行,將所居之五口窯洞取名為“五徵窯”,對徽縣民歌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形成宮廷音樂與民間音樂相結合的新產物。
清代徽邑進士張授,詩文過人,學識淵博,曾為侍讀翰林,先后侍奉乾隆、嘉慶兩代皇帝,后出任廣西學政,名節振奮,被朝中奉為楷模,榮耀鄉里,文化后生。近代教育家、書法家于右任1922年6月自陜入川,在徽縣停歇,留下了《徽縣早發聞耕者嘆息聲》等詩篇。
二、徽縣民歌的文化內涵
歷代文人的影響,詩詞文賦的吟誦和流傳,豐富了徽縣民歌的創作思想和表達能力,增強了徽縣民歌的文化內涵。人們除了觸景生情、即興隨編隨唱外,其所作所唱民歌內容由一般簡單的陳述發展到借助傳統文化形式,利用文學藝術手段根據民間故事、歷史事件、人物、神話傳說及其人民群眾生活中的典型素材,編寫具有文學特色、曲藝或戲曲特點的民歌作品。如筆者搜集的流傳于徽縣伏家鎮李窯村丁溝社的《踏雪尋梅》:
冬九寒天樹木殘,鵝毛大雪飛滿天;
久愛梅花,開在深山。
孟浩然抬頭用目看,一片風景在面前;
……
背背書包懷抱劍,一張古琴肩上擔,
你騎驢我步趕 ,一老一少登陽關。
此歌表述了孟浩然騎著毛驢,帶著書童,在冰天雪地尋賞梅花、品味冬景、熱愛大自然的文人雅趣。其表達形式既有具體人物形象、表演,也有道白(對白)和歌唱。
再如徽縣西北地域內普遍流行的《山伯訪英》:
鑼響鼓兒賽,閑言且丟開,
要唱梁山伯祝英臺,山伯訪英來
……
《山伯訪英》與《踏雪尋梅》作為人文趣事的記敘和縮影,表明徽縣民歌的內容及內涵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山野歌曲,不僅具有鮮明的文學色彩,而且具有強烈的思想感情和曲藝戲曲特點。這些在徽縣民歌中此類作品比比皆是,如《賣花線》《出曹營》《趙匡胤送金妹》《釘缸》《南橋擔水》等。
三、徽縣民歌的藝術特點
徽縣民歌以自身民族民間音樂載體的功能和形式,反映和謳歌了當地的人文歷史、社會、自然、風土人情以及人們的勞動、愛情婚姻、日常生活等,表達了人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是人們認識徽縣、了解當地社會現象、民風民俗的寶典和學習徽縣文明史不可取代的重要窗口。
徽縣民歌主要分為勞動歌、情歌、敘事歌等類型,多抒情,采取賦、比、興的文學手法,構成了表現形式豐富、風格粗狂而獨特的藝術特點。徽縣民歌語言純樸,旋律單純、直抒胸臆,比如水陽鎮茍家溝茍生貴的《糶黃米》:“黃楊木扁擔軟咻咻,擔上扁擔上秦州;頭上青絲如墨染,八寶金環墜耳邊;柳葉彎眉杏核臉,糯米銀牙尖對尖。”
再如,筆者的山歌《因特網通到了五徵窯》:
東山的日頭西山照,雨過天晴豁朗了;
羚牛抵角野鹿跑,三灘的老林沒邊稍;
金山大樓房高,因特網通到了五徵窯。
腳跟沒挪出山了,到了天涯海角了;
登月家么下洋家,鼠標輕輕點給下。
這首山歌語言純樸,簡明洗煉,文學藝術性強,以方言演唱,鄉土氣息濃郁,形象生動鮮明,體現民風民俗,富于原始美,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采用廣大老百姓易于操作的民歌形式直接反映地方信息化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富有創造性。
四、結語
徽縣民歌歷史悠久,豐富多彩,在民間流傳十分廣泛。20世紀80年代初,徽縣文化部門搜集整理了《徽縣民歌選》,收入民歌百余首,有20余首被選入《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甘肅卷》。近年來,徽縣文化、教育部門聯手開展非遺進校園活動。徽縣一中、徽縣實驗小學等把徽縣民歌列入《親近歷史,走進徽縣》《我愛徽縣》等校本教材,讓“讓非遺保護,從娃娃抓起”的口號找到了落腳點,為地方民歌有序傳承發展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