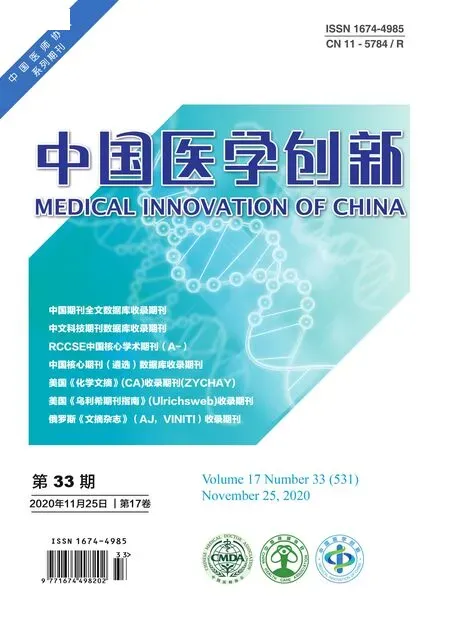3.0T磁共振IDEAL-IQ技術在原發性骨質疏松中的初步研究價值*
蘇青青 段早輝 周寧杰 洪翾 朱立文
原發性骨質疏松是一種隨年齡增長而必然發生的生理退行性病變,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導致病情加重。該病主要是由于機體的骨量降低、骨強度下降等因素導致的骨代謝機制異常,在臨床多表現為疼痛、脊柱變形或骨折等,導致患者的活動受限、生活無法自理,且增加了肺感染及褥瘡等發生率,不僅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同時也提高了致殘率與病死率[1]。近年來,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與醫療設備的更新,QCT 骨密度測量在骨質疏松診療的臨床應用已在國內外專家達成共識并廣泛應用臨床工作,但QCT 檢查主要測量的是骨密度改變情況,而無法評估骨髓脂肪含量,且具有一定輻射傷害[2-3]。磁共振成像(MRI)迭代最小二乘法水脂分離定量(IDEAL-IQ)技術作為無創脂肪定量技術,在對椎體病變導致的骨髓含量變化中得到初步應用[4]。鑒于此,此次探究將回顧性分析2018 年4 月-2019 年4 月本院收治的原發性骨質疏松患者40 例的病例資料,探討3.0T 磁共振IDEAL-IQ 技術在原發性骨質疏松中的初步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 年4 月-2019 年4 月本院收治的原發性骨質疏松患者40 例的資料,將其納入觀察組。納入標準:觀察組患者均符合《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2017)》[5]中相關診斷標準;觀察組患者資料完整。排除標準:因其他因素導致的骨折;伴有內分泌、代謝系統疾病;合并惡性骨腫瘤。另選擇同期本院健康體檢者40 例,將其納入對照組。本研究設計符合醫學倫理相關規定。
1.2 方法
1.2.1 檢測方法 (1)MRI 檢測。采用SIGNA Ploneer GE 3.0T MRI(美國通用電氣醫療集團生產)掃描儀,掃描線圈采用8 通道脊柱線圈。掃描序列如下:①矢狀位T2WI。設置TE 為102 ms,TR為2 900 ms,矩陣為352×256,視野(FOV)為320 mm×320 mm,層厚、層間距分別為4、1 mm,激勵次數設置為2 次。②矢狀位T1WI 序列。設置TE 為8.6 ms,TR 為550 ms,矩陣為320×224,FOV 為320 mm×320 mm,層厚、層間距分別為4、1 mm,激勵次數設置為2 次。③矢狀位抑脂STIR序列。設置TE 為68 ms,TR 為4 500 ms,矩陣為288×224,FOV 為320 mm×320 mm,層厚、層間距分別為4、1 mm,激勵次數設置為2 次。④矢狀位脂肪定量IDEAL-IQ 序列,翻轉角度為3°,設置TE 為2.6ms,TR 為5.5ms,矩陣為288×224,FOV 為320 mm×320 mm,層厚、層間距分別為4、1 mm,激勵次數設置為2 次。(2)定量CT(QCT)。采用西門子Somatom Defination AS64 排128層螺旋CT 對所有研究對象進行檢測,患者取仰臥位,屈膝使腰椎曲度消失,平呼吸狀態下取L2~4部位檢測,采用固體標準件體膜以及人體長軸平行墊于腰下,腰椎側位片中心與L3部位,椎體中央骨松質部分為感興趣區域。
1.2.2 圖像分析 將MRI 檢測圖像上傳至工作站,將IDEAL-IQ 序列檢測結果生成FF 值圖,由兩位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骨肌MR 診斷醫師于L1~4椎體進行感興趣區域的勾畫,感興趣區域大小為20~30 mm2,若出現結果不一致則進行商討確認結果一致為止。其中椎體骨密度值(T)為(測定值-同性別同種族正常人骨峰值)/正常人骨密度標準差。其中T≥-1 則表示正常,T 值≤-2.5 則表示骨質疏松。
1.3 統計學處理 此探究采用SPSS 18.0 處理數據,全部計量資料均經Shapiro-Wilk 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以()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四分位數表示[M(P25,P75)]表示,采用兩個獨立樣本的 Mann-Whitney U 非參數秩和檢驗;繪制受試者工作曲線(ROC)評估FF 值的診斷效能,得到曲線下面積(AUC),AUC>0.7 提示預測價值理想,并采用雙變量Pearson 直線相關檢驗分析T值與FF 值的相關性,r<0.5 表示弱相關,0.5≤r≤0.8表示中度相關,r>0.8 表示顯著相關。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觀察組男25 例,女15 例;年齡52~84 歲,平均(67.42±5.35)歲;病程1~35個月,平均(15.72±1.63)個月。對照組男27 例,女13 例;年齡50~83 歲,平均(67.38±5.62)歲。兩組基礎資料(年齡、性別)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兩組T 值與FF 值對比 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T 值較低,FF 值較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T 值與FF 值相關性 經雙變量Pearson 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雙能X 線骨密度儀(DXA)與磁共振IDEAL-IQ 序列檢查的T 值與FF 值間呈負相關(r=-0.502,P<0.05),散點圖見圖1。

表1 兩組T值與FF值對比

圖1 T值與FF值相關性散點圖
2.4 FF 值預測原發性骨質疏松的價值 將原發性骨質疏松作為狀態變量,將FF 值結果作為檢驗變量繪制ROC 曲線,結果顯示,FF 值檢測原發性骨質疏松反應性曲線下面積為0.793[95%CI(0.697,0.890],最佳閾值為41.83,靈敏度為97.50%,特異度為82.30%,約登指數為0.798,ROC 圖見圖2。骨量正常患者脂肪含量正常,無骨質疏松,見圖3。骨質疏松患者脂肪含量增高,存在明顯骨質疏松,見圖4。

圖2 FF值預測原發性骨質疏松的ROC曲線圖
3 討論

圖3 骨量正常患者MRI-IDEAL-IQ脂肪分數圖像

圖4 骨質疏松患者MRI-IDEAL-IQ脂肪分數圖像
原發性骨質疏松的主要特征是骨量丟失及骨結構破壞導致骨脆性及骨折易感性增加的生理退行性病變[6-7]。人體骨量取決于骨骼中破骨細胞的骨吸收、成骨細胞的骨形成動態平衡,在患有骨質疏松時,人體骨吸收超過骨形成而致病[8]。該病多見于老年及絕經后的婦女群體,不僅可導致患者出現腰背酸痛、行走困難等表現,還可能造成患者的脊柱變形而導致胸廓畸形,從而影響患者的心肺功能。
目前,臨床針對原發性骨質疏松的診斷多通過測量骨特定區域的骨礦物質含量、骨密度值以診斷骨質疏松,但單獨依靠骨密度值無法準確對骨含量進行解釋。相關文獻表明,骨髓中脂肪含量的增加能夠降低骨細胞的生成,從而導致了骨質疏松的發病,或加重了病情的嚴重程度[9-11]。對于骨密度的測量目前應用最多的為QCT,其作為三維體積骨密度測量技術,與其他骨密度測量技術相比具有許多優越性:QCT 可分離骨皮質和骨松質,松質骨感興趣區容積很大程度上不受脊柱退行性變的影響且QCT 可以應用3D 幾何測量參數,因此QCT 骨密度測量在骨質疏松診療的臨床應用已在國內外專家達成共識并廣泛應用臨床工作[12-13]。但QCT 測量的準確性和重復性受測量區有植入物、患者不能保持正確體位、近期靜脈注射對比劑等情況的影響,且該方法還具有一定的輻射損傷,同時無法測量骨髓脂肪的含量。脂肪組織在骨質疏松的疾病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對骨量的變化進行客觀反映,被認為是影響骨質疏松的重要因素[14-15]。目前,隨著MR 技術的日益發展,磁共振波譜成像測量技術被廣泛應用于脂肪定量的測定中。但由于磁共振波譜成像測量技術對掃描的要求較高,且后期圖像處理相對復雜,加之為保證圖像質量以及準確性,在檢測中大多僅能選擇單體素波譜成像,而單體素波譜成像1 次只能對1 個椎體進行掃描,導致實用性下降[16-17]。IDEAL-IQ 作為脂肪定量技術,具有操作簡單、掃描時間短、后期圖像處理簡便等優勢,其與骨密度雙能X 線吸收法相比具有可重復性高、無電離輻射應用愈加廣泛[18-20]。此外,該技術還可在1 次掃描中產生6 組圖像,無須進一步計算組織內的脂肪比且通過復數域重建脂肪比定量微調并通過除去相位錯誤提高診斷效率。本探究結果顯示,觀察組T 值較對照組低,而FF 值較對照組高,且經雙變量Pearson 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DXA 與磁共振IDEAL-IQ 序列檢查的T 值與FF 值之間呈負相關,與徐良洲等[20]結果一致。進一步做ROC,結果顯示,FF 值檢測預測原發性骨質疏松反應性曲線形面積為0.793[95%CI(0.697,0.890)],>0.7預測價值較好,約登指數為0.798,進一步說明了FF 值檢測原發性骨質疏松的診斷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但因本探究屬于回顧分析類,得到的結果可能與實際存在偏差,加之無較多的循證依據可作為支持,故結果的真實性與準確性還應繼續在未來進一步探究驗證。
綜上所述,3.0T 磁共振IDEAL-IQ 技術在原發性骨質疏松的診斷中效能較高,其FF 值能反映骨髓脂肪含量的變化,且在預測原發性骨質疏松中有一定價值,值得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