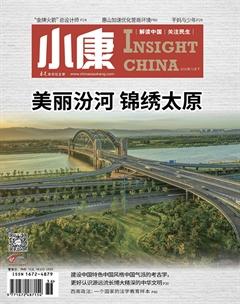人臉識別要遵循法律邊界
郭倩
近日,有關“人臉識別第一案”宣判的報道見諸各大媒體。“人臉識別第一案”判了,身為法學副教授的郭兵把自己的“臉”要回來了!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仿佛可以在郭兵的勝利中,安撫自己對人臉識別的擔憂。
然而,仔細閱讀法院判決,我們會發現,事情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根據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公眾號中公布的信息:2020年11月20日下午,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宣判原告郭兵與被告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判決野生動物世界賠償郭兵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1038元,刪除郭兵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征信息;駁回郭兵提出的確認野生動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關內容無效等其他訴訟請求。用郭兵自己的話說:“從判決內容來看,其實我的大部分訴訟請求沒有得到支持,對于沒有得到支持的訴訟請求部分,我都是不服的,我都會選擇上訴。”
既然退了錢,還要回了“臉”,郭兵為什么還要上訴?這恰恰表明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對人臉識別技術濫用的深深憂慮。富陽法院審理認為:“野生動物世界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指紋識別、人臉識別等生物識別技術,其行為本身并未違反前述法律規定的原則要求。但是,野生動物世界在合同履行期間將原指紋識別入園方式變更為人臉識別方式,屬于單方變更合同的違約行為,郭兵對此明確表示不同意,故店堂告示和短信通知的相關內容不構成雙方之間的合同內容,對郭兵也不具有法律效力,郭兵作為守約方有權要求野生動物世界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換句話說,郭兵之所以要回了“臉”,是因為野生動物世界一開始要求用指紋識別入園,之后就不能未經郭兵同意單方更改為人臉識別。而并不是因為野生動物世界要求人臉識別入園的做法違法。相反,如果一開始園方就明確要求用人臉識別方式入園,那么郭兵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同意,要么別來。筆者認為,這一判決理由非但不能減輕公眾對人臉識別濫用的憂慮,反而確定了這種濫用現狀的合法性。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案的爭議焦點同時也是公眾關心的焦點其實很明確,那就是:經營者處理消費者個人信息,尤其是指紋和人臉等個人生物識別信息時,法律邊界在哪里?我國《民法典》的第四編人格權的第六章規定了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的內容。依據該章規定,指紋和人臉信息屬于生物識別信息,其和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一樣都是個人信息。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然而,什么叫“過度處理”,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這也是導致人臉識別濫用的重要原因。這需要監管機關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明確,需要司法機關、執法機關在具體法律適用中加以確定。
人臉識別是個新事物,我們不能苛求立法速度與科技發展同步,但是刷臉技術成為資本驅動之下的“風口上的豬”,不管有沒有必要,什么場景都要加一個“刷臉”,這確實會給社會和個人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因此,我們要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搭建起防止人臉識別濫用的法律圍墻。對生物信息處理適用“必要原則”和“最小夠用原則”:對市場經營主體來說,能不用的,就不用;對政府監管主體來說,能慎用的,要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