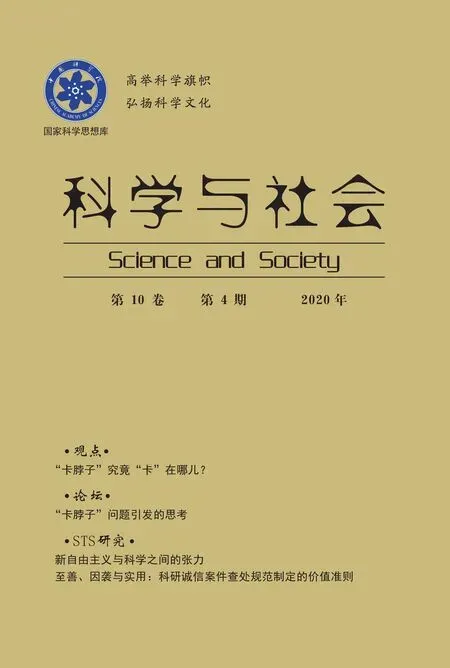打造創新型企業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一個關鍵
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焦點:中國受制于人的關鍵技術,特別是被“卡脖子”的技術和產品,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的創新型企業研發和控制著。中國應當將創新型企業的培育和扶植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只有企業在創新方面有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將“創新驅動”落實到市場競爭中的拳頭產品上,創新這個“引擎”和經濟發展才容易“掛擋”。
中國正著力提升創新能力,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目前,國家的整體科技水平離“創新驅動發展”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在諸多關鍵領域被發達國家“卡脖子”。面對嚴峻的競爭現實,我們須找準著力點,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新”(innovation)成為中國社會普遍關注和熱議的話題。“創新”本來是指將新概念的構想或技術發明轉變為新產品、新方法和新服務并進入市場的過程。我們姑且將之稱作狹義的創新。后來,“創新”被拓寬為新知識和新事物的創造,涵蓋了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等,并具體地衍生出科技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社會創新和文化創新等概念。
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工業化基本上都起步于19世紀60年代。意大利半島曾是近代科學革命(科學原創)的先行者,但其工業化與技術變革卻晚于英國和法國。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開始引進西方技術和走向工業化,在20世紀成為技術創新“后來者居上”的一個典型。近代以來,中國長期通過技術引進等舉措來實現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發展,到20世紀開始有所創新,20世紀90年代空前地重視創新。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進步顯著,科技論文產出躍居世界前列。與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國產業總體上處于國際上的中低端,在高端裝備、關鍵元器件、新材料和新工藝等許多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受制于人,甚至被“卡脖子”。我們有企業躋身世界500強,但其技術創新能力卻不夠突出。中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部門究竟為企業技術的進步和創新貢獻了多少新知識?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科學原創是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重要知識源,這一點充分展現在現代高技術領域。因此,我們怎么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從謀長遠發展著想,中國的確要擁有精干的基礎研究隊伍,使之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一個重要“方面軍”。科學家們希望政府穩定地支持高水平的基礎研究,安心地追求卓越的科學原創。
科學原創成果通常以論文等形式公開發表,容易被不同的國家、機構和個人分享。發表高水平科學論文是必需的,但這只是國家創新實踐的一個部分。科學原創向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的轉化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也就是打通科技和經濟之間通道的過程,這正是狹義的創新。創新能力強的國家及其企業更擅于合理選擇和消化基礎研究的成果,有效地將科學原創轉化為生產力,引領產業發展。
中國的大量重要科學論文以英文撰寫,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這些論文便于外國讀者閱讀,但不便于中國企業的廣大技術研發人員快速閱讀。國內很多企業的研發人員專心于具體的技術工作,并不常查閱各種外文論文,或者閱讀外文較慢,甚至因條件限制而查看不到多少外文書刊。面向國內的創新需求,中國科學家理應多以中文發表論文。科技評價體系的改革十分必要和迫切。
科學原創和技術創新未必總是遵循簡單的單向遞進關系。技術是兼具獨立性和開放性的知識體系,是直接的生產力。技術創新可能早于科學原創,形成重大的發明,并直接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19世紀美國在科學原創上遜色于西歐,但技術創新能力與歐洲的差距較小,有自己的技術特長和很強的產業競爭力。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曾經有相似的特點,比較擅于搭科學原創國家的“便車”。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有自己的定位,不可能包辦各種各樣的狹義創新,即不可能包辦那些應該由企業做的創新。企業面向市場的觸角要比科研院所和大學多得多,對用戶需求也更加敏感,擅長做量大面廣、多樣化的技術創新。大多數創新最終要通過企業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解決戰斗”。事實上,創新型企業掌握著影響市場競爭力的關鍵核心技術,成為發達國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在創新方面成為不可替代的角色,國家才有在國際競爭中討價還價的硬資格。事實上,中國受制于人的關鍵技術,特別是被“卡脖子”的技術和產品,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的創新型企業研發和控制著。
中國應當將創新型企業的培育和扶植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著力點。這也是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目前國家高度重視科研院所改革(如建設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的“雙一流”建設。相對而言,國家還須推出更多“實錘的”政策和改革舉措,促使企業真正成長為技術創新的主力。只有企業在創新方面有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將“創新驅動”落實到市場競爭中的拳頭產品上,創新這個“引擎”和經濟發展才容易“掛擋”。
中國企業制度有待進一步改革。多數骨干企業是國有的,國企領導是國家干部,政府有責任在促進改革方面發揮較大的作用。人們希望看到,企業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勇于和擅于創新,并因創新而得到應有的收益或補償,形成良性的發展機制。如果國有企業能夠闖出一條新路和新模式,以“主體”角色提升創新能力,不斷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與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部門相得益彰,那么,我們就可能早日建成世界科技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