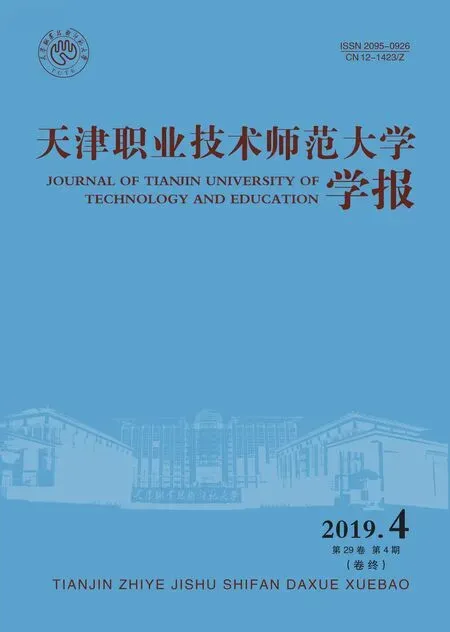埃塞俄比亞語言政策的歷史演變與現實挑戰
高莉莉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222)
語言政策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它具有鮮明的國家特點,一般來說指的是由國家制定的關于語言的重要準則和規定,以及體現一個國家語言態度、立場觀點和語言意識形態的語言文化[1]。語言是認識一個國家的鑰匙,語言政策研究是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語言國情和民情不可或缺的路徑[2]。埃塞俄比亞是東非大國,是“一帶一路”建設在非洲的重要節點國家,也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語言國家,了解埃塞俄比亞的語言政策對全面認識其國情、促進中埃合作和命運共同體建設起著重要作用。基于此認識,本文將聚焦埃塞俄比亞語言政策問題,對埃塞俄比亞不同歷史時期的語言政策做出梳理,探查語言政策的歷史演變,總結其多元復雜的語言狀況,并以多語教育的現實挑戰為例,對其語言政策實施中面臨的問題提出思考。
1 埃塞俄比亞語言政策的歷史演變
埃塞俄比亞位于非洲之角,采取以民族區域劃分為基礎的聯邦制政體。境內有80 多個民族,80 多種語言,以阿姆哈拉語為聯邦政府工作語言,英語為通用語,主要民族語言有奧羅莫語、提格雷語、錫達莫語等。其語言政策的發展可以從前海爾塞拉西時代(1930 年前)、海爾塞拉西時代(1930—1974)、軍政府時代(1975—1991)以及聯邦制時代(1992—今)這4個主要的歷史時期來進行考察。
1.1 前海爾塞拉西時代(1930年前)
從語言政策的角度出發,20 世紀30 年代之前,即前海爾塞拉西帝制時代被埃塞俄比亞本土學者稱為隱性語言政策時期[3]。這一時期沒有成文的語言政策,但歷代君王,特別是在埃塞俄比亞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3 位封建君主特沃德羅斯二世(1855—1868)、約翰尼斯四世(1872—1889) 和孟尼利克二世(1888—1910)都以其王權范圍內的不同語言實踐接續奠定了阿姆哈拉語作為埃塞官方語言的事實地位。特沃德羅斯是埃塞歷史上第一位把阿姆哈拉語作為正式書面語使用的皇帝,這一時期阿姆哈拉語已廣泛應用于國家的內政外交,該語言不僅被用于編年史的寫作,而且也成為皇帝本人與歐洲君主通信的書面語言。在約翰尼斯四世時代,阿姆哈拉語被指定為法庭用語,其作為通用語言的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現代埃塞俄比亞的構建者孟尼利克二世不僅延續了特沃德羅斯用阿姆哈拉語來撰寫編年史的做法,同時將阿姆哈拉語當作一種國家象征符號,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和使用。1898 年孟尼利克二世開展了阿姆哈拉語大規模掃盲讀寫計劃,史稱“互路一碼”(阿姆哈拉語,意為一起學習),并在其去世后由他的女兒扎烏迪圖接續進行。這個計劃進一步提升了阿姆哈拉語在埃塞國內的普及程度。19 世紀末,德雷達瓦和亞的斯亞貝巴出現了出版社,阿姆哈拉語是當時出版界使用的唯一語言。總的來說,前海爾塞拉西時代的埃塞俄比亞雖沒有明確的國家語言政策,但阿姆哈拉語作為國家通用語的事實地位已日漸形成。
1.2 海爾塞拉西時代(1930—1974)
在海爾塞拉西統治時期,出于構建較強國家認同的“大埃塞”和推進國內各民族交流的目的,封建皇權對內推行阿姆哈拉單語政策,并在1955 年《憲法修正案》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阿姆哈拉語作為國家官方語言的地位。隨后阿姆哈拉語成為全國各地小學的教育語言,政府文件公告均需使用阿姆哈拉語,海關文件要將外語翻譯為阿姆哈拉語,外國人如果想加入埃塞俄比亞國籍也需要能夠流利使用阿姆哈拉語[4]。1972 年以規范和推廣阿姆哈拉語為宗旨的埃塞俄比亞阿姆哈拉語學會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阿姆哈拉語作為國家官方語言的地位。在大眾傳媒領域,除了一家提格雷語的報紙外,阿姆哈拉語壟斷了其他全部的報紙。總的來說,在海爾塞拉西帝制時期,阿姆哈拉語的傳播和使用受到帝制政權的保護和扶植,封建王權推行單一語言和語言同質化對當時鞏固中央集權,加強國家認同,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在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中對一種語言的強制推廣無疑不利于其他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平等發展。
1.3 軍政府時代(1975—1991)
1974 年埃塞俄比亞推翻了封建帝制,成立了臨時軍政府管轄下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由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受東歐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政策影響,該黨在其推行的國家民主革命計劃中明確提出各民族在包括語言文化在內的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80 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亞建立了民族學院,研究民族構成和各民族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1985 年建立了語言研究院專門進行與民族語言相關的研究。客觀地說,與帝制時期阿姆哈拉語“一語天下”的局面相比,軍政府時期呈現出民族語言得到普遍承認,多語并行的態勢。1974—1975 年的掃盲運動就是政府推動民族語言使用的一個嘗試,政府在全國范圍內,以地區的主要民族語言為核心,開展了包括阿姆哈拉語、奧羅莫語、索馬里語、提格雷語、錫達莫語、阿法爾語等在內的15 種民族語言的掃盲培訓,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的母語。掃盲運動第一次在埃塞俄比亞實現了政府主導的多民族語言教學實踐,對喚醒民族意識,推動多語制的發展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由于當時掃盲運動的目標人群被定義為成人,忽視了學校在語言傳播中的重要性,當時所有小學仍將阿姆哈拉語作為唯一語種進行教授。教授民族語言的師資在事實上極大的不足,派去教授民族語言的教師自身對教阿姆哈拉語更有信心,加之當時政府高官大多數為阿姆哈拉人,對阿姆哈拉語使用的熟練度也是走上政府高位,獲得個人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從語言本身來看,大多數民族語言還沒有規范的書面語形式,與阿姆哈拉語言的發展存在很大的差距。諸多因素促使在語言普及中更多的當地人選擇使用阿姆哈拉語,因此掃盲運動、語言普及運動最終的結果反而是在農村地區進一步普及了阿姆哈拉語[5]。
1.4 聯邦制時代(1992—今)
多民族語言權力在埃革陣聯邦政府執政后頒布的1994 年《憲法》(也是埃塞俄比亞現行憲法)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憲法第一章第五條規定埃塞俄比亞的所有語言地位平等,阿姆哈拉語為聯邦政府的工作語言,聯邦的每個成員可以根據法律決定各自地區的工作語言[6],以此賦予各民族區域地方政府制定各自語言政策的權力。《埃塞國家教育和培訓政策》也規定出于兒童接受力和尊重少數民族發展自身語言權利的考慮,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語言由各州自行決定,或使用該州的民族語言,或使用可提供更大交流機會的其他語言作為教學媒介[7]。綜上所述,聯邦政府時期的語言政策以國家憲法的形式規定了不同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平等權利,體現了對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尊重。
2 埃塞俄比亞多元復雜的語言現實
埃塞俄比亞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多民族、多語言國家,境內80 多個民族中無一個民族人口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70 多個民族人口總和不到全國人口的1/4,其境內有80 多種語言,分布在9 個民族自治州和2個特別市。埃塞俄比亞多元復雜的語言現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民族語言數量繁多,譜系復雜,各民族語言發展不均衡
據第3 次國家人口和住房普查(2007)數據①,在埃塞俄比亞已識別的80 多個民族中,人口總數超過100 萬的民族僅有10 個,如表1 所示。

表1 2007 年埃塞俄比亞人口總數超過100 萬的民族
據Ethnologue(民族語言網)的統計,埃塞俄比亞有88 種語言,大多數語言屬于亞非語系,以閃米特、庫希特和奧莫語族為主,其中閃米特語族使用者最多,約占50%,庫希特語族使用者占到43.5%,奧莫語族使用者占到5.3%;另外還有少部分屬于尼羅-撒哈拉語系,其使用者主要聚居于西南邊疆,埃塞俄比亞和蘇丹邊境地區。不同民族語言的發展程度差異較大,有些語言既具備發達文字體系,如在非洲之角廣泛使用的阿姆哈拉語,也包括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瀕危語言的昂格塔語(Ongota)、格法特語(Gafat)等。
2.2 采用母語+阿姆哈拉語+英語的多語教育模式
鑒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53 年提出的“在教育中使用本地語言”的號召,阿姆哈拉語在國家歷史上長期的主導地位及其在國內不同民族間交流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英語作為一種國際交流通用語等多方面的考慮,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在國內推行母語+阿姆哈拉語+英語的多語教育模式,即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教學語言為民族語言,中高等教育階段教學語言為英語,作為聯邦政府工作語言的阿姆哈拉語和國家通用語的英語也是各州基礎教育階段的語言必修課程,英語是高等教育入學考試全國統考的考試科目。這樣一種制度安排體現了政府在推進母語教育,鼓勵民族語言與文化發展,構建國家認同意識以及促進對內、對外交流的多元考慮。
2.3 教育語言多元化,各聯邦州在教育語言的選擇和使用上具有較強的差異性
埃塞俄比亞是民族區域自治基礎上聯邦制國家,由9 個聯邦州和2 個特別市組成。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語言由各州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自行確定。因民族構成和分布情況差異性較大,各州確定的教育語言及數目均有不同,體現出較強的異質性。如在包括45 個民族的南方州,基礎階段的教學語言包括錫達莫語、沃拉伊塔語、哈迪亞語、古拉格語、蓋莫語、卡法語和阿姆哈拉語等在內的多種不同的民族語言,而在奧羅莫州,奧羅莫語為州政府確立的基礎階段唯一的教育語言。目前有22 種民族語言在不同地區作為學校的教學語言在使用。
2.4 外語教育多樣化
從外語角度來看,埃塞俄比亞雖無被殖民歷史,但由于英語作為現代國際語言的地位,在埃塞俄比亞使用最廣泛的外語就是英語。盡管與其他非洲英語國家如烏干達、肯尼亞等這些具有歐洲,特別是英語國家殖民歷史背景的國家相比,在埃塞俄比亞大多數人的英語能力仍相對有限[9]。然而,英語作為國家通用語的地位早在20 世紀50 年代就已經確立。除了英語以外,法語和阿拉伯語都在埃塞俄比亞有較長的教育歷史,創建于1908 年的埃塞俄比亞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孟尼利克二世學校就是一所法語學校。而埃塞俄比亞的地緣位置和伊斯蘭教在該國的宗教和文化影響都促成了阿拉伯語在埃塞俄比亞,特別是埃塞俄比亞穆斯林中的廣泛使用[10]。近年來,隨著中非關系的快速發展,埃塞俄比亞一些大學在中國孔子學院總部的支持下設立了孔子學院、孔子課堂和漢語教學點,開設了中文本科專業,每年畢業人數為100 人左右。
3 埃塞俄比亞語言政策的現實挑戰
盡管有埃塞俄比亞聯邦憲法賦予了各民族語言平等的國家語言政策,但在語言政策的實施中則體現了聯邦制下各民族州較強的自治性,各民族州情況各有不同,語言政策在實施中面臨著諸多挑戰,從多語教育的實施中可窺一二。
從本土語言角度來說,阿姆哈拉語作為聯邦政府的工作語言,是國家多語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各州基礎教育階段的一門語言必修課,但各州開課時間和時長不同,如在提格雷州阿姆哈拉語面向三年級到八年級的學生開設,在奧羅莫州和索馬里州則是面向五年級到八年級學生,在阿姆哈拉州不僅是教學語言,而且也是從一年級到八年級學生的語言必修課。對于母語為非阿姆哈拉語的學生來說,僅僅在規定的年級把阿姆哈拉語當作是一門課程來學習,對滿足使用該語言進行口頭和書面自由交流的目標仍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在充斥了語言背景高度異質化個體的大學校園里無法用阿姆哈拉語進行交流的學生也并不鮮見,這也是各州阿姆哈拉語教育現實差異的一個集中體現,阿姆哈拉語能力的不足必然會影響學生未來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事務以及適應不同地區間流動等方面的機遇,因此本土學界也不乏認為現行語言政策過于政治化而缺乏對語言教學本身的認真考慮[11]。
在母語教育上,由于民族語言的經濟價值遠不及阿姆哈拉語和英語,不少民族語言,特別是人口較少的民族語言使用者無法正確認識到母語的價值,導致一些群體的母語教育缺乏受教育者的內在學習動機。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的掣肘,各州在民族語言教育實施的過程中師資、教材(課本、輔助性閱讀材料)、硬件設施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客觀條件局限。有些地區學生人數與課本數的比高達10~15 ∶1[12],加上少數民族語言報紙、民族語言編寫的兒童書這些可用于輔助閱讀的材料嚴重不足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都增加了政策實施的困難。
從外語教育上來看,在目前基礎階段教學語言民族化的情境下,各州對英語課程的開課時間和學時總數等方面還沒有統一的規定。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日常生活中英語的使用受到學習者的家庭教育水平、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的限制,特別是在鄉村地區,更是缺乏語言使用的條件,加上師資、硬件等資源的不平衡都導致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學者認為:“在埃塞俄比亞,英語事實上僅被受過良好教育的經濟政治精英所掌握”,也有研究發現,僅有5%~10%的埃塞俄比亞本土員工在涉外場合可以有限使用英語來理解和表達[13],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多數當地人的英語水平依然有限,在實際使用中英語作為通用語地位的要求和應起的作用仍遠未達到。近年來,興起的中文教育以啟蒙性質的培訓為主,本科層次的教學僅有3~4 所大學開設,每年培養的畢業生人數與較高的市場需求相比,顯得頗為不足。隨著中非合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將漢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如喀麥隆、南非、烏干達等國,但埃塞俄比亞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語言教育政策鼓勵中文教育的發展,漢語也還未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4 結 語
海爾塞拉西時代對阿姆哈拉語言的強制推行剝奪了其他民族的語言使用和發展的權利,成為了民族沖突的根源之一。軍政府時代雖然提倡并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民族語言平等的主張,但語言普及運動的失敗也進一步促進了阿姆哈拉語的發展,各民族語言地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埃革陣執政后,在憲法賦予不同民族語言平等的同時,鼓勵各民族自治州自行選擇自己的州政府工作語言和教學語言,試圖在保持國家政權一體化和尊重各民族語言文化的差異性間尋求平衡。但是,由于各民族地區經濟實力和資源配置能力的不平衡,在語言政策的落實中也表現出較大的不同,特別是在經濟薄弱的地方發展民族語言面臨著較大的制約。近年來出現的反阿姆哈拉語作為官方語言的思潮,一方面體現了地方民族文化意識的進一步覺醒和聲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埃塞俄比亞民族語言的發展現狀和人民的期待還存在較大差距,政府應在發展經濟,惠及民生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將國家發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不僅是在物質文化上,而且在保證精神生活和民族文化多樣性上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語言政策體現的是政府的語言計劃,埃塞俄比亞聯邦制政體決定了語言政策的規劃和落實由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地方政府在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擁有更大的權力,但在資源配置和統籌方面卻又更多地依賴于聯邦政府。在埃塞俄比亞這樣一個發展型國家中,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要充分重視其民族文化和語言多元復雜的構成,在語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科學協調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和資源,最大化發揮語言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服務交際方面的作用。
注釋:
①截至目前,埃塞俄比亞曾進行過3 次人口和住房普查,分別為1984 年、1994 年和2007 年,第4 次人口和住房普查原定于2017 年舉行,但因各種原因而推后,目前尚未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