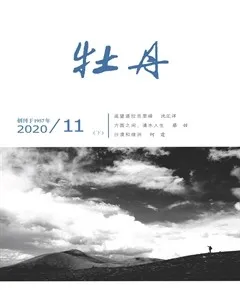夢中的杏子樹(外一篇)
離開家鄉(xiāng)已經(jīng)有近二十年了。老家院壩邊的杏子樹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我的夢中,那綿軟、香甜、質(zhì)樸、濃烈的家鄉(xiāng)味道總勾起我濃濃的鄉(xiāng)思鄉(xiāng)情。
杏子,性熱。杏子成熟后,顯現(xiàn)的是那種略微發(fā)暗的橙黃。用手輕輕捏一下,杏肉和杏核便分開了。把杏肉送入口中,我便嘗到一種甜甜酸酸的味道。
杏子在唐宋詞中經(jīng)常被提及。我至今依稀記得“春色滿園關(guān)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等耳熟能詳?shù)脑娋洹?/p>
我家的杏樹是爺爺生前栽的,那時候我有七八歲。爺爺把成熟的杏子剝了,取出杏核,用鏟子在院壩邊的空地上刨一個小坑,把杏核種進去,再用水瓢舀水澆灌。第二年春天,院壩邊便長出一棵小杏樹苗,樹苗長出淺黃色的圓形葉子,葉柄處還隱隱透出一兩點模模糊糊的高粱紅,很可愛。爺爺就找?guī)讐K磚頭,在杏樹苗四周筑起一圈小圍墻,隔三岔五澆一次水。不知不覺地,那棵小杏樹竟長起來了。
春天,樹枝上長出粉紅色的花苞,而后花兒開放,雪一樣的白。幾年過去,那棵小樹苗便長成了幾米高的大樹,枝繁葉茂。七月份,杏子便長得如一枚雞蛋大了。
那個年代,我們經(jīng)常和爺爺在杏樹下乘涼,聽爺爺給我們講那永遠也講不完的故事。我們都很愛爺爺。家里收入不高,母親往往把成熟的杏子背到集市去賣,用賣得的錢給我們?nèi)⒚觅I上一雙涼鞋或是一件襯衫。我們也跟著母親到集市上幫母親賣杏子。母親和兒時的我們叫賣聲悠揚悅耳,吸引了很多顧客。母親一邊數(shù)錢,一邊撫摩著我們的頭,欣慰地笑。家里因為有杏子,因而從未買過其他水果。在家的時候,吃到杏子,真是很好的美味!金黃的杏子上,薄薄的杏皮隱隱透著紅,吃到嘴里綿軟香甜,雖然比不上蘋果、香蕉等水果的滋味正宗,可其綿軟香甜中又透著一種濃濃的家鄉(xiāng)味道,那淳樸的味道洋溢著常人無法理解的美。
那時候,孩子們把吃完的杏核聚在一起,像打彈珠那樣,用手指彈杏核。若是自家的杏核能打到對方的杏核上,那么就算贏了,對方的那枚杏核自然歸自己所有了。那時候,孩子們很喜歡玩打杏核游戲,玩得不亦樂乎。
后來,爺爺去世了。爺爺?shù)碾x開使我們很傷心。沒有人呵護院壩邊的杏樹了!再后來,哥哥在一家公司上班,收入頗豐,決定把老屋拆了,重建樓房。由于地勢限制,修樓房需要把杏樹刨了。但是,包括哥哥在內(nèi),我們一家人都舍不得把它刨了。畢竟,這棵杏樹陪伴我們二十幾年啊!我們與杏子樹有著二十幾年的情感!不情愿地,杏樹還是被刨了。我思念杏樹,雖然思念無形,但它揪得人心疼!每次回老家,我都站在院壩邊,回憶那棵杏樹。在我面前,那棵杏樹仿佛就瑟瑟地站在風中。我想念故鄉(xiāng)的杏樹,想念爺爺。如今的孩子們怎么知道這里曾經(jīng)有一棵杏樹?怎么知道是誰種的,為誰開花結(jié)果呢?這棵杏樹有我的鄉(xiāng)愁,有我的思念。
如今,杏樹在農(nóng)村很少見了。有農(nóng)諺說,桃三杏四梨五年,棗樹當年就換錢。人們不想花上很長時間來等幾棵果樹開花結(jié)果。現(xiàn)在的人們大多數(shù)去城里打工,再也沒有栽種杏樹了。要栽的話,一般都栽那種經(jīng)濟價值高的作物,誰還會去種一棵杏樹呢?
感謝你,孤寂而多情的杏樹!你已傾心地贈給我紫色的詩意。時光倏然,杏韻猶存,我將用它去采擷、去捕捉默默守望香滿家鄉(xiāng)的人生奇觀!
家鄉(xiāng)的杏樹體現(xiàn)著一種精神,豁達坦蕩,低調(diào)平凡。它不嫌土地的貧瘠,只要有陽光、有水分就足矣。它從不索取,從不貪婪,紅粉的花,翠綠的葉,相互襯托,相互依偎。它沒有葉子的感嘆,沒有花的低吟,葉子和花共同用肩膀托起一片美麗,用心去經(jīng)營生命的光彩。家鄉(xiāng)的杏樹,它一往情深地默默矗立著,只求內(nèi)心的安寧和實在。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種光彩,一種氣度。
我怎能忘記家鄉(xiāng)的杏樹!
滑竿悠悠
滑竿是中國西南地區(qū)特有的一種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用兩根結(jié)實的長竹竿綁扎成擔架,中間架以竹子編成的躺椅或用繩索結(jié)成的坐兜,前垂腳踏板,這樣,一副滑竿便制成了。中國西南地區(qū)山地面積廣,滑竿較為盛行。特別是峨眉山上的竹椅滑竿已經(jīng)流傳幾千年。滑竿已不局限于交通工具,更是當?shù)孛耖g習俗的一種體現(xiàn)。
滑竿通常由兩人抬扛,在抬扛時,前后不斷地傳話,被稱為“報點子”,就是前面的人告訴后面的人前方路面的情況。一喊一答,加上四川特有的地方話,特別好聽!比如,前面路很平,前呼“大路一條線”,后應“跑得馬來射得箭”;前面的路彎拐多,前喊“彎彎拐拐龍燈路”,后應“細搖細擺走幾步”。見啥說啥,振奮精神,鼓舞干勁,其生動風趣,與船夫號子有異曲同工之妙。
過去,滑竿不僅是人們出行的交通工具,在抗戰(zhàn)期間還成了抗日戰(zhàn)場上的擔架。我們在抗日影視劇中看到的抬傷兵的擔架,其實就是一種簡易的滑竿,只是沒有椅子罷了。我也有坐滑竿的經(jīng)歷。那次是學校組織教職工到雅安碧峰峽旅游。在碧峰峽游玩時,游客會時常聽到“滑竿、滑竿”的招攬聲,那粗獷的音調(diào)和著清脆的流水聲長長地回蕩在青山綠水間。下坡路上,轎夫的腿輕捷得連他自己也不能夠止住,他們蹣跚地控制著狹小的山路。他們的血液驕傲地跳動著,好像他們停住了呼吸,只聽到草鞋接觸石階的聲音。一到爬坡的時候,轎夫的腳步便不響了。他們開始喘息,他們的肺葉開始擴張,那碎片做的衣裳在吱吱嘎嘎響的滑竿下面有秩序地向左或向右地擺動。汗珠在他們頭發(fā)上靜靜站著,他們走得就出奇的慢。坐在滑竿上,我隨著轎夫沉重的腳步起伏在一升一落之間。在那么多的石級上,若有一個石級不留心踏滑了,連人帶滑竿要一齊滾下山澗。滑竿悠悠,雖然有些怕,但坐在滑竿上觀賞沿途秀美的風光,別有一番感覺,滑竿隊伍在碧峰峽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轎夫為游客送去了便捷的服務,一步一個腳印經(jīng)營著自己的生活。
我的老家川北南充農(nóng)村過去也有抬滑竿的習俗。由于當時沒有修公路,交通不便,遇到有人生病,沒法坐車,更不用說坐救護車,只好坐滑竿。滑竿由當?shù)厣韽娏训拇迕駚硖В话惆才艓讉€人換著抬。山路陡峭崎嶇,抬滑竿的大漢往往是汗流浹背,肩膀紅腫。就是這顫悠悠的滑竿,幫著山里人走出山村,去山外治病。而如今,山里修了公路,交通方便,一遇到病人,都乘車到城里,再也不坐滑竿了。滑竿漸漸在農(nóng)村消失,成為歷史。人們懷念滑竿,喜愛滑竿文化,不僅僅在于當年滑竿對交通的貢獻,它更能讓人們深感巴蜀勞動人民的淳樸善良和聰明才智。
對于滑竿,我想,轎夫兩人的肩膀本來是扛不起的,但他們扛起來了;本來不應該扛在他們肩上的,但他們也扛起來了。我總以為,抬著滑竿的不是兩個人,而像輕飄飄的兩盞燈。那兩盞燈忽閃忽閃的,永遠在山澗亮著,照著通往山頂或山下的路,照亮著游人的心!
(南充市嘉陵區(qū)龍蟠初級中學)
作者簡介:賈海(1974-),男,四川南充人,本科,一級教師,研究方向: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著有個人散文集《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