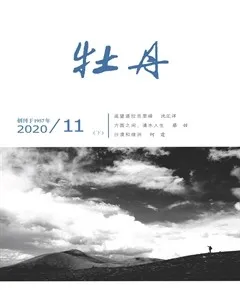從《高老莊》和《秦腔》看農裔知識分子精神返鄉困境
趙麗妍 程航
“返鄉”是現當代文學中不斷被書寫的主題,故鄉既可以指向給予作者豐富生命體驗的實體家鄉,又指向現代人在精神失落后追尋的靈魂棲息地。從《高老莊》和《秦腔》,賈平凹筆下的農裔知識分子經歷了從歸鄉到棄鄉的人生體驗,其間展現了城市文明對傳統文明的逐步侵蝕。傳統文明的場域變成荒野,進一步帶來知識分子精神救贖的幻滅,這一創作指向的轉變體現了作者對返鄉困境和文化流失的思考走向成熟。
“返鄉”是現當代小說中經久不衰的主題,知識分子將對道德、人性、美的期望寄托在故鄉的土地上。賈平凹剝離了知識分子返鄉時的英雄光環,展現了他們在文明的縫隙中精神失重的掙扎,表達了作者對城鄉文化沖突和現代文明的思考。《高老莊》和《秦腔》是作者“返鄉”主題的代表作品,從這兩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文化沖突和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思考走向成熟。通過返鄉者的視野,讀者看到的不是雞犬相聞的桃花源,而是鄉土文化逐漸流失、價值體系崩潰的“荒野”。子路最終訣別故鄉,而夏風以鄉土否定者身份登場,自始至終留給故鄉的就是一個決絕的遠離背影。知識分子不再以拯救者的姿態俯視鄉土世界的落后和愚昧,生活的激變和文化的錯位使他們遭遇著精神危機。
一、文明沖突下的掙扎與抉擇
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伴隨著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對峙和抗爭,兩種基于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形態的文明在搶奪各自的陣地。學者蘇沙麗指出,現代性是一種同化且普世的力量,是關于“進步”的歷史必然性。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現代文明以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擠壓著傳統文明的生存空間。城市無疑是現代文明的象征,鄉土世界經歷著文明沖突帶來的痛苦抉擇。返鄉的知識分子有著矛盾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他們出身農村,傳統的倫理秩序、價值取向和風俗習性被印刻在血液之中,成為他們精神向度和文化取向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們接受了現代教育,長期生活在城市,現代文明逐漸占據了思想上風,現代文明的視野給予了他們理性的批判視野。返鄉的知識分子本就是文明沖突的個體縮影,他們懷著對故鄉詩意想象,試圖通過返鄉來濯清心頭浮世灰塵,但是此鄉非彼鄉,文明沖突激烈的故土加重了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焦慮。
子路返鄉之后始終將自己置身于故鄉之外,從城市人的視角俯視故土和故鄉的變遷,不自覺地用現代文明的批判視野來看待高老莊發生的一切。但是,子路在潛意識中主動脫下大學教授光鮮的外衣,逐漸變得猥瑣、自私、冷漠、軟弱和邋遢,西夏恍惚之中看到子路變成豬。子路自詡為傳統血脈的拯救者,帶著換種的目的回到高老莊,試圖重現鄉村高大的風采,但是自己始終游離在鄉土生活之外,無法抵抗傳統文明強大的文化慣性,換種只是南柯一夢,知識分子自身精神萎靡困頓,也無法肩負拯救鄉土的重任。現代文明的外衣無法掩蓋子路的鄉土身份,子路同樣無法承受鄉土文明的重負。子路最后在父親的墳頭發出“我也許再也不回來了”的哭喊。知識分子在兩種文明的夾縫中尋覓不到靈魂的棲息地,只能通過拋棄故土的一切來逃避精神萎靡的現狀。
與子路的拯救論不同,夏風認為傳統文明是歷史的渣滓,被舍棄是既定的宿命。白雪和夏天智是秦腔的擁護者,白雪放棄省城優渥的生活環境,即使秦腔淪落到只能在農村紅白喜事上表演,她也沒有動搖過決心。夏天智癡迷于秦腔文化,死后枕著秦腔臉譜書下葬。夏風處處顯示出對秦腔的輕視,直言縣秦腔劇團是“草臺班子”,認為秦腔難登大雅之堂。文明沖突通過父子、夫妻沖突得以展現。最后,夏風與白雪金童玉女的婚姻失敗,夏風“錯過”夏天智的葬禮。最終,流行音樂取代了秦腔,而倫理秩序被功利化的價值觀取代,傳統文明被逐漸邊緣化。白雪被形容成閃爍著圣光的佛女,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寄托了拯救傳統文明的期望。婚姻的破滅意味著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有著無法彌合的鴻溝,強行結合只會生出“畸形兒”。夏風與白雪的關系隱喻了兩種文明沖突,可以明顯看出現代文明始終占據上風,帶著不可置疑的批判視角來審視著傳統文明的存在。夏風對秦腔的詆毀、嘲笑,正如現代文明大舉進入鄉土,逐漸侵占了傳統文明的生存場域。
父與子的斗爭與訣別可以從不同的文化角度來進行書寫,五四時期子對父叛離可以看出是文明的進步,而當代鄉土小說中父子的斗爭不再帶有文化進步的激進和喜悅,更多的是深沉的悲切和無奈。子路和夏風最終都以絕鄉的姿態來割裂自己與傳統文明的聯系,而形式上則表現為“絕父”。子路主動在父親墳頭表示要永訣此鄉,而夏風則是“被拒絕”參加父親的葬禮,從此再未回過故鄉。父親是歷史與舊文化的代名詞,在宗法制父權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鄉土世界,父親更是不可撼動的權威存在。子對父的訣別隱喻著隔斷與故鄉的血脈,從此走上“無父無鄉”的道路,漂泊的靈魂只會游蕩在城市的上空,故鄉從此成為記憶中的永無鄉。夏風和子路雖然帶著不同的文化觀看待傳統文明,但結局殊途同一。所不同的是子路主動訣別,而夏風是“被缺席”。雖然在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這場較量中前者始終處于下風,但子輩對后者的抉擇同樣帶著巨大的文化傷痛。
二、鄉土倫理秩序的崩潰
知識分子家園想象中的故鄉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即使是冷峻犀利的魯迅在返鄉之前也對故鄉抱有希望。學者李華指出,“故鄉想象背負著作家文化思考、文化想象與文化承諾的重建的理想,及其背后的文化家園的毀塌與重建”,文化家園的毀塌源于鄉土文化的流失。鄉土文化的基礎是家族宗法文化,成為維系鄉土世界穩定的文化和道德準則。傳統文明倫理秩序幾千年來維系著鄉土世界的靜謐祥和,仁義孝悌的價值取向成為人們向往田園生活的重要原因,這一切在現代文明的進攻下成為歷史的灰塵。
如果說土地孕育出鄉土文化,那么農業運作方式則是鄉土文化存在的經濟根基,卻逐漸成為落后、貧窮的象征,鄉土世界被迫納入現代化的進程。人們拔出土地里生長了幾千年祖祖輩輩的根,試圖為它找到另一種生長方式。鄉土倫理秩序走向崩潰的第一步就是“地之子”們對土地的遺棄,農業經濟的衰微是鄉土文化沒落的信號。《高老莊》中的村民靠地板廠生活,高老莊的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秦腔》中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經濟之間矛盾通過夏天義的抗爭有深刻的體現。清風街年輕一代越來越多走向外面世界,即使從事的是為人不齒的職業,甚至時刻面臨生命危險,土地荒蕪、人丁流失,人主動解除了與土地的聯系,融入現代化進程中,將故鄉遠遠拋在身后。夏天義始終堅守著對土地的保護和尊重,不理解子孫們為什么要拋棄土地:“不明白這些孩子們,為什么不踏踏實實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虧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卻留不住他們。”夏天義的淤地壯舉猶如愚公移山般的悲壯,最終在淤地時被泥石流埋葬,完成“生于斯、長于斯、葬于斯”的宿命。
土地逐漸消失在經濟和文化的視野之外,水泥地與高樓大廈取代了土地的位置,土地承載的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尊老孝悌的倫理秩序逐漸隱入歷史深處。美國學者艾愷指出,“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上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東西作為代價”。現代化浪潮憑借自由貿易的經濟方式涌入鄉土世界,給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帶來了致富的門路,卻以鄉土價值觀和倫理秩序的喪失為代價。悲劇不以外界因素的介入而改變,正如西夏的努力沒有阻止高老莊村民對蘇紅的侵害,夏天義的死也未能喚醒子孫們的孝義。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底線,功利論慢慢取代了詩意的視角。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就與取舍被精細地量化,量化的標準就是金錢。高老莊的村民為了搶木材偷偷襲擊白云寨的村民,這與子路印象中樂善好施的淳樸作風大相徑庭。秦腔中雞鳴狗盜、男盜女娼的墮落作風大行其道。《高老莊》中展現了在外來文明的刺激下村民們心中滋長的貪婪和私欲,在《秦腔》中,鄉土價值體系已經被以功利主義和叢林法則為核心的現代價值體系取代。
鄉土現代化的過程勢必包括了鄉土倫理道德與發家致富的物質欲望之間的交鋒,人的尊嚴和精神被一步步摧毀。高老莊人在集體狂熱之下完全拋棄為人本性的善良。故鄉只能是記憶中的詩意家園,一旦踏上故土,美好的想象化為對現實的憎恨、對自我的厭惡,知識分子返鄉之后見到的是這樣道德失序、價值混亂的“荒野”。對于子路,這樣的故土無法承放游子漂泊的靈魂。鄉土倫理秩序的崩潰下高老莊人徹底失去了自詡高貴的血脈,矮個短腿的生理特征折射出鄉村精神家園的失落。子路雄心勃勃的換種計劃成為一個笑話,這樣的高老莊人值得拯救嗎?能夠被拯救嗎?子路自身性能力退化、與西夏的分歧、與故鄉的訣別也顯示出知識分子和故鄉一樣處于現代文明的圍攻之下,遭遇了家園失落的精神危機。
清風街或許沒有發生過這樣人寰盡失的慘劇,但實用主義的思維蠶食著每個人對道德的堅守。對于夏風,這樣清風街無法喚醒他對故鄉的愛與尊重。雖然夏風一心向往城市,但故土的意義不會因為游子的愛憎取舍而發生改變,清風街無疑也是他安頓心靈的家園。夏風發現家鄉竟存在賣淫而感到詫異和羞慚,目睹堂兄弟們的墮落行徑而心痛。夏風在往返城鄉之間發現故鄉與城市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對于這種改變,夏風同樣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他與白雪婚姻的失敗以及畸形孩子的出生也意味著游子失去了重新回到故鄉的可能。
三、返鄉知識分子不可承受之重
賈平凹選擇農裔知識分子來承擔自己對社會變遷、鄉土文明走向和精神家園構建的思考,一方面是因為他本人就是農裔知識分子,從作品人物的迷茫焦慮和思考尋覓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一方面是因為農裔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時期有著特殊的文化思考意義。學者肖云儒指出:“你能分明感到作家的情感傾向由原先的戒備城市轉而為一定程度上的接納城市,由原先的依戀鄉村轉而為一定程度的排拒鄉村。”
農裔知識分子對于鄉土文明有著深厚的感情與依賴,其身上的農民根性和鄉土氣息使他們有著強大的精神韌性,憑借著鄉土賦予的踏實能干、堅韌謙遜的品質進入城市,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植根在血脈中的鄉土氣阻礙他們進一步融入社會。子路和夏風往返與城鄉之間,終究不能完全融入城市這一文化場域之中。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是歷史、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最終歸宿。城市憑借著優越的生活條件、深厚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就業市場吸引了鄉村人涌入城市。知識分子被城市文明所吸引,并接受了現代文明教育,認同并將其作為自己的思想導向,但是城市中精神失落和道德淪落也使他們開始質疑現代文明的合理性。子路回到遠離城市的家鄉,但故鄉的面目全非比城市的冷酷排斥更加難以接受,子路最終訣別家鄉,引生也一直盼著夏風的歸來。農裔知識分子往返與城鄉之間,城市和鄉土的現狀對他們產生精神沖擊,在精神家園構建和失敗之中,農裔知識分子感受到了人文精神的孱弱,深陷入精神矛盾之中,精神返鄉面臨失敗。
知識分子對故鄉和土地有著深刻的迷戀,并通過書寫來不斷強化這種迷戀。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土地承載著他們對更高層次精神追求的希望。對土地的理想化、精神化和形而上的詮釋使故鄉成為他們的精神歸屬,故鄉從一個生存空間轉變成一個“理想化概念”。無論是子路還是夏風,對于故鄉都有著理想化的傾向,子路懷著對故鄉的憧憬踏上歸鄉之路,即使夏風全盤接受城市生活觀念,也對清風街上存在賣淫行為,以及夏天義子孫們背離倫理的行為表示無奈和氣憤。而“土地對于農民,更是物質性的,其關系也更功利性。他們因而或許不像知識分子想象的那樣不能離土;他們的不能離土、不可移栽,也絕非那么詩意,其中或更有人的宿命的不自由,生存條件之于人的桎梏”,農民依賴土地僅僅是為了生存,當他們的物質欲望遠遠超過土地所能滿足的限度時,“離土”就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農民果斷地拋棄往昔的生活方式,拋棄依附在這種生活方式上的道德觀念和倫理秩序。知識分子將其視為背棄和墮落,而農民將其視為“識時務者為俊杰”。知識分子離開故土那一刻就注定了他們是故鄉命運的旁觀者,對于故鄉的面目全非,他們可以感到哀傷、憤怒和無奈,卻無法譴責那些留下的人的選擇。
四、對精神返鄉困境的反思
從子路到夏風,知識分子的返鄉之旅越來越艱難,作者對文化的反思也走向成熟。如果說子路對故鄉的感情是懦弱的熱愛,夏風則是善意的冷漠。子路對高老莊不聞不問的表面暗藏著對自我懦弱的譴責、對故鄉往昔的追憶,在父親墳頭的哭喊也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反觀夏風對于清風街上的人友善親切,雖然稍有怨言,但是盡量利用自己的人脈和身份地位解決父老鄉親遇到的問題。衣錦還鄉的知識分子回報鄉親的背后是文化的疏離和淡漠。夏風對于鄉民們道德意識的淪喪和尊嚴的遺失停留在吃驚、氣憤和無奈的情緒階段,沒有子路那種詩意的想象與殘酷現實的撕扯帶來的精神上的痛苦。夏風已經割裂與清風街的血脈聯系,之所以回到故鄉僅僅是因為父母尚在。夏風對于鄉民們的耐心與禮貌是出于現代文明中的責任與義務,是一種社會契約精神的體現,并不是鄉土文化中的鄉情規約。子路正在經受文化交鋒帶來的心靈陣痛,夏風已然實現了文化置換。子路的離鄉讓人們看到了知識分子面臨精神危機時的孱弱和可笑,但是對他的痛苦也心生一絲憐憫,大家何嘗不是另一個子路呢?夏風的離鄉如此決絕果斷,不給讀者留有一絲的幻想,讓人們心生涼意。
“返鄉”包含著返回、尋覓和建構多種層面的嘗試,但是故鄉已經變得面部全非,尋覓失去了方向,建構沒有了文化根基,“返鄉”無疑成為知識分子不可觸碰的傷痕。在《高老莊》中,作者將希望寄托在西夏和蔡老黑身上,希望包容開放的現代文明和勇猛剛毅的游俠精神的結合能形成強有力的文明,那么子路或許會重新返鄉。但是,作者在《秦腔》中親手粉碎了這種希望,給綿延了幾千年的鄉土世界立了一面無字碑,將其中的是非取舍留給后人評價。夏風會成為清風街世代相傳的驕傲,承載著故鄉的榮耀和光輝,但不會是故鄉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對于“返鄉”的失敗,夏風雖然表現得冷漠,但是并不意味著夏風經歷的精神掙扎會比子路輕。在《秦腔》中,作者通過冰山一角的手法展現了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尷尬的地位,服務員不認識大作家夏風,卻請局長簽字。中國鄉土知識分子從鄉村故土的無奈逃亡,也預示著他們對能夠實現其人生理想、人生價值和展示其精英角色的舞臺空間的再次苦苦追尋。子路離鄉后試圖在大學教授的社會身份上找回心靈的位置,即使這位置只是虛偽的謊言。夏風同樣認為城市才是放置靈魂的棲息地。但是,城市能夠滿足他們嗎?在城市中,農裔知識分子只會經歷更多、更復雜的精神震蕩。
人是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的小縮影,文化多樣化使作家們自覺對人的精神歸向進行形而上的思索,同時伴隨著文化反思和精神批判。賈平凹筆下的農裔知識分子們在物欲與道德的撕扯中掙扎、在反思和批判中尋找心靈的平衡點,他們試圖在紛繁復雜的生活形態中找尋精神返鄉的路標,但是文化的對立和流失使他們迷茫、焦慮直至放棄。每一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過去和未來的爭論中砥礪前進,堅持著對理想的追尋。在文化的遺失和重建中重尋返鄉之路是知識分子的時代和歷史宿命。
(長春理工大學)
作者簡介:趙麗妍(1981-),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