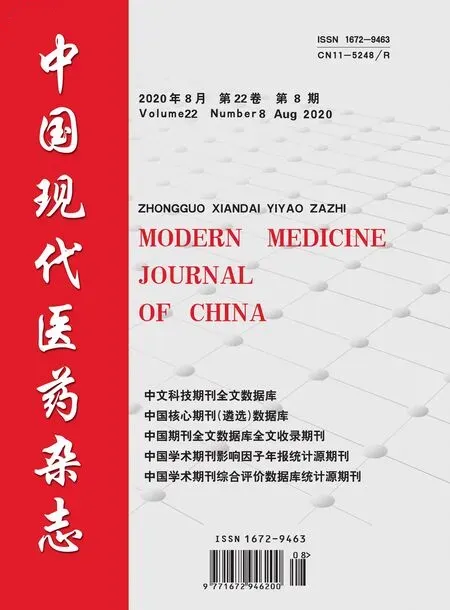外泌體在幽門螺桿菌中的研究進展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是常見的致病菌之一,感染率極高。Hp感染不僅可以導致多種胃腸道疾病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胃癌等,還與許多胃腸道外疾病(如血液病、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相關[1]。外泌體作為新型的細胞間信息傳遞媒介,可攜帶生物信號分子調控多種細胞生理活動,從而影響Hp 相關疾病的發生與轉歸。本研究總結外泌體在Hp感染致病方面的最新進展,從而為了解Hp 致病機制以及尋找潛在的Hp 相關疾病生物標記物提供新思路。
1 外泌體概述
1.1 外泌體性質與功能外泌體是由機體多種細胞釋放的一種納米級膜性小囊泡,直徑30~100nm。幾乎所有細胞都能分泌外泌體,其存在于各種生物體液中,包括唾液、血漿、尿液、腦脊髓液、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和關節液等[2]。外泌體主要是由內吞體在高爾基體的作用下向內凹陷形成包裹mRNA、miRNA、蛋白質、脂質等生物活性分子的多泡體(multivesicular body, MVB),MVB 再與細胞膜融合后釋放到胞外基質中[3]。當外泌體被受體細胞攝取后,其可通過其攜帶的蛋白質、核酸、脂類等調節受體細胞的生物學活性,從而參與到機體抗原提呈、免疫應答、細胞分化、細胞遷移、腫瘤侵襲等方面[4]。
1.2 外泌體的組成外泌體的組成較為復雜,主要分為蛋白質、核酸及脂類。外泌體中的蛋白質一類是非特異性蛋白質,大部分是來源于親代細胞中參與MVB 形成的細胞質和膜蛋白,如細胞骨架蛋白、核糖體蛋白、跨膜蛋白、膜聯蛋白、熱休克蛋白及黏附蛋白等,這類蛋白主要用于鑒定外泌體,與細胞來源無關;另一類則是不同來源外泌體的特異性蛋白質,這類蛋白質與細胞信號轉導功能相關,在抗原提呈、免疫、腫瘤等生理病理過程中發揮作用[5]。外泌體核酸部分主要包括mRNA、miRNA、rRNA、lncRNA 等[5]。這些轉錄相關物質被包裹在外泌體中被受體細胞攝取,從而引起細胞功能改變。外泌體富含脂質,尤其是膽固醇、鞘磷脂、己基神經酰胺和前列腺素等[6]。
1.3 外泌體與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關系外泌體能夠調節宿主與病原體的相互作用,參與傳染性疾病、炎癥性疾病和腫瘤等多種疾病的病理過程。在病原微生物感染時,外泌體中的活性成分發生改變: 一是外泌體中的宿主蛋白質、核酸等由于病原體感染而發生改變,二是外泌體可攜帶病原體特異性生物分子。外泌體在病原體感染中也發揮著雙重調節作用:一方面,外泌體可攜帶病原體相關抗原向免疫系統呈遞信息,從而激活宿主防御反應;另一方面,外泌體有利于病原體生存和發揮其致病作用,從而導致感染擴散。如鳥分枝桿菌感染誘導的巨噬細胞外泌體可以促進巨噬細胞表達HLA-DR、CD40、CD80、CD81、CD86、CD195 以及分泌IL-6、IL-8、IL-10、INF-γ、TNF-α,表明外泌體中的抗原成分可以激活巨噬細胞產生免疫反應[7]。此外,HIV 病毒能夠利用外泌體傳遞自身蛋白Nef,Nef 蛋白可誘導CD4+T細胞凋亡,從而實現病毒免疫逃逸[8]。
2 外泌體在幽門螺桿菌感染中的作用
Hp感染誘導產生的外泌體可出現其所包裹的生物活性分子如miRNA、蛋白質的改變,在胃部及胃外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1 幽門螺桿菌感染相關外泌體miRNA外泌體傳遞的miRNA 與內源性miRNA 作用相似,但來源不同,前者可來源于其他細胞或器官。miR-155 在Hp 誘發的胃炎中表達上調,在體內或體外Hp感染的巨噬細胞中高表達[9]。Wang 等[10]研究發現,來源于 Hp感染的巨噬細胞的外泌體中miR-155 同樣顯著上調,攜帶miR-155 的外泌體被巨噬細胞攝取內化后可調節巨噬細胞中多種促炎介質和炎癥相關蛋白的表達,TNF-α、IL-6、IL-23、CD40、CD63、CD81 和MHC-I表達上調,而MyD88、NF-кB下調,這提示外泌體miR-155可充當新型負調節劑微調Hp感染的炎癥反應并通過MyD88,NF-κB 炎癥反應途徑調節Hp感染巨噬細胞的免疫反應。Li等[11]研究發現,Hp感染的胃黏膜細胞GES-1 源性外泌體及患者血漿外泌體中miR-25升高,miR-25 通過靶向Kruppel 樣轉錄因子2(KLF2)調節NF-κB 信號通路,導致IL-6、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血管細胞粘附分子1(VCAM-1)、細胞間粘附分子1(ICAM-1)表達增加,從而促進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另有研究表明外周血單核細胞源miR-25-5p 的表達與冠心病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12],表明Hp感染可通過外泌體miR-25 影響動脈粥樣硬化,而miR-25/KLF2 軸是Hp 相關冠心病的潛在靶標。綜上表明,Hp 誘導產生的外泌體中miRNAs可介導免疫調節、動脈粥樣硬化等重要生理病理過程,從而調節胃腸道疾病及胃外疾病的發生、發展。
2.2 幽門螺桿菌感染相關外泌體蛋白在Hp感染后,外泌體內宿主蛋白可發生改變。外泌體可以介導Hp感染相關的胃癌細胞與巨噬細胞之間的細胞表面受體酪氨酸激酶間充質-上皮轉換因子(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 MET)轉移。MET 在實體惡性腫瘤的發展、侵襲和血管生成中起關鍵作用。Hp感染誘導胃癌細胞的外泌體中活化MET 上調,此富含活化MET的外泌體可以被巨噬細胞內化,促使巨噬細胞極化為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TAM 進一步發揮促腫瘤作用[13]。Chen 等[14]研究發現,Hp陽性慢性胃炎患者血清外泌體通過可溶性IL-6 受體(soluble IL-6 receptor, sIL-6R)介導的IL-6 反式信號調節IL-1α表達。IL-1α 在許多人類疾病如慢性Hp感染的發病過程中顯示出促炎作用。
此外,Hp 特異性蛋白可分泌到誘生的宿主細胞外泌體中。研究表明,Hp陽性患者胃液中的細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含有Hp 毒力因子細胞毒素相關蛋白(cytotoxin associated protein A, CagA)和空泡細胞毒素(vacuolated cytotoxin A,VacA),能夠誘發胃炎及胃癌[15]。Shimoda 等[16]研究發現,在CagA 陽性Hp菌株感染的胃癌患者血清外泌體中可檢測出CagA,且外泌體經AGS 細胞內吞后,CagA 經酪氨酸磷酸化后可刺激AGS 細胞形態學發生“蜂鳥”表型變化,表明外泌體可以攜帶CagA 進入循環,并將CagA 遞送到遠處的器官和組織。血清流行病學研究表明,CagA 陽性Hp菌株感染與冠心病、缺血性中風以及先兆子癇有關[17~19],這提示CagA可能導致胃外疾病的發展。最新研究表明,Hp感染的胃上皮細胞源性外泌體中CagA 通過下調轉錄因子PPARγ 和LXRα表達來抑制膽固醇轉運蛋白轉錄,從而誘導巨噬細胞源性泡沫細胞形成并促進動脈粥樣硬化[20]。這些研究結果提供了一種新的機制來解釋Hp感染引起的胃外效應,即外泌體可攜帶Hp 毒力因子進入循環,參與Hp 相關胃外疾病的發生、發展。
2.3 外泌體與細菌胞外囊泡Hp 不僅可以誘導宿主細胞產生外泌體,其自身也可分泌細菌胞外囊泡(outer membrane vesicles, OMVs)。OMVs可將細菌自身生物活性分子(如毒力因子、毒素和黏附分子等)轉移到宿主細胞中,從而增強宿主體內的細菌存活率和致病性[21]。研究發現,Hp TK1402菌株分泌的OMVs 參與形成細菌生物膜,有利于菌體定植與致病[22]。Zhang 等[23]研究發現,與Hp 同屬螺桿菌屬的豬螺桿菌(Helicobacter suis, H.suis)可釋放含有γ-谷氨酰轉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的OMVs,其與人類癌細胞分泌的含有GGT的外泌體結構十分相似,因此推斷癌細胞釋放的富含GGT的外泌體能夠在宿主周圍組織中產生與細菌GGT 相似的效果,可能與癌癥轉移機制有關。
3 外泌體是幽門螺桿菌感染相關疾病潛在的生物標志物
外泌體攜帶的生物活性分子具有其源性細胞的特征,因此很適合作為診斷標志物。Kyosuke等[24]發現Hp 根除治療后的胃癌患者血清外泌體中miR-335 的表達顯著低于對照組,這表明外泌體miR-335可能是Hp 根除治療后胃癌發展的有效生物標志物。另有研究表明,胃癌患者血清外泌體miR-301 的表達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明顯升高,其表達升高程度與腫瘤大小、胃癌分期和Hp感染密切相關,因此外周血外泌體miR-301 的檢測有望成為診斷胃癌及評價預后的重要指標[25]。Yamamoto等[26]研究表明,使用胃液外泌體DNA對BARHL2進行甲基化分析可用于臨床中胃癌的早期檢測,其不受胃黏膜萎縮或伴隨胃癌發生的Hp感染的影響。目前,外泌體在Hp感染相關疾病診斷中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并沒有作為生物標志物用于快速診斷中,因此仍需深入研究。
4 展望
目前,外泌體在Hp感染相關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外泌體在Hp感染中的雙重作用有待進一步研究,Hp 自身分泌的OMVs 與宿主細胞外泌體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也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外泌體內富集的信息分子成分也有待進一步闡明。總之,Hp感染相關外泌體的研究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相信隨著研究深入,能更好地闡明Hp 的致病機制并在相關疾病診斷、防治上發揮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