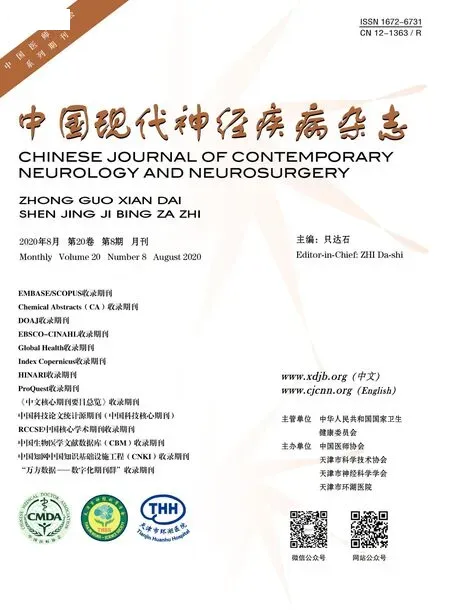創傷性腦損傷誘發的凝血功能障礙研究進展
徐新尚 峰曲鑫 王寧
創傷性腦損傷(TBI)具有高發生率、高病殘率和高病死率的特點,我國人口基數大,創傷性腦損傷病例高于其他國家[1]。由于創傷性腦損傷的原發性腦損傷發生于瞬間,通常無法對其實施有效干預,加強針對其繼發性腦損傷發病機制和干預措施的研究,是降低創傷性腦損傷病殘率或病死率的關鍵[2]。創傷性腦損傷后繼發性腦損傷機制主要包括神經炎癥反應、凝血功能障礙、氧化應激反應,以及線粒體功能障礙等[2],其中創傷性腦損傷誘發的凝血功能障礙(TBI-IC)即創傷性腦損傷凝血病是誘發繼發性腦損傷的重要機制之一,以血液高凝狀態并迅速進展為消耗性低凝狀態為特征,二者相互作用,使患者預后不良[3-4]。據研究顯示,創傷性腦損傷后伴發凝血功能障礙患者的死亡風險是不伴凝血功能障礙患者的10倍,其預后不良風險甚至可高達30倍[5]。因此,早期發現、及時糾正凝血功能障礙對降低創傷性腦損傷患者病死率、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目前對其病理生理學機制尚不十分清楚,導致診斷與治療過程充滿困惑[6]。
而對顱外創傷如四肢骨折、實質臟器損傷等繼發的凝血功能障礙即創傷性凝血病(TIC)的發生機制業已闡明,包括廣泛性組織損傷、失血性休克和組織低灌注引起的代謝性酸中毒、大量補液引起的血液稀釋和低體溫等[7-8],此為一種“丟失性”、稀釋性凝血功能障礙。然而,臨床上單純創傷性腦損傷患者鮮見大量失血,針對顱內高壓需限制液體攝入量,且患者更多表現為高熱而非低體溫,提示TBI-IC的發生機制有別于創傷性凝血病。凝血功能障礙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可于創傷后數分鐘即升高,而凝血酶原時間(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延長則出現的較晚,表明由高凝狀態逐漸轉至低凝狀態,呈現消耗性凝血功能障礙[9]。近年細胞微囊泡(MVs)領域的新發現,或可以解釋局限性創傷性腦損傷所致系統性凝血功能障礙的原因[3];同時,組織因子(TF)釋放、內皮細胞損傷、血小板功能障礙、纖溶活性異常和蛋白C(PC)系統激活等相關病理生理學機制也已取得共識。筆者以TBI-IC病理生理學機制為重點,綜述該領域最新研究進展,擬為臨床診斷與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一、流行病學特點、臨床特點及診斷
1.流行病學特點由于目前尚無統一診斷標準,TBI-IC發生率在不同國家、不同研究團隊的報道中差異較大,為10%~97%[6]。TBI-IC與創傷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常用評價指標包括Glasgow昏迷量表(GCS)評分(≤8分)、創傷嚴重程度評分(ISS,≥16分)、休克指數(SI≥1)等[10];逾2/3的重型顱腦創傷患者傷后可誘發凝血功能障礙,且傷情越嚴重、凝血功能障礙發生越早,重癥患者在入院前多已存在凝血功能障礙[11]。與鈍性傷和沖擊傷相比,穿通傷后凝血功能障礙發生率更高[12];腦挫裂傷常伴有廣泛性微血管和血腦屏障破壞,特別是老年患者更易發生凝血功能障礙[13]。此外,合并貧血、高血糖、低收縮壓,以及影像學提示腦水腫、中線移位、蛛網膜下腔出血等均為重要危險因素[6]。值得注意的是,既往創傷性腦損傷常見于45歲以下青壯年,其中交通事故傷為主要致傷原因;隨著老齡化因素的上升,近年來約有50%以上的患者為5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且以摔傷為主[14]。摔傷主要導致腦挫裂傷,加之大多數老年人均有服用抗凝藥或抗血小板藥病史,故老年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凝血功能障礙發生率更高,且大多預后不良[15-16]。Probst等[17]基于9070例鈍性創傷性腦損傷患者的研究顯示,華法林或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服藥史是創傷后進展性出血性損傷(PHI)等繼發性腦損傷的重要危險因素。近年服用靶向口服抗凝藥(TSOAs)的人群比例逐漸增加[18],由于各項研究所納入的創傷性腦損傷類型或嚴重程度等有所不同,造成評價TSOAs對創傷性腦損傷后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發生率和病死率影響的結論不盡一致[18-20]。
2.臨床特點TBI-IC患者的凝血系統和纖溶系統改變可持續至創傷后3天甚至更長時間[21]。高凝狀態可以導致血管內微血栓形成,由此而引起腦血流量(CBF)減少,以及鐵蛋白、含鐵血黃素等腦組織神經毒性物質沉積,是創傷后早期繼發性腦梗死等缺血性損傷的重要原因[22]。動物實驗證實,創傷性腦損傷后數小時即可見微血栓形成,形成部位與神經元損傷區域具有高度相關性[23-24]。與高凝狀態繼發血栓形成相比,消耗性低凝狀態主要引起進展性出血性損傷,表現為在腦挫裂傷、創傷性腦出血等原發灶基礎上發生的進展性顱內出血(創傷后數小時內)、遲發性顱內出血(創傷后6~48小時)或全身出血傾向[10,14];約有50%的患者于創傷后48小時出現進展性出血性損傷,預后不良,且死亡風險超過無凝血功能障礙患者的5倍[25]。
3.診斷TBI-IC的臨床診斷標準為常規凝血功能試驗結果異常,包括凝血酶原時間、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INR)、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FIB)和D-二聚體等,但這些實驗室指標特異性較低且無法解釋創傷性腦損傷后發生凝血功能障礙的潛在原因[10]。血栓彈性描記圖(TEG)可實現床旁實時監測凝血和纖溶級聯反應,其診斷能力優于常規凝血功能試驗,但基于血栓彈性描記圖的臨床診斷標準尚未建立[26],因此進一步探明TBI-IC患者凝血系統和纖溶系統異常改變的時間進程、建立血栓彈性描記圖的特異性參考值范圍,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隨著針對TBI-IC病理生理學機制研究的深入,一些具有潛在臨床診斷價值的生物學標志物(如細胞微囊泡)逐漸被發現并有望實現臨床轉化[27]。
二、潛在病理生理學機制
1.細胞微囊泡細胞微囊泡是細胞激活、損傷或凋亡后自胞膜表面脫落的、具有雙層脂質膜結構的微小囊泡,直徑100~1000 nm[3]。其形成時胞膜內層磷脂酰絲氨酸(PS)等陰離子磷脂外翻,為凝血級聯反應提供磷脂表面,故具有極強的促凝活性。Nekludov等[28]的研究顯示,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外周血和腦脊液中具有高促凝活性的細胞微囊泡(PS+MVs)數目顯著增加,以血小板和內皮細胞源性為主。天津醫科大學張建寧教授團隊首次在創傷性腦損傷小鼠模型外周血和損傷腦組織中檢測到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源性微囊泡,即腦源性微囊泡(BDMVs)[29-30],此后Nekludov等[31]證實重型顱腦創傷患者外周血中亦存在這種腦源性微囊泡。因此,推測腦源性微囊泡可能是TBI-IC的啟動和傳播因素[29-30,32-33]:(1)創傷后血腦屏障破壞,受損腦組織釋放腦源性微囊泡進入血液循環,啟動凝血級聯反應,誘發系統性高凝狀態并迅速進展為消耗性低凝狀態。(2)于小鼠尾靜脈注射經體外制備的腦源性微囊泡,可模擬創傷性腦損傷小鼠凝血系統和纖溶系統改變。(3)游離線粒體(exMTs)約占腦源性微囊泡的55.2%,通過其膜表面心磷脂發揮促凝、促血小板激活作用。(4)腦源性微囊泡可以引起血管內皮細胞損傷或激活,導致血管內皮促凝活性增強或血管內皮屏障破壞,從而加重TBI-IC。(5)乳凝集素(lactadherin)可以有效清除細胞微囊泡,減輕創傷性腦損傷小鼠凝血功能紊亂和血管內皮屏障破壞程度。因此,以腦源性微囊泡為生物學標志物和治療靶點的基礎與臨床研究,可以為TBI-IC的臨床診斷與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2.組織因子與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腦組織富含凝血活酶,以組織因子為主[34]。創傷性腦損傷后受損的腦組織可釋放組織因子進入血液循環,通過與凝血因子Ⅶa結合,啟動外源性凝血途徑,同時促進內源性凝血途徑,導致系統性高凝狀態;隨著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耗竭,轉為消耗性低凝狀態,伴隨繼發性纖溶系統亢進,最終導致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35]。彌散性血管內凝血可發生于創傷性腦損傷后6小時,由于纖維蛋白沉積和微血栓形成,導致機體缺血性損傷和難以糾正的出血傾向[36],而且創傷性腦損傷早期發生的彌散性血管內凝血常伴隨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等不良事件[37]。Nekludov等[28]發現,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外周血和腦脊液中存在表面高表達組織因子的細胞微囊泡(TF+MVs),提示組織因子可通過綁定細胞微囊泡而發揮促凝作用。Tian等[29]認為,創傷性腦損傷小鼠外周血中的腦源性微囊泡通過其膜表面組織因子介導凝血酶生成及其與血小板結合而介導血小板激活,促進凝血級聯反應。
3.血管內皮細胞損傷血管內皮細胞損傷或被激活,使其促凝-抗凝系統失衡,血管內皮促凝活性增強被認為是導致TBI-IC的早期事件。糖萼是襯于血管內皮細胞表面的一層蛋白質-多糖復合物,包含抗凝血酶Ⅲ、組織因子途徑抑制物等抗凝物質,使生理狀態下的血管內皮細胞具有抗凝特性[38]。由于創傷性腦損傷后交感神經興奮和兒茶酚胺過度分泌,導致糖萼代謝受損和凝血級聯反應的發生,而創傷性腦損傷后血漿糖萼降解產物多配體蛋白聚糖-1(syndecan-1)水平變化與凝血功能障礙的發生及預后不良密切相關[38-39]。血管內皮細胞損傷或激活后釋放的另一關鍵性促血栓形成物質,為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其可通過介導血小板向血管內皮損傷部位粘附以促進血栓形成[3];而在創傷性腦損傷急性期大量釋放的高黏附活性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具有促進血栓形成和凝血功能障礙的作用,這一作用可被特異性整合素樣金屬蛋白酶與凝血酶13型(ADAMTS-13)所阻斷[33]。Kumar等[40]經研究顯示,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外周血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表達水平和黏附活性增強、ADAMTS-13水平相對不足,導致中至重癥患者凝血功能紊亂、預后不良。進一步探究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在TBI-IC發生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機制,進而開展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抑制藥干預TBI-IC的基礎與臨床轉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關注的是,以血管內皮細胞為核心的炎癥反應與血栓形成相互促進,“血栓炎癥(thromboinflammation)”的概念逐漸取得共識并受到重視[41],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膿毒血癥、心肌梗死和缺血性卒中等疾病,以及血小板、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NETs)和vWF/ADAMTS13等,有可能在血栓炎癥的發生與發展中發揮一定作用[41-42]。基于血栓炎癥的研究可能為TBI-IC的臨床診斷與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4.血小板功能障礙研究顯示,血小板過度消耗與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相關:當創傷性腦損傷患者血小板計數<175×109/L時,進展性出血性損傷風險顯著增加,<100×109/L時死亡風險增加9倍[43];但血小板計數正常的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同樣可發生進展性出血性損傷[44],提示血小板計數(即血小板的“量”)可能并非起決定作用。經血栓彈性描記圖分析證實,TBI-IC患者在創傷早期即存在血小板功能障礙(即血小板的“質”),表現為由二磷酸腺苷(ADP)和花生四烯酸(AA)介導的血小板聚集能力減弱[45]。其中,ADP途徑抑制(ADPi)被認為是誘發TBI-IC的重要原因,ADPi≥60%的患者發生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和死亡的風險顯著增加[45-46]。因此,有學者將創傷性腦損傷后血小板功能障礙定義為ADPi≥60%,并推薦其為血小板輸注閾值[46-47]。但Kay等[44]認為,ADPi≥70%可能更具臨床指導價值。創傷性腦損傷后血小板功能障礙的發生機制目前尚未明確,Martin等[48]的研究表明,創傷性腦損傷后釋放的細胞微囊泡表面高表達二磷酸腺苷受體P2Y12,通過競爭性結合二磷酸腺苷,從而抑制由后者介導的血小板聚集;此外,由Donahue等[49]構建的創傷性腦損傷血小板功能障礙大鼠模型,為相關機制和干預研究提供了動物研究模型。
5.纖溶系統活性異常目前認為,創傷性腦損傷后的高凝狀態繼發纖溶系統亢進可增加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等不良事件的風險[50]。D-二聚體是纖溶系統亢進的特異性標志物,血漿D-二聚體水平于創傷后顯著升高,且與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和預后不良呈負相關[50-51],尤其是入院時血漿D-二聚體≥3.04μg/ml是預測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重要參考指標[51]。但Xu等[52]認為,D-二聚體/纖維蛋白原比值是更具有優勢的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預測指標。不同于繼發性纖溶系統亢進這一主流觀點,Hijazi等[53]指出,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發生與發展可能是受損腦組織釋放組織型或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t-PA或u-PA)引起的原發性纖溶系統亢進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亦有基于血栓彈性描記圖等新型檢測技術的研究顯示,創傷性腦損傷患者極少合并纖溶系統亢進[54]。近年來,纖溶系統亢進的相反狀態——纖溶系統阻滯(fibrinolysis shutdown)越來越受到關注,其發生機制可能與t-PA和(或)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PAI-1)表達水平和活性失調有關[55],其中,纖溶系統阻滯是創傷性凝血病患者最為常見的纖溶狀態[56]。目前關于纖溶系統阻滯的研究較少,僅Leeper等[57]報告纖溶系統阻滯現象在兒童創傷性腦損傷患者中極為常見且與預后不良相關。創傷性腦損傷后纖溶活性改變及其與TBI-IC間的關系尚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6.組織低灌注與蛋白C系統激活創傷性腦損傷后失血性休克可引起組織低灌注,使血栓調節蛋白(TM)水平升高,后者通過與凝血酶結合激活蛋白C為活化蛋白C(APC),后者可滅活凝血因子Ⅴa和Ⅷa,同時抑制PAI-1活性,從抗凝和促纖溶兩方面導致低凝狀態[58]。上述作用機制已經證實與創傷性凝血病密切相關[7-8],但其在TBI-IC發生中的作用仍存爭議。組織低灌注和蛋白C系統激活可加重TBI-IC,但失血性休克在創傷性腦損傷中并不常見,未合并失血性休克性組織低灌注的患者其活化蛋白C水平與TBI-IC并無關聯性[37,59-60]。Sillesen等[61]經對創傷性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豬模型的觀察發現,創傷后即刻凝血系統和纖溶系統即出現異常,而蛋白C系統激活則發生于創傷后2小時。因此,與創傷性凝血病不同,組織低灌注和蛋白C系統激活是TBI-IC的危險因素,但非必要因素[37,59-60]。
三、治療進展
早期糾正凝血功能障礙與降低病死率和改善預后相關,因此入院后應立即進行凝血功能試驗和(或)血栓彈性描記圖以監測凝血系統和纖溶系統狀態[62]。目前尚無TBI-IC相關治療指南,需借鑒創傷性凝血病的治療方案,如2019年歐洲創傷出血高級處理特別工作組(Task Force for Advanced Bleeding Care in Trauma)發布的《嚴重創傷出血與凝血障礙管理歐洲指南(第5版)》(簡稱“歐洲指南”)[63],但是由于二者發生機制存在差異,該方案是否適用于TBI-IC尚無明確的循證醫學證據。中國神經外科重癥管理協作組最新發布的《中國神經外科重癥管理專家共識(2020版)》[64]對急性創傷性出凝血功能障礙給出了指導意見。
1.針對凝血功能紊亂的治療原則對于創傷前有抗凝藥服藥史的患者,早期應用特異性拮抗藥或凝血酶原復合物可以逆轉抗凝藥引起的凝血功能紊亂[65-66];而合并失血性休克患者,則應重視對“致死性三聯征(低體溫、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礙)”的積極干預,“歐洲指南”推薦限制性液體復蘇方案,維持平均動脈壓(MAP)>80 mm Hg(1 mm Hg=0.133 kPa)[63]。2019年發表于Lancet的氨甲環酸治療創傷性腦損傷Ⅲ期臨床試驗(CRASH-3)顯示,創傷后3小時內予氨甲環酸可安全、有效降低輕至中型創傷性腦損傷患者的死亡風險,但對重癥患者無明顯療效[67],推測可能與創傷后出現的不同纖溶狀態有關,即氨甲環酸僅對纖溶亢進者有效[50,55]。值得注意的是,尚有小樣本臨床試驗顯示,氨甲環酸對改善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和預后無效[68]。
2.輸血治療輸血治療是TBI-IC的常規治療手段,但目前大多為經驗性治療。來自歐洲和以色列等20個國家的數據顯示,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入院后靜脈輸注血小板或新鮮冰凍血漿(FFP)的比例為52%和73%[69],但二者對TBI-IC的有效性仍有較大爭議,目前尚無明確結論[70-72]。對于創傷前服用抗血小板藥的創傷性腦損傷患者,若合并血小板功能障礙且需接受手術治療,建議靜脈輸注血小板并維持血小板計數>100×109/L[47,63];對于疑似進展性出血性損傷且凝血酶原時間和(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正常參考值1.50倍的患者,建議靜脈輸注新鮮冰凍血漿以補充凝血因子[63]。盡管已知貧血是TBI-IC的危險因素,但多數試驗提示靜脈輸注紅細胞對改善凝血功能無效,甚至可加重病情[73-74]。Yuan等[75]認為,靜脈輸注小劑量(20μg/kg)重組凝血因子Ⅶ(rFⅦa)可有效糾正TBI-IC、預防進展性出血性損傷且不增加血栓形成風險。“歐洲指南”推薦,重組凝血因子Ⅶ可作為常規治療無法控制的大出血或TBI-IC持續存在的替代方案[63]。Stolla等[76]在“TBI-IC輸血治療研究進展”中指出,目前所報道的輸血治療TBI-IC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臨床試驗大多呈陰性結果,但這些研究中以小樣本、回顧性或混雜因素較多的臨床試驗居多,缺乏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此外,進一步開展不同血液成分對TBI-IC影響的機制研究將為輸血治療適應證、輸血成分和輸血量的選擇提供理論依據。
四、小結
盡管TBI-IC的研究業已取得長足進步,但其確切的發生與發展機制尚不明確,亦缺乏有效的早期診斷和干預措施,尚待進一步的基礎與臨床研究。一些新興領域如腦源性微囊泡、“血栓炎癥”和纖溶系統阻滯等相關研究為TBI-IC的診斷、預防與治療開拓了新的思路。此外,創傷性腦損傷患者同樣存在老齡化趨勢,針對老年創傷性腦損傷患者的個性化治療也應是今后關注之重點。
利益沖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