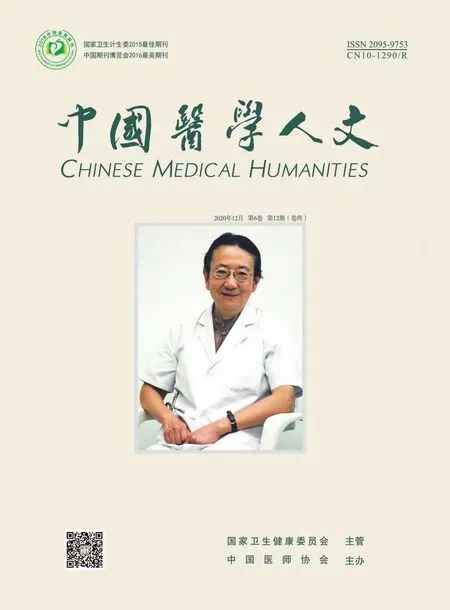臨床是什么
——從“奧斯勒命題”說開來
文/王一方 耿 銘
現代醫學越來越精細化,卻患上了母題空洞癥,如同脊髓空洞癥,母題的空洞帶來觀念行為的迷思與乏力,譬如“醫學”“健康”“臨床”“療愈”,并非百度搜索引擎或者百科全書給出的解讀。醫學并非只是一門科學,而是源自科學,高于科學,健康也并非軀體無疾,而是身心社靈的平衡與和諧,以及生命全程、社會全方位、產業全鏈條的關懷與服務,同樣,臨床并非只是簡單地回到患者身邊,“離床”的遠程會診與虛擬現實技術再造的臨床實訓基地都是對臨床概念的拓展,但臨床的真諦是什么?仍然需要我們深思,需要我們熟慮,需要我們回歸“奧斯勒命題”。
臨床是什么?這不是一個問題,卻是一個需要深究的命題,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奧斯勒沒有抽象地論述臨床醫學的學科建構(不同于基礎醫學、預防醫學的范式),而是樸素地告訴他的弟子們,臨床就是把更多的時光安排在患者的床邊,去觀察、去聆聽、去觸摸,去思考,隨著現代技術對臨床醫學的介入,他又提出要將實驗室建在病房,儀器拉到床邊,讓技術最大限度地為患者服務,以實現“患(弱)者為尊”的人道主義夙愿。
臨床的背后是學歷與閱歷,專業知識(技術)與綜合素養(人文),能力與魅力的關系,醫護成長境遇千差萬別,但必須重點強調其臨床實踐的歷練(如規培的門檻,執業醫師考試門檻)。價值導向必須把解決問題的實操能力放在論文發表、外語素養等要素之上。中國現代臨床醫學泰斗張孝騫、林巧稚不是論文大王,而是臨床大師。在他們的感召、示范、引領下,協和醫院產生了一批“癡迷臨床,以解決患者疾苦為樂趣”的臨床大夫,許多人后來成為了臨床大師。
重實踐能力是一個價值風標,其背后隱含著對臨床真諦(即著名的奧斯勒命題)的認知與理解。早在一百年前,奧斯勒就提出:“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這是一個充滿實踐理性的命題,臨床的本質是病床邊的陪伴、見證、撫慰、關懷。實驗室也需要建到病房里(要驗證的應該是人文的力量)。在奧斯勒看來,如果不是個體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醫學也可能是科學,而不是藝術。多變性是生命定律,世界上沒有兩副面孔是一模一樣的,也沒有兩個生命個體是一模一樣的,因此,在疾病的異常條件下,也不會有兩個病人表現出同樣的病理反應和病態行為。相反,奧斯勒認定越無知,就越教條主義,越迷信書本和既有的指南。所謂“好醫生治病,偉大的醫生治病-人”,當代臨床大師胡大一教授十分欣賞奧斯勒的這一名言,反感那些“看病不看人,懂病不懂人,治病不治人”的所謂名醫,因為醫學是人與人的故事,而不只是人與機器的故事,人與金錢的故事,敘事醫學的創始人麗塔·卡倫更進一步發展了奧斯勒的臨床智慧,認為疾病、死亡不是一個事故,而是一個故事,療愈、療護的努力讓這些故事有了溫度。現代醫學不應該高冷,而應該高暖。
為何醫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是因為生命境遇具有永恒的不確定性與無限的可能性,正是因為這些可能性導致的疾病復雜性、多樣性、藝術性塑造的患者個性,醫護人員必須尊崇主體性,對沖客觀性、齊一性、標準化。醫學存在藝術性,旨在對沖、稀釋、軟化醫學的科學剛性,希望在科學性與藝術性之間保持張力。于是,醫學從業者必須具有雙重職業性格:科學家+藝術家,而這份歷練來自臨床實踐的磨練。
著名醫學家,耶魯大學醫學院前院長劉易斯·托馬斯認為:醫學是最年輕的科學,醫療技術只是半吊子技術,病因治療的比例并不高,而必須輔以發病學治療、癥狀學治療與安慰劑治療,醫生常常需要在諸多不確定的信息下做出正確的判斷。許多疑難疾患面前,醫生做出正確判斷的前提不是檢測報告,而是經驗與直覺。如果將特魯多(墓志銘)箴言“有時去療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改為臨床路徑的啟悟,應該是“有時去循證,常常去敘事,總是去體驗。”
三百年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經嘲諷那些只在書本中鉆研醫學的人,他們開知之甚少的藥,治療他們知之更少的病,治療他們完全不知的人。因為,醫護只有經過臨床的實踐摔打之后,才明白藥理知識是相對確定的,疾病(病理)知識不確定性增加(個體性,混沌性),病人的境遇是千差萬別的。
毫無疑問,醫護人員對臨床意義與價值的認知決定他們的眼界與境界,職業進階的高度與深度,也決定著他們的職業回饋,臨床大師永遠是年輕,永遠最快活。
首先,臨床是科學與人文,技術與人性的深度融合,詹啟敏院士認為醫學有兩只翅膀,一只是飛速發展的醫療技術,另一只則是生命關懷的人文秉性。僅憑一只翅膀發力肯定飛不高,飛不遠。韓啟德院士將醫學人文比喻為“方向盤”與“剎車片”,決定著職業生活(行車)的方向與節奏,避免翻車(人生事故)。
其次,臨床交往是醫者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源自馬克思的名言“認識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既包括醫-患關系(相愛-相殺,溫暖-冷漠,悲憫-傲慢),也包括醫-醫關系(同行沉默與文人相輕)、醫-護關系(是支使關系,還是合作關系)、醫-藥關系(相互補臺,相互疏離)、患-患關系(同病相憐,相互支撐,相互攀比、埋汰),每一對關系的背后都是職業藝術的細細流淌。臨床也是人類苦難境遇的總和:醫者每天都面對疾病、殘障、衰弱、死亡、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心靈的投射,社會關系的傾斜,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殘酷性,反美學(活色生香,死朽衰臭),反生活(餓/渴不思食/飲,恩將仇報),反常識(人財兩空,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臨床更是實踐難題,醫患之間存在著永恒的無法相知之幕(醫者的專業知識與判斷力優勢于患者與家屬,信息的泛濫增加了醫患之間相知的障礙與難度),醫患陌生親密關系,面臨著快速親密關系締結的難題,只有在慢病語境中,才有所緩和,久病成良醫,久病成知己,醫患之間才會有更多的理解和認同。
其三,臨床也是醫護體驗的總和:有人興奮(嗜血性),有人壓抑/沮喪(暈血、暈尸),平衡感最重要(理性與經驗,美與丑,權威性與親和力,知利害-得失,高下清濁,進退-收放),因此,臨床是綜合技能(勝任力)的集合:共情,溝通,關懷,照護,手術,藥物。臨床還是氣質的外展:醫護必須具有開放性,親和力,宜人性,正念(積極心理)與包容性。
最后,臨床是哲學,充滿了辯證法,講求對立統一,保持張力與平衡。需要不斷地進行實踐中的反芻、反思,或稱之為否思性思維,既是自我否定的批判性反思,也有建設性反思,包括對單純生物醫學模式的反思,擺脫各種決定論(基因決定論),機械論(刻舟求劍),從疾病到疾苦,生物到生命,心理到心靈,現象到意象,干預到順應要完成一次次轉身。也就是說,臨床干預的反思不僅要拓展思維半徑,還要致力于方向的轉折,從軀體干預到心理干預,靈性干預,從戰爭模型(病因消殺)到姑息順應模型(安寧療護),知是非難易,輕重緩急到進退收放。具體的臨床范疇包括五個方面,可簡稱為“五要五不要”:要干預,不要干預主義,適度而不過度干預,著眼于扶弱,而不是助強、助狂,不僅在軀體層面干預,還要在心理-社會交往-靈性層面干預,不僅要救助,還要拯救-救贖,接納姑息妥協,順應生命的自然歸途;要技術,不要技術主義,手中有技術,也不濫用,有高新技術,依然保持對生命的敬畏;要科學,不要科學主義,科學不是萬能的,接納、探究臨床中的不確定性、偶然性、偶在性,藝術性;要規范,不要教條主義,追求個性化,適度講規范,適時講變通,因人應時因地制宜;要創新,不要獵奇主義,拒絕“新就是好,老就是朽”。
最近,在韓啟德院士《醫學的溫度》新書發布會上,韓先生用一段箴言來揭示臨床醫學的真諦,那就是“醫學亦人學,醫道重溫度”,這也是奧斯勒命題最貼切的當代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