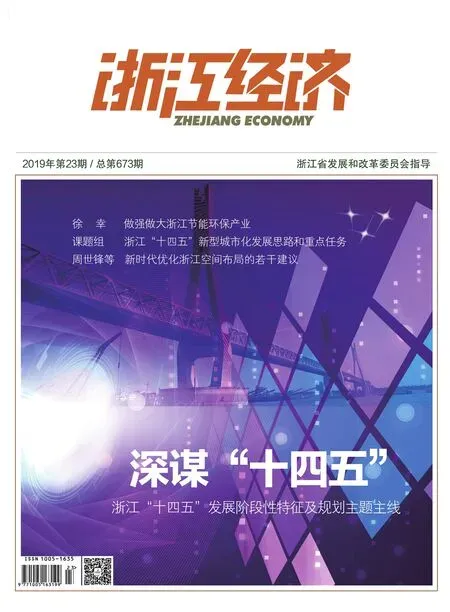信用體系建設:從自發秩序到制度秩序
□陳海盛 應瑛 白小虎 郭文波
作為撬動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制度供給,信用體系建設通過構建信用監管制度,明確規則和執行規則,為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全新思路
“自發秩序”和“制度秩序”切換是市場化改革的共性問題。自發秩序是我國經濟啟動市場化改革初期的特殊性一面,而從自發秩序向制度秩序切換才是市場化改革的一般性和總體方向。經濟發展的現實困境充分顯示了從特殊性向制度一般性過渡的現實障礙。作為制度有效供給的重要方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及實踐,有助于倒逼市場主體行為從軟約束向硬約束、從自發秩序向制度秩序進行深層次的轉變,撬動全面深化的市場化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內在要求
受經濟發展的歷史與階段的限制,全國乃至浙江所擁有的建立法治經濟的制度要素相對缺乏。建立和維護新的市場秩序要求政府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定位和能力結構,但由于多年形成的慣性,政府難以完成從直接掌控企業和經濟向建立和維護市場秩序所需的觀念和角色轉變。與此同時,逐步突現的不同利益主體與仍然強大的行政權力的結合,孳生了大量的腐敗,扭曲了正在建設中的市場規則,更進一步地加重了經濟無政府主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開始大力整頓市場秩序、加強市場監管,其重點在于規范市場行為、打破地方封鎖和打破行業壟斷,有利于支撐生產和交易活動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復雜的形式展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信用經濟。要保證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必須建立和完善市場規則和市場秩序。市場規則是以法規、法律和倫理道德等形式規定或表現出來的市場行為規范和規則,主要包括市場進入與退出規則、市場競爭規則、市場交易規則、市場仲裁規則等;市場秩序則是由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法律體系和社會觀念等規范、形成和保持的經濟運行的有效狀態,包括市場主體秩序和市場交易秩序等。
正如錢穎一教授所認為的那樣,現代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其基本規則就是基于法治的規則。以法律的方式界定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政府以及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使中國走向法治經濟將是今后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的重點和中心。浙江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長期目標,就是要建立基于法治的經濟制度體系,其中包括以適當的法律體系規范市場中不同主體的行為,同時必須建立專業化的監管機構,以共同認可的程序和規則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行管理和監督。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規則、市場秩序與市場的有效性存在密切關系,兩者能否建立、完善和有效執行,關系市場化改革的成敗。在市場經濟自發秩序情形下,由于市場規則不健全,市場秩序時常出現混亂,通過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有效支撐,市場監督和管理更加及時、有效和精準性。
制度創新在市場化改革中占據重要角色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完成經濟交換所必需的制度的復雜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只解決簡單的交換問題,有的要解決跨越時間和空間、涉及眾人的交換問題。經濟交換的復雜程度是契約層次的函數,而契約則是在擁有不同專業化程度的經濟體系中完成交換所必需的。
當交換的成本以及不確定性較高時,非專業化是一種保險的方式。而專業化程度越高、有價值特質的數量越多、可變性越強,就越是需要借助可靠的制度,來支撐個人從事復雜的契約行為,并使條款執行上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
現代經濟體系中的交換包含有許多可變的屬性,并且交換延續的時間也較長,故非得依賴于制度的可靠性不可。此外,要保證制度對市場經濟的持續可靠性支撐,隨著時代變化還應對制度進行相應創新,以適應經濟發展實際。
信用建設是撬動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制度供給
商品、服務以及代理人的表現,均具有多種屬性,且屬性層次的高低隨樣本或代理人的不同而不同。高昂的成本使得對這些層次的衡量不可能是全面的或完全精確的,辨明每一交換單位的各種屬性之層次高低所需的信息成本,是這種意義上交易費用的根源。交易費用包括衡量交換物之價值的成本、保護權利的成本,以及監管與實施契約的成本。
市場經濟形成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三種形式的交換類型。首先,在經濟史出現過的大部分交換,都是與小規模生產以及地方性交易相聯系的人際關系化的交換。重復交易、文化同質,以及缺少第三方實施,是這種交換的典型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交易費用盡管很低,但由于專業化與勞動分工尚未發育完全,因而交易成本很高。在這種交換中,經濟體系和貿易伙伴圈子的規模都很小。接著是非人際關系化交換。當交換的規模與范圍擴大后,交換雙方都將努力使其非人際關系化。但交換的種類與次數越多,就越是需要訂立更為復雜的合約,從而客戶化與人際關系化就越不容易做到,演化形成非人際關系化交換。在這種形式的交換中,各方主要受到家族紐帶、契約義務、交換抵抑,以及商人行為準則的約束。最后是存在第三方實施的非人際關系化交換。它是當代成功經濟體的重要支撐,而在這些經濟體中,包含著現代經濟成長所不可或缺的復雜的契約。第三方實施遠非理想、完美,因而交換各方仍然要動用大量的資源來發展與客戶的關系。但其他方法,如交換方的自我實施以及信任等,也都不可能完全奏效。這并非因為意識形態或規范不重要,它們當然重要,況且人們在傳播這些行為準則方面也花費了大量的資源。這只是因為,投機、欺詐,以及規避責任等的回報在復雜社會中也同步增長了。正因為這樣,具有強制力的第三方才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創建一系列規則來使各種非正式約束能發揮作用,是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實施的最佳途徑。純粹自發的第三方實施系統的交易費用是相當高的,而由政治組織作為第三方、動用強制力量來實施合約,則在監管與實施合約方面存在著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
作為撬動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制度供給,信用體系建設通過構建信用監管制度,明確規則和執行規則,為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全新思路。信用建設對市場化改革的支撐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通過建立各地區各部門交流機制為實施懲罰提供必要的信息,使稽查缺失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懲罰通常是一種公共品,即使全體受益,而成本卻由少數人承擔,因而制度還為那些承擔懲罰他人的職責的個人提供激勵。需要強調的是,信用體系創建了一種可以帶來可靠承諾的制度環境,建立起一個包含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以及實施在內的復雜的制度框架,在這個框架下法律訴訟和信用監管相互補充,使市場經濟的低成本交易成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