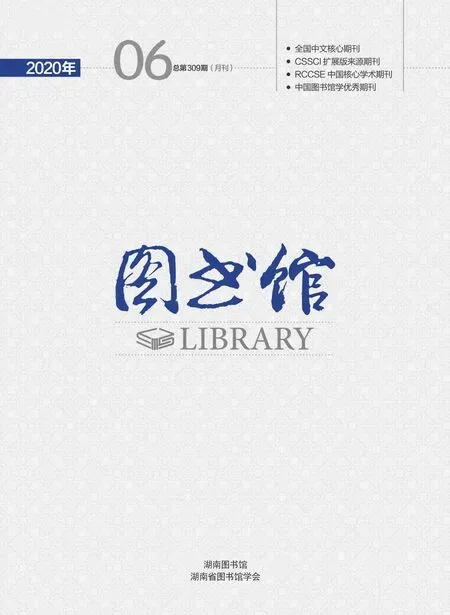多元、融合、跨界和創(chuàng)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推廣模式研究*
周笑盈 魏大威
(國家圖書館 北京 100081)
1 理論與實(shí)踐現(xiàn)狀
回溯人類文明的發(fā)展,科技與文化一直都是時(shí)代發(fā)展的主旋律。文化積累推動(dòng)科技發(fā)展,科技進(jìn)步促進(jìn)文化生產(chǎn)、加速文化傳播、豐富文化積累。深入研究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推廣模式,總結(jié)規(guī)律、發(fā)現(xiàn)重點(diǎn)、為我所用,對(duì)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發(fā)展、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現(xiàn)代技術(shù)條件下,文化傳承和文藝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模式和社會(huì)需求發(fā)生了重大改變,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繁榮與發(fā)展,持續(xù)制定并出臺(tái)了一系列文化扶持政策,多次強(qiáng)調(diào)以技術(shù)手段創(chuàng)新文化發(fā)展,加強(qiáng)新媒體與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聯(lián)合發(fā)布《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提出要保護(hù)傳承文化遺產(chǎn),推進(jìn)數(shù)字化保存和傳播,滋養(yǎng)文藝創(chuàng)作,綜合運(yùn)用各類載體,融通多媒體資源,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充分發(fā)揮圖書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機(jī)構(gòu)在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作用[1]。2017年2月,文化部發(fā)布《“十三五”時(shí)期文化發(fā)展改革規(guī)劃》,提出“到2020年,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體系初步形成”“建設(sh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示范區(qū)”“把弘揚(yáng)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發(fā)展現(xiàn)實(shí)文化有機(jī)統(tǒng)一起來,緊密結(jié)合起來,在繼承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繼承”[2]。2017年10月18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yùn)興,文化強(qiáng)民族強(qiáng)。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3]
我國政府歷來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在中央和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實(shí)施了中華古籍保護(hù)計(jì)劃、曲藝傳承發(fā)展計(jì)劃、中華傳統(tǒng)文化百部經(jīng)典、公共數(shù)字文化工程等一系列文化工程項(xiàng)目。
在文物保護(hù)與展陳領(lǐng)域,新技術(shù)提高了準(zhǔn)確性與工作效率。在文物保護(hù)中,三維激光掃描技術(shù)、無人機(jī)、近景攝影測(cè)量等非接觸式的三維信息采集技術(shù)協(xié)助了文物修復(fù),如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利用TLS數(shù)字化技術(shù)掃描重慶大足石刻千手觀音,形成精確模型,用于千手觀音的搶救性恢復(fù)[4]。在文物展陳領(lǐng)域,將RFID 、傳感器、視頻圖像、網(wǎng)絡(luò)等新興技術(shù)用于藏品管理[5]。
在文化傳播和服務(wù)推廣領(lǐng)域,媒體融合促進(jìn)了傳統(tǒng)文化傳播。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huì)開幕式設(shè)計(jì)的巨幅中國寫意長卷和2018年平昌冬奧會(huì)的“北京8分鐘”利用機(jī)器人演出展示中國最先進(jìn)的高科技和人工智能;2015年故宮博物院的“端門數(shù)字館”項(xiàng)目,通過運(yùn)用AI、VR、語音圖像識(shí)別等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了觀眾與歷史人物對(duì)話,大大提升了觀眾體驗(yàn);國家典籍博物館《甲骨文記憶》展通過設(shè)計(jì)投影互動(dòng)場(chǎng)景,讓觀眾全方位了解甲骨文的起源故事。伴隨智能移動(dòng)終端的應(yīng)用與推廣,傳播智慧化、管理智慧化和服務(wù)智慧化與智能手機(jī)、平板電腦、車載智能終端、可穿戴設(shè)備、智能化家庭設(shè)備等實(shí)現(xiàn)了深度融合。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開發(fā)智能聊天機(jī)器人“小圖”;故宮博物院設(shè)計(jì)了掌上應(yīng)用《每日故宮》;國家圖書館利用在線網(wǎng)絡(luò)公開課MOOC平臺(tái)促進(jìn)傳統(tǒng)文化推廣,發(fā)布國民通識(shí)教育課程,通過微信公眾服務(wù)平臺(tái)開通了“國家圖書館”“掌上國圖”等10余個(gè)公眾號(hào)[6]。
在文化產(chǎn)品的開發(fā)與利用領(lǐng)域,資源整合提高了公共數(shù)字文化服務(wù)效能。國家圖書館運(yùn)用“國家數(shù)字文化網(wǎng)”整合各類音視頻資源,通過“春雨工程”“文化幫扶”等項(xiàng)目促進(jìn)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上海博物館通過開發(fā)可視化數(shù)據(jù)管理中心,建立起博物館核心數(shù)據(jù)資源支撐平臺(tái);杭州圖書館于2016年底與螞蟻金服洽談合作,引進(jìn)智能咨詢機(jī)器人項(xiàng)目。
在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開發(fā)與應(yīng)用領(lǐng)域,技術(shù)應(yīng)用提升了產(chǎn)業(yè)附加值收益。國家博物館設(shè)立了多個(gè)文創(chuàng)實(shí)體店(紀(jì)念品店、博文齋、名人名家店、國博茶藝館等)和10多個(gè)銷售點(diǎn),設(shè)計(jì)開發(fā)文創(chuàng)產(chǎn)品3 000余款,與阿里巴巴、上海自貿(mào)區(qū)等共同打造“中國文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交易平臺(tái)”;杭州市利用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優(yōu)勢(shì)、高校人才資源優(yōu)勢(shì)和自然生態(tài)資源優(yōu)勢(shì)設(shè)立文創(chuàng)園區(qū)和文創(chuàng)特色小鎮(zhèn)。電影、動(dòng)畫、綜藝產(chǎn)品的開發(fā)如火如荼,國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大魚海棠》《大圣歸來》等都實(shí)現(xiàn)了經(jīng)典傳統(tǒng)文學(xué)作品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
筆者通過分析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與推廣的應(yīng)用現(xiàn)狀,從傳統(tǒng)文化的建設(shè)主體、內(nèi)容種類、傳播渠道、服務(wù)方式四個(gè)層面,將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與推廣模式總結(jié)為多元主體共建模式、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模式、跨界組合傳播模式和創(chuàng)新用戶體驗(yàn)?zāi)J剑瑥暮诵囊亍⑸a(chǎn)流程、主要特征、發(fā)展趨勢(shì)幾個(gè)維度對(duì)模式內(nèi)容進(jìn)行具體分析,對(duì)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呈現(xiàn)的特征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為推動(dò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服務(wù)的理論研究和實(shí)踐探索提供借鑒。
2 多元主體共建模式
多元主體共建模式具有明顯的多元性特征,其發(fā)展趨勢(shì)呈現(xiàn)為:由政府一元體系發(fā)展為政府、企業(yè)和第三部門三足鼎立的三元體系,政府、企業(yè)和第三部門互為補(bǔ)充,共同提升。多元主體共建模式的核心組成要素包括:“政府主導(dǎo)”+“社會(huì)參與”+“市場(chǎng)配置”。
2.1 政府主導(dǎo)
政府是文化服務(wù)體系的核心,是文化服務(wù)的組織者、管理者和監(jiān)督者[7],負(fù)責(zé)組織和監(jiān)管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投資與供給,保證產(chǎn)業(yè)鏈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政府通過制定相關(guān)的規(guī)則與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規(guī)范市場(chǎng)行為,保證市場(chǎng)效率。
在文化服務(wù)方面,政府是投資主體。因?yàn)槲幕?wù)涉及到國家軟實(shí)力的提升與公益性事業(yè)的發(fā)展,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同時(shí)可以適當(dāng)引入市場(chǎng)資本,鼓勵(lì)私有資本進(jìn)入。在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方面,政府與市場(chǎng)要加強(qiáng)合作,主要的合作方式包括:外包、委托、特許經(jīng)營等方式,以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優(yōu)勢(shì),提升公益性與效益性。
2.2 社會(huì)參與
社會(huì)參與的目的既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更高的文化需求,也是為了彌補(bǔ)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wù)的不足,而政府在社會(huì)參與過程中主要負(fù)責(zé)提供充分的政策保障,通過制定經(jīng)濟(jì)性的政策(如產(chǎn)業(yè)政策、財(cái)政稅收政策)和非經(jīng)濟(jì)性的政策(如文物保護(hù)政策等)引導(dǎo)企業(yè)生產(chǎn)公共文化產(chǎn)品,提供政府期望的公共文化服務(wù)。
社會(huì)廣泛參與在合作形式上主要表現(xiàn)為兩種形式,一是政府與社會(huì)信息提供商、內(nèi)容生產(chǎn)商、渠道傳播商、投資運(yùn)營商、配套服務(wù)商等文化企業(yè)單位進(jìn)行合作;二是與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例如技術(shù)研發(fā)公司、內(nèi)容生產(chǎn)公司、應(yīng)用開發(fā)公司、終端供應(yīng)公司、平臺(tái)推廣公司進(jìn)行密切合作。主要的合作方式包括項(xiàng)目共建、資本投資、戰(zhàn)略運(yùn)營。
2.3 市場(chǎng)配置
消費(fèi)社會(huì)的崛起,促進(jìn)傳統(tǒng)的文化事業(yè)和文化服務(wù)內(nèi)容進(jìn)入到文化消費(fèi)領(lǐng)域,傳統(tǒng)文化開始以公眾更為廣泛接受的方式進(jìn)入文化消費(fèi)和文化市場(chǎng),展覽、文創(chuàng)、公共教育等新興模式推動(dòng)文化傳播,使文化事業(yè)與文化產(chǎn)業(yè)邊界變得模糊,大眾文化消費(fèi)圈層逐漸形成。
傳統(tǒng)的文娛產(chǎn)業(yè),例如文化藝術(shù)、文化娛樂、文化創(chuàng)意等非經(jīng)營性文化行業(yè)與電子商務(wù)、社交網(wǎng)絡(luò)、在線娛樂、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等行業(yè)不斷融合,推陳出新,形成了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數(shù)字創(chuàng)意等UGC(用戶生成內(nèi)容)模式。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促進(jìn)了公共文化服務(wù)的組織體系變遷,通過市場(chǎng)的持續(xù)性發(fā)展,各種企業(yè)既可以獲得相應(yīng)的資本收入,又可以促進(jìn)文化傳播進(jìn)而提升社會(huì)效益。企業(yè)在將收益追求放在第一位的同時(shí),更多具有社會(huì)責(zé)任感的企業(yè)家開始通過公共文化服務(wù)形式回報(bào)社會(huì)。
3 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模式
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是指在現(xiàn)代科技驅(qū)動(dòng)下,將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打通,貫穿形成一條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模式,最終實(shí)現(xiàn)提升傳統(tǒng)文化產(chǎn)品和藝術(shù)表演產(chǎn)品“體驗(yàn)力”和“表現(xiàn)力”的目的。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的突出特點(diǎn)是強(qiáng)調(diào)在現(xiàn)代科技驅(qū)動(dòng)下以數(shù)字技術(shù)豐富和提升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容生產(chǎn)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一是文化形象創(chuàng)作;二是文化形式的展示包裝;三是文化娛樂內(nèi)涵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挖掘。
依據(jù)內(nèi)容生產(chǎn)流程,筆者將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的核心組成要素概括為:“特色I(xiàn)P開發(fā)”+“現(xiàn)代科技演繹”+“周邊產(chǎn)業(yè)拓展”。
3.1 特色I(xiàn)P開發(fā)
IP 概念主要是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其核心是指大量用戶喜愛的一個(gè)事物。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特色I(xiàn)P不再局限于文學(xué)作品,而是強(qiáng)調(diào)廣泛的體驗(yàn)與互動(dòng),在泛娛樂的互聯(lián)網(wǎng)與移動(dòng)時(shí)代,特色I(xiàn)P可以創(chuàng)造粉絲經(jīng)濟(jì),利用互動(dòng)娛樂的新生態(tài)打通游戲、文學(xué)、動(dòng)漫、影視、戲劇等門類,文化企業(yè)或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文化IP進(jìn)行市場(chǎng)擴(kuò)展,以核心IP為競(jìng)爭(zhēng)力創(chuàng)造更多社會(huì)效益和經(jīng)濟(jì)效益。
特色文化IP與傳統(tǒng)意義上文學(xué)藝術(shù)經(jīng)典形象塑造的區(qū)別主要在兩點(diǎn):① 粉絲效應(yīng)發(fā)酵。傳統(tǒng)文化形象的塑造往往單純依賴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IP注重產(chǎn)業(yè)效應(yīng)與市場(chǎng)效果,文化IP的知名度需要經(jīng)過市場(chǎng)檢驗(yàn),強(qiáng)調(diào)多維主體的連接和產(chǎn)業(yè)價(jià)值的賦能。② 民族性特質(zhì)解構(gòu)。隨著文化IP理念的進(jìn)化,從文化傳承與推廣的視角看,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性成為了全球化概念,中國特色的文化形象需要具有多元?jiǎng)?chuàng)意,但其文化價(jià)值理念和民族文化內(nèi)涵卻是不能改變的。例如根據(jù)傳統(tǒng)文化IP改編的流行歌曲或電視劇,需要具備豐富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才能實(shí)現(xiàn)IP效應(yīng)的延伸,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語境之下,傳達(dá)正面能量和主流文化才能在全球化領(lǐng)域被廣泛接受。
3.2 現(xiàn)代科技演繹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深刻變革了人與人、人與信息、人與服務(wù)之間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科技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生產(chǎn)在互聯(lián)網(wǎng)、云計(jì)算、大數(shù)據(jù)等基礎(chǔ)設(shè)施不斷完善的前提下,開始探索基于不同生活應(yīng)用場(chǎng)景的服務(wù),筆者結(jié)合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特點(diǎn),整理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合內(nèi)容生產(chǎn)下的三大場(chǎng)景。
第一技術(shù)場(chǎng)景:人工智能,人機(jī)交互。“人工智能+傳統(tǒng)文化”“人機(jī)交互+傳統(tǒng)文化”是指借助人工智能、人機(jī)交互等技術(shù),進(jìn)行文化創(chuàng)作,打破文化跨語言、跨地域、跨文化傳播的壁壘。主要代表性的技術(shù)分為兩類:機(jī)器學(xué)習(xí)類和虛擬現(xiàn)實(shí)類,機(jī)器學(xué)習(xí)利用知識(shí)圖譜、自然語言處理、計(jì)算機(jī)視覺、生物特征識(shí)別等技術(shù)完成自動(dòng)學(xué)習(xí),典型的代表如:百科知識(shí)圖譜、多場(chǎng)景自動(dòng)翻譯、AI記者等成果;虛擬現(xiàn)實(shí)利用AR、VR、MR等技術(shù)在傳統(tǒng)文物保護(hù)、展覽、展示領(lǐng)域得到廣泛應(yīng)用,帶來視聽感官交互體驗(yàn)的全面升級(jí)。
第二技術(shù)場(chǎng)景:移動(dòng)音視頻內(nèi)容生產(chǎn)。其最突出的特點(diǎn)包括三點(diǎn):“場(chǎng)景化”“個(gè)性化”“趣味化”。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讓人類的時(shí)間和注意力逐漸碎片化。伴隨著80、90、00后這些互聯(lián)網(wǎng)一代的主流娛樂消費(fèi)群體的崛起,閱讀習(xí)慣逐漸從文字閱讀向聲音、視覺閱讀轉(zhuǎn)型。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短視頻的發(fā)展,短視頻的出現(xiàn),源于自媒體的發(fā)展,滿足了年輕人的碎片化閱讀需求,成為了傳統(tǒng)文化全新的趣味化表達(dá)形態(tài),例如抖音平臺(tái)上累計(jì)播放量過億的傳統(tǒng)文化相關(guān)話題超過10個(gè)。傳統(tǒng)文化移動(dòng)音視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激活了傳統(tǒng)文化原有的生命力,強(qiáng)調(diào)了傳統(tǒng)文化精神。除此之外,網(wǎng)絡(luò)綜藝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推廣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紀(jì)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圈粉無數(shù)。
第三技術(shù)場(chǎng)景:現(xiàn)代視覺技術(shù)展示。一種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聲光技術(shù)使舞臺(tái)演出更具沖擊性,在傳統(tǒng)文化的會(huì)展和演出領(lǐng)域,運(yùn)用現(xiàn)代聲光技術(shù)可以讓藝術(shù)與科技形成共鳴;另一種表現(xiàn)為全息影像技術(shù)再現(xiàn)虛擬形象,利用聲音和光線,通過計(jì)算機(jī)編程形成不同的搭配組合,可以在舞臺(tái)生動(dòng)再現(xiàn)不存在的人和物,營造出炫麗的聲光場(chǎng)景。例如G20杭州峰會(huì),西湖上全息投影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充分展現(xiàn)了江南韻味、中國氣派、世界大同,利用數(shù)字動(dòng)畫技術(shù)再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戲曲服裝和舞蹈中人物的形態(tài)、色彩與動(dòng)作,利用沉浸式體驗(yàn)技術(shù)再現(xiàn)中國古典詩詞中描寫自然運(yùn)動(dòng)的漢字形態(tài)。
3.3 周邊產(chǎn)業(yè)拓展
根據(jù)傳統(tǒng)文化IP開發(fā)周邊產(chǎn)業(yè),宣傳群體的范圍得到了極大擴(kuò)展。傳統(tǒng)文化周邊產(chǎn)業(yè)營銷主要有兩個(gè)關(guān)鍵點(diǎn)。
第一,載體衍生創(chuàng)新。傳統(tǒng)文化IP的周邊載體形態(tài)主要分為三種類型: 漫畫、影視、游戲。從市場(chǎng)的規(guī)模角度看,中國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文化生產(chǎn)大國和游戲市場(chǎng),每年電影、電視劇、動(dòng)畫、游戲等產(chǎn)量都位于世界前列。
一方面文化IP 具有衍生性與反哺性,可以利用其他不同的資源創(chuàng)造出新的IP,并利用IP的傳播效應(yīng)完成IP改編和系列衍生。例如由經(jīng)典網(wǎng)絡(luò)IP改編的電視劇《甄嬛傳》《瑯琊榜》等作品。電影《花木蘭》《功夫熊貓》等外國影片開始融入中國元素,國際電影市場(chǎng)越來越青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作品中的展現(xiàn)。再以故宮博物院為例,它將自身打造為文化IP的同時(shí),不僅涉足視頻制作行業(yè),打造了紀(jì)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等作品,還利用移動(dòng)端開發(fā)APP 《每日故宮》,利用網(wǎng)絡(luò)購物平臺(tái)打造“故宮淘寶”,建立文化體驗(yàn)感十足的文創(chuàng)商店和古色古香的超級(jí)主題餐廳等周邊產(chǎn)業(yè),其發(fā)展模式值得我們研究、探索和借鑒。
另一方面,在快速發(fā)展的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周邊產(chǎn)業(yè)營銷的新型模式還改變了傳統(tǒng)的融資形式和商業(yè)模式,帶來了類似網(wǎng)絡(luò)眾籌這種開放互動(dòng)的融資新模式。
第二,主流品牌引領(lǐng)。雖然文化IP的熱潮不斷涌現(xiàn),但盲目跟風(fēng)、追求“快餐化”利益、隨大流低俗化的問題仍然不斷出現(xiàn),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IP的開發(fā)缺乏優(yōu)質(zhì)的內(nèi)容資源,藝術(shù)審美和社會(huì)價(jià)值觀低俗化已成為內(nèi)容生產(chǎn)模式的主要問題,傳統(tǒng)文化IP的開發(fā)與全產(chǎn)業(yè)鏈運(yùn)營不僅是為了獲利,更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加入到保護(hù)和宣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的行列之中[8]。打造傳統(tǒng)文化IP,要注重把握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核心,傳達(dá)正面積極的價(jià)值觀可以進(jìn)一步提高思想核心,凝聚文化價(jià)值。
4 跨界組合傳播模式
萬物互聯(lián)背景下,行業(yè)與行業(yè)之間、學(xué)科與學(xué)科之間的界限逐漸被打破,筆者結(jié)合對(duì)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與推廣的概念和應(yīng)用現(xiàn)狀,從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服務(wù)行業(yè)上下游、教育行業(yè)三重角度對(duì)跨界組合傳播模式進(jìn)行解析,將跨界組合傳播的主要特征總結(jié)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貫通”+“公共服務(wù)盤活”+“智媒教育助力”。
4.1 網(wǎng)絡(luò)服務(wù)貫通
跨界組合的重要方式之一為互聯(lián)網(wǎng)與傳統(tǒng)文化的組合,“互聯(lián)網(wǎng)+”的時(shí)代背景順應(yīng)了這種發(fā)展趨勢(shì),依托大數(shù)據(jù)、云計(jì)算、物聯(lián)網(wǎng)等新興技術(shù),傳統(tǒng)文化與互聯(lián)網(wǎng)服務(wù)呈現(xiàn)出脈絡(luò)貫通的發(fā)展趨勢(shì)。
4.1.1 深耕O2O+SOLOMO聯(lián)通移動(dòng)理念
O2O 是 Online To Offline,SOLOMO 是 Social、 Local、 Mobile的縮寫,強(qiáng)調(diào)社交化、本地化和移動(dòng)化。O2O+SOLOMO的聯(lián)通移動(dòng)理念強(qiáng)調(diào)利用社交網(wǎng)絡(luò)開發(fā)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線上線下服務(wù)功能和交互性個(gè)性化的社區(qū)服務(wù)功能,重新定義了傳統(tǒng)文化的服務(wù)模式、服務(wù)流程和服務(wù)方式。
微博、微信和短視頻平臺(tái)是三種最常見的基于用戶關(guān)系進(jìn)行信息共享與傳播的平臺(tái),強(qiáng)調(diào)用戶曝光率和影響力。傳統(tǒng)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也開始通過建立公眾賬號(hào)展示自身資源傳播文化理念,同時(shí)通過在新媒體平臺(tái)上發(fā)布圖片、視頻等多媒體信息,利用轉(zhuǎn)發(fā)和評(píng)論增強(qiáng)與用戶的溝通和互動(dòng),增強(qiáng)用戶粘性,構(gòu)建用戶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例如“抖音”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等開展合作,在博物館日舉辦了第一屆“文物戲精大會(huì)”,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國家圖書館通過購買、自建、聯(lián)建等方式積累了大量數(shù)字資源,針對(duì)這些數(shù)字資源進(jìn)行有效整合,搭建微博、微信、手機(jī)APP、網(wǎng)頁聯(lián)動(dòng)發(fā)展的互聯(lián)網(wǎng)服務(wù)拓展模式,開發(fā)“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數(shù)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等公眾服務(wù)賬號(hào);開發(fā)“掌上國圖APP”,實(shí)現(xiàn)書目查詢、續(xù)借、講座培訓(xùn)通知等服務(wù);利用移動(dòng)服務(wù)平臺(tái)發(fā)布專題資源,如“從莎士比亞到福爾摩斯:大英圖書館的珍寶”“圣賢的足跡,智者的啟迪,孔府珍藏文獻(xiàn)展”等。利用新媒體技術(shù)重構(gòu)傳統(tǒng)文化傳播內(nèi)核,打通文化生產(chǎn)、傳播、營銷、消費(fèi)等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可以使各領(lǐng)域有效關(guān)聯(lián),提高了產(chǎn)業(yè)鏈的整體運(yùn)行效率,例如下游的用戶渠道可利用用戶數(shù)據(jù)為生產(chǎn)公司提供數(shù)據(jù)支持。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也可聯(lián)合自媒體平臺(tái)、音樂網(wǎng)站、游戲網(wǎng)站、直播平臺(tái)等完成內(nèi)容多次分發(fā),延長傳統(tǒng)文化傳播的內(nèi)容產(chǎn)業(yè)鏈,拓展其生命周期。
4.1.2 借力云技術(shù)強(qiáng)化網(wǎng)絡(luò)設(shè)施
借助云技術(shù)強(qiáng)化網(wǎng)絡(luò)設(shè)施,特別是利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區(qū)塊鏈、5G等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文化產(chǎn)業(yè)數(shù)據(jù)互聯(lián)、可視化與智能化。以圖書館為例,依托云計(jì)算技術(shù)搭建服務(wù)平臺(tái),以云存儲(chǔ)的方式匯聚各類特色館藏資源,利用大數(shù)據(jù)、云計(jì)算、網(wǎng)絡(luò)爬蟲等技術(shù)獲取各類型、各載體數(shù)字資源,例如視頻資源、網(wǎng)絡(luò)信息資源,構(gòu)建多源異構(gòu)的數(shù)字資源體系,針對(duì)異構(gòu)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合處理,完成數(shù)據(jù)篩選,滿足用戶需求;通過云服務(wù)端、云客戶端、共享空間等結(jié)構(gòu)完成數(shù)字資源的共享共建、長期保存和高效傳輸。
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特色資源云服務(wù)平臺(tái)由IaaS層(基礎(chǔ)設(shè)施即服務(wù))、PaaS 層(平臺(tái)即服務(wù))、SaaS 層(軟件即服務(wù))三層架構(gòu)構(gòu)成,囊括了數(shù)據(jù)—系統(tǒng)—服務(wù)—用戶四個(gè)維度,實(shí)現(xiàn)了從數(shù)據(jù)采集—系統(tǒng)構(gòu)建—用戶服務(wù)的3層整合模型。IaaS層主要由云計(jì)算、云存儲(chǔ)、云緩存及云數(shù)據(jù)庫構(gòu)成,采用統(tǒng)一的元數(shù)據(jù)描述框架構(gòu)建特色資源數(shù)據(jù)池,利用唯一標(biāo)識(shí)符技術(shù)完成資源統(tǒng)一調(diào)度;PaaS層采用Web Service框架,負(fù)責(zé)對(duì)特色館藏資源的組織發(fā)布調(diào)度與管理分析,完成與其他應(yīng)用程序的關(guān)聯(lián);SaaS層以讀者和用戶為核心,是圖書館特色資源的服務(wù)門戶,通過統(tǒng)一用戶管理系統(tǒng)完成用戶實(shí)名認(rèn)證和單點(diǎn)登錄,面向不同圖書館提供標(biāo)準(zhǔn)接口,實(shí)現(xiàn)工作流的統(tǒng)一管理和調(diào)度。
4.2 公共服務(wù)盤活
伴隨供給側(cè)改革,傳統(tǒng)的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與出版發(fā)行行業(yè)、資源供應(yīng)行業(yè)等文化服務(wù)的上下游開始出現(xiàn)全盤激活、深度融合的服務(wù)趨勢(shì)。
4.2.1 公共文化服務(wù)整合升級(jí)
公共文化服務(wù)整合升級(jí)以公共數(shù)字文化融合工程為代表,公共數(shù)字文化融合工程是“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服務(wù)”的時(shí)代背景下提出的創(chuàng)新性工程,在資源、平臺(tái)、移動(dòng)服務(wù)、業(yè)態(tài)合作與機(jī)制創(chuàng)新等方面完成一站式的公共文化數(shù)字資源的整合,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平臺(tái)、統(tǒng)一界面、統(tǒng)一目錄、統(tǒng)一培訓(xùn)、統(tǒng)一推廣。在資源建設(shè)方面,梳理公共數(shù)字文化資源服務(wù)總目錄,推出“全民閱讀”“藝術(shù)普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準(zhǔn)扶貧”等專題內(nèi)容。在用戶層面,推出專題門戶網(wǎng)站,即“國家數(shù)字文化網(wǎng)”和“兩微一端”移動(dòng)應(yīng)用平臺(tái),聯(lián)合各地市圖書館建設(shè)“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以公共數(shù)字文化云為基礎(chǔ)形成“一網(wǎng)兩館”的平臺(tái)格局,針對(duì)基層服務(wù)的實(shí)際應(yīng)用場(chǎng)景和傳輸網(wǎng)絡(luò),設(shè)置專門的應(yīng)用客戶端。在文化推廣方面,開發(fā)專題品牌,以“美好生活”為重點(diǎn)發(fā)布文化服務(wù)目錄,利用公共文化大數(shù)據(jù)平臺(tái)整合用戶數(shù)據(jù)、資源數(shù)據(jù)、服務(wù)數(shù)據(jù),完成統(tǒng)一的采集、存儲(chǔ)、分析與展示。
4.2.2 聯(lián)動(dòng)下游服務(wù)行業(yè)創(chuàng)新亮點(diǎn)
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出版發(fā)行行業(yè)、信息服務(wù)行業(yè)、資源供應(yīng)行業(yè)同屬于文化服務(wù)行業(yè)的上下游,跨界組合傳播模式的出現(xiàn)需要相關(guān)主體盤活彼此資源,實(shí)現(xiàn)共贏。聯(lián)動(dòng)下游服務(wù)的具體實(shí)現(xiàn)方式主要包括兩點(diǎn):一是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與書店、出版社、數(shù)據(jù)庫商進(jìn)行跨界合作;二是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與其他行業(yè)下游產(chǎn)業(yè)如商場(chǎng)、交通運(yùn)輸、電子商務(wù)、酒店等機(jī)構(gòu)共同致力于閱讀空間和文化氛圍的營造。
國內(nèi)典型案例有內(nèi)蒙古圖書館與新華書店合作的“彩云服務(wù)”,通過搭建云平臺(tái),整合圖書館與新華書店機(jī)構(gòu)的圖書資源,利用服務(wù)終端直接為圖書館讀者和購書者提供借閱服務(wù);浙江圖書館的“U書快借”服務(wù)采用“你選書,我買單”的方式,利用浙江圖書館的借書證直接實(shí)現(xiàn)圖書采購;圖書館與其他行業(yè)的下游產(chǎn)業(yè)合作如國家圖書館與京港地鐵合作的公益項(xiàng)目“M·地鐵圖書館”,通過設(shè)立站內(nèi)圖書館,打造圖書專列主題車站,開展圖書漂流活動(dòng)等形式,為公眾提供免費(fèi)電子圖書在線閱覽,方便讀者利用碎片化的出行時(shí)間感受閱讀魅力。
4.3 智媒教育助力
科技與教學(xué)法的深度變革整合了科技與教育相融合的學(xué)習(xí)新形態(tài),出現(xiàn)了包括泛在學(xué)習(xí)、定制學(xué)習(xí)、混合學(xué)習(xí)、沉浸式學(xué)習(xí)、社群學(xué)習(xí)等多種形式的學(xué)習(xí)體驗(yàn)?zāi)J剑瑢W(xué)習(xí)時(shí)空由單向走向多維,學(xué)習(xí)體驗(yàn)由集體學(xué)習(xí)變?yōu)樽灾鲗W(xué)習(xí),智慧教學(xué)與新興技術(shù)深度融合。隨著泛在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化移動(dòng)化技術(shù)的進(jìn)步,智媒教育與傳統(tǒng)文化逐步走向深度融合,新的學(xué)習(xí)形態(tài)呈現(xiàn)出內(nèi)容活化、課程多元、終端多樣、個(gè)性定制等特點(diǎn),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教學(xué)軟件、教學(xué)終端、公眾號(hào)、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手機(jī)APP、多媒體教室等形式打造“空中教室”,利用智能終端使教學(xué)內(nèi)容擺脫空間與時(shí)間限制。
5 創(chuàng)新用戶體驗(yàn)?zāi)J?/h2>
傳統(tǒng)文化傳承與推廣的最終落腳點(diǎn)是用戶的心理感知,用戶心理感知主要包括三個(gè)方面:娛樂感知、美學(xué)感知和情感感知,筆者結(jié)合用戶心理感知的三個(gè)維度,將新型用戶體驗(yàn)消費(fèi)的發(fā)展趨勢(shì)總結(jié)為:“文創(chuàng)賦能”+“體驗(yàn)營銷”+“文旅融合”。
5.1 文創(chuàng)賦能
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以內(nèi)容為內(nèi)核,通過發(fā)揮創(chuàng)意力完成內(nèi)容設(shè)計(jì)。伴隨體驗(yàn)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到來,消費(fèi)者對(duì)文化產(chǎn)品中的審美價(jià)值和情感需求大大超過了其對(duì)產(chǎn)品本身的功能需求,隨著我國主流消費(fèi)向中產(chǎn)階級(jí)的過渡,文化產(chǎn)品中是否包含充分的文化內(nèi)涵,背后是否有動(dòng)人的故事設(shè)計(jì)都成為了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競(jìng)爭(zhēng)的關(guān)鍵,而美感、情感和娛樂感成為了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三大核心要素。
伴隨AI時(shí)代的到來,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也開始向智能化的方向轉(zhuǎn)變,新技術(shù)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帶來了新的科技附加值,其重要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三大領(lǐng)域:
自動(dòng)內(nèi)容敘事。利用人工智能完成智能語音識(shí)別和自動(dòng)內(nèi)容制作,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谷歌從2001年就開始研究機(jī)器人新聞,2015年騰訊推出了自動(dòng)寫稿機(jī)器人,之后新華社推出了“快筆小新”寫稿機(jī)器人,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海量新聞的篩選、寫稿校對(duì)等方面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影視娛樂領(lǐng)域,新技術(shù)也充分運(yùn)用在了電影、電視劇等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制作中,例如美國迪士尼和皮克斯公司充分運(yùn)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自動(dòng)生成動(dòng)畫圖像、提高畫面分辨率、評(píng)估劇本,好萊塢制片人用AI算法預(yù)測(cè)票房。
衍生產(chǎn)品創(chuàng)新。故宮博物院運(yùn)用新科技保護(hù)、監(jiān)測(cè)、展示故宮的文化遺產(chǎn),通過場(chǎng)景體驗(yàn)的形式連接更多博物館受眾;開發(fā)故宮娃娃、彩妝、包袋、服飾、辦公用品等文創(chuàng)衍生品;利用微信小程序、抖音、手機(jī)APP等社交媒體推出“《胤禛美人圖》”“皇帝的一天”等游戲設(shè)計(jì);與影視行業(yè)合作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等紀(jì)錄片與綜藝節(jié)目;與時(shí)尚界、美食界、游戲界聯(lián)合推出了“上元燈夜活動(dòng)”“稻香村聯(lián)合糕點(diǎn)禮盒”“故宮口紅”等產(chǎn)品,體現(xiàn)故宮品牌的親和力和科技感。
精準(zhǔn)用戶畫像。人工智能技術(shù)通過個(gè)性化的推薦和精準(zhǔn)匹配完成用戶畫像。News Republic、Instant Article等媒體都開始應(yīng)用用戶畫像方式分析用戶閱讀習(xí)慣,基于用戶興趣模型為用戶定點(diǎn)推送相關(guān)內(nèi)容。
5.2 體驗(yàn)營銷
體驗(yàn)營銷是近幾年新興的文化娛樂形式,強(qiáng)調(diào)消費(fèi)者的體驗(yàn)價(jià)值,其典型代表為沉浸式體驗(yàn),即通過建立虛擬現(xiàn)實(shí)、增強(qiáng)現(xiàn)實(shí)、混合現(xiàn)實(shí)等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在虛擬世界中營造一種視覺新形態(tài),注重身臨其境的真實(shí)體驗(yàn),為參與者提供無限接近現(xiàn)實(shí)情境的虛擬環(huán)境,以保證其全新的體感參與。
體驗(yàn)營銷以影像聲音為主要元素滿足消費(fèi)群體的日常生活審美,注重五官感受和體感參與,主要形式包括虛擬仿真、虛擬社區(qū)、虛擬現(xiàn)實(shí)角色扮演等形式。例如應(yīng)用逼真的三維虛擬場(chǎng)景增強(qiáng)參與者與作品之間的互動(dòng)性,滿足了觀眾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感知,讓觀眾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有了深刻理解,典型代表是“科技+文化”沉浸式的藝術(shù)展覽,迪士尼、環(huán)球影城以電影IP為原型,充分運(yùn)用全息投影完成相關(guān)的情境設(shè)定和藝術(shù)展覽,讓虛幻的場(chǎng)景得以具象化。
體驗(yàn)營銷中的民族文化認(rèn)同以講故事為核心,不僅讓受眾理解到傳統(tǒng)文化的知識(shí)內(nèi)容,更讓受眾自覺地帶入認(rèn)同感,在產(chǎn)生情感共鳴的同時(shí),理解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核心和精髓,例如數(shù)字動(dòng)畫《乾隆南巡圖》用立體互動(dòng)的模式再現(xiàn)了乾隆盛世的輝煌,人們可以通過三維數(shù)字動(dòng)畫感受到乾隆南巡時(shí)儀仗的威武和清朝市井百姓的生活狀態(tài)。
5.3 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的主要路徑是將傳統(tǒng)文化思想融入到旅游產(chǎn)品研發(fā)環(huán)節(jié)中,其主要形式包括四類:民俗旅游類項(xiàng)目推介本地歷史文化資源;節(jié)慶活動(dòng)普及傳統(tǒng)文化知識(shí)與形象;自主創(chuàng)新產(chǎn)品迎合現(xiàn)代消費(fèi)觀與價(jià)值觀;利用影視業(yè)、媒體業(yè)促進(jìn)旅游效益提升[9]。傳統(tǒng)文化+旅游也開始呈現(xiàn)新的創(chuàng)意特點(diǎn):
定制化。從跟團(tuán)游到自由行,再到定制旅游,人工智能與旅游的深度融合標(biāo)志著旅游業(yè)進(jìn)入3.0時(shí)代:通過大數(shù)據(jù)分析并充分了解用戶的消費(fèi)習(xí)慣、餐飲偏好和興趣愛好,以旅游者需求為導(dǎo)向,例如考慮出行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是否符合旅行期待和錯(cuò)峰出行要求;通過智能分析為游客提供更細(xì)化的服務(wù)提示和接收智能反饋。
情感娛樂化。旅游企業(yè)及相關(guān)部門借助電視、網(wǎng)絡(luò)媒體、電臺(tái)、報(bào)紙等多種宣傳媒介針對(duì)旅游地文化特色進(jìn)行宣傳[10],例如杭州宋城的《傳奇世界》主題公園,將鐵匠鋪、藥店、雜貨鋪等真實(shí)再現(xiàn),邀請(qǐng)表演人員進(jìn)行專業(yè)表演,讓整個(gè)公園處處都體現(xiàn)出了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
生活美學(xué)化。生活美學(xué)化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一大趨勢(shì),特別是年輕人群體在進(jìn)行日常消費(fèi)時(shí),不僅看重旅游的娛樂價(jià)值,更看重旅游的文化價(jià)值。過慣了高樓林立的城市生活,就向往綠水青山、沃野田園的休閑旅游方式,鄉(xiāng)村旅游與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可以形成特色產(chǎn)業(yè),強(qiáng)化旅游者的感性認(rèn)識(shí),例如端午節(jié)的祭祀、詩會(huì)、龍舟賽、茶園茶藝文化游等[10]。
6 總結(jié)與發(fā)展思考
在四個(gè)模式類型中,建設(shè)主體、內(nèi)容種類、傳播渠道、服務(wù)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相融合的關(guān)系。從整體看,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呈現(xiàn)四個(gè)重要特征:
一是從單向融合到滲透交叉融合。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新技術(shù)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目前新技術(shù)與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已進(jìn)入融合轉(zhuǎn)型期,單向度、淺層次的融合已不能解決傳統(tǒng)文化的生存問題,多層次的融合開始出現(xiàn),呈現(xiàn)出全新的融合特點(diǎn)。多層次的融合可以幫助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文化基因的基礎(chǔ)上更廣泛地吸收世界多元文明和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時(shí)代技術(shù)。
二是從協(xié)同發(fā)展到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主要強(qiáng)調(diào)兩方面的特性,第一是互動(dòng)性,第二是虛擬性。思維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在體制領(lǐng)域則為文化體制的根本性改革。
三是從要素兼顧到路徑落地。傳統(tǒng)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是科技要素與傳統(tǒng)文化要素相互集聚與互動(dòng)發(fā)展的過程。集聚的過程是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演進(jìn)過程,最終依然要落實(shí)到實(shí)踐的結(jié)果上。實(shí)踐層面的路徑落地,主要借助公共數(shù)字文化服務(wù)體系和文化產(chǎn)業(yè)的協(xié)同發(fā)展,兩者共同助力數(shù)字中國文化建設(shè)。
四是從民族自信到全球視野。首先是要考慮世界科技發(fā)展的背景與中國科技強(qiáng)國戰(zhàn)略的彼此融合,在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的時(shí)代背景之下,統(tǒng)籌考慮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信息技術(shù)的全球化;其次是在中華文化自信的基礎(chǔ)上重構(gòu)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兼具革命文化、社會(huì)主義先進(jìn)文化等文化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