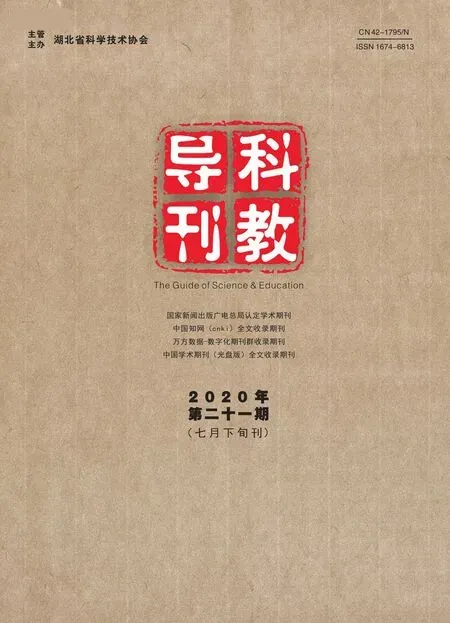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中的意義及有效實踐
羅 艷 姜海婷
([1]南京醫科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 江蘇·南京 211166;[2]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 江蘇·南京 211166)
在醫患溝通研究框架下,醫學生語言能力問題漸開始受到關注,但相關成果還很少,研究范圍也僅局限于如下向度——對醫學生語言能力狀況的調查、討論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的重要性以及探索可能的路徑方法,每個向度的研究都還不充分。
所有關于培養路徑的探討中,一個十分有價值的領域還未被關注,即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中的重要意義及實踐。這是本文將專門研討的主題。
1 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中的重要意義
應該說,一切的經典文化學習,對語言能力的提升都是有意義的。而中華經典文化,對提升醫學生語言能力的好處,從普遍意義上說,是跳過了翻譯的限制和文化的隔膜,更親切和直接,更容易受益。酈波先生在《詩酒趁年華》這本書的序言里說過,“只要是中國人,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基因,那就是對母語文化的天然擅長。”[1]
而從醫學生所需具備的語言能力的特殊性來說,中華經典文化更是資源豐富的寶礦,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
1.1 有益于培養形象生動的語言傳達能力
醫學專業知識和術語,對于普通病患來說往往是抽象的,醫患溝通時,醫生若能將專業的醫學內涵形象生動地傳達給病人,可以讓病人更好地了解病情,加強配合,減少不必要的誤解、焦慮甚至摩擦。因此,形象生動的語言傳達能力,對于醫學生來說很重要。
善于形象闡釋抽象概念、思想和情感,是中華經典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無論是先秦諸子的哲思,還是唐詩宋詞、散文小說的情懷,以形象化手法來呈現,都是優秀作品不可或缺的特質之一。
比如,僅用“五千言”傳達宇宙哲思的《老子》,因善于用喻,寥寥數語便能讓深奧的義理變得形象可感。習總書記引用過其中的名句——“治大國,若烹小鮮”,[2]治大國所需的觀微謹慎,普通人如何能深刻體會,但烹小鮮時需細致掌控火候的情境,卻人人可感,國家治理之道與日常烹飪聯系起來,抽象道理立刻變為具體可感的形象情境,讓人豁然明朗。翻開先秦諸子經典,孔孟、老莊、墨子、韓非等等,把抽象內涵變得形象、生動、具體,是共有的出色筆法,《莊子》不僅用喻突出,還善用故事做比、善用形象傳神的詞語來呈現,在形象化表述方面可謂登峰造極。
用喻、用生活情境和具體意象來表達復雜情思,也是唐詩宋詞常見的修辭。精妙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3]就活用了生活中常見的具象,傳神表達了一種深沉、復雜、含蓄、幽微的情思——至死不渝的愛,無窮無盡的思念、別恨,對理想、事業、情懷等堅定執著的追求……都可從中找到形象生動的注解。
唐宋以來的散文,有追求“文以載道”的傳統,道與理也是抽象的,如何讓說道說理變得明達,形象化修辭也必不可少。比如,凸顯論說功力的《張中丞傳后敘》,韓愈在一片圍攻中為許遠辯駁時,以“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4]十分形象地類比了當時的局勢和許遠的處境,有力地說明了敗局的無可挽回與罪責的無辜。
此外,中國古代經典小說,無論短篇還是長篇,《三言二拍》、《聊齋志異》,還是《西游記》《紅樓夢》,形象生動的修辭,都是突出的筆法。
對于醫學生來說,中華經典文化是培養形象化語言能力的資源豐厚的寶庫,若能用心精選佳篇,引導他們欣賞、感悟、學習,對提升形象生動的語言傳達能力,會有很大的助益。
1.2 有益于培養共情的語言表達能力
醫生在與患者溝通時,如何用恰當的言語鼓勵患者說明病情、說出內心的疑問和潛在的焦慮,并用言語有效地撫慰患者,如何在與患者發生誤會甚至矛盾沖突時,敏銳捕捉到問題所在,及時用恰當的語言應對和化解,都特別考驗醫生是否具備能夠共情的語言表達能力。
共情的語言表達能力,與情商和語言文化的有效積累都密切相關,而中華經典文化是培育這些素養的豐饒沃土。五千年從未間斷的中華文明,積淀了高度的人情智慧和經驗,無論是觀照人世的哲學,評鑒過往的史學,還是表達情思的文學,都卓絕于世,為共情能力和恰當表達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太多的經典范本。
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中國哲學主流——儒家,其核心思想是“仁”,從解字上看,一邊為單人旁,一邊為“二”,寓意“二人一體”而為“仁”,字結構本身的意蘊,就特別強調交互性、一體性,強調相互的關照、尊重和愛,而儒家對“仁”的諸多延伸闡釋,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6]等,也特別強調對自我和他人的同時關照,以及相互的體諒與成就。精讀與“仁”內涵相關的經典篇章,可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地提升醫學生的共情能力和恰當表達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經典文化有一個特質,就是文學、哲學、史學相交融。哲學和史學經典,往往是文學的經典;文學經典,又常常透著深刻的哲學思悟和歷史觀照。因此,精選中華文史哲的經典篇章來教學,常可以在提升心靈觀照能力和語言能力上,事半功倍。
1.3 有益于培養簡練的語言傳達能力
對于“簡練”,現代作家中語言功夫堪為翹楚的老舍先生,曾有過明晰闡釋——“簡練不是簡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邏輯性強不強,準確不準確。只有邏輯性強而又簡單的語言,才是真正的簡練。”[7]從這個意義上說,簡練的語言傳達能力,恰是醫患溝通中,醫生所需具備的。病人的病征病情等,往往綜合了多重信息,在有限的問診交流時間中,如何盡可能滿足病人需求、圓滿表達,就特別需要具有化繁為簡的語言表達能力。
簡練,也是中華經典文化在語言表達上的一個重要特征,言簡意賅,字字金石,沒有連篇累牘的贅述。老舍先生在談到如何培養簡練的語言表達能力時,曾指出:“古代書本上的語言,即使自己不學著寫,也應該看看。這有好處,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怎樣才能夠寫得簡練。古文古詩有個好處,真簡練……我們的語言在世界上是以簡練著稱的。”[8]精選中華經典文化范本研讀,對于培養醫學生簡練的語言表達能力,大有裨益。
綜上,中華經典文化對提升醫學生所需具備的語言能力,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與中小學階段的語文基礎教育不同,醫學院校相關內涵的教學應較為系統、有針對性,向更高境界和層次引導,這不僅需要教師精心遴選篇目、用心圍繞主旨來設計教學,在實踐上不斷研究探索,更需要學校相關層面的重視和大力支持。
2 以有效的實踐,實現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上的意義
2.1 善于依托及整合資源,創建優質教學內涵和方案
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上價值意義的實現,是一個較新的探索,沒有現成的路徑可復制,甚至要從空白中披荊斬棘地開拓和建設。醫學院校尤其是西醫性質的院校,相對于高水平綜合性大學來說,文科資源有著不可避免的差距,古典文化教研力量的不足更是突出。因此,靠單個醫學院校,創建優質教學內涵,實現良好的教學目標,是比較困難的。
向高水平綜合性大學的專家資源借力,同時醫學院校之間的相應資源形成聯合,共同研究和探索針對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的中華經典文化教學,集眾智慧、遴選內涵、設計方案,尤為重要。
2.2 重視最有效教學形式,探索多元化途徑配合
醫學生專業學習任務繁重,留給語言能力培養的教學空間十分有限,需要努力構建高效合理的培養模式。
必修課在成績中權重較高,不僅要求較嚴,對學生各類評獎也有較大影響,是最能保證學習態度和效果的教學形式。因此,與語言能力培養相關的中華經典文化教學,十分需要必修課的教學形式,同時基于語言能力培養是一個長期積淀的過程,還需配足課時、保證時長,才能達成良好的教學效果。
不過現實中,無論怎樣,醫學院校對這類課程的必修課安排,空間畢竟有限,而語言能力培養又是無法一蹴而就的,因此,還應探索更多途徑,來豐富和完善相關教學,更充分發揮中華經典文化在醫學生語言能力培養中的價值意義。比如:積極創建與課程相聯的網絡課程,拓展教學的寬度和深度;努力提供充足的選修課資源,延伸語言能力的培養;大力探索在課外實踐中,與學工部門或學生社團聯合,打造以語言能力提升為導向的中華經典文化精品活動等等。
2.3 適當依托中華經典文化與醫藥學的關聯,提升醫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親近感
對于專業學習任務很重的醫學生來說,學習專業知識以外的內容,除了需要意識到重要性、必要性,還要有一定的興趣支撐,才能更好地參與其中,更好地受益。中華經典文化相關的課內教學和課外活動,可以考慮一些與醫藥相關聯的內涵設計,來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親近感。
比如:“有人做過統計,《詩經》全書提到的各類病名有十五種,涉及的藥用植物多達二百多種。”[9]《詩經》,既是儒家經典又是重要文學經典,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10]大意是不學《詩經》,就不知道怎么去言談表達,我們完全可以遴選《詩經》中涉及醫藥內涵的篇目,來進行與語言能力培養相關的教學。實際上,不只是《詩經》,“幾乎古典文學的各類體裁都有涉及中醫藥的作品,反過來,中醫藥的各類知識包括醫理、臨床疾病診療、方藥,乃至針灸、養生、醫史人物事件等,也都在古典文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11]為我們的相關教學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
更便利的是,其實不少專門梳理相關內容的優秀成果已經問世。比如,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過一套中華文化與中醫學叢書,《古典文學與中醫學》分冊,以文學體裁做分類,呈現了很多有趣的古典文學與中醫學相聯的實例,這套叢書還另有三冊,分別從中國儒釋道哲學內涵出發,研究了與中醫學的關聯。而陜西中醫學院的炎繼明先生,更是潛心編著了厚厚四大本——《中國古典詩歌與中醫藥文化》叢書,詳實列舉了從先秦至唐歷時千年、與中醫藥文化有關聯的詩歌,涵蓋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等諸多名家名作,更有詳細的注釋、譯文和醫理解析。
我們可以從如上這些優秀成果中,獲得很多有價值的參考和啟示,在相關教學和課外實踐活動中,依托中華經典文化與醫藥學的豐富關聯,提升醫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親近感。
語言能力的培養需要長期的熏陶和浸潤,醫學院校應努力探索適合有效的教學內涵和方案,來持續、甚至深化和強化醫學生語言能力的培養,這樣,他們在進入職業角色后,才不至于在語言交流上突感無力和局促,才能更好地化解醫患之間的種種溝通障礙。而在相關教育探索過程中,中華經典文化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向度和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