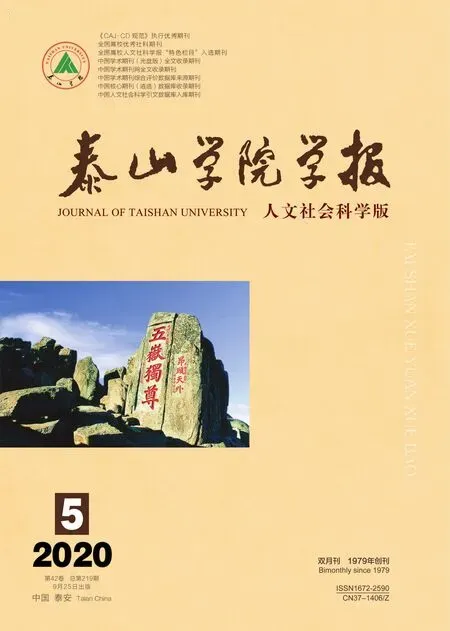肥城元代兩篇先塋碑文考釋
梁圣軍
(肥城市左丘明研究院,山東 肥城 271600)
記錄家族世系的石上族譜是產生于金代的一類碑志文,與此前出現的家廟、神道等碑志不同,其建立的主體是中下級官員家族。元代將這種新式碑文稱為新塋碑或先塋碑,元朝濟南人潘昂霄有評:“先塋、先德、昭先等碑例,似與神道碑、墓志碑不同。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創業于國朝,已前唐、宋、金皆無之。”[1]可視為時人對先塋碑看法的代表。
蒙古統治下的新興官員家族廣泛認為,先塋碑或新塋碑是一種正式的銘葬和修譜方式,是特殊背景下新興的志墓作品,具有尊祖收族的作用。各大家族利用石刻記錄宗族世系,使立碑具有與編纂家譜一樣的社會功能。先塋碑記反映了元代軍功家族以始遷祖為始祖的宗族逐步形成的過程,其在北方出現并迅速普及,與蒙古征服所引起的社會、文化變動有很密切的關系。先塋碑詳細紀錄家族世系、仕宦經歷,形成了表彰功勛與記錄族譜兩類功用并行的局面,其撰寫方式反映出修撰者期望以碑記明確家族世系、褒揚前代德業以凝聚家族共屬意識的目的。后來元朝廷也開始把先塋碑賜給功臣家族,如1348年《康里氏先塋碑》。[2]元代滅亡后,先塋碑這一形式也開始衰落。
據日本學者飯山知保統計,目前已知的元代先塋碑超過250通,但此統計數據并不完全包括山東肥城及其周圍縣市。肥城及其周圍地區先塋碑眾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元代兩篇先塋碑未見其它史載,對于研究宗族史和地方史有很大價值,本文試對其進行考釋和評價。
一、肥城及其周圍地區先塋碑略舉
肥城及周圍地區從廣義上講,指泰山前汶水北汶陽一帶,此地有很多元朝時軍功家族先塋碑,在此略舉如下:
1.肥城劉海碑。①劉海,其傳見《肥城縣志》。該碑位于肥城市西北部,碑額一面為豎排兩行正書“宗派之圖”,另一面為豎排兩行篆字“故都統劉公墓志銘”。該碑由“奉訓大夫、孟州知州前集賢待制楊遇撰并篆額,承事郎、前濟寧路肥城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兼勸農事段繼祖書丹”;“大德二年(1298)十二月望日,孫昭信校尉、后衛親軍千戶淙,男昭信校尉、后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都鎮撫,改授本衛千戶致仕源立。”
2.泰安先塋碑。禹氏先塋碑一通,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三)載,宋朝石氏先塋之外,有禹氏先塋,在山口南三里余;時氏先塋碑,在縣東南時家莊前;趙君先塋碑,縣西南七十里南仇莊。趙君即趙榮,武略將軍,子趙暄蔭補北仇寨巡檢、縣尉、縣令,大德五年(1301)翁仲森立碑,另據肥城《邊院鎮志》載:“趙君先塋,王家堂村東半里許。”
3.石氏先塋碑。《重修泰安縣志》(卷十四)《藝文志·金石》載:“《石氏先塋碑》,至大元年(1308)乙卯月仇進善撰篆額并書。按碑乃石顯為其父皋立。皋墓在高腴地方古佛寺西北,距汶水數百武,碑斯在焉。石門華表巋然猶存。略稱金季盜為民害,皋仗劍歸于東平嚴侯,侯親任之,命主由西徐寨,及元欲收威炳,皋當受命于朝,自憫衰老,退以壽終。顯后遂繁衍。”另有埠上道士張志純,1288年前請杜仁杰撰寫的《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4.東平先塋碑。陳氏先塋碑,見王旭《蘭軒集》(卷一四)載至元二十七年(1290)東平《陳氏阡表記》;祁氏先塋碑,見民國版《東平縣志·金石志》載金祁氏新建塋域記;元東平韓氏先塋碑銘(在周家營);另有元《故武略將軍汶上縣尹侯君神道碑》。
5.平陰先塋碑。解氏先塋碑,見康熙《平陰縣志》(卷八)《碑記》,有《元征行水軍萬戶解侯賈珎墓志銘》。解賈珎,徐解村人,累世為農,元朝滅亡南宋時成為戰將。至元七年(1270)六月帥敢死隊從主戰伐,八年破鼓城,九年破樊城重傷,十一年從解萬戶,十二年三月大戰岳陽樓,十二月戰潭城。為蒙古征宋立下戰功,前后賞賜中統寶鈔甚多。劉氏先塋碑,見平陰縣玫瑰鄉焦莊村西劉氏新塋坊,刻寫“劉氏新塋”四字,立柱上刻有“前福建閩海提刑、元大德十年(1306)”等字樣,現剝蝕難以辨認。
6.寧陽先塋碑。劉氏先塋摩崖石刻,位于葛石鎮陳家店村西北、告山蟠龍嶺西部山南,刻字上下排列,“劉氏先塋”左下方有“元首伍年十二月”7個字①按“元首”當為“元狩”,即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可能是最早的先塋題刻[3];圍子里劉氏先塋碑,位于東疏鎮圍子里村西北1500米,封土早年被夷平,地表僅存劉氏先塋記碑一通,立于后至元四年(1338)十月一日,碑陽額題篆書“劉氏先塋之記”[4],由東平進士郭謙撰文書丹并篆額,碑陰額題“宗祖之圖”4字,下為劉氏族譜。碑文記述了劉氏宗族興衰及重修先塋等事宜;董氏先塋之碑,位于微山縣兩城鄉北薄村內,為大德四年(1300)立。
肥城及其周圍先塋碑的撰立時間集中在1290至1320年間,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金末山東人面對板蕩之世,心中已不存忠于哪個朝廷的觀念。金朝、蒙古均為外來民族,宋朝南下腐朽不堪,故而順應潮流、保民衛家是時人的選擇。漢族軍功階層為蒙元滅亡金國和南宋立下汗馬功勞,但逐漸威脅到蒙古貴族的利益,故而至元末年“元欲收威炳”。為削弱世襲漢族上層階級的影響,當時的朝廷規定不準為個人樹碑立傳,《通制條格·雜令·立碑》就載“至元二十九年(1892)三月,中書省御史臺呈:……據見任官不應立碑,并犯貪污已立碑者,合行除毀。都省議得:今后職官在任,雖有政績,不許立碑。其先已建立者,若犯貪污,即令除毀。違者究治。”同時對民間墓葬、家廟祭祀、神主、民房和碑刻有嚴格規定。《元史·刑法志·禁令》載:不能做墓地祠堂。“諸職官居見任,雖有善政,不許立碑,已立而犯贓污者毀之,無治狀以虛譽立碑者毀之。”在此政令下,地方豪強勢力便通過為祖先立碑,間接為個人顯功揚名。
二、肥城譜牒中元代兩篇先塋碑文考釋
碑銘可以補充、豐富歷史文獻,碑銘文獻蘊含的歷史演變具有特別的意義。肥城先塋碑是時代的產物,是特定社會環境內的文化反映,其中肥城《姬氏志》所載的《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銘》和《武氏族譜》所載的《奉符武君先塋之碑》為研究肥城地方歷史和元朝的社會生活、軍事戰爭提供了一手文獻,在此特別予以考釋。
(一)王載《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考釋
山東姬氏為周公后裔,金朝時其中姬仁一支居山東汶上姬家溝(今中都街道姬溝村)。周公七十代裔姬成,在至元初為本邑典庾出納,合郡皆稱廉平,曾修訂族譜《姬氏志》。姬成三子,長子姬聚、次子姬順、三子姬顯。在中統元年(1260)到至元八年(1271)間,姬顯隨兄長入住肥城縣城。姬聚為控鶴(禁衛軍),官至肥城縣尉,姬顯及其女婿繼為控鶴。姬姓后裔定居肥城東程村繁衍生息,子孫眾多,分支陸續遷至肥城境內外各地,東程村成為部分遷出人員心中的祖居地,存有姬姓家譜。老譜見有光緒九年(1883)續修六冊《姬氏志》、民國二十四年(1935)續修八冊《姬氏志》(《姬氏家志》)。新譜有1989年續修的十冊共三套《姬氏志》,2016年姬勇主筆重修三卷,定名《肥城姬姓家譜》。汶上姬氏另有1961年石印的姬氏志《汶上縣姬氏家譜》一卷、1988年編修的《續修姬氏志》即《續修姬氏族譜》、1990年的排印本《姬氏志》以及2018年新修的《姬氏志》20卷。
光緒九年(1883)續修《姬氏志》抄錄了王思誠、孔聞詩、黏本盛等人的舊版家譜,由汪寶樹、孫毓汶等人作序,內容包括自序、歷朝各代的舊序、禁例、姓源、德業、封號、頌、古跡、詩文,甚至包括祭祀《器物考》以及拜祭先祖的詳盡步驟,是研究周公及后裔的難得史料,后來的重修本都沿續錄下這些重要內容。《姬氏志》光緒卷五、民國卷九所載的《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銘》由元朝碑文全文抄錄,原抄錄者和抄錄時間已不可考,其原碑石已無存。該碑銘文章未見于歷代地方志和金石書目,也不見載于《全元文》,對研究元朝的政治、軍事、文化、地方社會和家族變遷具有重要價值。全文照錄并加標點如下:
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銘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翰林院編修、授承事郎濟寧路肥城縣尹兼營奧魯勸農事王載撰
肥城縣儒學直學張進善書并題額
洪范五福,言富而不言貴。蓋富能潤屋,充實于中者也;貴能榮身,芬華于外者也。況富貴于人,天之所靳。二者固不能兼有,則富貴亦豈人之所易得哉。余觀所謂富貴者,惟汶陽姬氏先代其似之。
按姬姓本出于周公,后譜系未沒。確有可考祖仁,家于汶上。明經術,習詞章,嘗領鄉薦,為貢士。邦人榮之,皆謂之姬貢元家。至金源氏時,其族藩衍,金昆玉季百有二十余輩。膏腴之田,千頃有寄。一門之間,衣冠濟濟,華萼相輝,塤篪伯仲,名著桑梓。春秋展省,歲時宴集,尊卑長幼禮儀相先。齊魯之邦,孰不景慕?殆金源南遷,公帑赤立,乃括富民錢以犒軍士。是家車運當五錢以充國用,為兩凡二十五。見者聞者,咸欽慕焉。后值亂離,其曾大夫輩行,僅存十數。用是蕩析,或居羅家寨,或居付村,或居任都,或寓青山,或寓李村,或寓胡氏庵,或寓第三牌性。祖孝弟忠信,安處鄉枌,勤儉治生,服務田畝。以壽終于乙丑之歲(1265)。祖妣張氏,紡績織纴,昕夕不怠。沒于歲之壬辰(1292)。父成,明敏篤實,材力有余,至元初,為本邑典庾出納,惟公母付氏,辛勤起家,見亨生祿,俱七旬有八。男孫三人。伯聚,仲順,叔顯。聚以忠力,至元八年(1271)選充控鶴。既食其祿,仍復其家。屢蒙賜賚金帛楮幣。后敕授海漕部綱副千戶,從宣慰阿八赤開通膠河,督造運艦。遂授中書省札,為盤(般)陽路淄川縣冶頭店巡檢。調濟寧路肥城縣尉,蔚有能聲。仲順家居奉親。叔顯繼為控鶴,殞于二十五年(1288)之九月。贅婿馮貴襲其職。亦俱蒙天寵,賜予良多。由此觀之,可謂榮矣。
故嘗謂汶陽姬氏,元公苗裔也。昔也如彼其貴而富,今也如此其富而貴。則姬氏慶門,福澤未艾,蓋可知已。余以歲庚子(1300)叼令肥城,君乃狀其先世行實,及其譜系,來征鄙文,刻之堅珉,以光泉壤。義在同寅,故不敢辭。乃為之序次其事,而繼之以銘。銘曰:
于惟姬氏,汶上族居。祖榮鄉貢,宗支百余。
上腴之田,頃以千數。輸財助國,錢皆當五。
富而能訓,玉季金昆。詩書禮義,人稱慶門。
其后亂離,析居田里。惟祖諱義,不忘桑梓。
孝弟信忠,名譽著聞。處家以儉,治生以勤。
有子傳芳,典司庾計。有孫扈從,茲焉為尉。
奉先進孝,勒石汶陽。松柏青青,泉扃有光。
大德五年(1301)二月十四日,曾孫男濟寧路肥城縣尉姬聚立石。
姬聚立碑,主要是祭祀祖先,也是自我標榜與表達。碑文中所記金元之際人物與史事,多可與正史相印證。如文中載錄一條重要食貨資料:“殆金源南遷,公帑赤立,乃括富民錢以犒軍士。是家車運當五錢以充國用,為兩(通輛)凡二十五。”反映了金朝晚期在對蒙古戰爭時財政窘迫,采取了搜刮民間的措施。姬氏作為富戶,被迫獻進犒軍,運送25輛車的當五錢充國用。當五錢亦稱折五錢,指一枚值五文,就是折合五個平錢使用的錢,最早出現的當五錢是北宋神宗年間的熙寧通寶。金朝的錢幣曾效仿遼朝,實行五等錢制。據《錢潛》記載,金朝衛紹王崇慶年間(1212)曾鑄有崇慶元寶篆書當五大錢,至寧元年(1213)鑄至寧元寶錢真書折五錢。[5]金章宗時(1168—1208)亦以交鈔與錢并行。而到了元朝,姬聚在至元八年(1271)選充控鶴,“屢蒙賜賚金帛楮幣”。由此可知桑皮紙印刷紙幣與金銀和布帛都能同時作為貨幣使用,且元朝蒙古帝國的戰爭機器,不但有強大滾動的兵力動員能力和后勤保障,還有“至元通行寶鈔”這樣方便的財政支撐。
姬聚和姬顯在元代均為控鶴。控鶴原指得道成仙①古人謂仙人騎鶴上天,語出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后特指宿衛近侍之官。初,唐武后嘗置控鶴府,其后歷代禁軍亦有以控鶴為名者,成為皇帝的近幸或親兵的名稱。《元史·世祖本紀》記載,中統二年(1261)十二月“初設控鶴五百四人,以劉德為軍使領之。”控鶴在元朝屬于特權階層,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特權騷擾魚肉百姓,碑文中反映了此一情況,可與《通制條格》卷第二十七《雜令·控鶴等服帶》所記禁控鶴騷擾官府百姓之事相印證。元代軍籍職務多世襲,姬氏一族中有多人出任此類皇帝親軍,顯赫無比,家族勢力也因此而漸達鼎盛。
神道碑中還涉及一條開通河道史料,也頗重要。碑文記載,姬聚任海漕部綱副千戶,跟從宣慰史來阿八赤開通膠河,督造運艦。《明史·河渠志》亦記載,“元至元十七年(1280),萊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地三百馀里,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至元十八年(1281),“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來督視,寒暑不輟……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阿八赤即來阿八赤,寧夏人。至元十九年(1282)膠萊河被廢,停止運糧。姬顯“遂授中書省札,為盤(般)陽路淄川縣冶頭店巡檢。”碑中所記姬聚督造運艦之事,可補正史細節。
碑文亦可補有關志書記載之缺。查《肥城縣志》,涉王載的記載有“縣西北七十里傅家岸(今屬東阿)有元王載撰武安王廟碑”一句,另《全元文》載王載曾撰《抹汗遺愛碑記》。從碑文可知,大德四年(1300)肥城知縣由段繼祖改換為王載,又記大德五年(1301)肥城縣尹王載撰《仁公神道碑銘》。所以此處記載可補肥城有關志書時間之缺。
(二)劉紱《奉符武君先塋之碑》考釋
肥城武氏祖居寧陽西皋村(今鶴山鄉沈西皋村),明朝弘治十年(1494),十三世貢生武得玉遷居泰安州第六鄉孫伯保武家莊。①今名莊頭村,元明清屬于泰安,1949年劃歸肥城。莊頭廣孝思堂存乾隆元年(1736)《武氏族譜》,二十二世武孟起等考碑銘、神軸②祭祀用的祖先名諱的掛軸、傳聞,草成族譜。乾隆二十七年(1762)書刻譜碑,并續族譜兩本。此后光緒十八年(1892)、民國二十二年(1933)、2002年、2006年數次續修,內容完備,資料豐富。
《武氏族譜》載有兩塊元朝《奉符武君先塋之碑》,一塊是泰安州奉符縣教諭劉紱撰文,漳州路龍嚴縣主簿易孫仁書寫篆額,至元二十六年(1289)千戶、成都鎮撫武進立石;另一塊是顏之晦撰書并篆額,延祐二年(1315)百戶武全、同弟社長武成立石。此兩碑均已經被毀,歷代地方志和金石書目均不見載,《全元文》也未收錄,今只留存于《武氏族譜》之中,是非常珍貴的文獻。其中,劉紱所撰碑文詳細描述了碑主武進的生平事跡,其中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在此對其全文照錄并加標點如下③碑文據《武氏族譜》2005年抄錄。肥城市博物館王新華提供資料。:
奉符武君先塋之碑(碑額篆書)
泰安州奉符[縣]教諭劉紱撰文
漳州路龍嚴縣主簿易孫仁書并篆額
至元二十六年春三月,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成都鎮撫武進,介郡人郭珪、宋榮輩,踵門而來。謂余曰:進,邑之鄙人,起身武弁,賴祖宗之遺陰,膺國家之寵榮,佩銀符,食天祿,于今有年矣。向以採薪之疾,不能竭忠報國,乞身謝事。奉朝命,俾男襲進職,得閑居于泰山之陽。復何幸耶。重念先世考妣,雖附葬以禮,而碑銘闕如。敢丐先生文,以表諸塋域。則列者生者俱有光焉。予以故舊,不敢以鄙陋辭。
按武氏世為奉符西高人,進之先高曾而下,俱不仕。祖季汝翁諱安,一諱賢。祖妣任氏。父贈君浩源諱深。軀干魁梧,性資純真。宗族鄉黨以孝悌稱。尤力于為善。無老稚皆知其為吉人也。自羅兵亂,守業農耕,而治家有法,蓄積豐實,而特樂予。歲饑,出其余饒,以濟貧乏,全活者無數。故人人以陰德歸之。晚年優游里社,頤養天和。賓客過從,幾無人知其以子貴也者。春秋七十有六,溘從運往。德配李恭人,四德夙嫻,臺范丕懋,勤儉惠慈,以相夫子。說者謂其所以富而無驕,貴而無侈,博施濟眾,以廣受乎陰德之歸者,賢內助之力蓋居多焉。先贈君享年七十五沒。
子男三人。長曰貴,早卒。次曰進,即今鎮撫也。次曰聰。進娶閆氏、趙氏、徐氏。孫男五人。貴之子一人,名節。進之子一人,曰國貞,一名成。閆氏所生,襲父職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成都鎮撫,配銀符。聰之子三人,長曰志,次曰中,三曰思。女孫一人,適里人張氏。曾孫二人。孫男一人,名就。女孫一人。
進天資英偉,而有將略。人未之識也。及壯,以智勇聞。至元六年(1269)天兵收復江南,以良家子系軍籍。在甘縣籍于張萬戶麾下,張公奇焉,拔置左右,其親用非他人可比。及收取襄陽、樊城、陽邏堡等處,以功充管軍百戶。至元十四年(1277),討熊飛及二王,敕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明年,改昭信校尉,職如故。至元二十年(1283),朝廷以拘留使者何子志等,是以有占城之役。是役也,中書右丞相總海舟運糧,以給海南。令進率銳卒防護,過于木棉二山。巨賊黎德等,恃其獷悍,大肆剽掠。出沒無常,運道幾梗。進至數接戰,身先士卒,奪其鳴船百余支,殺賊千余人,追奔逐北,踰白藤角,而生擒黎德。一軍威服其。是歲,偽歐王逆叛,朝廷命越的迷失以討之。元帥府遣進翼下軍以從。進直抵其寨,與賊力戰,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殺賊數千人,偽歐遁去。進引兵入山而擒之。是時,無陣不戰,無戰不勝。其攻城平賊之力為多。帥府特列其功于朝,授銀符,升承信校尉。調軍馬允當,又祗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為次受鎮守隆路招討萬戶府劄付,充成都鎮撫。提進渡淮過江,屢獲功勣,酌擬領本千戶軍劄付千戶印信。進為人勇敢多大略,自處行伍中,盡忠竭力,不顧其身。復能推讓不伐,人尤此多之。
君子曰:古者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公劉匪居匪康,疆場積倉。其后周公猶推本稼穡之艱難,而作為樂歌。進之先,農家也。子孫蕃衍甚盛,遂能光大其門閭。非積德其何能及此耶?父子忠孝福祿方來。是可銘也已。銘曰:
岱宗之陽,汶水之泱。武氏一門,其族寖昌。
其族維何,厥初力穡。非惟務農,兼種其德。
迨乎府君,居家克勤。鄉黨義稱,宗族孝聞。
薦罹饑荒,能也所藏。濟貧周急,動罔不臧。
閭里懷之,親戚依之。何以報德,陰德歸之。
為善之利,神理昭示。躬不驕吝,以貽后嗣。
有子而賢,克紹爾先。于公高門,此得其傳。
神奮威武,董茲師旅。不顧其軀,以報明主。
乃討群兇,盡力竭忠。悉平群盜,爰定厥功。
篆佩銀符,榮膺龐命。寬猛相濟,鎮蜀德政。
譽重于朝,勲書于策。曰予何德,先祖之德。
門閥日隆,福祿方興。父既致仕,子復是承。
古求忠臣,孝子之門。順親有道,以事一人。
皇帝曰俞,方叔召虎。鳳篆龍章,顯汝父母。
今名著聞,孝心凄惻。丘垅嵯峨,林樹森植。
刻石勒銘,著此芳聲。以慰幽明,以傳億齡。
大元國至元二十六年(1289)歲次己丑仲呂月上旬谷旦。
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成都鎮撫進立石。
據該譜記載,武氏始祖為武圃,字雨畦,金朝人,六子。次子武善,字仲懿;四子武安,又名武賢,字季汝。兩者后人皆置先塋之碑。武氏祖墓位于黃家西皋村琵琶山之陽,墓封土高大,墓地有石碑、石人、石獸等。咸豐元年《寧陽縣志·古跡·塋墓·元》記載“敕贈承信校尉武深墓,在縣西三十里西高村東,墓碑螭首龜趺,墓道左右翁仲森列,石獸無缺。”另記“誥封顯武將軍武進墓,在縣西三十里琵琶山前,墓碑螭首龜趺,墓道左右翁仲森列,石獸無缺。”清朝時原來“豐碑屹立”的石碑已經“第字跡患漫,惟余碑額篆書‘顯武將軍武公銘記’及‘誥封顯武將軍’‘寬猛相濟風’有十余字可識”。武進、武國貞、武祥、武士英、武凈傳記載入光緒十三年《寧陽續志·人物·武功傳》之首,武元、武全入《寧陽續志·人物·忠義傳》,黃恩彤皆有贊。但武氏僅為中下層武官,其事跡在正史中并不見記載,故此碑文可補史之遺缺。
從碑文中可知,碑主武進字君光,至元六年(1269)以良家子弟身份隨軍,參加了元世祖朝一系列內外爭戰。趙翼《廿二史劄記·元史·黷武》稱元初“有事于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于閩廣,先后十余年。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軍人從間道始得歸。征占城,舟為風濤所碎十之七八,國王已逃,官軍深入為所截,力戰得歸。世祖時用兵已四十余年。世祖即位,又攻討三十余年。無歲不用兵,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這些戰事武進大都身預其役,對此,碑銘有濃墨重彩的描述。
武進先在萬戶張弘范(1238-1280)麾下任親兵,參加了平定南宋之役。先后隨其南下襄陽、樊城、陽邏堡,因功被授予管軍百戶,累記功勞做到忠顯校尉、管軍總把,又改正六品昭信校尉。此后宋恭帝降元,宋宗室趙昰、趙昺先后被擁為帝,在東南沿海堅持抗元。1279年崖山(今廣東新會崖門)海戰,左丞相陸秀夫背著趙昺跳海自盡,宋亡。時武進奉命隨忙兀臺、唆都等率舟師追殲宋二帝。碑文稱趙昰、趙昺為“二王”,可見是站在元廷立場,不承認二人為宋皇帝。
武進參與了越的迷失①越的迷失即也的迷失,以驍勇賜號拔都兒,歷任江西參知政事、福建參知政事。征戰的大部分戰事。平宋之役中,武進先后參加對熊飛②熊飛,廣東東莞人,1276年守潮、惠二州,攻廣州,復韶州。后御元軍于南雄,不支奔韶州。元軍圍韶州,熊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黎德③黎德,廣東新會人,1283年參與林桂芳與趙氏建立的羅平國,年號延康,有船艇7000之眾,號稱20萬義軍。與歐王④歐王,即廣東人歐南喜,時在清遠稱王,建元稱號,設官置署,眾號十萬。執殺元將合刺普華,切斷通往占城的餉道,并進襲廣州,兵敗后走新會,與黎德會合。的戰斗。武進以討熊飛有功升職,奉部途經木棉二山時,遇上黎德軍截擊。武進身先士卒,殺兵千余人,激戰一日后生擒黎德,立有大功。《元史·本紀世祖》所載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己丑,“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也的迷失禽獲海盜黎德,及招降余黨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黎德以徇,以黎德弟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即指此役。后于新會戰歐王、黎德,武進直抵敵寨,擒獲歐王。
占城之役中武進也有所表現。占城之役,是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282-1284)元軍攻占城國⑤蒙元時,越南的北部屬于交趾(安南),中南為占城(占婆)。的作戰。1277年,忽必烈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漢軍7萬,船500艘和云南兵6000人、黎族兵1.5萬人,以海道萬戶張文虎運糧17萬石攻交趾。海路軍途中遇交趾船400艘,斬4000余人,俘百余人。元朝立占城行省,企圖以此為據點向海外擴張。1282年,忽必烈派遣江浙、福建、湖廣兵5000人,海船百艘,由唆都率領,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交趾、占城兩國國王都躲進深山進行游擊戰,口頭投降而不給土地與兵員后勤實利。此役中武進率銳卒防護海舟運糧,保護運道。另族人武元任領軍都鎮撫,從征交趾,但不幸陣亡。
譜載:武進子武國貞襲父原官,尋遷武義將軍、征西副元帥。大德時(1297-1307)擢升顯武將軍(從四品武官)、川西萬戶總管府萬戶管理、軍民都總管。數年召還,至大二年(1309)仍開府蜀中。大德五年(1301)后為征西副元帥,并在邊塞置萬戶總管府。至大二年(1309)死在任上。武進之孫武祥延佑二年(1315)隨元明宗出鎮云南,泰定(1324-1328)時為河南副元帥。武進曾孫武士英至正初(1341)官指揮使。元孫武凈,行杻密院同知。武浄在籍起兵,“族之力能執兵者皆與焉”,至正二十一年(1361)與察罕貼木兒擊降田豐于東平,次年以兵圍益都(青州),田豐復叛,武浄率本部奮力戰死。其子武璥,至正二十二年(1362)率族之勇士踏敵營,七入七出,卒奪親尸還葬于武家莊,尋以元運告終,伏處鄉里。武氏以武力稱雄,是元朝統治的既得利益者。元末紅巾軍起義之后,武氏解甲歸田,開始了詩書耕讀的生活。
以上是劉紱《奉符武君先塋之碑》中記載的重要內容,可謂融碑主個人史、所在家族的宗族史和地方史于一體的重要歷史資料。
三、肥城譜牒中元代兩篇先塋碑文的價值
考察肥城譜牒中的元代先塋碑文,可以確定參與者多是地方性人物,受委托撰碑人多是公眾和朝廷認可的儒者。撰文者在行文中盡量避免提到蒙古人的名字,稱反抗者為盜賊,極力稱頌碑主英勇善戰、忠貞多智等個人品德,可見參與者或主動或迫于形勢認可并順應了元朝的統一大勢,代表了當時地方豪強在朝代更迭動蕩之際的心理和外在行為表現。撰文者通過征引《詩經》《左傳》的典故宣揚華夏正統的思想意識,體現出在異族入侵的高壓態勢下,漢族知識分子依然堅守儒家思想,希望在亂世中留守住傳統精神家園的努力。碑文中關于人名、地名、時間、稱謂、職務、世系、戰事等信息的詳細描述,既體現了在朝代更迭之際個人的宦海浮沉、家族興亡,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面貌,對地方歷史人物的考證、歷史細節的補訂、重要歷史事件的重新梳理和認識有重大價值。
肥城武、姬氏的神道碑和先塋碑是譜牒中的碑文代表。新碑刻形式的普及,揭示了社會變動引起的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張力,這是元朝武力起家階層立先塋碑的共同文化背景。在當時蒙古勢力的殘酷統治下,地方豪強勢力通過為祖先立碑間接為個人顯功揚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存訂正史料和傳承弘揚文化的作用。對此,汪寶樹在《姬氏志·序》中有名門宗譜“經典所不載者,足以訂史傳之訛,而補方策之不足”的評論,將“多信而有徵”的家族碑銘、地方資料提高到文化史實文獻的地位。進一步深入挖掘地方譜牒中各種碑文的記載并進行系統、科學的拓展研究,可以深化后人對歷史的認識,征正史之不足,大大擴充現有的研究視野、方法和途徑,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