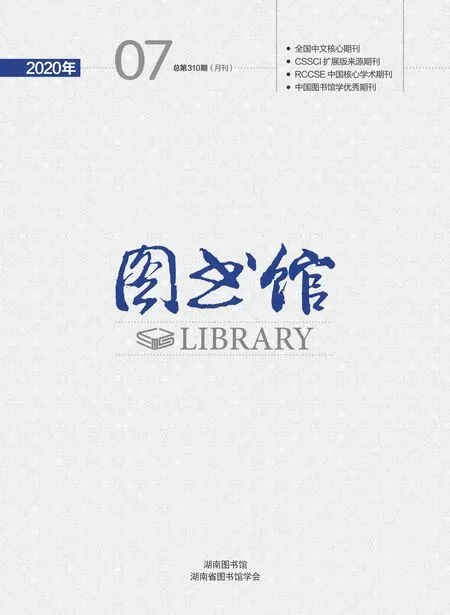中國目錄學傳統的當今表現
——目錄學去哪了?
陳志新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5)
目錄的編制即編目。“目”指篇(局部章節)卷(整體文獻)的名稱,“錄”是關于文獻的內容、作者信息以及對其評價等的說明。目錄,也稱書目,是讀者與文獻之間發生聯系的中介、橋梁乃至目的地。
長期以來,《目錄學概論》是圖書館學、情報學的重要核心課程。但是,近十幾年的圖情學科專業教學改革,使得它逐漸邊緣化。如今,開設這門課程的圖書情報學專業已經不多了。正在開設的信息組織(分類主題)、信息描述(編目)和文獻學(古籍的流傳、類別與現狀)(目前,還并不是每一所高校都開設文獻學)等三門課程,已經涵蓋、能夠涵蓋《目錄學概論》課程的要旨了嗎?
1 中國目錄學的千年傳統
中國目錄學傳統重視內容編目,而不是形式編目,具有“重分類,輕編目”的特點。
王重民先生通過研究甲骨認為,中國目錄工作的雛形,在殷商時期已經出現。老子做過周朝史官,負責管理圖籍;孔子編書刪定六經、制定教書育人教材,都屬早期的目錄活動。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廣覽博收,窮盡圖書,逐一校讎,增刪材料,條別篇章,確定書名和篇名,勘核文字,寫成定本,提要鉤玄,編寫敘錄,按照當時的學術認識,序列分類。書有所屬,非孤魂野鬼;類有所指,非空而論道。《七略》重點創建了7大類,38小類,形成6略38種603家的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總目錄,比西方第一部正式的圖書分類法《萬象圖書分類法》,足足早了一千五百年[1]。
漢代班固,開創史志目錄,繼承劉向、劉歆父子的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西晉荀勖著《中經新簿》,反映史學新特點,改七分為四分,顯后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端倪。隋唐時期,魏征在《隋書·經籍志》中,明確我國經史子集4大類、40小類的分類定制。宋代鄭樵,主張通錄古今、類例之法優先、泛釋無意和互著別裁,發展了漢代以來的目錄學。清代目錄學家章學誠指出,目錄應能使讀書者“即器亦明道”。他的代表作《校讎通義》旨在“宗劉”(繼承劉向、劉歆)、“補鄭”(彌補鄭樵的不足)和“正俗”(糾正時弊)。清代收納天下圖籍,篩選近一萬種圖書,將經史子集傳統發揚光大,形成4大類、44小類的詳細分類系統,容納手抄的7部《四庫全書》,分藏全國各地。
中國的目錄學傳統,在學術原理上為讀者指示門徑,沿門徑,直達經過篩選校訂的最佳原始文獻,面向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取得不朽業績。中國古代目錄的主流,并不是拘泥于某個具體的圖書館(藏書樓)。中國古代杰出的目錄編制者,沒有止步于文獻校勘,也沒有拘泥于財產清單,而是高屋建瓴,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進行知識梳理。一方面,形成從具體到抽象的縱向維度上最長的以分類為主的語義網絡,另一方面,形成從此類到彼類的橫向維度上最寬的以分類為主的語義網絡,最終實現目錄學騰飛,以帶有提要和類序的分類目錄體例,開辟從“圖書整理”到“知識整理”的道路。今天,本體、知識網絡負責學術原理上的指示門徑,集成眾多參數指標的搜索引擎算法排序自動展現最好的信息原文,呈現信息編目、信息組織與搜索引擎三者合流的特征。自動化技術手段,再現并拓展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環境下,集成的、方便的、一體化的信息產品,正在如人所愿、如火如荼地積極建設之中。
然而,在老子、孔子的時代,在劉向、劉歆的時代,在隋唐宋元明清,我們華夏兒女一直擁有這種信息組織、信息編目與信息原文一體化,并且能夠與千年之時代俱進的信息產品!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以停上《目錄學概論》課程的方式,認為我們的千年目錄學傳統是沒有意義的從而必須放棄呢?
2 中西編目的差異
在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側重點等方面,中國古代編目與西方近現代編目存在差異[2]。
西方近現代編目條例包括三大組成部分——書目著錄(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檢索點選取(access points)和規范記錄(authority records)。目錄職能包括兩個——特定檢索和聚合檢索。特定檢索要求著錄時完全照錄題名頁,聚合檢索則要求具備統一(uniformity)的特性,即同一著者的統一標目、同一作品的統一題名和同一主題的統一標題詞。中國古代刪繁就簡,排除目錄的上述兩種功能的矛盾,直接到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領域發力——從秦漢始,形成不惜萬難千苦搞定最佳版本、提要鉤玄敘述該書大義、歸入學術分類門徑的做法,徹底超越了西方近現代的書目實踐和書目理論。
西方編目一直盛行“著者原則”(author’s principle),識別著作責任者是其編目的重要步驟。幾個方面的原因形成“著者原則”:第一,西文尤其拉丁文語系,由于語法上的倒置形式,常使書名中具有實際意義的詞匯不突出,書名中無實際意義的語法功能詞卻位于書名之首,若以書名字順排序,造成書名以“the、and和of”等語法功能詞開頭的書籍集中在一起,無益識別與檢索。相反,著者姓名具有較強的區別性,通過著者,更能集中同一個人的不同著作,起到某種聚集的功效。第二,西方14世紀興起文藝復興運動,人文主義盛行,強調人本身的價值,反映在文獻著錄和檢索中必然突出著作的責任者。第三,歐美各國歷來將著作視為個人財產,并由國家法律予以保護。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容易聯系到該著作系何人所著。關于“著者原則”,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古代并無上述森嚴壁壘,圣人著書,為天下,非為一己,責任者和財產屬性并非第一考慮。直奔書,直奔知識自身,直奔學術脈絡,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從19世紀至今,西方的編目實踐,其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潘尼茲將“查檢式目錄”推進到“圖書館資源的有效指南”,從一書擴展到一館資源。卡特提出特性檢索(查詢)和族性檢索(集中),即查詢和集中并重,進而實現目錄多途徑檢索的功能。第二,從20世紀40、50年代起,奧斯本、柳別斯基等重視編目原則和目標,強化特性檢索和族性檢索的概念,該主張出現在目前流行的書目記錄的功能需求(FRBR)、資源描述與檢索(RDA)中的“作品”概念以及“發現、識別、選擇和獲取”的編目四功能之中。第三,20世紀60年代之后,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滲透至編目領域,出現書目著錄標準化、書目控制、資源全球化以及強化檢索等現象。第四,21世紀,隨著社會進步和讀者個性化的發展,傳統圖書館已從文獻信息的加工,發展為對信息的組織,進而達到知識管理的層次。從分類編目到信息組織再到信息資源管理,就是一個對傳統分類編目工作不斷擴大、更新與升級的過程,增加了目錄的“導航”(navigate)功能,即通過書目實體之間的等同、相關和從屬關系,從已知作品導向其他作品。至此,圖書館目錄的功能擴展為:確認、聚合、選擇、導航和獲取,實現從知識導航到信息篩選再到提供原文的全過程——掃描、復制、電子化、數據庫、云存儲和大數據如此方便、快捷,使得線索與原文,不需轉換,沒有阻隔,電腦終端前,可以獲得一切原文信息,電腦終端即資源。這樣,提供文獻線索,過度注重信息描述,反而成為累贅的事情。中國古代已經實現了的“線索與原文沒有阻隔”在當代正成為逐漸擴大實現的現實。
1998年由國際圖聯組織編寫的《書目記錄的功能需求》(FRBR),從實體、屬性、關系的角度,重新定義書目記錄的內涵。FRBR不把個別的數據作為分析的對象,而是將從眾多的數據中提煉出的共同點作為研究的客體,目的在于讓信息編目實現本該由信息組織實現的類聚檢索職能。以FRBR和RDA為代表的西方最新編目實踐,把原來屬于信息組織和信息檢索的東西,比如,規范、時間地點特征描述、知識體系、主題圖以及本體等,增添進編目,目的在于要實現一條龍式的貫通服務。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目錄學傳統格外高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一方面,從學問之源頭入手;另一方面,落腳于直接給讀書人提供最佳的信息原文[3]。
在FRBR書目實踐中,“作品”、“載體表現”和“單件”分別與規范記錄、書目記錄和館藏記錄相對應。“作品”是FRBR提出的全新編目概念,是被后來2009年《資源描述與檢索》(RDA)重點實踐的編目事項。抽象實體的“作品”,是指獨特的智力或藝術創作,不能把某一個單獨的具體事物與“作品”對應。雖然“作品”需要通過某些個體或者某些內容表達來實現,但是“作品”本身只存在于不同內容表達的共性之中。對于FRBR和RDA,上述解釋是其核心的內容之一,也是中國編目界在理解國際最新編目變化時,比較難以處理和理解的內容。然而,歷史具有驚人的重復特征,今人認為最新的東西,在原理的角度上,古人早已具備。FRBR和RDA最為晦澀難懂的“作品”,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已經實踐過——“作品”雖然是抽象的編目概念,它難道比《七略》的6大類38小類更抽象嗎?現代編目,雖然逐漸添加分類、主題的標示,逐漸祥盡揭示內容特征,其做法,難道比劉向、劉歆父子為每部書撰寫題錄、提要、小序,更加詳盡嗎?
3 目錄學的未來
歷史是唯物的,歷史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目錄之學,不會隨著當今中國大學取消了目錄學課程,其實踐活動便停止了,其理論價值便消失了。在大數據、可視化、云存儲、人工智能、FRBR、RDA、本體、主題圖等理論和技術的綜合作用下,目錄之學將以嶄新的面貌重新煥發自身內在的永恒力量與永久魅力。
展望未來,古老的《目錄學概論》課程將鳳凰涅槃、歷久彌新。我們將繼承發揚目錄學的光榮傳統和精神魅力,不僅做古人已經做過的事情,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還能做古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如今,目錄工作已經走出了一個個圖書館、檔案館、情報所,走出一個個數據庫,走出一個個局域網。如何在這無垠的信息海洋中發現信息、整合信息、重組信息,建立信息與知識之間的聯系,使之納入一個巨大的有序知識系統,跨越各種障礙實現最大限度的共享和互操作,提供高精度的檢索等,也就成了文獻編目的重要任務。老子、孔子、劉向、劉歆等無數古代中國人,窮經皓首,孜孜以求,選定好本,校訂無誤,編寫提要,做出敘錄,揭示學問門徑,用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指示后人以學習之路、學習之法,奉獻后人以最好的信息文本。新技術條件之下,可以用機器生成各領域可視化的、本體化的知識揭示之地圖,可以像搜索引擎那樣通過算法,把最好的信息,首先推薦給用戶。古代完全靠大學問家才能做校勘并選定最佳文獻原文的事情,由于大學問家的人數有限、精力有限,畢其一生,僅能就那些重要和重大的學科門類,展開這種知識揭示和信息提供工作。我們的機器和算法,力大無邊,可以日日夜夜地在各個領域一刻不息地做這樣的加工和整理工作。
搜索引擎化的編目,編目化的搜索引擎,信息組織化的編目,編目化的信息組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這一趨勢表明我們的工作,正在淡化信息描述、信息組織、信息檢索和信息服務的界限;表明我們的工作環節,融合了用戶調研、采訪、編目、流通、外借與典藏;表明我們的信息工作類型,混合了書本、文稿、電子的、網絡的、音樂、縮微等各種載體形式。信息管理的新特點和新趨勢,日已呈現。
4 結語
筆者不是主張恢復本科生十幾年前《目錄學概論》教學的原樣,而是認為應把中國古代優秀的目錄學理論與實踐的精華,擺在未來目錄學課堂教學的第一章,大力探討如何在大數據、云存儲和人工智能的信息環境下,更好地實現和發展古人的精神與追求,創制出更加優異、便捷的目錄產品。新開設的《目錄學概論》課程,應總結和提出更好的技術路線與實現方案,繼往開來,以適應偉大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