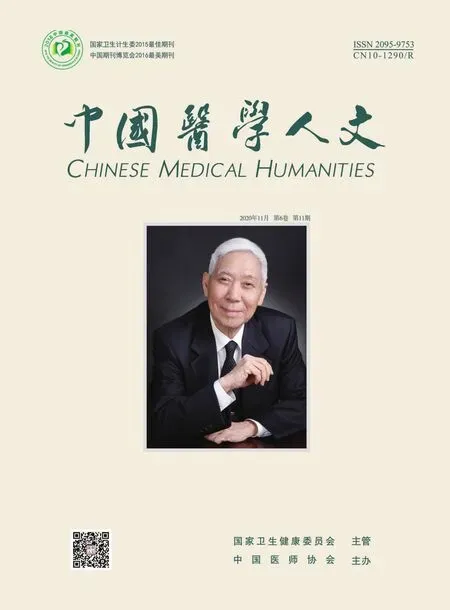媒體·人文·責任與抗疫
文/王魯湘
2020 年9 月27 日上午,第四屆中國醫(yī)學人文大會在京召開,中國當代文化學者、鳳凰衛(wèi)視著名主持人王魯湘為大會作報告。
醫(yī)生職業(yè)具有天然的神圣性。我們一切人文的精神,其實從文明發(fā)生的角度來看,它來源于神性。比如說我們醫(yī)生的“醫(yī)”字,它的繁寫就告訴我們,它其實是來自最古老的、萬物有神的一種宗教的思想,一種原始的巫術,從這種原始的巫術分離出了醫(yī)學,而且我至今認為這種分離并不是徹底的,而且不需要徹底。
也就是說醫(yī)學再怎么向科學進軍,向科學發(fā)展,也不能脫離神性,因為神性才是我們人性最后的形而上的依據(jù),否則人性最后會墮落為動物性,墮落為物性。我非常認真仔細地聆聽了郎景和醫(yī)生的演講,他不僅是一個醫(yī)術高明的醫(yī)生,還是一位哲學家,一位心理學家,一位詩人,一位書法家,他還是一個特別好的布道者。我相信在郎醫(yī)生的心里是充滿著神性的。神不一定是我們原始信仰中一個具體可感的、人格化的造物主,它應該是信仰中的全能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一個存在,它是我們哲學上所說的本體,是一個抽象的、一個信仰的對象,由對象發(fā)展出了我們人文精神的整個價值體系。
所以在中國哲學中間,醫(yī)術從巫術分離出來以后,就成為了仁術,“仁”是仁義道德的“仁”,一直到今天,我們也稱醫(yī)術、仁心仁術。“仁”這個字,一個單立人,旁邊一個二,那就是兩個人,它指的是一種人際關系,兩個人就有了人際關系,有了人際關系,就必須有一種指導的理念,指導人際關系的理念,其實就是人文精神。它不是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不是人和物之間的關系,是兩個人和兩個人以上的人際關系。那么醫(yī)生的工作其實就是處理這種關系。
仁術背后的人文精神,先秦儒家也好,道家、墨家也好,其實對它都有深刻的、系統(tǒng)性的探討。懸壺濟世,是儒家精神在醫(yī)學和醫(yī)術上的一種體現(xiàn);救死扶傷也是這種精神的體現(xiàn);包括道家追求長命百歲,也是在探索生命的奧秘;墨家所說的大愛,我們現(xiàn)在經常說的大愛無疆,是墨家的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墨家是中國俠客精神的鼻祖,俠之大者,不是救死扶傷,就是匡扶正義。所以在中國的古典哲學中間,其實有著深厚的、醫(yī)學的人文主義精神的資源。
這種人文主義的資源,我覺得可以歸納出幾點。
首先是生命至上的一種宗教情感。就是對生命本身,尤其是人的生命本身,把它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個地位不是推論出來的,它是一個信仰,一個信念,是一種哲學精神。這種哲學精神就是要去探究生命背后的意義、價值,這種哲學精神也是一種科學精神,就是要探討生命背后的奧秘。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一種精神,就是懷疑主義精神。郎景和院士的報告中,我從頭至尾聽到的就是一個醫(yī)生的懷疑主義精神的貫徹,他的懷疑主義其實就是建立在生命至上以及敬畏生命的不可知,它的神圣性。我們不要把生命當成一個物件,不要把生命當成一堆物質的集合,那樣我們就會陷入一種技術的異化當中。
其次,作為一個媒體人,更多的應該結合媒體在這一次新冠疫情中發(fā)揮的作用以及對它的思考。這一次的疫情應該說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疫情。在此之前,人類發(fā)生過的所有的疫情都是局部性的、區(qū)域性的。但是這一次是真正地實現(xiàn)了瘟疫的全球化。瘟疫的全球化確實和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這樣一個歷史進程,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我們看,1492 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從16 世紀進入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也就是跨洲際之間的人類的交往,包括后來的航海大發(fā)現(xiàn),全球貿易網的形成開啟了500 年的全球化進程。當時人類的文明實現(xiàn)跨越式的發(fā)展,過去孤立于各個地區(qū)的人類發(fā)展的文明成果,得到了跨州際的交流,包括很多過去封閉在某一個地區(qū)的一些物產,也開始跨州際的交流,人類文明可以說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時,瘟疫的傳播,疾病的傳播,包括人類生命所受到的威脅也是同比例的增長。
再次,這一次的新冠疫情,我覺得是幾個要素的疊合。第一,它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次瘟疫暴發(fā),全球的交往,史無前例地達到了一個地球村的水平。第二,就是我們正好疊合了手機普及的這么一個歷史階段。幾乎人手一機,一機在手,通曉天下之事,這是在過去的大瘟疫時代所沒有過的情況。第三,互聯(lián)網和自媒體的發(fā)達。這幾個要素重疊到一起就是今年新冠疫情全球暴發(fā),我們媒體人面臨的一個新的局面。所有的疫情的暴發(fā),當然瘟疫本身的傳播性、致死率非常可怕,但是比這個更可怕的其實是信息的傳播,所以當有疫情發(fā)生的時候,不管在什么時代,在什么政治制度之下,權力當局第一反應就是封鎖消息,他們封鎖消息并不見得帶有天然的惡意,而是為了避免比瘟疫本身更恐怖的恐慌。因為這種恐慌很可能在我們還沒有對付瘟疫本身的時候,就已經耗盡了我們的社會資源,因此封鎖消息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怎么封鎖,封鎖到什么程度?在何種時機之下讓信息透明,卻又是一種政治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在過去傳統(tǒng)媒體時代這個事情好辦,但在今天人手一機、互聯(lián)網瞬間連接全球的時代,又有這么多自媒體在獨立發(fā)布各種信息的時候怎么辦?這是這次新冠疫情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在這一次疫情中間,我估計所有人其實都經歷過了這種煎熬,你被封閉在家里,你對外界已經絕緣,小區(qū)封了你出不去,有些地方做得更絕,連道路都封了,路都給挖斷了。還有一些門上被釘上了釘子和板子,貼上封條。大家試想一下,如果3-5 個月這種狀態(tài)的封閉,在沒有手機和外界溝通的情況之下,我們的精神病院是不是要多很多病人?我們能夠度過這么艱難的封閉期,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手機和互聯(lián)網還有自媒體的存在,這些亂七八糟、莫衷一是、搞不清真假的信息其實平衡了我們的心,中和了我們的焦慮,讓我們的思維不至于鉆一個牛角尖。
這次我們能夠比較順利地在一種初始的、倉皇失措的情況之下,逐步地走向穩(wěn)定正常,并在全世界率先走出疫情的陰影,我們也表彰了很多共和國的英雄,抗疫的英雄。其實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是“非小人無以養(yǎng)君子”。鄭板橋畫竹子,竹子的下面經常要畫一些荊棘,之前有人問鄭板橋,你為什么要把荊棘和竹子這么高尚的君子的東西畫到一起?鄭板橋說“非小人無以養(yǎng)君子”,這句話是孔夫子的話。其實在這次疫情中間,沒有這些自媒體的存在,我們的整個疫情階段的信息環(huán)境是不好的。當我們只聽到一種聲音的時候,水至清則無魚。
最后,我覺得作為一個媒體人,我們聯(lián)系到這樣一場疫情,聯(lián)系到治病和信息的關系,其實中間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一些哲學問題,但是我們恰恰在控制信息的時候,我們犯形而上學的錯誤。郎景和院士的講座讓我認識到,其實一個真正高明的醫(yī)生,面對一個病人的時候,哪怕是一個很普通的病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做媒體何不如此,管理媒體、管理信息更是如此,這是我的一點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