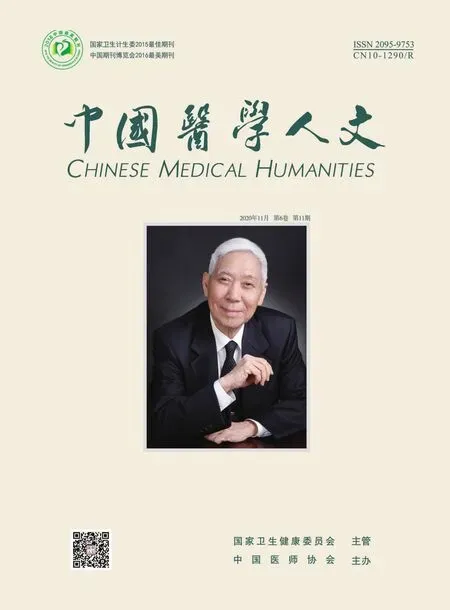北宋名醫龐安時與文豪蘇東坡的情緣軼事
文/柴玉慧 李成年
中國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歷久彌新,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學,對其傳承和發揚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對中醫學來說,更是其厚植的土壤。本文將通過講述宋代文豪蘇東坡與“鄂東四大名醫”之一龐安時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簡述他們相識相知的過程,來展現文人與醫者之間的惺惺相惜之情,以及傳統文化與中醫學相互促進,共助民族文化發展的優良模式。
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在其濃厚的文化渲染下,文人曉醫、醫者通文,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并在其歷史進程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宋代當朝統治者尤其重視醫學,甚至還親自研習醫學,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文人志士,無不以知醫、學醫、懂醫為榮2。一代文豪蘇東坡,代表官場,為受災百姓布粥施藥3、創辦病坊、抗擊疫情,或作為文苑秀士,與杏林圣手問疾談醫、交友酬答,或自己研習醫理,以求養生良方4,無不體現醫學與傳統文學相互交融,彼此促進的良性發展模式。
宋代的醫藥文化發展情況及原因
眾所周知,五代十國時期,戰亂紛紜,國家分崩離析,百姓流離失所,直到趙匡胤登位稱帝,建立宋朝,并逐漸穩定局勢,開明如斯的宋太祖便開始了他“右文抑武”基本國策的施行。不可否認,宋代在其歷代統治者“尚文”的治理下,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繁榮發展。醫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醫學能在宋代蓬勃發展,主要原因有三。
宋統治者對傳統文化及醫學的重視。從趙匡胤建立北宋,到北宋結束,其中有多位統治者均愛好醫學,甚至身體力行,如太祖為其弟治病,太宗大量收集民間良方,真宗親自給大臣診治疾病,仁宗研制的“三圣湯”對咽喉口舌疾病頗有療效,徽宗更是親自編著醫術《圣濟總錄》2。上之所好,下之所趨,在當朝統治者如此影響下,宋朝文武百官、文人志士,或文醫雙棲,或與杏林結交,如沈括、蘇東坡與龐安時等人。文人以文會醫,醫者為其診病,醫者的傳奇故事成為文人最好的創作素材,醫者在文人的熏染下加深了其對傳統文化的喜愛與認識,并在相互交流、切磋中結下深厚的友誼。
經濟文化與科技的發展成為醫學崛起的最佳推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5,給各類醫書的刊刻與發行帶來了極大便利,在宋代統治者大力支持下,彼時的醫書隨處可得。加上宋代經濟的快速發展,購買醫書并不會給普通民眾帶來經濟壓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宋代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其他各行各業興起甚至蓬勃發展的必要因素。由于時代背景因素,宋代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有一種疑古的思想,“理學”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了,“理”打通了理學與中醫學之間的橋梁,宋代理學家“格物致知”,極盡探求事物之理6,宋代醫家同樣重視醫理,把理學融入到中醫學,是宋代中醫學上的一大進步。
自然氣候變化及戰后疫情迫切需要醫學的發展。由于宋代所處的時代背景,戰爭頻發,戰后疫情泛濫,加之宋以后,氣候開始變暖,溫熱病和時行病流行3,一方面,狹義傷寒論應用于不斷發生變化的新的病情有所局限,這就迫使醫家們探索新的醫學理論;另一方面,疫情也給醫家們提供了實踐理論的機會。比如宋代名醫龐安時,出生醫學世家,聰明過人,過目不忘,再加上他的勤奮好學,弱冠之年就能領悟《黃帝內經》《難經》等多本古籍醫書的精髓大意7。龐安時治病,并不總是拘泥于古方,他會根據實際情況,如當時的氣候變化及戰后疫情特點,深研其病因病機,并在王叔和編次整理的傷寒論基礎上,結合自身經驗,深入研究廣義傷寒論,對其進行增補,擴大其治病范圍,并成書《傷寒總病論》8,不僅如此,他還創立了“寒毒”“異氣”學說,認為傷寒與溫病是不同類的病癥,應分而論之,還將溫病分為伏氣與天行兩類7,為后世溫病學的發展開辟道路。
蘇東坡與龐安時初相識
文苑巨星蘇東坡,成長于宋代,亦成就于宋代。官場不如意的他,把絕大多數精力都用在文學上了,使他在文學上成績斐然。他現存詩就有2 700 多首,千古第一,現存詞有340 余首,現存文章4 800 余篇,涉及多個文體,多個方面。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宋詞”的加持。他一改曾經難登大雅之堂的伲儂小唱,擴大詞的題材范圍,豐富詞的意境和社會內容,開創豪放派,把“詞”提到了與“詩”并列的地位9。我們耳熟能詳的“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就出自蘇東坡之手。
蘇東坡令世人折服的地方并不止于他的文學修養,更在于他豁達的人生情懷。元豐二年(公元1779 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元豐八年(公元1785 年)返京。海明威曾說,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是不能被打敗10。在黃州數年間,他幾乎沒有俸祿,生活拮據,但這些并沒有打垮他。他在沙湖,置辦田地,聊以慰藉。卻在買田時不慎患病,遂找龐安時治病。《東坡志林》:“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11,也是在這里,他與龐安時結下不解之緣。
蘇東坡與龐安時成為莫逆之交
龐安時幫蘇東坡看好病之后,蘇東坡特別高興,交際達人蘇東坡便邀請龐安時去郊游。《東坡志林》有云:“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11。蘇東坡覺得龐安時醫術了得,此后多次找龐安時看病,當時,蘇東坡在書法上與黃庭堅、米芾、蔡襄齊名,寫得一手好字。他在繪畫上的造詣也頗深,與文同、米芾一起創立了宋代文人寫意畫派。而愛好書畫且行醫不志于利的龐安時如遇知己般,常常不收蘇東坡診金,讓蘇東坡以字畫做酬。不僅如此,龐安時還將患者送的幾代人藏品廷跬墨拿去跟蘇東坡交換字畫12。龐安時與蘇東坡之間的友情就在“你來我往”中日漸升華。蘇東坡欽佩于龐安時的醫術醫德,還經常介紹朋友去找龐安時看病,如他對當時的大官蘇頌說:“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醫不識,故用藥不應耳。蘄水人龐安時者,脈藥皆精,博學多識,已試之驗,不減古人。度其勢未可邀致然,必詳錄得疾之由,進退之候,令見形狀,使之評論處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與書,庶幾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于利,某頗與之熟,已與書,今候公書至,即為詳處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與蘇子容書》)13。如若不是與龐安時相交甚密,且十分看好他的醫術,蘇東坡怎會如此自豪地向蘇頌推薦龐安時。
文壇巨擘與杏林圣手之間的思想碰撞
在宋代“尚醫”風潮的影響下,研究醫理已成為當時文壇的時尚,作為文壇巨擘的蘇東坡當然也不例外,在醫學上,他雖然沒有像專業醫者那樣對醫理研究的相當透徹,但是他常常會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且樂于跟龐安時相互探討,他們常有書信往來,在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上蘇子瞻端明辨傷寒論書》有他給蘇東坡的回信:“安時所撰傷寒解,實用心三十余年……士大夫雖好此道,未必深造,宮妒朝嫉者眾,吹毛求瑕,安不爍金,更望省察狂瞽之言。千浼臺聽,悚息無地。”蘇東坡也曾給龐安時寫信:“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后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元祐四年,蘇東坡在任杭州知府,期間杭州疫情嚴重,蘇東坡急百姓所急,苦百姓所苦,籌資建立最大的平安醫院——安樂坊,不僅如此,他還請好友龐安時來坐診治病,因其種種措施,在此役中,活人無數4。他在惠州時,曾以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為名,作了五首詠藥詩,即《小圃五詠》。蘇東坡撰寫的《蘇學士方》和沈括的《良方》被后人合編為《蘇沈良方》。《蘇學士方》中的大部分內容均為蘇東坡自居黃州開始,直至儋州期間所寫1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蘇東坡在醫學上的造詣與龐安時有著莫大的關系。
在儒、道、佛等方面頗有研究的蘇東坡能與龐安時成為莫逆,除了他們有相似的愛好之外,還有一點也至關重要,即他們都有仁愛精神,作為一個醫者,仁愛是其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的必要條件。而受孔孟之道多年熏陶的蘇東坡,對其核心要義——仁愛,更是深得要意。兩個如此相像的人相遇,自是一見如故,相交甚歡。
結 語
傳統文化與中醫學,相互交融,自古有之,也是中國民族文化得以枝繁葉茂的重要方式,這一形勢在北宋尤為突出,其典型代表,蘇東坡與龐安時,就是在問疾談醫,研討醫理,吟詩作對,鑒賞書畫等進行民族文化交流活動時成為密友,這正是傳統文化與中醫學相互促進的現實表現。對當代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