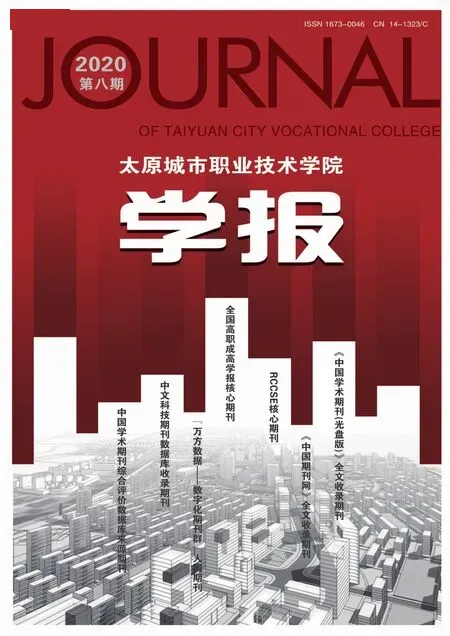陳獻章的仁心行思述略
■金 瑛
(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7)
陳獻章,字公甫,居士石齋,世稱“白沙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詩人,生于公元1428年,卒于公元1500年。他所處在明代中后期的社會轉型時期,政治上遭遇土木之變,學術上處在獨尊程朱理學的背景之下。陳獻章作為這一時代的經歷者,他發展了孟子的“仁,人心也[2]”和明道先生的“仁者以天地為一體”[9]的觀念。他把仁理解為自己的本心,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出發,主張“以道為本、心具萬理”,通過靜坐體認來自覺自身行為,并擴充引申為“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4]的自然狀態,不斷重建人的道德價值,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
一、尊親孝母:人心之仁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評價白沙先生之學說道:“有明之學,至自沙始入精微”[1]。雖程朱理學在明代居于正統官學的地位,社會思想有著一定的束縛性,但陳獻章卻能另創新徑、始創心學,這也成為明代哲學思想由程朱理學向心學演進的發端。陳獻章并沒有具體去闡明“心”的定義,而是更多地把“心”作為一個哲學修養的出發點,由此提出“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命題,即“我”就是“心”。這不僅僅是他心學本體論的基礎,也是他踐行孝道倫理的理論依據。
從中國傳統孝道來看,自從“孝”真正成為一個普遍的道德規范和基本原則后,尊親、孝親就成為了孝的主要內容。在《論語·為政》篇中,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2]“孝”在孔子看來,首先是提供給父母飲食、保證父母的溫飽冷暖,讓其無生活之憂。其次,要做到感激父母,敬重父母;如果只給其溫飽無敬愛之心又和養犬馬有什么差別呢?這就不是真的孝,而只是基礎的孝,是孝的開端。除此之外孝是有層次之分的,它不僅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更是“立身行道,揚名后世,以顯父母”[3],此是儒家倡導的孝道,自古儒家人士多數看重孝道,“在親為親”“在君為君”,皆是人性使然,又以“愛親”為大,陳獻章也是如此。
陳獻章把孝視為“愛親”的基本行為。陳獻章生于嶺南一殷實之家,他曾自述:“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于九歲,以乳代哺。”[4]他是遺腹子,他的母親早年就開始守寡,為照料兒子遭盡了苦難,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這使得陳獻章更加明孝之本,懂綱常倫理。他強調:“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4]。孝悌出于本性,不用教化而至,愛戴其親、行孝道是其他行為的始源,能通乎神明而光耀四海。陳獻章重孝道,對母親的話言聽計從。他屢次科舉不盡如人意,但母親希望他能再參加考試,盡管心中不愿他仍遵從母親的意愿。弟子張詡敘述先生古稀之年多病痛,常擔憂自己先行去世不能送老夫人終,故“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愿某后母死”[4]。在他最后一次離開家鄉去京城做官時,聽聞母親病重的消息,便當即上奏《乞終養疏》要回鄉照顧母親。他對母親的孝心是他本心自發的自覺行為,孝行是陳獻章本心意愿所遵循的“仁”。
“仁心”是人所特有的,孔子講“仁者愛人”,人心之仁是成為人的重要標志。由“仁”入“孝”,心作為道德主體,遵從孝道,就是順應“仁道”的要求。“仁”這個內在的德性在外在的表現是孝,孝是順應天道的,是實施仁的具體行為。在《論語·為政》篇中,子夏問孝。子曰:“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2]對于具體的孝來說,“非但事親一事為然”[4],而是要一以貫之;不只是“豐其養,厚其葬,”[4]還要做到“夫孝子之事其親,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4]。即行孝心應是出自真誠并發自內心地對待長輩,不能只說不做,徒有“孝”的美譽,也不應以通常的“豐養、厚葬、生封、死贈”作為孝的標準,這種人為標準的孝,只表現在外在行為而不是內在動機。“孝”應是人心甘情愿的行為,陳獻章以為人若無仁義之心,不懂綱常之理,就難稱其為人,不過是“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4],茍殘生命、知饑渴,甚至有著喜怒哀樂,懂得富貴、權勢,不外乎“禽獸”而已。以上說法,在成化庚寅年所作《東曉序》中有相關論述: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4]。
“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獸者幾希矣。”[4]
人們通過耳、目、口鼻、四肢來認識外界事物,易受到外部器官的遮蔽。如果人們能摒棄世俗事物的影響,而人心之“仁”也正是區分人和動物的重要標志。
陳獻章的孝道觀應從仁心之性中去認識,他的主張在于使人擺脫外界的干擾,讓本心之理顯露以至明理。他把教化從外在的道德規范轉化成為內在的價值要求,提倡人們以孝為仁心之本,符合“仁道”的要求去遵守孝道,這也就使得其倡導的孝道倫理建設在了家族血緣維系和個體自覺的基礎之上。
二、用則行,舍則藏:貫通本心之處世
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對其弟子顏淵談及“用之則行,舍之則藏”[2]。這一觀念成為古代儒者的處世意識。在中國古代,人們通過求取功名來獲得統治者的賞識,進而入朝做官,服務于統治者并為社會帶來穩定,使得國泰民安,有如此作為才算是光宗耀祖,實現人生價值。陳獻章也不例外,他“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4],具有儒家積極的入世思想,謀求科舉仕途。他20歲中鄉試第九名,21歲入京赴春闈,中副榜進士,進入國子監讀書,而仕途受挫,24歲會試再次下第后,陳獻章對以科舉入世達濟天下的可行性產生了“學止于舉業而已乎”的疑問,開始反思為學的最終目的。他返回家鄉、拜師求學,亦有自筑“陽春臺”,閉門不出,潛心靜坐學習古今典籍。終有一天,他著力用澄靜之心來為人處世、日用酬答,方才能“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找到心與理的“湊泊吻合處”。他曾自述這一經過:
“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師友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久之,然后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樂也。體認物理,稽諸圣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源委也。于是煥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茲乎!”[4]
陳獻章歷經“惟在靜坐”的十年工夫,使得“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此心之體”即“心體”,也是他“心體”自我貫通找尋到的根基。至此,他發現由于“心體”的顯現,事物能隨心所欲,各有頭緒來歷。陳獻章認為,這是此心與此理“湊泊吻合處”的“自得”,就正如“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4]般。這是成化二年秋,39歲的陳獻章躊躇滿志,懷揣學識,再次赴京趕考,在一次交友聚會上,國子監祭酒邢讓令其和宋儒楊龜山作詩時所作。詩中自述十多年的求學經歷,又說明其志向,此詩一出,轟動一時,朝中有人言“真儒復出也”,但此次赴京,陳獻章仍與仕途無緣。
在處世問題上,陳獻章認為主要取決于當朝者以及時勢,“時勢”是決定出世還是入世的關鍵,“時勢”使你顯,你才“顯”,不可強求而為之。其在《韶州風采樓記》中談及了對時運的看法:“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于圣人。用則行,舍則藏。……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茍哉!”[4]此篇以顏回問為邦為例,認為一個人是否有作為,與個人和社會(國家)有著一定的關系。這一認識的來源,一是孔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2]的天命觀、時運觀;二是現實來源的自身經歷(多次考取功名失敗),這些經歷成為陳獻章人生旅途中的寶貴財富,有了深切的人生體會。他還曾有在京任職的經歷,不但職位不高而且還是個苦差事,但他卻每日手捧案牘,兢兢業業地與眾官研討,不負這“時勢”給予的機會。陳獻章闡述道:“夫士能立于一世,……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于同也”[4]。“夫人之去圣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圣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4]。即使人們的“進退”之路不盡相同,人也應注重自身的修養功夫,把握主體向內求索,使仁心本性完整具足,達到身心統一貫通,進而有所作為、有所價值。
陳獻章一生幾次官場進退,都不刻意趨炎附勢,也不放棄任何一次出仕的機會,該“顯身手”時就“顯身手”,時勢不造于我時就“藏”。而“舍則藏”的重點在于藏,如何“藏”決定了“舍則藏”的性質。陳獻章所表達的是一種積極的“藏”,他隱居后雖過著逍遙自在、灑脫自如的生活,但他“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4],時刻不忘儒家修養“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茍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4],以修治其身,完具本心之仁。在隱、舍之時,陳獻章用更多時間去體認思索、塑造理想人格,用自身行動去實現人生的價值,創立了跨越嶺南地區、頗負盛譽的“江門學派”。
陳獻章靜坐體認、貫通本心中所表現出來的處世積極性還在于對功名利祿不強求,他提出:
“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人。”[4]
“儉德茍不殘,厚祿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謠渺遺情。”[4]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返。”[4]
他認為人的苦與樂不基于外在的富貴名利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敢于做真實的自己,不在人世間迷失、喪失自我。陳獻章主張通過靜坐體認,使心體隱然呈露,識得自得之樂才是人內心之真樂,體會到“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相融,時與會意,悠然而適,……死生焉得相干”[4]。這種超越物我和名利的追求,最終是希望達到“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4]般的自得之樂。
陳獻章從靜坐到靜心,從靜心再到靜思,主體在不知不覺中發現“到此境界,愈聞則愈大,愈定則愈明,愈逸則愈得,愈易則愈長”[4],體悟到人在世俗困頓中應隨時進退且不“滯于一處”。因此,他指出“圣賢處事無所偏任,惟親義何如,隨而應之,無往不中。隨其氣質,剛者偏于剛,柔者偏于柔。”[4]即處世應不偏不倚、合乎中道,使柔者不偏向柔,剛者不偏向剛。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處事要做到“隨而應之”,須用本心去“理會氣象”,故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4]。只有審時度勢,理會氣象,才能使事務處理得體,又能使自身免于禍難。也就是說,陳獻章把外部氣象好壞看作是重要的,但同樣沒有忽略人之本心對氣象的“理會”和把握,體現了他處世態度上對內部人和外部環境統一的追求。陳獻章退隱修身、傳道授業,符合他靜坐體認的心性功夫涵養,是其自我體悟、本心貫通后的精神狀態和生命境界的表現。
三、率乎自然:生生境界之仁
《易傳·系辭》上講:“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這是儒家宇宙生成論之基,是儒家思想的仁學精神根基[10]。仁的最高層次在于追尋天地萬物具為一體,即天人合一的境界。陳獻章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主張“惟仁與物同體”[4],以天道之仁為本,行仁踐義源于生生不已經之天道,強調“以道為本”,并認為道“無心”,故謂之“以自然為宗”。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價白沙先生之學,說道:“先生學宗自然”,是故其“道本自然”[1]。弟子湛若水也對先生的“自然”做了解釋,曰:“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于天然,故曰自然也”[4]。自然是不需任何外力的化化生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切無非“鳶飛魚躍”,合乎規律的存在和發展。在他看來,“一痕春水一條煙,化化生機各自然。”[4]“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4]認為自然界中,草木有枯榮,生死以及萬物的變化都是自然現象,一切都“化化生生”任其自然。“道”是宇宙之本,心外無理。陳獻章強調加強自身修養,使心中之理呈現出來,達到心道合一的境界。他說:“此理(道無邊無際)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連。……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又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都是鳶飛魚躍。”[4]這番景象與其說是他對理的新詮釋,不如說是自得于我的境界論體驗,體現著陳獻章對人之本心的高度認同和弘揚。在他看來雖客觀世界紛繁復雜,但只要做到“心具萬理”,就可以達到道心合一的涵養境界,自我得之、自我樂之。陳獻章把“自然之樂”視之為真樂,以自然為宗,強調“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4],且以此作為人生最高價值的追求。他認為如果達到了“真樂”,就能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超脫出來,忘卻得失、灑脫自如,保持自然本性去尋求“自得、自樂”的理想境界。于是他“或浩歌山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得健步上崢嶸,萬里直見滄波橫。更馮猛手碎嵯峨”[4],放情于山水,逍遙于自然,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追求人與自然的統一。他側重心體的內省,保持個人和天地自然同體,通過體認自我的本真狀態去行踐,追求人與自然高度契合的精神境界。他提出要“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于俗,斯可矣”[4],提倡依照人的心性自然地處世言行,不受制于俗世的壓抑和約束。世間萬物的存在都是自然的,天地萬物乃至宇宙都無法超出道所規定的范圍而獨立存在,而人之本心將在宇宙中無限存在。這點在《示湛雨》的書函中有著十分形象的表述,“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4]他承認客觀事物真機活潑、化化生生之規律,歸納出“心具萬理”的論斷,主張主體求之于此心,才會有所自得,最終將“道”呈現出來。
另外,在陳獻章體驗“無累于外物,無累于形骸”的生命行踐過程中,飲酒也是他達到這一目標的寄托方式。他在《春日寫懷》之二中,寫道:“一殤復一曲,不覺夕陽殘。好景只我醉,春風人未閑。青紅今滿路,風日來登山。何日海日鳥,鼓翅蓬萊間。”[4]在姹紫嫣紅的山林之中獨自暢飲,不覺夕陽已至,在迷醉之中自己變成海鳥展翅飛往蓬萊仙境,進入了逍遙的自得境界。這樣的自得又能有誰與之相及!為了表達這種追求精神自由,追求“狂”的境界,他“去年對酒人面紅”[4]又“盡數籬邊菊,一花拈一卮”“只許木犀知此意,晚風更為盡情香”[4],有著詩人狂放豪情。他通過飲酒,使生命氣質在酒的激勵下得到縱情的釋放,飄飄乎而循然自得,獲得了人與自然一體的心靈自由。他的意境亦然從詩作上升到人生哲學的意境,因而得趣于心之氤氳,“蓋其得趣于心之氤氳,以心之玄為酒之玄;真樂何從生,生于氤氳間。氤氳不在酒,乃在心之玄”[4]。在此,可顯露出陳獻章既充滿責任感,能夠踐履審慎,鑄就了理想人格的范本,又能與自然合為一體,勇于追求人生之真樂。
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陳獻章溘然辭世,為他七十二年的坎坷人生畫上了句號。他主張要有仁義道德之心,強調“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正”[4],而不由外界所強加的意志決定。在他看來“仁”即是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天道自然流行,化生萬物的本性。他主張通過靜坐發端本心之仁,使人之本心與整個自然界關聯起來,實現整體的普遍生命聯系,以此修養方法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境界中踐履實踐,在“靜者識其端,此生當乾乾”[4]的精神狀態下追求統一圓滿的人生理想。
陳獻章一生致力于內圣外王之學,其個人經歷、自身修養、文章作品等,足以展示他的仁心行思下“鳶飛魚躍之機”的生命境界,有著自己所要追求的內心之所向。他尊親愛孝的倫理觀、本心貫通的處世觀、化化生生的境界觀都致力于人性的改善和思想的進步,我們能從中體會其思想主張對生命體驗的影響,對當今社會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