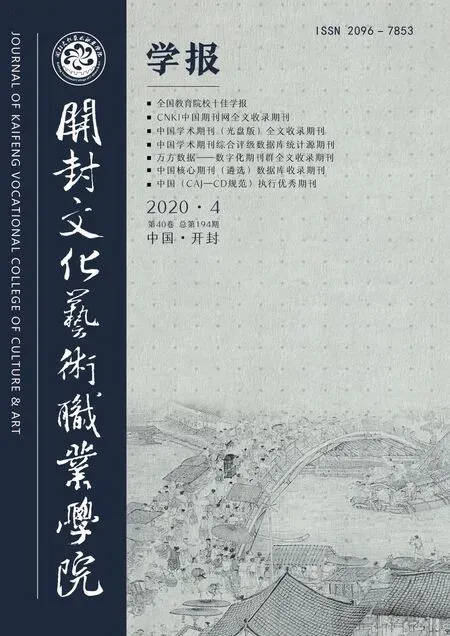王士禛與元好問論詩絕句的比較研究
謝一鳴
(西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一組結構比較完整的論詩絕句,詩人成功發掘了論詩絕句的體制潛能,在論詩絕句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翁方綱的《石洲詩話》、宗廷輔的《古今論詩絕句》、郭紹虞的《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等中都有相關論述。王士禛的《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這組論詩絕句雖是效仿遺山而作,卻也顯現出其獨特的詩學思想和藝術風格。兩組詩都經常被四庫館臣用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為引論,有一定的相關性和差異,卻少有學者作進一步分析。筆者將從創作背景與動機、創作技巧與藝術風貌、詩學主張三方面對比分析這兩組詩,以期彌補這一空白。
一、創作背景與動機
在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題下,詩人明確指出寫作時間和地點為“丁丑歲三鄉作”,也就是金朝興定元年(公元1217年)。當時詩人28歲,避兵于福昌縣三鄉鎮,雖偏僻,卻是亂世中的一時安穩之地,還有趙元、李汾、英禪師等一眾詩人聚集在這里。他們經常舉行詩會,游吟酬唱。在當時的詩壇上,元好問已經嶄露頭角。當時的文壇盟主趙秉文極為稱贊稱他的《箕山》《琴臺》等詩:“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而王士禛的《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作于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九月間,即王士禛29歲之時,是其任揚州推官的第4年。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舉行歌詠集會,如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與陳維崧、陳允衡、蔣階等人泛舟紅橋,相互唱和。此外,他結交了一批在當時具有影響力的江南詩人,如錢謙益、林古度、冒襄等。兩組論詩絕句都是詩人初登詩壇,與文人集會酬唱時探討詩藝的產物。
在這兩組論詩絕句中,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的創作動機比較明確。詩人第一篇便指出“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1]58。宗廷輔在《古今論詩絕句》中道“此自伸其論詩之旨也”,可見詩人是以“疏鑿手”自任而創作的這組詩,意在繼承杜甫“別裁偽體”的精神。詩人最后一首又道“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1]84,既有自謙之意,也自覺創作此詩有“書生技癢”的輕狂。而在王士禛這組論詩絕句中,詩人仿若置身事外,客觀地對歷代作家作品點評議論,但從詩人的選材和個別詩句中也不難發現其創作的意旨和態度。詩人在選材上傾向于山水詩人或呈現出淡雅清新風格的作家作品,盡量避免選取沉郁雄渾、現實深刻的作家作品進行評價,這和詩人在這一時期積極結交江南遺民詩人的行為不謀而合。作為一個清初統治者與遺民詩人之間的調節劑,作為一個有性情有風雅的詩人,王士禛的選材傾向既符合統治者的期望,也能夠贏得遺民群體的認同。同時,王士禛這組論詩絕句顯然掙脫了清初詩壇唐宋詩學的桎梏,論及明詩的數量幾近一半,難得的是,他對元詩和民歌也未曾忽略。詩人對元、明及民歌的品評可以看作是對清初詩壇補偏救弊的自覺行為,也表現了他力圖摒棄偏見、博采眾長的目的和態度。
二、創作技巧與藝術風貌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大量運用了對比、設問、比喻、引用等修辭手法,擴大了論詩詩的內容,增加了詩歌的藝術性和形象性。如第22首引用德誠和尚“一波才動萬波隨”比喻蘇、黃詩歌的新奇,使詩歌形象生動,末句的發問則意味深長,引人深思:翁方綱認為是“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于論蘇、黃發之”,有“力爭上游”之意;潘德輿則謂“明以滄海橫流責蘇”;宗廷輔以為“變本加厲,咎在作俑”,雖責蘇、黃而更重防弊。在元氏論詩絕句的基礎上,除了上述修辭手法之外,王士禛在詩歌中大量增加了用典的手法。第1首“巾角彈棋妙五官,搔頭傅粉對邯鄲”[2]325中“巾角彈棋”出自《世說新語·巧藝》,在這里指魏文帝曹丕,和后兩句中的“風流濁世佳公子”[2]325曹植進行對比。此外,還有第2首“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有千秋幼婦詞”[2]325中的“幼婦詞”與第13首“詩人一字苦冥搜,論古應從象罔求”[2]336中的“象罔”等。除了對比、設問、比喻、引用等修辭,王士禛擅長通過用典來增加絕句的內涵,形成有張力的空間,同時激發人的聯想,引人深入思考。
兩組詩雖然在創作技巧上沒有太大差異,卻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藝術風貌。筆者認為,這與兩位作者所處的環境及他們對詩歌創作的獨到見解有關。元氏寫作此詩時是金興定元年(公元1217年),當時金朝占據北地,且各民族在此交流融合。元氏自身就是鮮卑族后裔,山西忻州人,一生大多數時間活動在山西、山東、河南等地,在這種北方民族文化土壤的滋養中,他的這組論詩絕句呈現出明顯的直爽率真、自然清新的北方特質。此外,其詩歌的藝術風格也是主壯美、尚自然,如他在第7首中所道“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1]63。清朝同樣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卻是一個統一的王朝,與宋、金對峙的局面畢竟不同。王士禛雖是山東新城人,也屬北方,但寫作這組詩時正值他任揚州推官期間,輾轉于江南各地。在與江南詩人結交來往之后,王士禛本就清遠沖淡的詩風更加古澹含蓄。在詩歌的藝術風貌上,王士禛追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他的這組論詩絕句也正是渾然天成、富有神韻。
三、詩學主張
元氏與王氏的這兩組論詩絕句涉及的詩學理念都比較廣泛和細致,筆者就兩位詩人在詩學主張上的主要異同進行討論。在對唐宋詩學的態度上,元氏近唐而微貶宋,王氏則顯現出兼容并包的態度。元好問在《小亭集引》中認為唐詩是“絕出于《三百篇》之后者”,可見其對唐詩的推崇。他在這組詩中論及宋人宋詩的僅有6首,且態度顯而易見,第27首不滿元祐以來蘇、黃等人的變古,第28首更是直言江西詩社之弊病。而王士禛在這組詩中則表現出對唐、宋詩學兼容并包的態度。王世禛初操唐音,晚年自述“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3]163,但這個轉變絕非一蹴而就的。從這組論詩絕句中可以發現,他寫作這組詩時就已經不全然是宗唐的主張了。正如王世禛自己所言,這時他已“眼見宋元詩”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差異是兩人對于韋、柳詩歌的看法。元好問第20首云“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1]72,可見其對柳宗元詩歌的喜愛。與元好問以柳繼謝的看法不同,王士禛傾向于以韋繼陶,認為柳不如韋,他在論詩絕句中說:“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蘇州?”[2]332那么為什么王士禛如此推崇韋應物,認為柳氏不如韋氏呢?這要從兩人詩歌的選景和情感表達兩方面加以分析。在選景上,韋應物偏重于山水清幽雅致的一面,柳宗元則多選取景物空寂冷峻的一面入詩。在情感表達上,韋應物比較含蓄委婉,而柳宗元更加直接激越。所以胡應麟認為韋應物“清而潤”,柳宗元則“清而峭”。顯然,韋氏的詩歌在情和景方面都更貼近于王士禛的審美。
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認為元氏30首論詩絕句“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雖不一定準確,但就這兩組詩來說,兩人在詩學主張上也確有相近之處。在作家的人品論上,元好問和王士禛都認為詩人的人品非常重要。王士禛在第20首中道批評了嚴嵩這樣應制獻媚的詩人,借“青詞”諷刺他格調低下。元好問第6首則對潘岳在《閑居賦》中顯露的高潔與事實上的“拜路塵”行為進行批判。除了對詩人人品的看重,兩位詩人同有尚妙悟的詩歌主張。王士禛認為,作詩寫文應當有所感悟而自然成章,所以他贊揚何景明“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2]342。元好問第11首云“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1]67其也在說明詩人興會、靈感的作用。
結語
王士禛的《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與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有一定的相關性。第一,兩位詩人有著相似的創作背景,但元好問是以“疏鑿手”自任來品評由魏晉到唐宋歷代有特點的作家作品,而王士禛是以博采眾長的態度自覺地對清初的詩壇補偏救弊。第二,兩人在創作技巧上也大多選取同樣的修辭手法來擴大絕句的容量,但在藝術風貌上,元氏更加率直清新,王士禛則顯現出古澹含蓄的風格。第三,這兩組論詩絕句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人的詩學主張上,元好問表現出近唐的傾向,而王士禛更多的是一種兼容并包的態度。在具體的對柳宗元和韋應物的態度上,元好問比較推崇柳宗元,韋應物的詩歌則更貼近王士禛的審美標準。比較這兩組論詩絕句能夠使人們對元氏和王氏的詩歌風貌和詩學思想有進一步的認識,也能夠加深對論詩絕句的理解和把握,填補對論詩絕句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