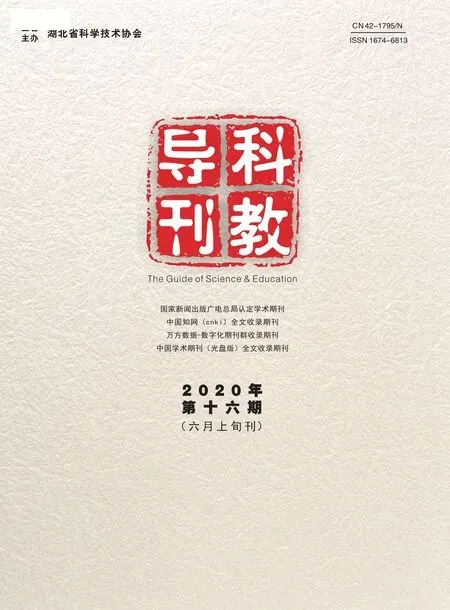李元陽碑刻文獻初析
羅 諾
(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大理 671003)
碑刻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國自古就有刻石記事的傳統。碑刻文獻由其于制作的特殊性,與紙質文獻相比極少出現誤、訛、脫、偽等現象,因此具有極高的原始性與真實性;碑刻文獻能從側面展現一個時代的社會歷史文化。對明代大理白族文人李元陽碑刻文獻的整理研究有利于豐富李元陽研究的成果以及深化拓展云南少數民族的地區文化。
1 李元陽生平及思想概述
1.1 李元陽生平簡介
李元陽生于1497 年,卒于1580 年,大理府太和縣人;自幼喜愛讀書,二十歲成為郡學生員,求學期間廣泛涉獵各類書籍,尤以儒家經典為好。
自明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開科取士以來,李元陽于嘉靖壬午年鄉試,中云貴兩省第二名;嘉靖丙戌年會試登榜,為三甲進士。政治黑暗加之李元陽剛正不阿的性格使其仕途坎坷。在“大禮議”之后,他就因為得罪權貴被貶為江西分宜縣令。后因抵御海盜有功、斷案公正而被當地百姓愛戴便遷戶部主事,后升遷為御史。但因多次得罪大學士夏言,便被“大學士于行在補公荊州”①,借機將其調往湖北荊州,任荊州知府;到荊州后便修筑堤壩,治理水患。嘉靖辛丑年因父親去世,李元陽便辭官歸隱,據史料記載其辭官之日當地百姓“遮道泣送,數日不絕”。②
回到大理之后李元陽沒因官場失意而丟掉社會責任感,他在修建橋堤道路、編寫府縣志、重建崇圣寺三塔等諸多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李元陽一生走過許多地方,交游也十分廣泛。與楊慎、楊志云、張居正、李贄等諸多名公、前輩、文學名家關系甚好。楊慎稱贊其“蜚英早歲謝臨川,高興歸來李謫仙”。③李元陽自身也留下了諸多文學作品“所著有《中溪漫稿存稿》《艷臺雪詩》等書,行于世”。④
1.2 李元陽理學思想概述
明王朝在邊地的一系列措施,推動了邊疆地區對中原王朝文化認同的步伐。隨著中原文化的傳入,云南地區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并行的現象。李元陽思想的形成與個人經歷和當時云南思想文化的發展狀況是分不開的。
李元陽理學思想的形成主要在他辭官回鄉之后。因為性格的原因李元陽仕途坎坷,當時的知識分子擺脫痛苦煎熬的最好藥方就是“理學”,加之他與中原士人、理學家交游甚廣,因此,他在歸鄉之后“家居四十馀年,精研理學”。⑤
李元陽的理學思想境界十分宏闊。他將佛、道思想融入到儒家思想當中,在詩歌中也表達了“三圣本一初,至理無中邊”⑥的三教合一融合的思想。他的理學著作《心性圖說》具體分析心、性、意、情四者,提出了一套融合儒釋道的心性說,是其理學思想的集中體現。李元陽認為“性”是本體,“心”“意”“情”是“性”的流變,所以產生了“惡”,心性論思想體現了儒學的主導地位,是“授佛入儒,以儒為本”⑦的做法。
李元陽借鑒道家的養氣也學習佛家的救苦度厄、修身養性。他將佛、道、儒三者相融綜合運用到社會實踐和個人修養上。
2 李元陽碑刻文獻的分類及主要內容
李元陽現存碑刻文獻共33 通,主要收錄在《云南叢書 中溪家傳匯稿》《大理叢書·金石篇》等文獻中。其中《云南叢書中溪家傳匯稿》中收錄20 通;《大理叢書 金石篇》中收錄6 通;《鶴慶縣志 地理志》中收錄3 通;其余4 通分別收錄在《大理叢書 中溪全集》《浪穹縣志略 藝文志》《云南縣志 藝文志》《大理文化》中。
毛遠明將碑刻分為“記事贊頌”“哀誄紀念”“祠廟寺觀”“詩歌散文”“圖文”“應用文”“石經”“題名”“特殊”⑧九大類;張正明科大衛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中,將碑刻分為“農林”“商貿”“交通”“水利”“婦女”“官紳”“家庭”“鄉約民規”等十七類;⑨卞利將碑刻分為“宗族”“公益事業”“人物”“文化教育”“宗教”⑩五大類,本文結合上述文獻中的收錄情況,根據李元陽碑刻文獻的具體內容,參考上述分類,將收集到的李元陽碑刻三十余通,大致分為哀誄紀念類、記事贊頌類、祠廟寺觀類三大類,主要集中在哀誄紀念類,現簡述如下:
2.1 哀誄紀念類
主要包括墓志銘、墓表等,此類碑刻有25 通。
明代后期,社會階級矛盾尖銳,但是李元陽有著儒家“修身齊國治天下”的民本思想,他呼吁“以德治國,造福于民”,他認為“節用愛人,己任其勞”方為“德者”。 面對黑暗的政治,李元陽剛正不阿,不趨炎附勢,敢于與黑暗官僚勢力做斗爭,即使在辭官歸鄉之后仍然憂國憂民,基于此民本思想,李元陽所銘表之德人、義士、鄉大夫多為忠于人民、至誠惻怛的父母官:《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墓表》中記錄了禮部尚書楊一清與玩弄政權的閹人劉瑾之間的斗爭。正德年間,太監劉瑾掌控大權,“國事惟其意指而已,危亂之機已在旦夕”,劉瑾不僅內批罷免楊文襄職位還企圖將其逮捕入獄,楊文襄不忍見天下因閹黨大亂便“日夜籌度,不遑寢處”,]最終借安化王反寧夏一事將劉瑾誅殺;《參議石溪潘公墓表》記載布政司參議潘瑞生平。當時總督武定人郭勛手持大權,氣焰熏天,趨附郭勛者多蒙重賞,得金銀,但是潘瑞“持廉秉正,方抵阿附之徒”;《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所載唐子才始任平陽縣知縣時,就常問民生疾苦,大修水利,能忠于國也能孝于家,可謂“君子愛之,小人畏之”。
在明代黑暗政治環境中,士大夫想在痛苦煎熬中求得解脫,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種值得信仰的精神支柱來得到心靈的解放,李元陽是在理學中尋求解脫,借道家之氣,學佛家之法。觀之其所銘所表者,大有醉心道教自然之道、不追求權勢的尋道之人:《大明奉直大夫知四川潼川州事張公墓表》中張鳳羽秉持“三十不第不再試,四十不仕不趨名,五十不歸貪夫徇財,六十不休眾庶馮生” 的人生觀;《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中唐子才辭官歸鄉后,便談玄講道,言做官之倦,在家“衣布茹淡,散發不櫛,恬如也”;《書淑洲楊君墓版》中講述楊淑洲昔日為父母而做官求升合之祿,后因父母去世便辭官歸鄉,不再仆仆于車塵之中;《建昌教授東山張公墓志銘》中記載張仲衡是“游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 的神仙人……正是因為嚴酷的政治,這些士大夫不再追求在萬馬齊喑的政治環境中有所建樹,而開始成為醉心自然的尋道之人。
2.2 祠廟寺觀類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祭祖,天神、地祗、祖宗特別受到尊奉,封壇、建祠、立廟是極其鄭重的事情,隨之便產生出許多神祠、神廟,同時也產生出大量神祠之碑。 大理作為妙香佛國,自然有著數不勝數的祠廟寺觀,相應的碑刻也就隨之產生,李元陽碑刻文獻中,此類碑刻共有4 通。
隨著中原文化的傳入,大理地區流傳的佛教與中原傳入的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三教寺就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產物。《點蒼山玄真觀碑》記載了玄真觀(即中和寺)的建設過程,玄真觀始建于嘉靖四十五年,隆慶二年建成, 本位于大理城中,因“與人居雜處,喧囂濁穢,神所不歇”,于是李元陽擇點蒼山中和峰,用時三年修了這座新玄真觀。在這座寺觀中,同時供奉著道教神像和佛教神像,這就是大理地區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三者交融的產物。除此之外,《玉皇閣創建碑記》中記載玉皇閣創建過程,提到“至謂儒釋道之為三教,本乎一理” 也是大理地區三教并崇的體現。
明代初期,雞足山佛教文化開始興盛,到明代中后期更是全山無處不僧,這一時期,雞足山佛教文化景觀十分豐富。《寂光寺碑》記載寂光寺陳設、修建等情況。寂光寺位于雞足山,初名花椒庵,嘉靖初年奸黨為報殺子之仇將寺廟摧毀,禪詩本帖同楊舟等人于嘉靖三十七年重修。
《普淜三元宮碑記》記載姚安普淜三元宮的建造過程。嘉靖初,費玉鳴始建西山三元宮,但因年代久遠,在楊楠的倡議下,眾人買田拓土籌款重建此宮并新修觀音閣于殿后。
明代漢文化在大理地區通過多種渠道傳播,衛所制度的推行、商業貿易的發展、官學的設立以及中原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開科取士等措施都促使漢文化迅速進入大理地區,對漢文化的學習、吸收、采納成為白文化不斷發展的自覺與不自覺的意識和實踐。 基于此背景,大理地區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出現是中原文化與邊疆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中原王朝對邊疆有效治理的措施之一。
2.3 記事贊頌類
記事碑銘中記錄的各類歷史事件,大者如:征戰、典禮、民族交往等;小者如:建祠興學、治水開渠、修橋鋪路等。“無不伐石立碑,撰文以記之。或自敘個人之事,或記他人之美,或紀國家之功”。 李元陽碑刻文獻中此類碑刻有5 通。
明中葉以后,地方土官與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銳,在此情況下,明中央開始了改土歸流。但在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原王朝與土司政權常常有意志沖突,武定府的改土歸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云南平諸夷碑》一碑正記載了嘉靖年間云南地區改土歸流中的武定府鳳氏叛亂,其后又相繼有姚安高鈞、易門王一新叛亂,終被呂光洵平定后,改為流官。
《平夷寇碑》記載萬歷元年鄒公奉皇帝之命剿除夷寇一事,當時云南的賊寇西有鐵索、赤石崖;東有獛蝲。鄒公從十月至此次年二月,先后剿滅東西賊寇,其間還利用余糧設戍守、作城垣、建署宇,李元陽銘碑贊之。其余三通《大理造輿梁碑》《榆水龍關碑》《鶴慶軍民府城碑》分別撰之以頌王希元因地勢水勢之所宜修筑二橋;大理在山水交處建龍首、尾關;鶴慶由郡到城的轉變及建造過程三事。
明代白族的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考試融入上層社會,以此改變了自身及民族的命運。因此他們大多關心社會和人民,發掘和提升地方民族文化。李元陽對平夷寇、筑橋、建城等事件的立碑撰文以贊頌充分展現以李元陽為代表的白族精英對邊疆民族地區穩定建設的關心和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認同。
3 李元陽碑刻文獻整理研究的價值
目前學術界關于李元陽本人的研究較為全面,對其生平事跡、文學成就、思想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前人對于李元陽的研究,更多使用其詩文資料而較少關注碑刻文獻。李元陽碑刻文獻中所反映出的明代社會風貌和士人氣節,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正史的不足并豐富相關研究的史料,如對改土對流中武定府風繼祖叛亂的記載,可為研究明代云南地區武定府的改土歸流提供史料。
碑刻文獻作為金石的一種,是與契約文書等同等重要的原始文獻,通過整理研究,有利于豐富對李元陽研究和對碑刻整理的成果同時對于弘揚地方文化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通過對李元陽碑刻文獻的初析可厘清李元陽思想在云南地區的傳播的具體途徑,對于認識白族文哲發展史和尋求少數民族中華認同思想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意義。
最后,從現實意義來看,該研究有利于促進漢族和白族等少數民族之間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認同,對于構建云南和諧的民族、文化關系和弘揚和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有一定現實價值和意義。
注釋
①② 明故賜進士通議大夫荊州知府盡資治尹前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李文肅公墓志.李元陽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590.
③ 楊慎.贈李中溪.李元陽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595.
④⑤ 劉文微.滇志·人物志·李元陽.李元陽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591.
⑥ 李元陽著,施力卓總校編.李元陽文集·詩詞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213.
⑦ 李松松.明代理學對白族哲學思想的影響——李元陽心性圖說新釋.2015:13.
⑧ 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9.
⑨ 張正明,科大衛.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