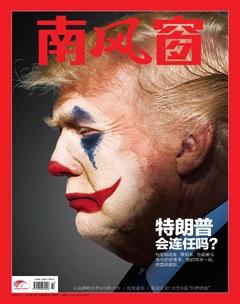莫西子詩 故鄉像莎士比亞一樣
尤丹娜

初見莫西子詩,他正在吃一碗米線。
2019年的北京冬日,氣溫接近0℃。這家云南菜館就在莫西子詩家附近的商場里,很普通,寫著菜品和價格的結賬單隨意地攤在桌上。他戴著一頂草帽,留著胡須,標志性的黑框圓眼鏡上有蒸騰的食物熱氣。
看我來了,打了個招呼,他又趕快把自己的注意力收回到面前的碗里,草草吃完剩下幾口,像個被午休結束時間圍追堵截的普通上班族。
“你吃魚腥草嗎?”莫西子詩忽然問我。緊接著,他介紹說,這是他老家的一種口味奇特的食材。伴著這段對話的是菜館里此起彼伏“請您接單啦”的外賣提示音,讓我恍惚間生出一種是在和朋友對坐聊天的錯覺。
“莫西子詩”,彝語中是“太陽光芒”的意思。2014年,在《中國好歌曲》的舞臺上,彝族歌手莫西子詩將俞心樵的詩作《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譜曲并演唱。詞曲驚艷震撼,一度成為大熱金曲,人們折服于他的動情演繹,追逐窺探他的個人生活。
但此后,他相繼發行《原野》《月光白得很》兩張專輯,都沒有收錄這首紅極一時的“血腥情歌”,而是以頗有門檻的彝語、詩歌為詞,以大眾極為陌生的口弦聲、吆喝聲為旋律,專心吟唱屬于彝族的聲音。
與“規避大熱金曲”一致的,是他不喜歡接受采訪。但只要應下來了,開口時,就會分外真誠。
比如現在,他特意從桌對面起身坐到我旁邊的椅子上,“這樣聊天會聽得清楚一點”。我放好電腦回過頭,便撞進一雙誠摯的眼睛。
“阿杰魯”
阿杰魯,彝語中是“不要怕”的意思。
那是2008年,一個尋常走在下班路上的時刻,莫西子詩忽然發現自己會寫歌了。不會五線譜、不懂樂理的他,腦海中忽然蹦出一段旋律—有個聲音對他吟唱,是“雨又下了,風又起了,一年又一年”的意思。緊接著,一句“阿杰魯”被漸漸放大,占據了整個腦海。
彼時,莫西子詩已經走出家鄉涼山彝族自治州多年,在北京相繼做過幼兒園老師、導游、翻譯、公司職員等不同職業。觸角越多,在這個巨型城市中輾轉的不安感愈盛。“是不是該回家了?”
他想要退縮,但這段旋律留住了他。
“千千萬萬人都在走音樂這條道路,怎樣證明是‘你?對我來說最寶貴的就是彝語。”彝語是莫西子詩的“錨”,是被人潮淹沒時確認自己來處與歸途的“很真實的感覺”。
“風起了,雨下了,蕎葉落了,樹葉黃了……”這首由莫西子詩獨立創作的第一首彝語歌曲《不要怕》,在發表5年后通過《中國好聲音》的舞臺被大眾熟知。副歌部分反復吟唱的彝語“阿杰魯”像是輕柔的搖籃曲,安撫著人們驚悸的靈魂。
突然涌進腦海的“阿杰魯”其實有跡可循。
從小,“旋律”便是莫西子詩生活的組成部分—彝族祭師畢摩在儀式上的念白、民族節日中的彝語“說唱”、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民族樂器、老人農閑時撥弄的口弦……“不覺得那是音樂,就是日常”。
初中的時候,彝族原創音樂組合“山鷹組合”來莫西子詩所在的學校演出。三個人抱著吉他,彈琴唱和聲。莫西子詩從沒見過這種表演形式,演出結束后,他跑去問別人:“那個發聲的東西是什么?”
別人告訴他是吉他。20世紀90年代的大涼山,吉他頗為罕見,全校只有一個師兄擁有唯一的一把。莫西子詩就每天追著他,跟他學習一些簡單的指法。
在莫西子詩看來,這是自己真正的音樂啟蒙。骨子里流淌的彝族血液和學生時代簡單的吉他指法,共同構成了他最初的音樂世界。
《不要怕》之后,彝語成為莫西子詩音樂的重要標簽。
最近,莫西子詩又發表了一首彝語新歌《阿依阿麼咕》。“阿依阿麼咕”是“媽媽我愛你”的意思。“彝族人從不會直接去說‘媽媽我愛你的,他只會做一些內斂的自我表達。”在莫西子詩眼中,彝族一直是很含蓄的民族。所以在這首歌里,莫西子詩用彝語這樣唱:“媽媽,我要去到最高的山頂,去把最茂盛的那些樹枝都砍來給你燒;我要去到那河邊,去把最清澈的水都舀來給你喝。”以此來表達彝族人說“愛”的方式。
“千千萬萬人都在走音樂這條道路,怎樣證明是‘你?對我來說最寶貴的就是彝語。”彝語是莫西子詩的“錨”,是被人潮淹沒時確認自己來處與歸途的“很真實的感覺”,他想了想,又再次補充,“不是感覺,是如同一個物件,它真的存在”。
一年又一年,有收獲也有失去,生活總在變化,但彝語始終在那里,是“不要怕”的溫柔安撫,也是不斷涌現的靈感與生機。
“就像那首詩說的那樣”,莫西子詩用略顯生硬的普通話背誦著:“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針尖上的蜂蜜”
莫西子詩確實很喜歡詩。
“詩歌是文字語言中比較高級的一個表達方式。”在他看來,那些作為“漢語不太好的少數民族”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的感受,詩歌都可以言簡意賅地表達。
以詩歌作品作為歌詞,也是莫西子詩音樂作品的一大特色。
彝族特色音樂作基底的“迷幻山歌”遇到寓意無窮的現代詩,往往會碰撞出更遼闊的詩意。莫西子詩的成名作《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歌詞便來自詩人俞心樵的同名詩。
當年,這首歌出爐,作家桑格格在網上評論道:“莫西子詩的淳樸凈化了俞心樵的瘋狂,俞心樵的瘋狂深刻了莫西子詩的淳樸。”
含蓄害羞的彝族人莫西子詩寫不出“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歇斯底里,但借著詩歌的羽翼,他可以在旋律里剖白自己暗流涌動的愛意。
“月亮在深夜照亮了一切的骨頭”。在北方籍詩人的這句詩里,莫西子詩找到了大涼山的月光。最終,莫西子詩用高亢清亮的旋律演繹了這首冷寂的詩,他質樸蒼涼的嗓音為這幅夜色披上一層悲憫的外衣。
2018年,莫西子詩發行專輯同名曲《月光白得很》,歌詞來自東北詩人王小妮的同名詩。第一句是“月亮在深夜照亮了一切的骨頭”。
讀起這句時,莫西子詩想起了自己在涼山州螺髻山下度過的童年。那時,他每天上學總要走上五六公里才能到學校,清晨離開家時,天還黑著,只有銀白色的月光淺淺地照著前路,也照亮了遠處如黑色骨頭的連綿山脈。
在北方籍詩人的這句詩里,莫西子詩找到了大涼山的月光。最終,莫西子詩用高亢清亮的旋律演繹了這首冷寂的詩,他質樸蒼涼的嗓音為這幅夜色披上一層悲憫的外衣。
莫西子詩提到他正在籌備的下一張專輯。里面還將有一首歌,歌詞來自云南詩人雷平陽的《親人》: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它省,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因為其它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因為其它鄉,我都不愛。
“這聽起來太普通了對吧?”可再讀幾次,置換成自己的故鄉,莫西子詩就輕易地找到了共情,“我只愛我寄宿的大涼山,因為其它地方我都不愛;我只愛我寄宿的村子,因為其它地方我都不愛。”
大涼山……
只要說起大涼山,“漢語不好”的莫西子詩也會變成“話嘮”,略帶急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為心愛的大涼山構想很多種未來。
每次回家,看到那些與他兒時一樣在山路間奔波的小孩,莫西子詩會很自然地想“給大涼山建個什么”。
于是,他發起了“荒原計劃”—“荒原”同樣來自詩歌,取自艾略特的《荒原》,但莫西子詩想表達的是“有待喚醒的土地”。從大山里走出來,他想給這里一些支持,讓它變成一片沃土。
“要建一座圖書館,又不只是圖書館,而是一個集合的藝術空間,里面有電影、文學、繪畫、攝影,甚至是舞蹈、各種各樣的音樂……讓村子里面的孩子也來接觸藝術,把我這么多年在外面見到的東西和資源帶回去,把外面音樂藝術圈的朋友也帶過去,和大涼山的人們互動,給大涼山更好的發展……”
他幾乎忘記了我的提問,兀自澎湃地說下去,手指在桌面上快速畫著圈,是一個個腦海中的藍圖。
雷平陽在那首《親人》里總結道:“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
大涼山,是寡言的莫西子詩“針尖上”的那一口甜。
故鄉像莎士比亞一樣
大涼山也總會變的。
莫西子詩最近一次回家時,村子里到處都在修房子、搬遷,村民們正在擺脫相對原始的狀態,住進整齊的新房,也將有更好的衛生條件。
只是不能再保留火塘了。
從前,彝族人的生活起居都是圍繞火塘展開的。圍坐在火塘的日夜、空氣中無處不在的煙火味,是莫西子詩難以忘懷的故鄉元素。
“有點惆悵,”他說,“沒有火塘之后,我總覺得好像什么東西斷了一樣。”所以,每次回到大涼山,他會特意和朋友們帶著食材到很高的山上,用過去有火塘時的烹飪方法野炊。
為了把那“斷了的東西”接起來,莫西子詩還特地去拆遷的地方撿了很多有火塘時才會用到的瓶瓶罐罐,搭了一些木臺子,把搜集來的物品用線懸掛起來,制作成了一個簡單的裝置展。參觀展覽的人,既可以欣賞這些物件,了解彝族人的傳統生活,也可以用發放的小木棍在這些器物上敲敲打打,聽它們的“回聲”。
莫西子詩就像一只鳥,他飛出了他的巢,看到了更高遠的天空,想要去探索更寬廣的世界,甚至說“尋找一些東西”。尋找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像鳥兒一樣到處走啊走,最終的歸宿還是這個地方。”
這個名叫“荒原留聲”的展覽呈現了彝族人的舊日生活,也承載了莫西子詩內心深處的眷戀。他再次用背詩來表達心情:“假如我是一只鳥,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如今的莫西子詩大多數時間都在北京。北京有大涼山沒有的藝術氛圍,有新鮮的人與事為他的音樂創作提供養分。
在北京,如果想念故鄉,他會約朋友一起去吃家鄉菜,用彝語聊天。當然,還有另一種更“便捷”的方式能夠讓音樂人莫西子詩隨時回到記憶中的故鄉。
他從外衣兜里拿出彝族樂器口弦,也叫響篾—小小一只,收在一個精巧的竹筒里,伸展開的薄銅片像欲飛的翅膀。他輕輕敲擊了一下,音色蒼涼曠遠—是大山的聲音。
“它是最接近土壤的一種樂器,也是和我的特質最靠近的聲音。”在機場或車站等候,別人都在玩手機時,莫西子詩會拿出口弦來輕輕敲響,古老的故鄉遠在天邊,也近在指尖。
正如他譜曲演唱的另一首詩,俞心樵的《南方像莎士比亞一樣》,“回憶、顫栗、再一次流下淚水/我是南方的……南方南方/南方和莎士比亞一樣都是說不盡的”。俞心樵來自“南方”,正如莫西子詩來自“大涼山”—故鄉像莎士比亞一樣,是說不盡的。
莫西子詩就像一只鳥,他飛出了他的巢,看到了更高遠的天空,想要去探索更寬廣的世界,甚至說“尋找一些東西”。
尋找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像鳥兒一樣到處走啊走,最終的歸宿還是這個地方。”
要是回不去了呢?“心里面的歸宿還是這里。”
他講起了彝族的火葬—將故去的人用四根木頭架起來,抬到彝族的祭師畢摩那里,由畢摩算好良辰吉日,再到空地或森林間將肉身燃燒。
彝族的婚喪、涼山的嫁娶。即使走出這么遠,莫西子詩依舊非常篤定:“我以后也會是這樣的。”
采訪結束,莫西子詩明顯地松懈下來。他有點抱歉地向我解釋不喜歡接受采訪的原因。“我的音樂和生活都太平常了,也很少會去想那么多‘為什么,”他拿起椅子上的厚外套說,“這么冷的天,你那么遠趕過來,我怕你會失望。”
他拿出有線耳機,從凌亂的一團線里找到頭塞進耳機孔里,抖一抖理順,把手機塞進外衣兜里,戴上耳機,扣緊帽子,再次回到了他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