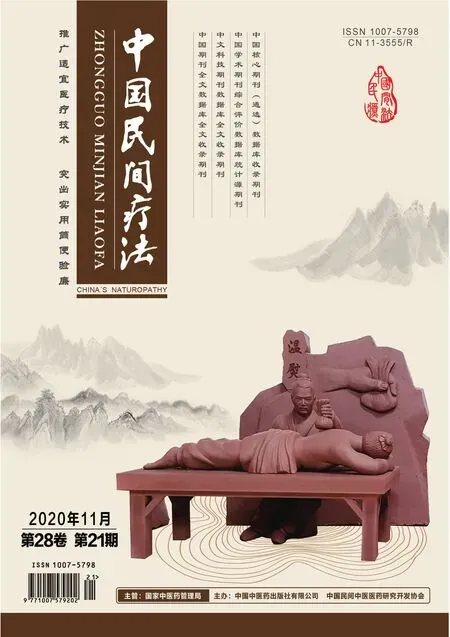附子治療復發(fā)性口腔潰瘍體會
張馨月,余海龍
(西南醫(yī)科大學,四川 瀘州646000)
復發(fā)性口腔潰瘍(recurrent oralulcer,ROU),又稱復發(fā)性阿弗他潰瘍,是臨床最常見的口腔黏膜疾病[1]。該病是以唇、舌、頰、上腭等處口腔黏膜發(fā)生的單個或多個潰爛點,伴有反復疼痛或刺激時疼痛為特征的口腔疾病[2]。該病患病率可達20%,兒童、青壯年和老年人均可發(fā)病,且常周期性反復發(fā)作。西醫(yī)認為,該病病因可能與局部環(huán)境、機體免疫等因素相關(guān),暫無特效藥物。
ROU屬于中醫(yī)“口瘡”“口糜”或“口破”等范疇。《圣濟總門錄·口齒門》載:“口瘡者,由心脾有熱,氣沖上焦,熏發(fā)口舌,故作瘡也。”目前較多醫(yī)家認為,該病中醫(yī)病機為火邪致病[3],故多從火熱論治。該病常見證型為心脾積熱證、胃火熾盛證、陰虛火旺證、寒熱錯雜證和脾虛陰火證[4]。筆者父親臨證“重脾胃、助扶陽”,治療ROU因火熱病機而復發(fā)者,強調(diào)重視陽虛病機,并應(yīng)用溫熱之附子獲得良效。現(xiàn)將附子治療ROU的體會總結(jié)如下。
1 適應(yīng)病機
1.1 中陽不足 《諸病源候論·口舌候》載:“足太陰脾經(jīng)也,脾氣通于口,臟腑熱盛,熱乘脾氣沖于口舌,發(fā)于唇,則唇生瘡而腫也。”《脾胃論》言:“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有時而顯火上行。”“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所以,若中陽不足,脾胃虛衰,陰火上炎于口,累傷口唇、膜肉,而發(fā)為口瘡。當以甘溫除熱,或溫中暖下,土厚方能降浮火。《瘍科心得集》云:“脾元衰弱,中氣不足,不能按納下焦陰火,是以上乘而為口瘡糜爛者。”《丹溪心法》言:“口瘡,服涼藥不愈者,因中焦土虛,且不能食,相火沖上無制,用理中湯。”《醫(yī)貫·先天要論下》中論及口瘡時也認為:“上焦?jié)駸?中焦虛寒,下焦陰火……胃虛谷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逆而乘之,反為寒中,脾胃衰微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景岳全書·口舌》亦言口舌生瘡,雖然上焦之熱者多,但也有因酒色、勞倦過度、脈虛而中氣不足者,不可寒治,提出“補心脾,或滋腎水;或以理中湯,或以蜜附子之類反而治之”。脾胃虛弱、中氣不足導致口瘡歷行已久,實應(yīng)重視。而究其陽虛之因,多為稟賦不足,脾胃素虛,或飲食養(yǎng)生不慎,寒涼傷脾。
1.2 腎陽虛衰 腎中陽氣不足,溫煦失司;腎失潛藏,虛陽上浮而成虛火。火為陽邪,腎經(jīng)夾系舌本,其火上炎至咽喉,耗氣傷津,則出現(xiàn)口干、咽燥但不欲多飲的表現(xiàn);上竄口腔,則出現(xiàn)潰瘍,但潰瘍反復發(fā)作,愈合慢于實熱證口腔潰瘍者。此類潰瘍多表現(xiàn)為紅而不鮮,痛而不甚,不易潰,不易斂。《壽世保元》論口瘡:“火衰土虛也,八味丸主之。若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不時而動,或無定處,若從腳起,乃無根之火。亦用八味丸。”《金匱翼》詳細論述了腎虛口瘡的病機及治法:“而腎虛之候,又有二端,一者腎臟陰虛,陽無所附,而游行于上者,宜六味之屬,壯水戀火;一者臟內(nèi)寒,陽氣不安其宅,而飛越于上者,宜七味、八味之屬,溫臟斂陽也。”《景岳全書·口舌》謂:“凡口瘡六脈虛弱,或久用寒涼不效者,必系無根之火。”《醫(yī)理真?zhèn)鳌穼⒚婺[、口瘡、口臭、目赤、耳癢等癥狀,稱為“虛火上沖”“腎不納氣”,認為是元陽外泄、虛火上炎,治之宜早,可用附子收納浮火。因此,腎陽虛的原因可有陰損及陽,或素體陽虛不足,陰盛格陽,或寒濕久侵,或食養(yǎng)不慎。
2 臨證應(yīng)用
2.1 功效 附子屬溫里藥,味辛、甘,性大熱,有毒,歸心、腎、脾經(jīng),可補火助陽、回陽救逆、散寒止痛。《本草求真》謂附子為補先天命門真火第一要劑,張錫純謂其“為補助元陽之主藥”[5]。金元時期,附子補火助陽的功效細化為以溫脾腎之陽為主。《本草備要》認為其可“補腎命火,回陽”,又能“引補氣藥以復散失之元陽,引補血藥以滋不足之真陰,引發(fā)散藥開腠理……引溫暖藥達下焦”。現(xiàn)代藥理學研究表明,附子有鎮(zhèn)痛、抗炎的作用,抗炎過程中,烏頭類生物堿起重要作用,表現(xiàn)為抑制發(fā)炎、炎性滲出、發(fā)熱、疼痛等主要癥狀的惡化[6]。此外,附子單用或復方應(yīng)用還可調(diào)節(jié)機體免疫功能[7-8]。故附子治療口腔潰瘍可能起到抑制炎癥、調(diào)節(jié)免疫的良好效果。根據(jù)上文病機分析,附子治療陽虛,具有振奮陽氣、溫陽散寒、攝引浮火的功效。明·趙獻可認為附子可治龍火上迫,引火歸元。清·張隱庵言:“凡火氣內(nèi)衰,陽氣馳于外,急用炮熟附子助火之原,使神機上行而不下殞,環(huán)行而不外脫。”
附子有毒,在應(yīng)用時應(yīng)注意炮制、把握合理的劑量和正確的煎煮方法。筆者父親臨證多選用在膽巴溶液中制過的附子,以提高口腔潰瘍治愈率。視病情劑量取20、50、100 g不等,分別煎煮30 min、1.5 h、2 h左右,煎煮過程中不加冷水,全過程用開水煎煮。陰虛、實熱體質(zhì)患者不宜用,以免加重病情。
2.2 配伍 基于陽虛型口瘡的病機特點及病位,附子還需與不同的藥物配伍才能更好地發(fā)揮療效。總的說來,主要是與調(diào)整中焦陽氣的理中藥與攝納下焦元陽的溫腎助陽、引火歸元藥配伍。
(1)理中藥 常配伍人參、白術(shù)、甘草、黃芪、生姜、柴胡、升麻等具有調(diào)理中焦的藥物,適應(yīng)于脾胃虛弱、中陽不振,甚至脾陽虧虛者,可以起到振奮陽氣、散寒除濕、消散陰火的作用,同時也有防“甘溫除熱”之意。《丹溪心法》言:“口瘡,久服涼藥不愈者,因中焦土虛,且不能食,相火沖上無制,用理中湯。”明·龔廷賢亦認為:“手足冷,肚腹作痛,大便不實,飲食少思口瘡者,中焦虛寒也,附子理中湯主之。”《醫(yī)貫》載:“胃虛谷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虛衰之火,被迫上炎,作為口瘡……用參、術(shù)、甘草補其土,姜、附散其寒,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口瘡中醫(yī)臨床實踐指南》中也提到脾虛陰火一證,用藥取補脾胃、瀉陰火、升陽之品。多項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配伍理念[9-10]。
(2)溫腎助陽、引火歸元藥 如肉桂、牛膝、杜仲、牡蠣、干姜等。肉桂味甘、辛,性大熱,歸腎、脾、心、肝經(jīng),收浮火下行的力度較強,既治陽虛證,又可以助附子引火歸元,與附子相須為用。取引火歸元之義時肉桂用量宜少,一般取2~5 g,宜后下。懷牛膝性平,歸肝、腎經(jīng),有補腎填髓、活血、引火下行等功效[11]。懷牛膝性下行,可以帶動腎中虛火下行,和附子相使為用。杜仲可以進一步提升腎中陽氣,此以“大火引小火”之法促使中上焦虛火下行。黃元御《四圣心源》認為,腎火為爐火,發(fā)動清氣上升,左路肝木升發(fā),右路肺水下降,中路脾胃運轉(zhuǎn),如此以腎火的推動作用促使整個臟腑氣血津液運行。陰虛體質(zhì)或濕熱體質(zhì)者,不可配伍上述藥物,筆者父親常配牡蠣,用量為15 g,先包煎30 min。正如祝味菊先生用附子時會與磁石或龍齒、牡蠣并投,借用溫陽與潛陽配伍監(jiān)制附子辛燥升浮之弊[12]。亦可用熟地黃配伍附子,以填補腎陰制附片之燥,這種溫陽滋陰配伍能較好地調(diào)節(jié)陰陽平衡[13]。蒲輔周先生治療復發(fā)性口腔潰瘍時,運用封髓丹加減,在瀉相火的同時固精,能治浮火上炎。脈沉者,加用附子引火歸元,并總結(jié)出“脈虛者,乃用補土補精補陽”之法[14]。“火神派”鼻祖鄭欽安提出封髓丹善治陽虛上浮所致虛火上沖證,擴充了封髓丹的功用和主治[15]。有研究顯示,應(yīng)用潛陽丹(砂仁、附子、龜板、甘草)聯(lián)合封髓丹治療口腔潰瘍也能取得較好效果[16-18]。
2.3 病案舉隅 患者,男,50歲,“反復口腔潰瘍10余年”于2020年2月12日就診。刻下癥:進食時潰瘍疼痛,潰瘍面顏色淡白,周圍泛白,潰瘍范圍約為0.5 cm×0.8 cm,伴四肢不溫、口不渴不欲飲,食生冷之物后疼痛加重,納差,小便清、量多,大便溏泄,睡眠一般,舌質(zhì)暗淡,舌體水潤,苔薄白,脈濡。辨證為腎陽虛證(虛火上浮),治以溫陽補腎、收納虛火。方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加減,組成:麻黃15 g,附片30 g(先煎1 h),細辛3 g,炙甘草6 g,肉桂10 g(后下),蒼術(shù)15 g,法半夏15 g,川牛膝15 g,雞內(nèi)金15 g(沖服)。4劑,水煎服后癥愈。
按語:畏寒、大便溏泄、腰膝冷痛、舌質(zhì)淡、舌體水潤、脈沉細或無力是腎陽虛衰的表現(xiàn)。腎者,水火之臟,患者陽氣虧于下,陰寒內(nèi)盛,浮火發(fā)而上,發(fā)為口腔潰瘍。麻黃附子細辛湯加減方中,麻黃宣發(fā)郁火;附子溫經(jīng)扶陽,助麻黃祛邪外出的同時,防止耗損陽氣;細辛辛散通絡(luò);炙甘草調(diào)和諸藥,制附子之毒性;肉桂溫補腎陽,助附子收納浮陽;川牛膝引經(jīng)絡(luò)火邪下行,配合肉桂、附子相使為用;蒼術(shù)溫中燥濕,健運脾胃,助腎中虛火運轉(zhuǎn)下行,為其開辟通路,與法半夏合用祛濕降逆,以降胃氣,帶動上焦虛火下行;雞內(nèi)金健脾行氣開胃,沖服較好,加強三焦運化。此外,附子劑量較大時,先煎1 h以上,至無口舌麻木之感為宜。
3 小結(jié)
《口瘡中醫(yī)臨床實踐指南》[19]和《消化系統(tǒng)常見病復發(fā)性口腔潰瘍中醫(yī)診療指南(基層醫(yī)生版)》[4]中雖有脾虛陰火證,但附子及附子常見組方均未被列入其方藥中,而臨床又確有使用。在該病辨證過程中,務(wù)必要注意陽虛型或虛寒型,同時也要注意微觀辨證,如潰瘍周圍黏膜充血和紅暈不明顯,潰瘍面凹陷,色呈淺紅或蒼白,疼痛較輕或不痛。臨證必要時可應(yīng)用附子類溫性藥物,合理配伍;切不可妄用清瀉之法,以免損傷正氣,因醫(yī)之過引起復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