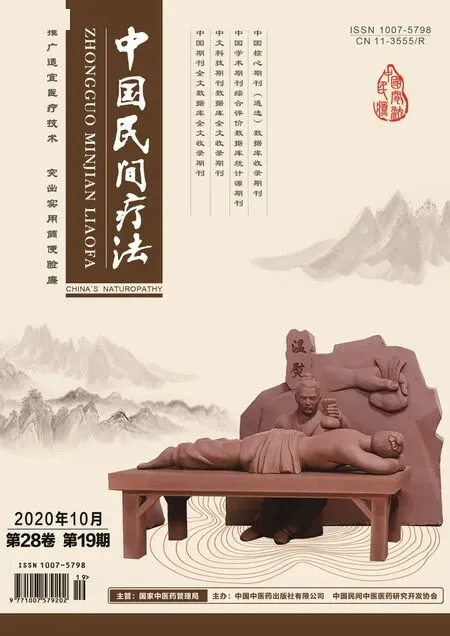火針聯合耳穴壓豆治療神經性皮炎1則
付 倩,李 嘉
(貴州中醫藥大學,貴州 貴陽550002)
神經性皮炎作為一種慢性皮膚神經功能性疾病,是臨床上皮膚科常見疾病之一。西醫治療神經性皮炎多采取抗組胺類藥物及糖皮質激素類藥物控制其癥狀,但無法達到完全治愈的效果,常因情緒、飲食等因素誘發。筆者在飲食、生活習慣等健康宣教的基礎上,采用火針聯合耳穴壓豆治療神經性皮炎1則,介紹如下。
1 病案舉隅
患者,女,30歲,2019年9月3日初診。主訴:反復右手拇指背側皮膚瘙癢8個月余。患者8個月前因熬夜、過食辛辣食品后出現右側拇指背側瘙癢,以夜間尤甚,前期自覺瘙癢可忍,故未予重視及診治,后每因受熱、精神緊張或過食辛辣食物后瘙癢加重,偶有脫屑、血痂,并出現手指背側團狀凸起。遂就診于貴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皮膚科,診斷為神經性皮炎,給予甘草酸苷膠囊口服及復方地塞米松軟膏外涂治療。患者自覺瘙癢癥狀發作時使用激素軟膏外涂治療后癥狀有所緩解,但未能治愈,長期反復搔抓致皮膚出現苔蘚樣損害,遂就診于針灸科門診。刻下癥:右側拇指背側有1個2 cm×1 cm的團狀凸起,局部皮損潮紅有血痂,自覺瘙癢難耐。平素心煩氣躁,情緒波動較大時,癥狀明顯加重,常伴夜間入睡困難、咽干等癥狀,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西醫診斷:神經性皮炎。中醫診斷:牛皮癬,肝郁化火型。治法:行氣解郁,養血潤燥,息風止癢。在健康宣教基礎上,給予火針聯合耳穴壓豆治療。治療方法:囑患者調暢情志,盡量避免患處接觸及使用刺激性物質,忌食辛辣刺激食物。火針治療方法:用75%酒精棉球于手指背側皮膚行常規消毒,取中號火針,針尖在酒精燈外焰燒至白亮后快速刺至皮損部位,快速進針,快速出針,因皮損部位為手指背側,淺刺即出針。皮損較嚴重處可適當增加針刺密度,操作過程中注意避免燙傷患者,結束后用消毒干棉球按壓防止出血,隔2~3 d治療1次,5次為1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耳穴壓豆方法:用75%酒精棉球于耳郭常規消毒后,將王不留行籽耳貼貼于雙耳肝、內分泌、神門、心、腎等穴,囑患者每日自行按壓3~5次,每次持續1 min,以患者自覺有麻、脹感為宜,于火針治療時更換1次。5次為1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治療后,患者自覺瘙癢癥狀較前明顯減輕,皮損部位無明顯血痂、脫屑等,團狀凸起范圍較前明顯縮小。繼續鞏固治療1個療程后,皮疹明顯消退,無明顯瘙癢癥狀。隨診3個月,患者訴皮疹已完全消退,未再復發,無瘙癢不適,夜間入睡困難、煩躁等癥較前明顯好轉。
2 小結
神經性皮炎是一種常見的皮膚神經功能障礙性疾病,臨床表現為陣發性劇癢難耐,以夜間尤甚,故患者常伴失眠;皮膚經搔抓后出現血痕或血痂,后期多出現明顯的皮損,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該病初期并無明顯皮損,僅有瘙癢感,經反復搔抓、摩擦,可出現苔蘚樣皮膚改變,其常因情緒異常、不良生活習慣及接觸有刺激性物質等誘發和加重。該病屬中醫“牛皮癬”范疇,亦被稱為“攝領瘡”。《外科正宗》云:“牛皮癬,如牛領之皮,頑硬須堅,抓之如朽木。”中醫認為該病發病主要有內外兩種因素,內因責之心血虧虛,心神失養;或肝郁氣滯,情志不暢,日久郁而化熱,血虛日久生風,血虛風燥,肌膚失養而致該病。《醫宗金鑒·外科新發要訣》言:“此證總由風熱濕邪,侵襲皮膚,郁久風盛,則化為蟲,是以瘙癢之無休也。”外因當責之風、濕、熱等外邪侵襲機體,亦是該病發生的主要原因。觀察本例患者舌、脈、癥,屬肝郁化火型,故治法以行氣解郁、養血潤燥、息風止癢為主。西醫治療該病多以抗組胺類藥物、鈣劑或糖皮質激素類治療,如復方氟米松軟膏[1]、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等,對癥治療僅能緩解其癥狀,遠期療效不佳,且易復發。
火針療法作為一種獨特的中醫外治法,在治療皮膚疾病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火針療法具有息風止癢、溫通經絡、散寒祛濕等功效,能夠有效調節病變局部氣血,疏通經絡。其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火針熱力,有效加快皮損局部微循環,調節皮膚神經,促進炎癥吸收,抑制介質合成,增強患者免疫力[2];借助火針溫熱刺激,增強氣血運行,疏通經絡,以熱引熱,疏通營衛,以祛風、濕、熱之邪[3]。耳穴壓豆療法是將王不留行籽貼于耳郭上相應穴位而產生治療作用的一種療法。《靈樞》云:“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耳部穴位與對應的經絡、臟腑功能關系密切,是疾病的反應點。本案選用耳穴肝以行氣疏肝;神門寧心安神,消炎止癢;心、腎調節對應臟腑功能,滋養心血。多穴共用,共奏行氣疏肝、養血潤燥、止癢等功效。研究表明耳穴埋豆加火針聯合治療神經性皮炎,能夠通過對相應部位的刺激,有效調節皮質神經興奮、抑制血管的舒張收縮等,從而實現抗過敏的治療作用[4]。
本案采用火針聯合耳穴壓豆治療神經性皮炎,療效顯著,有效發揮了傳統中醫治療方法的優勢,具有操作性強、患者接受度高等特點,值得在臨床上推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