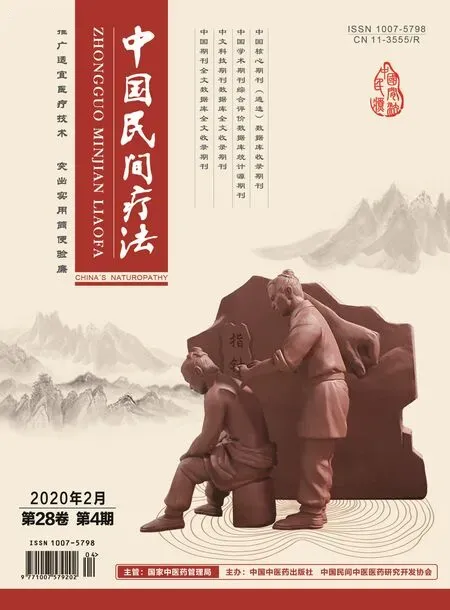八珍湯加減治療多系統萎縮驗案1則※
荊尚文,張林旭,康超茹,馬云枝,王保奇
(1.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450046;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 鄭州450000)
多系統萎縮(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是一種散發性、快速進展并累及多系統的進行性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以腦神經神經元脫失及膠質增生,皮質脊髓束變性,白質廣泛彌漫的少突膠質細胞胞質內纏結樣包涵體為主要病理特點[1],但由于MSA是進展性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常伴有典型的小腦型共濟失調和/或帕金森癥狀,故分為MSA-C型和MSA-P型。自主神經功能癥狀以尿頻、尿急、尿失禁、性功能障礙等泌尿系統癥狀,以及眩暈、暈厥、體位性低血壓、夜間高血壓等心血管癥狀為主,也有瞳孔、汗腺、呼吸、胃腸道、睡眠、認知、情緒等其他功能異常癥狀[2]。當前影像學檢查(頭顱MRI典型腦橋十字征)、電生理檢測、彩超、神經心理等現代技術有助于本病診斷及鑒別。治療方面西醫并無特效療法,腦神經保護藥物等相關對癥治療及康復功能訓練可改善病情,但由于本病起病隱匿,病因不明,進展較快,西醫藥物治療局限,預后較差。而中醫治療本病有著獨特優勢,可顯著改善自主神經功能癥狀,減輕運動癥狀,延緩疾病進程,且藥物毒副作用少。此外,中醫補益氣血、培本固元、治病求本的治療理念深入人心,已成為不二之選。本病多以“痿證”論治,現將1例八珍湯加減治療氣血虧虛型MSA病例報道如下。
1 病例介紹
患者,女,65歲,2019年4月2日初診。主訴:行走不穩,言語不清2年,加重伴頭暈1年。患者于2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行走不穩,言語不清,伴跌倒,無視物旋轉、肢體抽搐、惡心嘔吐,與頭位及體位改變無關,遂至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住院診療,診斷為“多系統萎縮C型”,給予營養神經等藥物治療(具體不詳)。近1年來行走不穩逐漸加重,出現雙下肢麻木無力,頭暈腦脹,飲水稍有嗆咳,言語含糊晦澀,現伴有少氣懶言,精神倦怠,腰酸困痛,失眠多夢,納少,小便頻數,控制不佳,大便干結,約3~4日一行,舌質黯淡,苔白,脈沉細弱。神經系統檢查:神志清,精神差,構音障礙,語聲呈爆裂音,高級智能檢查基本正常,顱神經檢查正常,四肢肌力、肌張力基本正常,病理反射陰性,行走不穩前傾,闊基底步態,閉目難立征睜閉眼(+),雙側指鼻試驗及跟膝脛試驗欠穩準,輪替試驗動作笨拙。輔助檢查:頭顱MRI示左側額葉輕度白質脫髓鞘,小腦部分腦溝較寬,建議動態觀察;頸部對比增強磁共振血管成像(CE-MRA)未見明顯異常(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2017年3月22日)。2017年6月26日河南省人民醫院行肛門括約肌肌電圖:肛門括約肌失神經改變,提示S3、S4水平失神輕損害,請結合臨床。2019年4月4日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行腦干薄層掃描3.0 T:雙側小腦半球、腦干萎縮,可見腦干典型十字征,考慮多系統萎縮可能,請結合臨床,除外系統性萎縮;左側腦室旁輕微腦白質脫髓鞘;雙側篩竇炎。彩超示:雙側頸動脈斑塊形成,雙下肢動脈內中膜毛糙并小斑塊形成,膀胱壁毛糙;心臟彩超示:左心房大,二尖瓣輕-中度狹窄,二、三尖瓣輕度關閉不全,肺動脈高壓(輕度),左心室舒張功能減低。常規心電圖正常。生化等檢驗基本正常。
初診:依據患者老年女性,行走不穩,雙下肢麻木無力,辨病為“痿證”;少氣懶言,精神倦怠,腰酸困痛,失眠多夢,納少,小便頻數,控制不佳,大便干結,結合舌質黯淡,苔白,脈沉細弱,辨證為氣血虧虛證,治以健脾益胃、補養氣血為主,兼顧滋補肝腎、化瘀通絡,方用八珍湯加減。組成:人參片5 g(另煎兌服),白術12 g,茯苓15 g,當歸15 g,川芎15 g,熟地黃15 g,白芍30 g,桑寄生15 g,杜仲15 g,牛膝30 g,酒蓯蓉15 g,蜈蚣2條,全蝎12 g,炙甘草3 g,12劑,水煎取汁400 m L,分兩次飯后溫服。
二診:患者自感行走不穩較前改善,頭暈緩解,失眠心煩,口苦咽干,舌質、脈象基本同前,守上方,加黃芪30 g,首烏藤15 g,合歡皮15 g,珍珠母15 g,以補氣養血、平肝安神,繼服16劑。
三診:上述諸癥俱減,出現納少腹脹,便秘難下,舌質暗紅,苔厚膩,脈似有滑象,守上方,黃芪量減半,加焦三仙各15 g消食和胃,加砂仁9 g加強益氣健脾之功,使補而不滯,繼服14劑。后鞏固治療,1個月后隨訪訴整體病情穩定,有好轉趨勢,并堅持長期中藥治療。
2 討論
MSA最終多以肢體萎廢不用、言語不清等為主要癥狀,故常以“痿證”論治。多因先天不足、久病體弱、飲食勞倦等,使五臟受損,氣血虧虛,五體失養,肢體筋脈失養而發為本病。《靈樞·經脈》提出“虛則痿躄”的總病機,故以補虛為治療大法,兼以祛邪。
本例患者年逾六旬,五臟精氣漸衰,臟腑功能減退,中氣受損,脾胃失健,氣血津液生化無源,加之久病肝腎精氣虧耗,先后天無以為資,氣血虧虛,筋骨肌肉失養則致痿。氣血是臟腑正常生理活動的產物,乃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之基,臟病必損氣血,反之,氣血病亦致臟腑功能失調[3]。脾胃乃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主四肢肌肉,若脾胃虛弱,則生化之源匱竭,氣血虧虛,四肢不充,正如《素問·太陰陽明論》云:“四肢皆稟氣于胃……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谷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西醫認為,血液中的白蛋白、血紅蛋白、淋巴細胞、單核細胞等營養物質維持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發揮免疫功能,保持穩態而不患疾病,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若氣血虧虛,血管無氣,腠理開闔失司,蛋白等精微物質外滲、消耗、減少,從而使免疫功能下降,則產生疾病。腎乃先天之本,腎藏精,主作強,腎精有賴后天水谷精微的不斷充養,脾胃虛弱,運化水谷精微乏力,無以充養先天之精,則腎精虧虛,終致氣血虧虛使百骸萎廢,行走不穩,麻木無力。脾腎之經脈循行皆連舌本,故脾腎陽虛、經脈失養則言語不清,飲水嗆咳;氣血無以上乘腦竅,腦竅失養則頭暈;腎陽虛衰,腎精不固,則腰酸困痛,加之氣虛膀胱氣化失司,則尿頻、失控;氣虛推動無力,血虛失于濡養,則大便干結;舌質黯淡,苔白,脈沉細均屬氣血虧虛之癥,一派虛象。正所謂:“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4]故治以健脾益胃、補養氣血為主,同時也要兼顧滋補肝腎、化瘀通絡。腎藏精,精血相生,腎精虛則不灌溉諸末;肝藏血,血虛則不濡養筋骨;久病必瘀,久虛必瘀,故要化瘀通絡,方選八珍湯加減。誠如吳崑《醫方考》所言:“血氣俱虛者,此方主之。人之身,氣血而已。氣者百骸之父,血者百骸之母,不可使其失養者也。”方中人參、熟地黃共為君藥,人參性味甘溫,大補元氣,補氣生血,熟地黃養陰補血,二者共用益氣養血;白術、當歸為臣,白術助人參之力以健脾補氣,血藥當歸與熟地黃補血和血,二者合用氣血兼顧,正所謂“氣旺則百骸資之以生,血旺則百骸資之以養”;佐以茯苓健脾養心,白芍養血斂陰和營,川芎為氣中血藥,活血行氣,使補而不滯;炙甘草益氣和中,調和諸藥,加桑寄生、杜仲、牛膝、酒蓯蓉滋補肝腎,以充先天;久病必瘀,加蜈蚣、全蝎蟲類藥物,此類藥善走竄,化瘀通絡之力強,以助血行濡養皮肉筋骨。相關研究表明,益氣養血、活血化瘀藥物與蟲類藥物聯合應用,可明顯改善局部缺氧狀態,促進神經施萬細胞的氧利用率和神經軸突的再生[5]。二診患者自感行走不穩改善,頭暈好轉,說明此方正中病證,故以繼用,并加大量黃芪以助補氣、壯筋肌,合“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氣能生血”之意。然出現心煩失眠、口苦咽干,此為肝陽上亢之癥,原方補益氣血,鼓動陽氣,致使陰不制陽,故以入心肝經的蜿蜒入絡藤類藥首烏藤、平肝潛陽貝類藥珍珠母及和血安神合歡皮以平肝養血、滋陰安神。三診患者出現納少腹脹,便秘難下,舌質暗紅,苔厚膩,脈似有滑象,此為患者體弱,大量補益之劑致使壅塞,故黃芪量減半,加焦三仙消積健脾和胃,加砂仁加強益氣健脾之功,使補而不滯。因本病療程尚短,其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長期觀察及大量臨床試驗觀察,以期提高多系統萎縮患者的生活質量,延長其生存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