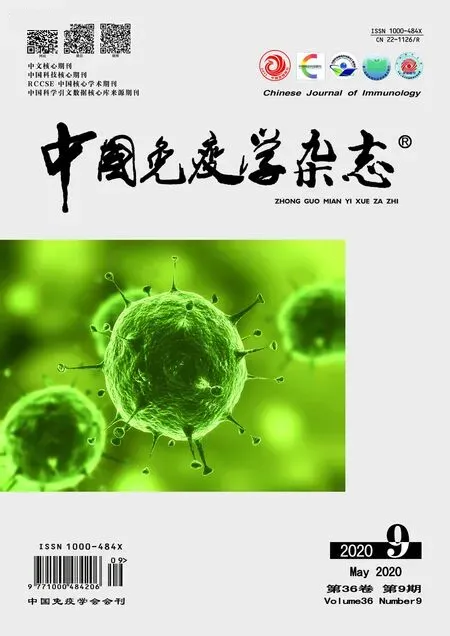T細胞受體庫在常見腫瘤免疫治療中的研究進展①
王娟娟 張 鍇 劉 莉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腫瘤中心,武漢 430023)
作為適應性免疫的關鍵細胞效應器,T細胞通過其表面的T細胞受體(T cell receptor,TCR)以識別和消滅腫瘤細胞。TCR由胚系基因于胸腺中進行V(D)J基因重排而形成,胸腺細胞經由復雜的陽性選擇和陰性選擇有序分化,發育成熟組成具有多樣性的T細胞庫,一個單獨T細胞中TCR的總數被稱為一個TCR repertoire或TCR profile。TCR庫會隨著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產生變化。每個TCR鏈都包含3個高變區,被命名為complementarity-determining region(CDR1-3),CDR3因其高度多樣性被作為決定T細胞克隆類型的區域。近年來測序技術的發展使我們可以更快更準確的評估TCR CDR3的多樣性,并評估TCR庫的克隆組成,包括TCR庫的大小、庫之間的相似性、V(D)J段使用、核苷酸插入和缺失、CDR3長度等[1]。研究表明,TCR庫在淋巴瘤微小殘留病灶的檢測、移植免疫治療后監測、自身免疫疾病的診斷等方面均有價值[2-4]。TCR多樣性是適應性免疫應答特異性的基礎,對于腫瘤免疫應答分子機制研究意義重大。有研究報道了免疫治療前后TCR庫變化與免疫應答之間的相關性,提示TCR庫作為腫瘤免疫治療潛在生物標志物的可能性[5]。本文將圍繞TCR庫與常見腫瘤免疫治療之間的關系展開綜述。
1 TCR概述
TCR是由不精確的體細胞基因重組產生的極其多樣化的基因編碼的異二聚體蛋白質,根據TCR基因,T細胞可分為α/βT細胞和γ/δT細胞。對于人類而言,大多數T細胞是α/βTCR,而γ/δT細胞占總T細胞的0.5%~16%(平均約4%)[6]。TCR的多樣性使得受體能夠識別各類抗原,從而激發出一種有效的適應性免疫反應[7]。
1.1TCR的檢測技術 TCR的檢測方法包括常規PCR、克隆以及測序。近年來,測序技術的發展讓我們能夠更加迅速且準確地獲取與TCR有關的海量數據。作為人類打開測序的開端,2001年人類基因組測序使用的Sanger技術是經典的一代測序[8]。通過對編碼TCR上可變區的DNA片段進行測序,從而了解TCR的多樣性。但測序成本高、通量低等方面的缺點,限制了其應用與推廣。高通量測序又稱第二代測序或下一代測序[9],是一種大規模并行測序技術,能一次并行對幾十萬到幾百萬甚至幾千萬DNA分子進行序列測定,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測序速度,并保持了高準確性。第三代測序方法即單分子測序,可直接檢測單個堿基信號,最大的特點是無需進行PCR擴增,因其成本較高,尚未廣泛應用。
1.2TCR的多樣性 為了應對多種病原體,T細胞必須能夠識別許多不同的非自身肽,因此,T細胞應表達廣泛多樣的獨特TCR。TCR的多樣性來源于專門的遺傳多樣化機制[10]。一方面,在人類中,TCR的基因區段包括TCRβ鏈的40~48個功能性TRBV、2個TRBD、12~13個TRBJ和2個TRBC基因以及TCRα鏈的44~46個TRAV、50個TRAJ和1個TRAC基因,多樣性通過在TCR基因重排期間組合不同的基因區段來介導。另一方面,重組過程中在V、J和D片段之間的連接點添加P(alindromic)和N(on-template)-核苷酸和/或N-核苷酸缺失可導致連接區突變,多樣性也由此突變產生。多基因片段、組合多樣性、連接多樣性形成了TCR的多樣性,從理論上講,重組機制產生的潛在多樣性估計高達1015[11]。
1.3TCR庫的異質性 腫瘤異質性是腫瘤治療的主要障礙之一,與腫瘤耐藥性的發生和腫瘤復發均相關。腫瘤異質性不僅存在于腫瘤細胞內,還可能存在于TCR庫中。TCR庫的差異一方面存在于腫瘤與正常組織或其他腫瘤之間,另一方面存在于同一腫瘤內的不同區域之間。差異表現在TCR庫的克隆組成、克隆型、CDR3多樣性以及CD8+T細胞的擴增等方面。以結腸癌為例,研究表明結腸腫瘤組織與相鄰的健康黏膜組織之間的TCR序列具有顯著差異[12]。一項關于卵巢癌的研究表明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TCR庫的克隆組成在每個卵巢腫瘤中表現出均一性[13]。而在腎細胞癌中,在腫瘤的不同區域TIL TCR庫的克隆組成是有差異的[14]。這些相反的結果提示源自不同腫瘤的TCR庫的克隆組成表現不同。關于胰腺癌的研究,通過分析TCR CDR3基因序列發現胰腺癌患者與健康對照組之間的TCR無顯著差異[15],各組之間CDR3的類型和長度相似,這種與正常組織之間差異不顯著的表現與乳腺癌、肺癌等腫瘤不同。此外,Reuben等[16]的研究對來自11個局灶性肺腺癌的45個腫瘤區域中的TCR進行了測序,觀察到腫瘤內T細胞的密度和克隆性存在實質性差異,大多數T細胞克隆均局限于單個腫瘤區域。TCR庫中的空間差異可能是由不同腫瘤區域中不同的新抗原驅動。
2 TCR庫與常見腫瘤免疫治療
T細胞受體介導T細胞識別不同的腫瘤抗原肽從而啟動抗腫瘤免疫的過程,是腫瘤免疫反應的關鍵環節[17]。腫瘤免疫治療包括單克隆抗體類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B)、治療性抗體、癌癥疫苗、細胞治療和小分子抑制劑等。隨著免疫療法的巨大成功,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B)療法獲得了極大關注。ICB最初被批準用于惡性黑色素瘤、肺癌,隨著近些年來免疫治療適應癥的擴大,針對乳腺癌、結直腸癌、前列腺癌等腫瘤的免疫治療研究浮出水面。接下來將重點闡述不同惡性腫瘤的免疫治療與TCR庫之間的相關聯系。
2.1惡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MM) 關于TCR庫與腫瘤之間的故事最初從黑色素瘤開始,早在1996年就有研究者分析了基于IFN-α/IL-2的免疫療法對TCR模式的影響[18]。隨后,Robert等[19]關于黑色素瘤患者的免疫治療研究發現抗CTLA-4的免疫治療會導致TCR庫的擴大,同時發現這種擴大與毒性增加有關。但Robert并未發現應答者和非應答者在抗CTLA-4治療的基線TCR多樣性存在任何差異。隨后有研究報道,TCR的多樣性與抗CTLA-4免疫治療后的臨床獲益具有相關性,這兩項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CTLA-4檢查點阻斷劑,即tremelimumab和ipilimumab[20,21]。
已有研究向我們證實了PD-1和CTLA-4抑制對黑素瘤患者外周TCR庫的不同影響,二者雖然都能重塑TCR庫,但是起作用的方式不同[22,23]。由于PD-1的作用機制,PD-1治療的TCR庫研究主要集中在腫瘤庫,而不是外周庫。Tumeh等[24]通過比較抗PD-1治療(pembrolizumab)基線和給藥后腫瘤活組織檢查的TCR克隆性,發現臨床應答者的樣本在抗PD-1治療后具有超過10倍的克隆擴增。然而Kuehm等[25]的最新研究表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會增強小鼠腫瘤浸潤性T細胞的頻率和效應功能,但并不改變TCR多樣性。與之前的研究有所矛盾,因此進一步的研究值得我們去探討。已有研究通過TCR測序對黑色素瘤患者進行分層,將其應用到臨床患者中,從而篩選出可能從免疫治療中獲益的患者[26]。免疫治療與TCR的關系在黑色素瘤中的研究為進一步探索其他瘤種奠定了基礎。
2.2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最近的一項研究,證明了肺癌患者中存在獨特的T細胞免疫微環境。該研究分析了15例肺癌患者的肺癌組織和匹配的遠處非腫瘤肺組織(正常肺組織)中的TCR庫[27],發現雖然T細胞克隆的總體分布在癌組織和正常肺組織之間是相似的,但是在克隆比例、TCR多樣性等方面有顯著差異,且腫瘤中較高的TCR多樣性與較差的臨床獲益顯著相關。
NSCLC的特征在于突變的逐步出現,其中某些突變促進了新抗原的產生,使TCR庫發生改變。同樣的,TCR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腫瘤的突變情況。Miyauchi等[28]研究了EGFR基因與TCR庫之間的關系,該研究收集了39對配對的(正常和腫瘤)肺腺癌組織樣本(其中20個具有EGFR突變)進行TCR測序分析,結果表明EGFR野生型腫瘤的TCR克隆擴增要比EGFR突變型腫瘤的克隆擴增更大。最近Joshi等[29]通過研究了TCR庫異質性與基因組異質性之間的關系,發現TCR庫的空間異質性反映了肺癌的突變情況。在腫瘤中選擇性擴增的TCR序列的數目在腫瘤內部和瘤體之間變化,與非同義突變的數目相關。此外,TCR庫被認為是免疫治療的潛在預測生物標記物,近期研究表明外周血PD-1+CD8+T細胞中TCR多樣性和克隆性可以作為患者對免疫治療療效和NSCLC患者生存結果的非侵入性預測指標[30]。
聯合治療對TCR庫的影響與治療方式有關。Wilkins等[31]在NSCLC中發現放療聯合抗CTLA-4治療可能重塑了TCR庫,并且針對新的腫瘤抗原出現了新的克隆型。除了放療,靶向治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研究也有報道[32],該研究發現FGFR抑制劑(erdafitinib)可導致克隆性下降,一方面可能是T細胞群體具有更均衡的克隆頻率分布,因而克隆數量更少;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抗原呈遞細胞(APC)暴露于腫瘤抗原庫而引發的免疫反應,是治療直接誘導的腫瘤細胞凋亡的結果。與單獨使用erdafitinib的治療相比,聯合治療使T細胞克隆分數和克隆性均顯著增加,這可能與抗PD-1治療推動了腫瘤特異性T細胞克隆的擴增有關。因此聯合治療可促進T細胞克隆的擴增以及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學變化,以增強抗腫瘤免疫力和增加存活率。
2.3乳腺癌(breast cancer,BC) 在乳腺癌TCR相關研究中,癌組織與癌周組織及腋淋巴結中T細胞的TCR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發現。Wang等[33]使用多重PCR和高通量測序分析了乳腺癌患者的腫瘤、鄰近非腫瘤組織和腋窩淋巴結中T細胞的TCR組成,研究發現腫瘤中的TCR庫多樣性低于淋巴結,但高于非腫瘤組織,并且可變基因和連接基因的使用頻率較高。該研究還發現陽性淋巴結增強了T細胞向腫瘤的浸潤和淋巴結中T細胞克隆的擴增,乳腺癌的分子表型也可以改變組織間T細胞庫相似性。關于乳腺癌免疫治療與TCR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多。最近一項關于雙重檢查點抑制劑的互補機制研究發現免疫治療可以擴展獨特的TCR庫[34],分析顯示TCR庫在抗CTLA-4治療后顯著變化,但未因添加抗PD-1治療而改變。具體原因有待我們繼續探討。在臨床上,免疫治療不僅可以單獨發揮作用,也可以聯合其他治療,例如放療、靶向治療或其他免疫療法,共同發揮抗腫瘤作用。Rudqvist等[35]發現乳腺癌的聯合治療后,不僅CD8/CD4的比率顯著增加,CD8+T 細胞的克隆擴增也較為顯著,而且出現了新的克隆型,CDR3的長度也明顯增加。
2.4其他腫瘤 Sheikh等[36]使用TCRVβCDR3序列的NGS來鑒定接受sipuleucel-T治療的早期前列腺癌患者腫瘤組織及外周血中T細胞亞群的變化,確定了用sipuleucel-T治療的患者中外周血與腫瘤組織TCR特征有更高的關聯性。這些發現表明sipuleucel-T可能通過增加抗原特異性免疫庫來調節腫瘤相關免疫反應,從而減少外周循環中T細胞的多樣性。相關的研究也在結直腸癌、膀胱癌、宮頸癌等不同腫瘤中開展[37-39]。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證明了TCR庫與腫瘤治療之間密切的聯系,為后續研究TCR作為生物標志物的可行性提供了支持。
3 結語
隨著測序技術的發展,TCR的相關分析不僅變得更容易,而且更準確[40]。免疫治療在不同的環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塑了TCR庫,同樣地,TCR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體內免疫應答狀態,可作為腫瘤免疫治療的潛在生物標志物。但其在更廣泛的研究和臨床應用中仍面臨挑戰,首先是獲益人群及治療領域的局限性,如何使更多的患者在免疫治療中獲益,如何應對免疫相關不良反應,如何擴大免疫治療適應癥等這些問題仍需繼續探究。其次,雖然TCR庫的測序分析能夠監測腫瘤內和外周血T細胞的存在以及數量和克隆擴增情況。然而,僅通過這一信息尚不足以完全反映適應性免疫應答,仍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來確認TCR庫作為預測標志物的可行性及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