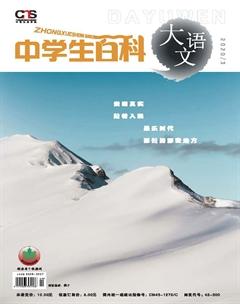那是一個晴天
[日]加藤周一
一個晴朗的早上,在本鄉校區大學醫學部的校園里,我跟同年級的學生們一起,一邊想著下一節課的內容,一邊朝著附屬醫院的方向走去。當時有個學生拿著一份在本鄉路上買來的報紙,在那兒宣讀號外。然后,嘈雜聲就像漣漪一般在我們中間擴散開來。不是因為誰說了句什么話,而是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反應匯聚到一起,之后就變成了一聲嘆息。就在那一刻,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事實清晰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我感到周圍的世界頃刻間面目全非。基礎醫學部的大樓、小樹叢、同年級學生穿的衣服,這些是一年多來我每天都在看、早就已經習慣了的光景。在這個寧靜的上午,初冬里的小陽春天氣,和煦的日光下,我所熟悉的這片光景一切如常,但同時,它又如初見般在我心里喚起了一個不尋常的、鮮明的印象。大概就像是我和我所熟悉的世界之間的紐帶突然斷裂的感覺。這個說法頂多就算一個解釋吧。那種感覺上的印象,就好比食物的味道,是很難用語言來表達的,但它又是那么鮮明,鮮明到當你再次擁有相同體驗的那一刻,一定會在瞬間認出它來。后來,戰爭結束,母親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周圍的光景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還有,當我遇到那位命中注定的女性時,東京的街道看上去也完全不像東京的街道。但我也不會為此而特別說些什么或做些什么。當我得知戰爭打響的時候,我也就是若無其事地穿過人群,朝著附屬醫院的方向繼續走去。當時我也不是不知道戰爭在步步逼近,只是我不敢相信,這場戰爭居然真的會把英美兩國作為對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結論會變成現實——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我跟同學們一起走進了附屬醫院的階梯教室,診斷學——應該是這門課吧——一如往常地上課、下課,而我卻茫然地坐著那里聽課。課上的內容我根本就沒聽進去,腦子里走馬燈似的在問各種問題:教授看著好淡定啊,他看了今天早上的號外嗎?或者,他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這么鎮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
“接下來會怎樣呢?”我一回家,母親就問我。“必輸無疑!”我像是要發泄什么似的說道。“真的嗎?”“還有別的可能嗎?”“你大伯倒是一直都說,那個海軍大臣行事魯莽,要照他的做法,可真讓人放心不下……這下會不會出什么大事呀?”“肯定出大事!”“這事兒,你可跟誰都別說!”母親說。
為了防備敵方來空襲,那天晚上就開始進行燈火管制,但我已經買好了票,打算去新橋演舞場看文樂。演舞場那天正好是大阪文樂劇團來東京新橋演舞場巡演。母親說道:“你還是別去了吧。有可能會白跑一趟呢……”我當然知道她擔心的不是我“白跑一趟”,但還是說了一句“不演的話我就馬上回來”,之后就出門看戲去了。
地鐵還是照常運營。我在銀座四丁目下車,街上一片漆黑。新橋演舞場門口幾乎沒有行人,只有演舞場的建筑物像個黑色的大塊頭,靜靜地匍匐在微白的夜空下。原來如此,巡演看來是取消了。但我又轉念一想,還是到入口看一眼去吧,沒想到入口的門開著,問訊處也有人,就是不見觀眾的蹤影。檢了票,走進劇場里頭一看,二樓觀眾席上只有我一個人,于是我就往前走,找了個正中間的位子坐了下來。再往下一看,正面池座里三三兩兩地坐了四五個男人,還是沒有一點要開演的跡象。我又琢磨,是不是一會兒該有個經理人之類的出來跟我們做個解釋,說一下怎么給我們退票的事兒。就在那個時候,上來兩個人,一個是義太夫(說書人),另一個拿著三弦琴,各自入席后,自報家門道:“今日為您說這段義太夫的是……”空蕩蕩的劇場里面,只有清脆的梆子聲在回響。然后,大幕拉開,木偶活了起來。
我很快就被義太夫和三弦琴的世界給吸引住了,“現如今,半七他……”——說起來,這真的是一幅不同尋常的風景。古韌大夫,面對沒有觀眾的劇場,穿越到遙遠的江戶時代,變身為商賈人家的女子,全部戲份就靠他一個人在那里扭動身體,用聲嘶力竭的道白,嘆息、控訴和哭泣。這里早就沒有了戰爭,沒有了燈火管制,沒有了內閣情報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個任何事物都難以撼動的、固若金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既能表現女子戀愛時的嘆息聲,及其所有的微妙的陰影,又能將其升華為一種風格,通過三弦琴和古韌大夫的聲音,二者嚴絲合縫的配合,得以完美演繹。唯有此刻,這個世界才無須通過密匝匝的觀眾,無遮無攔、毫無退讓地展現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這樣色彩鮮明地、威風凜凜地存在著,宛如一出悲劇,與劇場外面的另一個世界——軍國主義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現實——形成鮮明對比。古韌大夫是在孤軍奮戰嗎?大概也不是吧。江戶文化的全部內容都濃縮在他的身體之中。這是化為肉體的文化……所有這一切不是作為語言,而是作為難以撼動的現實,展現在我的眼前。夫復何求?
炸彈沒有立刻從我們的頭頂掉下來。在聽聞開戰的“詔敕”后,又傳來奇襲珍珠港的捷報,整個東京陷入狂喜的海洋,大家都高興得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
“我太高興了!我要唱軍歌!”某個大學教授說。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大快人心啊!”學生們說。報紙上,著名歌人寫了首《珍珠港》的和歌,詩人為有生之年能親眼見證這一盛事而感謝上蒼。
第二個月,有識之士在雜志上發文寫道,這才是真正的“近代的終結”,“大東亞共榮圈之路”暢通無阻,大日本帝國前途無量。作為艦政本部長,一直對開戰持批評態度的大伯是這么說的:“不過,奇襲珍珠港在戰略上的成功超過了預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當然,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高興得手舞足蹈的并不是只有東京。雖然我當時啥都不知道,但恐怕除了柏林這個唯一的例外,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首都,都在為這個捷報而高興不已。莫斯科得知日本軍隊不再向北、轉而向南進軍的時候,內心肯定是松了一口氣的——看來佐爾格的情報是真的。倫敦看到日本用行動促使美國正式參戰,內心應該是欣喜若狂的。聽說流亡中的戴高樂將軍得知此事后,馬上就自言自語道:“勝負已定。”美國,克利夫蘭,太平洋問題研究所的會議上,學者們正在為日本是否參戰而進行激烈的辯論。就在此時,傳來了珍珠港被襲的消息,學者們一時間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很快鎮定下來,并終止了會議。
所有人都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誰都知道,這下“法西斯主義肯定要完蛋了”。東京市民不知道全世界都在為此事高興,所以他們才會自顧自高興。我懷著黯淡的心情注視著東京市民的狂喜,感覺自己跟他們之間的距離從來沒有如此遙遠過。東京被炸后,我就在傷者的身邊,竭盡全力救治他們因燃燒彈而造成的皮膚灼傷。戰爭結束后,離開東京的時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邊,感到很多東京人就在我身邊。在海外漂泊的日子越長,就越會讓我思考自己內心深處的東京。但是,“珍珠港”那天,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那歡呼雀躍的人群里,沒有我。“珍珠港”那天,古韌大夫講述的“日本”離我越近,得勝后趾高氣揚的軍國“日本”就離我越遠。然而,古韌大夫所講述的并非完全是很久以前的傳說故事,那不也正是包含著我自己的感情牽絆、所有小小的悲歡、無可挽留地離我而去的那一切的,我無可替代的唯一的世界嗎?
跟我預想的不一樣,東京的生活并沒有因為開戰而發生很大的變化。英美軍隊,比中國戰場還要遙遠。我們家搬到了世田谷區的赤堤,我每天從那兒去本鄉校區上學。在這之前,美竹町的外祖父家生意越來越不景氣,他們早就把大宅子和澀谷的土地一起做了抵押,最后沒能贖回,就搬到目黑區的一個小房子住。我們家賣掉了美竹町的房子,在赤堤租房住。
從那時起,外祖父就靠陸軍發放的退伍金和變賣家具什物過日子。他還偷偷地寫起了“小說”。母親笑話他說:“那不是小說,是您的閨房情話吧?”在所有一切都結束之后,外祖父大概是在想辦法把最難忘的東西留下來吧。“小說”里面沒有寫發家致富的故事,也沒有寫戰爭,而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他去伊豆短期出差,母親一直把他送到東京站時不經意說的一些話;他帶著外甥們去買東西時,大家開心的笑聲;生意談得不順利,滿身疲憊地去找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不僅得到了對方的關照,而且對方還非常體貼地不讓他感到這份用心。小說文字稚拙卻古雅,我從字里行間讀懂了外祖父不得不寫這篇小說的緣由。他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活在當下的快樂——這些小說則是他對往昔的留戀。年老體弱的外祖父很快就在目黑區的小房子里離開了人世。
我依舊每天去醫學部上課,醫學部要求我們背誦的內容更不會有什么變化。另外,要是考慮去囤點物資或是預測將來提前準備好“疏散”的話,就不需要判斷什么日本幾年后會戰敗,會不會戰敗這些問題,肯定是去判斷明天會缺少哪些物資,東京什么時候被轟炸這些問題。現在,就在我的周圍,馬上就會有人為“必勝的信念”而激情燃燒,或是去囤點罐頭,或是去買點軍用物資,或是四處鉆營,敏捷地開始做“疏散”的準備。但是,我沒有考慮過要囤貨,也沒做“疏散”的準備,更沒有考慮過任何其他的具體行動。我沒考慮過具體行動的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條件讓我做出有利于具體行動的判斷,而是因為我本來就不考慮具體行動,所以才把判斷限定在跟我自身行動無關的領域。在做和行動無關的判斷時,排除掉帶有主觀愿望的視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在跟處于“沒落”過程中的家人們朝夕相處的過程中,預測了日本帝國整體的“沒落”。不管怎樣,超越“沒落”的唯一辦法就是去理解它。
然而,我的想法在行動方面沒能找到用武之地,卻在我和周圍人之間形成隔閡時發揮了作用。當時的東京街頭,身穿國民服的人越來越多,我就像一個游客,漫步其中。游客眼里的風景和當地人眼里的并無二致,不過能從同樣的風景里看出不同的意義來,由于這一緣故,他們常常會激起當地人的無名之火。“開什么玩笑!你說得倒是容易……”東京還沒有變成一片廢墟,但我經常會把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層被燒成荒涼廢墟的幻影。于是,頃刻間所有的一切都煥發出不可思議的美。堆放在赤門前水果攤門口的橘子和蘋果——在冬日午后的陽光照射下,那種顏色和冰涼的觸感,光是這種心理上的預感也足以讓我在路邊駐足良久。校園里銀杏樹的枯枝在空中拉起了一片細網;早春的新綠像是一層薄霧;兩邊研究室狹小的入口處,人們拿著書或背著包進進出出;還有三四郎池畔那片太陽地兒,總是靜悄悄的,好像沒人記得它似的;化學教室的紅磚墻上映照著落日斜陽;傍晚時分,護士們穿梭行走在醫院昏暗的走廊里,白衣飄飄;本鄉路上的書店和“白十字”窗戶上逐漸亮起的燈光;書店主人蹲在書架緊里頭看賬本,邊上擱著一個炭盆燒火……所有這一切都讓我著迷,帶給我無法言喻的感動。可以說就在這一刻,我可以說我第一次看到了皇居的石城垣、千鳥之淵的春水在發光。不,不光是這些,還有東京街道上的喧鬧聲、馬路上的坑坑洼洼、隨季節變幻的風吹在皮膚上的不同感覺——就在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所有這一切。我也許會幸存,也許不會,但是只要我走在街上,街道就是我的。
之后過了很多年,當我走在佛羅倫薩的廣場上,一邊隔著鞋底感受那里的石板地,一邊游覽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物時,心里想,自己大概不會再來這里了吧。然而,住在這個城里的人,他們肯定會帶著各種各樣的希望和悔恨、歡喜與悲傷去考慮自己的生意、市長選舉、葡萄酒的價格、教會新祭司的男子氣、隔壁家女兒生的小孩子的父親是誰……感受文藝復興時期石板地的不是我這個游客,而是每天挎著購物籃走在上面的城里的主婦。我不在東京生活的時候,發現了東京。托馬斯·曼曾說過“另一個德國”,詩人片山敏彥曾說過“另一個日本”。然而,這些都不存在。我從一開始就不是生活在那里,而是注視著那里。我自認為戰爭暴露了大日本帝國的真面目,但實際上,戰爭暴露的可能僅僅是我自己。(節選,有刪減)
賞析
加藤周一可謂是日本國寶級的評論家,曾在數所世界一流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有著日本“百科全書式學者”“知識巨匠”等美譽。他的文學評論和文化史著作皆成為后世對20世紀日本文化和思想研究的經典。加藤的自傳《羊之歌》收錄了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散文,不僅記錄了他的成長經歷,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本篇《那是一個晴天》出自《羊之歌》,哪怕是寫散文,作者的文風也更接近一名學者,加上日語文學常見的內斂疏離,這篇自傳小文便輕易給人一種置身事外的錯覺,哪怕作者描寫的是發生于自身的故事,經歷的也是日本近現代史上最跌宕起伏的年代,讀者仍能飄浮在世界之上,雖然可以看到世事變遷,但卻能不受其影響進行思考。
《那是一個晴天》開篇于一個特殊的日子: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天。從那天起,作者周圍的世界仿佛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卻又仿佛維持了原樣,生活仿佛依舊照樣進行,醫學院的課程沒有因此改變,文樂劇團的巡演照常進行,地鐵的運行也沒有受到影響……漸漸地,民眾的情緒開始變了,但作者對戰爭及其后果的思考卻像是一層罩子,將他隔離開來,確保他能免疫于戰時群眾的情緒——不管是來自日本群眾,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民眾。他對東京的“發現”以及對生活的感動,來自一種更抽象的感情,并不來自共情或者私人經歷,卻是大愛的一種形式,是對和平和日常生活的珍惜。
在做史料研究時,自傳和日記都算作原始資料,可以幫助研究學者更深入地了解當時普通民眾的想法,借用過去的視角審視過去發生的事件。但加藤本人便是學者,他對時事的記錄有學者的風格,一邊記錄一邊分析,帶給后世的讀者多層更有趣的真相。這是過去的人所見的現實,亦是過去的人對他們的真相的理解,最后是留給現世人的解讀——皆是從不同角度出發,盡力觸摸歷史的真實。閱讀,大量的閱讀,反復的思考,也是接近真實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