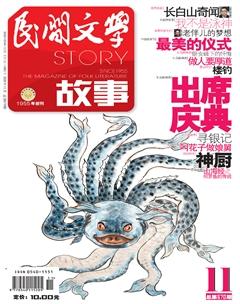出席慶典
程瓊
封山年逾八旬,是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文化名人。他自學成材的事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他詩詞曲賦、書法、繪畫等無所不精,主題大多是反映青白江區日新月異的變化,可以說他的作品就是青白江區的形象發展史。
這次青白江區要召開建區六十周年慶典,第一個想邀請的嘉賓就是他。工作人員把電話打過去,封山卻婉言謝絕了,相關領導上門邀請,也是一樣。封山說:“采訪可以,至于慶典,我就不參加了。”
籌委會也不敢強求,大家細細回顧了一下,此前舉辦的幾次建區大慶儀式,有三次邀請過他,但他都沒有參加。
“真是個怪老頭兒。十年才一次的大慶,多少人都夢寐以求出席,以見證歷史時刻,可他卻次次謝絕參加,真是不可思議。”籌委會副主任遺憾地說。
“會不會是怯場?”有人分析道。
從電視臺臨時抽調到籌委會工作的美女記者小李說:“我采訪過封老,他是老年書畫院的副院長。書畫院開年會,封老講話,根本不念稿子,但說出的話非常有條理,思維十分清晰,壓根兒看不出他年過八旬,說他怯場說不通。”
副主任沉吟一會兒后,對小李說:“封老雖然不愿參加慶典,但他本身就是一部青白江區的發展史。據我所知,解放后,他一直在我區工作,對我區的發展非常熟悉。剛才我跟你們臺長交流了一下,在電視上推出一個人物專訪欄目《輝煌六十年———我眼看家鄉》。封老是專訪中的第一個人物。小李,你先回電視臺,協助欄目組做好對封老的專訪工作。”
小李愉快地接受了任務:“好的,我會順便勸封老參加建區六十周年慶典。”
“如果封老參加慶典,你可就立了大功!”副主任高興地說。
第二天,小李就投入了采訪。在封家見到封老時,封老精神矍鑠,談笑風生,記性也好:“小李,去年年底我們書畫院開年會,就是你來采訪的。”
小李說:“封老,您記性真好。您今年高壽?”
封山爽朗地說:“米壽———八十八歲。‘八十八能合成個‘米字,所以稱為米壽。”
小李嘖嘖稱贊:“真看不出。封老,您的養生秘訣是什么?”
“哈哈,采訪偏題啦,你不是來采訪什么‘我眼看家鄉嗎?怎么現在成了‘我眼看養生了?”封老幽默地說道。
“偏一下題也是為正題熱身嘛。把您的養身之道說出來,也好讓更多老年人學習學習。”
“這就是我的養生之道呀。”
“什么?您還沒說呢。”
“你幫我說了呀:學習。學習就是我的養生之道。人腦是一臺精密的機器,長久不用,就會生銹,生銹了,就會癡呆。如果天天學習,天天用腦,腦子就會越用越靈活,想癡呆也癡呆不起來,這就是常言說的:活到老,學到老。”
小李點點頭:“您是我區自學成材的典型,年輕時多次被評為自學成材先進個人。請問,您自學的動力是什么呢?”
封老說:“不自學沒辦法呀,我參軍前只念過一年私塾,斗大的字也識不了幾筐。只有通過自學,日積月累,才能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包括不少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后,就停止學習了,結果漸漸跟不上形勢,被淘汰了。不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我也為之付出過代價,鬧過笑話。”
小李聽后,愣了一下。她大學畢業進入電視臺工作,也把書本扔到了一邊,平時有空都是打麻將玩手機。聽了封老的話后,她暗暗決定要繼續學習深造。
正式采訪開始后,封山積極配合,還到書房里拿出相關的照片、文章、日記、物件等讓小李拍攝。采訪中,小李了解到,封老是巴中人,在西南戰役中參加解放軍,當時才十七歲。解放成都后,四川肥料廠成立,他被調到該廠當秘書。當時很多南下干部都是文盲,封山好歹念過一年私塾,算是知識分子,雖然他寫的東西錯字百出,但領導們習慣了,也沒說什么。
隨著四川肥料廠、成都鋼鐵廠等企業的建設,職工和家屬人數猛增。職工生活、市政管理等問題凸顯了出來。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川肥料廠黨組向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作了關于在工廠建設地區設立工人鎮的請示,因為此地有清白江流過,所以該工人鎮就取名為青白江。
說到這兒,封山很鄭重地打開一個陳舊的皮箱,從箱底取出一本《四川肥料廠大事記》,翻開,取出一張發黃的信箋,遞給小李。
小李一看,上面的字是藍色復寫紙所寫,內容是當年四川肥料廠黨組向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關于在工廠建設地區設立工人鎮的請示,請示最后寫道:鎮的名稱可為成都市青白江鎮。
小李不解地問:“既然清白江流過本地,當初設區時為什么不寫作‘清白江,三點水的那個‘清白江?像黑龍江省的綏芬河市,就因為境內有綏芬河流過,所以取名叫綏芬河市。”
“這個,就是因為當時寫請示的那個人,知識有限,滿足于一知半解,寫錯了呀,把‘清白江寫成了‘青白江,把那三點水吃掉了!”
小李悟道:“封老,您就是當時寫請示的那個人?”
封山點點頭:“是呀,我當時也二十八歲了。可參加工作后,知識仍停留在當兵前的水平,因為那時我想,雖說我只念過一年私塾,可文化水平比那些文盲大老粗高多了。自我滿足,不思進取,結果就鬧了笑話,還是大笑話。直到青白江區成立后,掛了牌,才有人提出寫錯了,應該是‘清白江區。但事已至此,無法更改,只好一直叫青白江區,沿用至今。從那以后,我就發奮自學,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消滅錯別字,保證不再犯這種低級錯誤。”
“這就是您不愿參加建區六十周年慶典的原因?”小李問道。封山點點頭:“很多次慶典都邀請過我出席,可我都婉言謝絕了。我這個昔日的錯別字大王,沒有臉面參加呀。”
“封老,其實大可不必。曾有觀眾向我們電視臺反映過,既然青白江區有一條清白江,那為什么不把兩者統一為一個名稱,把區叫‘清白江區,或把那條江改名為‘青白江?網上論壇也征求過市民的意見,是沒有三點水的那個青白江區好聽,還是有三點水的清白江區好聽?結果絕大部分人都說是沒有三點水的那個青白江區好聽,因為這個青白江,更富有詩意:青天白日、青山白水、藍天白云。封老呀,您無意間的一次錯誤,造就了一個詩意地名的產生,全區人民都要感謝您呢!”
封老聽后,愣了半晌:“真的?”
小李說:“您比我爺爺年紀還大,我騙您干嗎?封老,您看這次六十周年慶典……”
“六十甲子一回頭,米壽老人有初心!好吧,這次慶典,我參加!”封老道。
采訪結束,小李告辭。她感到很欣慰:終于幫封爺爺走出內疚了六十年的陰影。
原來,小李的奶奶跟封山曾經是同事,封山當年寫錯別字的事,小李早就從奶奶那里聽說了。
那段安慰封老的話,是小李臨時發揮的。是呀,對于那些無法更改的現實,為什么不從正面挖掘出更多的美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