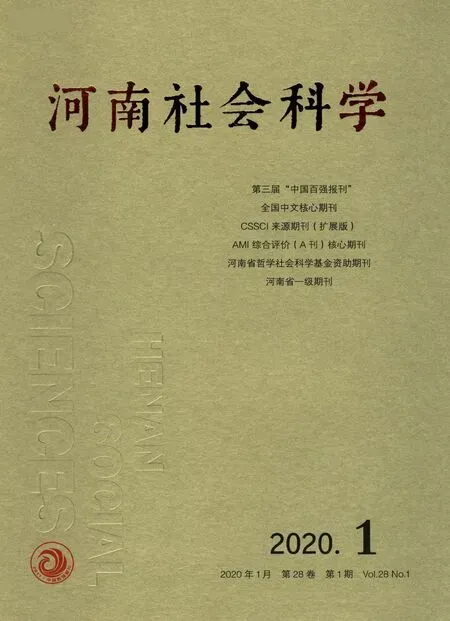中原學(xué)若干基本問(wèn)題再思考
周書(shū)燦,羅詩(shī)謙
(蘇州大學(xué) 社會(huì)學(xué)院,江蘇 蘇州 215123)
中原學(xué)是近年學(xué)術(shù)界提出并不斷受到學(xué)者重視的一個(gè)新的學(xué)科概念[1][2][3]。該概念一經(jīng)提出,就得到了部分學(xué)者的積極呼應(yīng)[4][5]。然而,作為一門(mén)綜合性極強(qiáng)的綜合性學(xué)科,尚有許多重要的關(guān)鍵性理論問(wèn)題有待學(xué)術(shù)界繼續(xù)作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對(duì)中原學(xué)的若干基本問(wèn)題重新作一番思考,以求教于學(xué)術(shù)界的同人方家。
一、歷史時(shí)期的中原非一般性的區(qū)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區(qū)
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中原”并非一個(gè)特定的區(qū)域名稱(chēng)。如《詩(shī)·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6]《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6]鄭箋:“中原,原中也。”[6]“原”屢屢出現(xiàn)于先秦文獻(xiàn)中,如《詩(shī)·小雅·常棣》“原隰裒矣”[6],《小雅·皇皇者華》:“于彼原隰。”[6]《毛傳》:“高平曰原。”《詩(shī)·大雅·公劉》:“于胥斯原。”[6]鄭箋:“廣平曰原。”《爾雅·釋地》則區(qū)分說(shuō):“廣平曰原,高平曰陸。”[7]在先秦秦漢時(shí)期人們的觀念中,“原”應(yīng)泛指大片廣平之地。《大雅·綿》“周原膴膴”[6],周原地處關(guān)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臨渭水,形如高阜,乃一片廣平之野。
古代文獻(xiàn)中,“中原”意即“原中”,尚可另舉數(shù)例。《國(guó)語(yǔ)·越語(yǔ)上》記載句踐對(duì)國(guó)人所言:“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guó)執(zhí)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寡人之罪也。”[8]《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以賢人君子,肝腦涂中原,膏液潤(rùn)野草而不辭也。”[9]《三國(guó)志·魏書(shū)·郭嘉傳》:“然策輕騎而無(wú)備,雖有百萬(wàn)之眾,無(wú)異于獨(dú)行中原也。”[10]通讀以上幾則材料,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上文字中的“中原”并非專(zhuān)指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今河南一帶。由此可知,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古代文獻(xiàn)中的“中原”約略相當(dāng)于“原中”,僅是一個(gè)泛稱(chēng)的概念。
“中原”名稱(chēng)從泛稱(chēng)到專(zhuān)稱(chēng)之演變,似亦經(jīng)歷了一段漫長(zhǎng)的時(shí)期。《國(guó)語(yǔ)》卷九《晉語(yǔ)三》記載公孫枝的一段話:“恥大國(guó)之士于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雖微秦國(guó),天下孰弗患?”[8]《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11]以上“中原”或與“天下”對(duì)稱(chēng),或與晉楚相對(duì),則此“中原”當(dāng)為語(yǔ)義相對(duì)明確的區(qū)域概念的專(zhuān)稱(chēng),大體相當(dāng)于今天的黃河中游地區(qū)。以后,《三國(guó)志·蜀書(shū)·諸葛亮傳》所記諸葛亮《出師表》中說(shuō)“獎(jiǎng)率三軍,北定中原”[10],諸葛亮所說(shuō)的“中原”,顯然指魏國(guó)所控制黃河中下游大片地區(qū)。謝靈運(yùn)《述祖德》有“中原昔喪亂”“萬(wàn)邦咸震懾”[12]之詩(shī)句,同樣,“中原”“萬(wàn)邦”對(duì)稱(chēng),學(xué)者認(rèn)為此“中原”當(dāng)指河南洛陽(yáng)一帶。“中原”語(yǔ)義從泛稱(chēng)到專(zhuān)稱(chēng)的演變,則顯然與中原地區(qū)在中國(guó)古代歷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
從中國(guó)古代歷史發(fā)展的進(jìn)程看,中原地區(qū)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搖籃和早期國(guó)家形成的關(guān)鍵性核心地帶。進(jìn)入文明時(shí)代后,中原地區(qū)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一直是中國(guó)古代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中心地區(qū)。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shuō):“昔唐人都河?xùn)|,殷人都河內(nèi),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guó)各數(shù)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guó)諸侯所聚會(huì)。”[9]在《封禪書(shū)》中也說(shuō):“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9]司馬遷的以上論斷,迄今基本都得到了田野考古資料的印證。司馬遷所說(shuō)的三河地區(qū)的河南,在西周王城洛陽(yáng)一帶,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稱(chēng)之為“中國(guó)”,唐蘭先生說(shuō):“當(dāng)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13]古人盛贊“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14],“欲問(wèn)古今興廢事,請(qǐng)君只看洛陽(yáng)城”[15],完全符合中國(guó)古代的歷史實(shí)際。正因?yàn)榇耍灰暈樘煜轮械闹性貐^(qū),與其說(shuō)為“天下之大湊”“道里均”[9],倒不如說(shuō)說(shuō)以上地區(qū)為“王者所更居”[9]的天下政治中心。
正由于“中原”在中國(guó)古代歷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與作用,文獻(xiàn)中往往“中原”“中國(guó)”相混稱(chēng)。諸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今夫韓、魏,中國(guó)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欲其霸,必親中國(guó)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9]以上是將韓、魏所在的中原地區(qū)直接稱(chēng)為“中國(guó)”。又如,《晉書(shū)·五行志》記載西晉時(shí)期江南童謠:“中國(guó)當(dāng)敗吳當(dāng)復(fù)。”[16]此處“中國(guó)”顯然是指定都于洛陽(yáng)的晉朝。《宋史·陳亮傳》記載陳亮的話:“荊襄之地……東通吳會(huì),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guān)洛……可以爭(zhēng)衡于中國(guó)矣。”[17]和前面兩則文獻(xiàn)中的“中國(guó)”語(yǔ)義類(lèi)似,陳亮所說(shuō)的“中國(guó)”顯然也是指的今廣大的中原地區(qū)。與此同時(shí),文獻(xiàn)中有時(shí)也以“中原”指代近代的中國(guó)。如鄭觀應(yīng)在《盛世危言·議院》中說(shuō):“況今中原大局,列國(guó)通商,勢(shì)難拒絕,則不得不律之以公法。”[18]以上“中原”與近代的“列國(guó)”相對(duì)應(yīng),則顯然以“中原”來(lái)指代近代的中國(guó)。
歷史時(shí)期的“中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搖籃和早期國(guó)家形成的核心地帶,在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期,中原是中國(guó)古代政治、經(jīng)濟(jì)的中心,中原還是中國(guó)古代主流文化、主導(dǎo)文化的起源地,被認(rèn)為中原學(xué)重要研究對(duì)象的中原文化,構(gòu)成中華文化的源頭和核心組成部分。正由于中原地區(qū)在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所具有的獨(dú)特的地位和作用,和歷史上地理范圍相對(duì)明確的關(guān)中、巴蜀、湖湘、荊楚、嶺南、燕趙、齊魯、吳越等區(qū)域地理概念不同,中原并非一個(gè)一般性的區(qū)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區(qū)。
二、先秦至北宋的中原學(xué)實(shí)乃中國(guó)學(xué),非普通的地域?qū)W術(shù)文化
早在中原學(xué)概念提出的前后,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某些地域特色極強(qiáng)的地方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及學(xué)科性質(zhì)、體系等重要理論性問(wèn)題進(jìn)行過(guò)大量有價(jià)值的探索,其中涉及若干重要地域?qū)W術(shù)文化的空間范圍、時(shí)間界限和重點(diǎn)時(shí)段問(wèn)題。如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蜀學(xué)’,是指四川地區(qū)的學(xué)術(shù),其重點(diǎn)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論,它是中國(guó)重要的地域?qū)W術(shù)文化。”[19]“其時(shí)間上限可考慮大體自蜀國(guó)、巴國(guó)開(kāi)始……蜀學(xué)研究的時(shí)間下限應(yīng)該及于當(dāng)今。”[19]亦有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湘學(xué)“專(zhuān)以湖南地區(qū)的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展為研究對(duì)象”[20],“特別是宋以后的湖南學(xué)術(shù)史”[20],“其下限大致地確定在清末民初之際”[20]。近年,有的學(xué)者指出,“徽學(xué)是一門(mén)以徽州歷史文化、特別是兩宋之際至民國(guó)建立前的徽州歷史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的區(qū)域史研究”[21]。嚴(yán)格地講,以上論述,并非皆為學(xué)術(shù)界的最后定論,某些論斷仍有大量可商榷之處,如既然蜀學(xué)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地域?qū)W術(sh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蜀學(xué)的下限是否應(yīng)該“及于當(dāng)今”?但總的來(lái)看,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以上地方學(xué)的重點(diǎn)時(shí)段,多自宋代至清末民初。
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中原學(xué)的空間范圍、時(shí)間界限等重要理論性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尚存在諸多分歧。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中原學(xué)’以中原哲學(xué)、政治、歷史、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制度為研究對(duì)象”[22],“在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體系中,‘中原學(xué)’既是源,也是流”[22]。另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中原學(xué)的研究,應(yīng)以廣義的中原概念為基礎(chǔ),以狹義的中原概念為核心而進(jìn)行布局”[23]。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中原學(xué)“是對(duì)傳統(tǒng)中原理學(xué)(宋學(xué)中二程之洛學(xué))的揚(yáng)棄,是對(duì)馮友蘭‘新理學(xué)’的‘接著講’,是以中原歷史文化為根基的當(dāng)代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科體系”[24]。也有學(xué)者指出,中原學(xué)“是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這一特定地域所存在的問(wèn)題為研究對(duì)象的專(zhuān)門(mén)學(xué)問(wèn)”[25]。專(zhuān)家普遍認(rèn)為,迄今為止,地方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尚未建立,尤其像中原學(xué)研究,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很有必要在新的學(xué)術(shù)背景下,對(duì)以上觀點(diǎn)進(jìn)行進(jìn)一步更為深入的思考。如,有的學(xué)者說(shuō),“‘中原學(xué)’既是源,也是流”,“源”和“流”之間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又如學(xué)術(shù)界既然普遍認(rèn)為,湘學(xué)、蜀學(xué)、浙學(xué)等學(xué)科均屬于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階段的地域?qū)W術(shù)文化,那么中原學(xué)是否屬于“對(duì)馮友蘭‘新理學(xué)’的‘接著講’”的“以中原歷史文化為根基的當(dāng)代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科體系”,頗為值得進(jìn)一步斟酌。
按照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蜀學(xué)、湘學(xué)、浙學(xué)等地方學(xué)空間范圍、時(shí)間界限和重要時(shí)段的一般理解,則中原學(xué)應(yīng)指歷史時(shí)期廣義的中原地區(qū)的學(xué)術(shù)文化。然而歷史上的中原地區(qū),從未形成為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文化區(qū)。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guó)家形成過(guò)程中,中原地區(qū)是一個(gè)八方輻輳的大舞臺(tái),“各地先進(jìn)的文化因素匯聚到中原,經(jīng)過(guò)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chē)貐^(qū)輻射”[26],從而加速著各地區(qū)的文明化進(jìn)程。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中原地區(qū)長(zhǎng)期是大國(guó)爭(zhēng)霸和戎狄攻略的重要戰(zhàn)場(chǎng)。顧棟高說(shuō):“春秋之初,宋、鄭號(hào)中原大國(guó)。”[27]“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zhàn)。”[27]“每當(dāng)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fā)難。”[27]“蓋以其地踞中原,關(guān)于天下之故。”[27]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魏國(guó)徙都大梁,《戰(zhàn)國(guó)策·魏策一》記載張儀稱(chēng)魏都大梁所在中原地區(qū),“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dá)輻輳,無(wú)有名山大川之阻……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28]。古人對(duì)今河南所在中原地區(qū)的軍事地理形勢(shì)作過(guò)評(píng)說(shuō):“河南,古所稱(chēng)四戰(zhàn)之地也。當(dāng)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zhēng);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shì)矣。”[29]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中原地區(qū)作為中國(guó)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中心和軍事戰(zhàn)略要地,自然也是東西南北文化匯聚和交流的重要地區(qū),籠統(tǒng)地將中原地區(qū)作為中原學(xué)研究的空間范圍,顯然很容易掩蓋中原文化與周邊各地區(qū)文化之間相互交流滲透的客觀事實(shí),自然也很難全面準(zhǔn)確地揭示和反映中原學(xué)的真實(shí)面貌。
中原學(xué)的時(shí)間界限可上溯至先秦時(shí)期百家爭(zhēng)鳴,下限則可以延伸至清末民初。與宋代以后逐漸興起的湘學(xué)、浙學(xué)不同,中原學(xué)則呈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保守性和落后的一面。如河南學(xué)者即曾實(shí)事求是地講:“河南的學(xué)術(shù)在明代就已經(jīng)顯示出明顯的保守性,這雖然與全國(guó)的總體趨勢(shì)大體一致,但河南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這種趨勢(shì)發(fā)展到清代愈加顯著,已處于學(xué)術(shù)低谷,不僅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江浙諸省,甚至落后于山陜地區(qū)。”[30]中原學(xué)最具特色的時(shí)段恰在春秋戰(zhàn)國(guó)至北宋時(shí)期,而該階段的中原學(xué)中有特色的春秋戰(zhàn)國(guó)諸子學(xué)、兩漢經(jīng)學(xué)以及宋代理學(xué),均非一般意義的地方學(xué)術(shù)文化,而是構(gòu)成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組成部分,因而其完全可以視為該階段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主干的中國(guó)學(xué)。
三、中原學(xué)學(xué)科理論體系建構(gòu)和中原學(xué)研究的幾點(diǎn)思考
除中原學(xué),近年學(xué)術(shù)界還陸續(xù)提出了長(zhǎng)安學(xué)、洛陽(yáng)學(xué)、北京學(xué)等學(xué)科名稱(chēng)。迄今為止,以上學(xué)科的命名似乎仍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爭(zhēng)議。如有的學(xué)者即曾實(shí)事求是地指出,“無(wú)論在學(xué)界抑或在社會(huì),長(zhǎng)安學(xué)的認(rèn)可度都存在一定問(wèn)題”[31]。諸如“對(duì)長(zhǎng)安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這樣重大的問(wèn)題,論者的看法都不一樣,至于一些小的方面,分歧自然就更在所難免了”[31],“長(zhǎng)安學(xué)的命題雖說(shuō)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較為空泛甚至大而無(wú)當(dāng)?shù)牧硪幻妗K幌褚延械摹鼗蛯W(xué)’、‘紅學(xué)’那樣范圍具體,易于把握”[31]。與此同時(shí),也有學(xué)者主張使用“浙東學(xué)術(shù)”或“浙東學(xué)派”這些同樣是歷史地形成的概念,而較少使用“浙學(xué)”這一更可能含有歧義的術(shù)語(yǔ),或許尤能突出浙江文化自南宋以來(lái)所形成的富有區(qū)別性的學(xué)術(shù)特征[32]。事實(shí)上,以上的問(wèn)題在中原學(xué)研究過(guò)程中也同樣存在。如2016 年12 月23 日,河南省社科聯(lián)在鄭州召開(kāi)的塑造中國(guó)特色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中原品牌與“中原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座談會(huì)上,有的學(xué)者即曾強(qiáng)調(diào),必須把“中原學(xué)”的概念和范圍界定準(zhǔn)確[33];另有學(xué)者指出,建設(shè)“中原學(xué)”學(xué)科必須有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和比較完整的框架結(jié)構(gòu)[33];進(jìn)一步梳理“中原學(xué)”,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范疇、基本問(wèn)題,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問(wèn)題[33]。總之,學(xué)者普遍認(rèn)為,“中原學(xué)”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總體來(lái)講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體系。從學(xué)術(shù)角度來(lái)研究“中原學(xué)”,顯然這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并且非常艱苦的工作過(guò)程[33]。顯然,加速中原學(xué)學(xué)科理論體系建構(gòu),是深入開(kāi)展中原學(xué)研究的當(dāng)務(wù)之急的基礎(chǔ)性工作。
筆者認(rèn)為,中原學(xué)學(xué)科理論體系建構(gòu)和中原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明確以下幾點(diǎn)認(rèn)識(shí):
第一,中原學(xué)研究應(yīng)擴(kuò)大學(xué)術(shù)視野,打破地域限制,立足中原,面向世界。中原文化具有很強(qiáng)的開(kāi)放性,以中原歷史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的中原學(xué),應(yīng)該打破狹隘的地域觀念,以歷史時(shí)期的中國(guó)乃至世界作為研究背景,才能準(zhǔn)確把握中原地區(qū)在中國(guó)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國(guó)家形成發(fā)展及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演進(jìn)過(gu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有的學(xué)者曾指出,“歷史上以河洛地區(qū)為中心的中原漢族人民不斷南遷,促進(jìn)了南方廣大地區(qū)的民族融合,同時(shí)將先進(jìn)的河洛文化帶到了南方和沿海地區(qū),贛、閩、臺(tái)等地的人民與河洛人有著共同的血緣關(guān)系,河洛文化對(duì)閩南文化、嶺南文化、客家文化、臺(tái)灣文化、贛鄱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34]。不唯如此,歷史時(shí)期中原地區(qū)的人口流入、徙出與民族融合問(wèn)題,歷史時(shí)期中原文化的跨區(qū)域輻射傳播與文化間雙向交流問(wèn)題,歷史時(shí)期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及社會(huì)治理等問(wèn)題的研究,也都往往與中原地區(qū)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同時(shí)又超越學(xué)術(shù)界所理解的中原地區(qū)的范圍。
第二,中原學(xué)涉及哲學(xué)、歷史、語(yǔ)言、考古、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人口、民族、體育、軍事、水利、醫(yī)學(xué)、天文、農(nóng)業(yè)等諸多學(xué)科門(mén)類(lèi),具有很強(qiáng)的綜合性。以前學(xué)術(shù)界界定藏學(xué)“是研究藏族社會(huì)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門(mén)綜合性學(xué)科”[35],隨著藏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目前學(xué)術(shù)界更強(qiáng)調(diào)其所具有的“跨學(xué)科、跨區(qū)域、跨文化和跨國(guó)界的特點(diǎn)”[36]。目前亦有學(xué)者指出,敦煌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以敦煌遺書(shū)、敦煌石窟藝術(shù)、敦煌史跡和敦煌學(xué)理論等為主,包括上述研究對(duì)象所涉及的歷史、地理、社會(huì)、哲學(xué)、宗教、考古、藝術(shù)、語(yǔ)言、文學(xué)、民族、音樂(lè)、舞蹈、建筑、科技等諸多學(xué)科,其學(xué)科性質(zhì)應(yīng)屬新興交叉學(xué)科”[37]。顯然,同樣具有新興交叉學(xué)科性質(zhì)的中原學(xué),也具有以上學(xué)科所具有的跨學(xué)科、跨區(qū)域、跨文化和跨國(guó)界特點(diǎn),以中原文獻(xiàn)整理和研究為基礎(chǔ),開(kāi)展跨學(xué)科、跨區(qū)域、跨文化和跨國(guó)界研究,顯然也是中原學(xué)研究未來(lái)的學(xué)術(shù)走向。
第三,中原學(xué)與河洛文化、洛陽(yáng)學(xué)、開(kāi)封學(xué)、安陽(yáng)學(xué)等學(xué)科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學(xué)術(shù)界尚無(wú)一致意見(jiàn)。有的學(xué)者說(shuō),現(xiàn)今各式各樣的“學(xué)”實(shí)在太多了,幾乎到了泛濫的程度[31]。這并非夸張之語(yǔ),頗為準(zhǔn)確地反映出了學(xué)術(shù)界當(dāng)下“學(xué)科林立”的狀況。有的學(xué)者評(píng)價(jià)近年洛陽(yáng)學(xué)研究,“僅僅有概念的提出,而缺乏深層的論述”[38]。從已有的洛陽(yáng)學(xué)研究成果看,很多學(xué)者對(duì)洛陽(yáng)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時(shí)間范圍、學(xué)科性質(zhì)等關(guān)鍵性的理論問(wèn)題,眾說(shuō)紛紜,且大多淺嘗輒止。顯然,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要講清楚中原學(xué)和洛陽(yáng)學(xué)等地方學(xué)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研究對(duì)象、時(shí)間范圍和重點(diǎn)關(guān)注領(lǐng)域是否完全吻合或差異甚遠(yuǎn),則顯得為時(shí)尚早。
第四,先秦至北宋時(shí)期的中原文化總體上構(gòu)成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組成部分,對(duì)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毛澤東早就講過(guò):“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guò)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wú)批判地兼收并蓄。”[39]胡錦濤也曾指出:“要全面認(rèn)識(shí)祖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相適應(yīng)、與現(xiàn)代文明相協(xié)調(diào),保護(hù)民族性,體現(xiàn)時(shí)代性。”[40]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dǎo)下,堅(jiān)持對(duì)歷史時(shí)期的中原文化批判地繼承,完善并創(chuàng)新,以中原歷史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的中原學(xué)才會(huì)不斷有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 河南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中美貿(mào)易摩擦對(duì)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的中長(zhǎng)期影響研究
- 中國(guó)對(duì)外直接投資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研究
- 推進(jìn)市縣人大預(yù)算聯(lián)網(wǎng)監(jiān)督系統(tǒng)建設(shè)的實(shí)踐與啟示
——以河南省Z市為例 - 服務(wù)與智慧雙輪驅(qū)動(dòng)的樓宇經(jīng)濟(jì)管理模式及實(shí)現(xiàn)路徑
- 比較視域中的馬來(lái)西亞政黨體制轉(zhuǎn)型:執(zhí)政惰性的理論視角
- 中原學(xué)發(fā)展專(zhuān)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