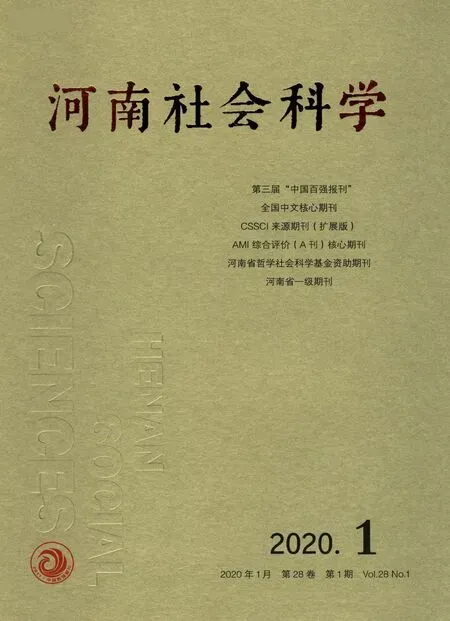從“唐宋變革”到“宋元近世”
——論宋代文藝思想的轉型特征及其典范性與近世性①
李飛躍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漢唐”“唐宋”“宋元”“宋明”是古典文學與歷史文化研究的基本范疇。在文學史上有“唐宋文學”與“宋元文學”的不同分期,藝術史上有“唐宋”與“宋元”之分,思想史上也有“唐宋”與“宋明”之別。基于不同視域,宋代文藝思想呈現不同的形態與景觀。“唐宋變革”與“宋元近世”是認識唐宋元時期歷史轉型有影響力的理論范式,但前者的立足點在于以漢唐觀宋,而后者則以元明衡宋,宋代的主體性與獨特性未能凸顯。將宋代文藝置于“唐宋變革”與“宋元近世”的雙重視域之中,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宋代文藝“繼往”的一面,也可以考察其“開來”的一面,凸顯作為相對獨立而非從屬并置的宋代文藝思想的本體特征與歷史地位。
一、宋代的社會新變與文化繁榮
宋代疆域雖然小于唐代,又不斷受北方和西方少數民族侵擾,但長期以來卻呈現出社會較為安定、經濟較大發展的局面。北宋太宗末年,全國僅400多萬戶,仁宗末年已增加到1200多萬戶,到徽宗初年更超過了2000 萬戶,人口總數突破1 億,超出漢唐一倍,是清代以前中國人口數字的最高紀錄②。南宋喪失了北宋近五分之二的疆土,寧宗末年的戶數仍超過1260萬。兩宋涌現了一批戶數眾多、商戶云集的大城市。唐代中期10 萬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3 座,到宋代中期已達46 座,尤其“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③。南宋城市的繁華程度較北宋有增無減,耐得翁《都城紀勝序》說:“自高宗駐蹕于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作,然中興以來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倍也。”④
宋代將城中非農業人口“坊郭戶”單獨編列,市民可靈活調整商業布局的空間和時間。馬克思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⑤北宋城市突破了漢唐“坊市制”限制,可面街設店。南宋城區的擴展又突破了城墻束縛,使市郊連成一體。坊市制度的破壞,區域性市場的形成,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都促進了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商業街區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屢屢出現,以及城墻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變了宋以前中國傳統城市的內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⑥美國學者施堅雅(U.W.Skinner)將這種城市化稱為“中世紀城市革命”⑦。城市人口的飆升和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加造就了平民社會與市民階級。宋代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礎性、結構性變化,影響和塑造了宋代文藝的基本形態。
鑒于五代藩鎮之弊,宋朝中央高度集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⑧。皇權鞏固后,開始重視文教事業,優待文士,借由科舉出仕的文臣超過歷代。君主多向文,宋太祖“性好藝文”⑨,太宗“銳意文史”⑩,真宗則“道遵先志,肇振斯文”[11],宋徽宗、宋高宗也都是文藝修養較高的君王。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達到極高峰,“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進的國家”[12]。科技成就尤其突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13]。宋代更是古典文學和文化高度發展的時期,當時朱熹已然斷言:“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4]政治氛圍相對寬松,文化管理較為開放,當時對詩文賦等文學創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管控嚴格,而對新興通俗文藝諸如說話、唱賺、雜劇等則放任發展。隨著新興文藝的影響越來越大,統治者開始對俗詞俚曲、雜劇說話等進行批評引導甚至查禁,但已屢禁不止。
唐代的三教論衡,至宋則趨向三教圓融。宋朝君主承認“三教之設,其旨一也”,號召“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15]。北宋大儒程顥之學“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16]。新儒家親近和出入佛老,道教和佛教也主張相互融攝。道教內丹派南宗開山祖師張伯端宣稱“教雖分三,道乃歸一”[17],天臺宗名僧智圓也主張“修身以儒,治心以釋”[18]。南宋理學取代佛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主要信仰,可以說就是一次宗教改革與思想革命。三教圓融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思維方式,賦予了講唱、戲曲、小說等敘事文學以濃郁的近世思想色彩。
宋代書院數量眾多[19],繼承了編刻、聚藏、傳播書籍的文化傳統,又汲取和融合了諸家文化特點,發展成為教育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術機構。經學上打破了“疏不破注”的師法,疑經思潮迭起。士人立德立言意識增強,重視獨立見解和質疑批判,具有較強的理性精神。“士”之身份和角色的變遷,反映了整個社會和文化由貴族化向平民化的轉變。“‘士’在唐代的多數時間里可以被譯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譯為‘文官家族’,在南宋時期可以譯為‘地方精英’。”[20]他們的主要經歷已非游宦從軍,而是轉向地方實業和文化建設,追求詩歌、書法、繪畫、音樂等文藝的全面發展,是才藝兼修和綜合素養較高的新式文人。“相對于唐人的漫游生涯和熱愛自然風物,琴、棋、書、畫、茶、酒、花、詩是宋代士大夫休閑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們沉醉于人文意境,追求一種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和悠閑脫俗的精神享受。”[21]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的變化,導致宋代文藝的形態和功能出現了全新變化。
與以往宮廷、幕府、地域文人集團不同,宋代文人借由家族、師承、黨派、書會、地域、流派等形成了具有共同愛好和審美追求的文人團體。隨著科舉、學校和書院的發展,形成了按師門學緣劃分的“蘇門六君子”,按照地域劃分的“江西詩派”,按照政治觀念劃分的“元祐黨人”等。他們有共同的文學主張與審美傾向,有意進行文集結撰,開始注意作品的保存、傳播及闡發。隨著《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編訖,《資治通鑒》《新唐書》《新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大批史籍相繼出版,產生了“百科全書式”的《夢溪筆談》和一代風俗寫照的《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宋人好質疑、好議論,本身就是對累積資料的一種批判接受和基于當時人們經驗的知識重構。
宋學的懷疑、批判、創新、兼容、尚簡等精神氤氳到社會生活、文學藝術領域,使宋朝文化呈現出獨特景觀,甚至成為古典文化發展的一道分水嶺。元人將漢、唐、宋稱為“后三代”[22],是置其于中古文化區間而言。后人則更多關注宋代對近世文化的塑造,錢穆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23]金毓黻說:“國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轉捩,凡有三時期:其一為秦漢,其二為隋唐,其三為宋遼金。”“宋代膺古今最劇之變局,為劃時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幾乎無一不與之相緣,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遼金史,實力治近代史之始基”[24]。法國漢學家謝和耐也指出:“11—13世紀期間,在政治、社會或生活諸領域中沒有一處不表現出較先前時代的深刻變化。這里不單單是指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而更是指一種質的變化。政治風俗、社會、階級關系、軍隊、城鄉關系和經濟形態均與唐朝貴族的和仍是中世紀中期的帝國完全不同。一個新的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說已是近代中國特征的端倪了。”[25]
概言之,中國社會在宋代已經走出了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為區間的中古,出現了一種類似于西方“文藝復興”的劃時代變革。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到價值觀念的種種新變,使宋代文藝思想發生了深刻轉向。宋代居于中國古典文藝承前啟后的階段,我們應從大歷史格局中審視宋代文藝的時代特征,將之放在中古以至新文化運動以前的長時段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著眼其對近世文藝尤其通俗文藝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宋代文藝思想的價值意義與歷史特征重新界定。
二、宋代文藝的歷史轉型與思想特征
宋代文藝處于中古向近世轉型時期,從活動主體、種類構成到形態功能都發生了深刻改變。
一是作為活動主體的文人職業化與藝人社團化。宋前文學創作的主體多是貴族或中上層文士,作品主要用于潤色鴻業、“為時事而作”,而宋代文學作者的身份地位、思想觀念及創作傾向都發生了改變。隨著科舉擴員和冗官現象日益增多,讀書人越來越難躋身統治階層,被迫另謀生路,以至士大夫子弟“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26]。一些文人以詩文為商品,走上了世俗化的市場之路。還有詩人化身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27]。有些文人與書商、伶工合作,直接參與文藝創演。據張政烺考察,周密《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條所載喬萬卷、武書生、王貢士、張解元、陳進士等23名演史者,“皆讀書人,萬卷極言其記誦之博也”,不過“此諸人未必皆出科舉,蓋有儒生試而不第者,所謂‘免解進士’‘白衣秀才’之類也”[28]。書會中亦有一些才高名重的公卿顯宦,但以低級官吏、商人、醫生、倡優居多。他們的文學創作主要是依據民間傳說或經史演義,采用賺詞、諸宮調、院本、雜劇、平話等多種文藝形式,呈現出與傳統經典文學的不同形態與功能。他們組成的永嘉書會撰有《白兔記》、九山書會撰有《張協狀元》、古杭州書會撰有《小孫屠》等,這些書會還兼營刻書與發行業務。新經典的生成,普遍具有集體化、通俗化與累積性特征。
社團化、集體化的文學活動,在民間文藝創演中最為通行。逢祭祀或節慶日,有歌伎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蘇家巷傀儡社、富豪子弟緋綠清音社等[29]。如淳熙年間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震山行宮朝拜極盛,有“緋綠社(雜劇)、齊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抵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凈發社(梳剃)、律華社(吟叫)、云機社(撮弄)”,可謂百戲競集。會社成員人數普遍較多,僅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人;川鮑老亦有一百余人”[30]。“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遏云、棹刀鮑老、胡女、劉袞、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覺錘架兒、侍女、杵歌、諸國朝、竹馬兒、村田樂、神鬼、十齋郎各社,不下數十。”[31]藝人們按照藝術門類交流心得,相互借鑒乃至共同創作和演出。他們分工細致,各有藝名,每種表演形式都有代表性名角。北宋聞名京師的講史藝人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小說藝人有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說諢話藝人有張山人,諸宮調藝人有孔三傳、耍秀才等[32]。崇寧、大觀以來,小唱最出名的是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當時說唱伎藝的專業化程度已非常高,如南宋時期的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33]。他們在慶祝傳統節日、婚喪嫁娶及宗教祭祀等活動中搭建樂棚、露臺、彩棚等臨時性表演空間,以及在酒樓、妓館、府邸等私人演出場所定時演出,逐漸發展為日常化文藝活動。文人的職業化和藝人的組織化,尤其文藝社團的出現與運行、文藝作品的商業化,標志著近世文藝基本形態的形成。
二是不同文藝種類的涌現與文藝思想的二元分化。宋代民間流行的文學體裁、題材很快成為雅俗共賞的流行文學。文人士大夫自覺從事不同層次的文藝創作,如晏殊、歐陽修在朝為官以詩文名,兼事艷科小道的詞的創作。宋太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精通詞曲、繪畫、書法,亦好雜劇、說話等藝術。孝宗時,“后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皇趙構很快辨識出:“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34]此外,洪邁、劉斧、皇都風月主人等從事小說創作和收集,沈括、陳旸、周密、陳元靚等熱衷于對民間歌舞的記載,都留下了傳世之作。在柳永、趙令畤、秦觀、曹組等人投入通俗文藝創作的同時,也涌現了一批天才的民間文藝家,他們基于實踐形成或改進了鼓子詞、諸宮調、賺詞、雜劇等文藝形式。包括纏令、纏達在內的賺詞,是詩詞曲等抒情藝術向戲曲、小說等綜合敘事藝術轉變的一大關節。“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有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35]“中興后,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為‘賺’。”張五牛因襲了賺鼓板的名稱,運用纏令、纏達等曲體結構發展成為新的說唱藝術,“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36]。據《夢粱錄》與《武林舊事》載,臨安勾欄的著名唱賺藝人達32人之多,其中李霜涯“作賺絕倫”。
傳統經典文藝與民間新興文藝共同造就了宋代文藝的大發展與繁榮。宋初時文與古文并爭,詩歌日常化與說理化、議論性與敘事性交織,發展成為江西詩派與江湖詩派競盛。俗詞與雅詞爭競,婉約派與豪放派并峙。音樂上雅樂與俗樂,繪畫上院體畫與民間畫齊頭爭進。當時影響較大的佛教門派有禪宗與凈土宗,前者流行于士大夫階層,后者普及基層民眾。禪宗從“不立文字”向“文字禪”蛻變,以俗兼雅。文藝的娛樂功能漸被政治和道德削弱,出現了“教化說”“言志說”“明道說”“比德說”等。一方面道學思想強化,排斥通俗文藝;另一方面民間文藝逐漸形成新的標準,具有了文學的獨立性,它們共同構成了宋代文藝多層次的豐富景觀。
三是傳統文藝呈現出總結性、集成性成就。宋代文學作品通過印刷傳播,不僅擴大了受眾面,也避免了抄寫中產生訛誤,促進了文體的規范與統一。宋代各類文學體裁、各種藝術形式都獲得集成性的空前發展。《宋史·藝文志》著錄宋人撰述達“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三卷”。其中,“有別集流傳者六百余家,如以無別集而文章零散傳世者合而計之,作者將逾萬人,作品超出十萬”[37]。宋代作家作品數倍于唐代,涌現了一批經典文學大家,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占六家,詩歌方面形成了西昆體,出現了歐王蘇黃等巨擘。歌詞方面有歐蘇、柳秦、周姜等爭艷,書法有宋體與“宋四家”競妍。各文藝門類都出現了具有宋代風格的代表性成就,宋詞、宋詩、宋畫、宋體、宋版、宋瓷、宋錦、唐宋大曲、宋金雜劇、宋元戲曲、宋元話本、宋代園林、宋代金石、唐宋傳奇、唐宋八大家、宋明理學等一系列文藝成就諸峰并峙,幾乎每個文藝類型都在宋代達到了極高水平。古典文藝在宋代取得了集成性和典范性成就,以至后來的主流文藝只能別開蹊徑。
宋人在詩歌、散文、詞賦、小說、戲曲等創作基礎上,也提出了具有概括性和創造性的理論。“文道說”“妙悟說”“興趣說”“點鐵成金”“別是一家”等理論,從深層和根本上探討詩詞文藝術的本質與功能。西昆體、江西詩派、江湖詩派流行的同時,反思一直未有停止,屢見對“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學問為詩”的反思。劉克莊《敘林希逸詩》說:“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主文,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38]《滄浪詩話》的產生,“標志著我國古典詩歌復古時期的開始,此后直至清末,古典詩歌基本上是在復古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39]。李清照《詞論》、王灼《碧雞漫志》、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等奠定了作為一代之文學的宋詞的史論基礎。《宋文鑒》《瀛奎律髓》《草堂詩余》等總集的編纂,以及以《醉翁談錄》《事林廣記》《唱論》《中原音韻》等為代表的基于觀演體驗和辨體尊體的宋元批評理論逐漸確立。
四是受眾平民化使宋代文藝開始注重日常經驗與通俗表達。接受對象的市民化或大眾化,促進了音樂、舞蹈、文史等文藝形式的通俗化轉型。仁宗年間,張方平奏論雅樂指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狠惡污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40]專供國家典禮的太常樂工竟由雜居里巷的市井屠販充任,而宋徽宗政和年間,“京師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內教舞”[41]。民間商業性講史活動日益活躍,汴京瓦市以講史聞名的藝人就有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霍四究、尹常賣等。其中,霍四究擅長“說三分”,尹常賣長于講述“五代史”(《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南宋時僅周密《武林舊事》中所載臨安瓦市講史者就有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等二十三人。此外,尚有“講諸史俱通”的王六大夫等。他們在向大眾講述歷史知識的同時,也開始用民間視角對史事和人物加工再造,為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等經典小說生成奠定了基礎。
“宋詩的日常生活化,可說是近世詩歌乃至近世文學的一個總體特征。”[42]宋詩較唐詩更注重寫實,貼近生活,“過去的詩人所忽視的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或者事情本身不應被忽視,但因為是普遍的、日常的和人們太貼近的生活內容,因而沒有作為詩的素材,這些宋人都大量地寫成詩歌。所以宋詩比起過去的詩,與生活結合得遠為緊密”[43]。宋詩議論時政,描寫民生,品藝說理,達到了“無事不可入”“無理不可窮”的境地。“凡唐人以為不能入詩或不宜入詩之材料,宋人皆寫入詩中,且往往喜于瑣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蘇黃多詠墨、詠紙、詠硯、詠茶、詠畫扇、詠飲食之詩,而一詠茶小詩,可以和韻四五次。”[44]“古未有詩”的題材物象、句式詞語等入詩,促進了宋詩語言的通俗化和近體詩格律聲韻的變異(如以古入律)。黃庭堅主張作詩“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其詞“酷似曲”,被后人稱為“蒜酪體”。楊萬里詩的“俗語”不少來自當時的口語白話,通俗易懂。范成大詩“平淺”,陸游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藝概·詩概》)。嚴羽力主學詩必去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等五俗,指摘的恰是宋詩中大量存在的創作現實。宋詩突破了唐詩的爛熟套數,趨近散文和口語的以文為詩,不避瑣碎的日常事物,不求雕琢出新的語言表達。“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45],幾成詩壇共識。如果將一部詩歌史簡化為詩歌語言形式的變化史,那么,“中國詩歌語言的演變過程中最具有‘革命’意義的變化,除了古詩到齊梁體詩及唐詩的那一次之外,就要算從宋詩一直延續到本世紀白話詩運動的詩歌語言演變了”[46]。
此外,柳永“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47],“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48]。后人稱歐陽修與“三蘇”文章的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49]。范仲淹《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以為“《傳奇》體爾”。黃庭堅自述“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50]。近世多數通俗文藝品種幾乎都在此時產生,如小唱、般雜劇、傀儡、講史、小說、影戲、散樂、諸宮調、商謎、雜班、弄蟲蟻、合聲、說諢話、叫果子等[51]。《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臨安瓦舍伎藝云:“唱涯詞只引子弟,聽陶真盡是村人。”因其題材與文詞通俗,故為村民所喜。用口語或白話寫出的小說,打破了文言對文壇的壟斷。六朝志怪和志人小說主要記載神異鬼怪和歷史名人,唐傳奇主要寫上層人物,宋元話本小說轉而將城市下層人物和日常生活作為表現對象,魯迅稱之為“平民底小說”[52]。描寫愛情婚姻的《調笑轉踏》《碾玉觀音》等作品熱烈贊頌自由戀愛、自主婚姻,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反抗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婚姻制度,體現了市民階層對愛情婚姻的看法和呼聲。市民階層成為作品主角,標志著中國文藝主體從貴族文士到平民大眾的歷史性轉變。
五是集成性與綜合化帶來宋代文藝形式的融通轉變。宋代文學從嚴辨體的同時,不斷出現跨界和打通,如以詩為詞、以文賦為詞、以詞為曲、以詩論藝等。蘇軾“以詩為詞”、周邦彥“以賦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提出了一批學理概念。不同文藝形式相互借鑒融合,書論、畫論和曲論普遍借鑒傳統詩論、文論術語,諸多文論或批評術語就是來自書畫、樂舞,書畫一體、詩畫一體已成為重要學術命題。儒釋道相互融合,宋詩好用佛典,化用佛道意象,抒發宗教體驗。
在民間藝人和專業行會推動下,各種說唱藝術爭奇斗艷,向著普及面更廣、綜合性更強的藝術形式發展。勾欄瓦舍集聚了眾多百戲雜技藝人,宮廷藝人、官妓、營妓等混雜其間。流行的嘌唱、耍令與吟叫同出一源,嘌唱“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為一體”,它們原本流行于街市:“若嘌唱耍令,今者如路岐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采合宮商成其詞也。”[53]相近藝術形式的結合,派生出新的說唱藝術“吟叫”,分為“下影帶”“散叫”“打拍”等。形式不斷翻新,內容更加豐富多彩。《東京夢華錄》載:“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54]唱賺吸收了多種藝術形式要素,在南宋中葉后又發展為覆賺,為后世的戲曲、曲藝所吸收。說唱包含說、談、講、論、言等多種成分,話本兼具聲音、圖像和文字三要素,已開始從依靠聲音為主的說唱、圖像為輔的變相轉向圖文結合的全相話本。
隨著文藝形式的綜合化、集成化,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說唱、戲曲等結合日漸增多。文學擴大影響需同其他藝術形式結合起來,才能擁有更為廣泛的受眾。小說、戲曲等皆文備眾體,甚至可以說是詩、詞、曲、文、賦等文學形式的整合與升級。流行后世的諸多通俗文藝就形成于這一時期,或者可在宋代找到源頭。為《夷堅志》提供素材的參與者超過五百人,多數虛構痕跡明顯。洪邁《夷堅支甲序》云:“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55]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春的禮部試,洪邁以吏部員外郎充參評官,其間三十名考官中有十一位是《夷堅志》素材的提供者[56]。各種文藝形式的結合與綜合,推動了從詩詞文賦等純文學向綜合化程度更高、文備眾體的戲曲和小說演變,因為“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如詞、散曲等)已不能滿足下層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巨制的戲劇、小說、評書等文藝作品應運而生。從此,詩文主宰文壇的歷史宣告結束,戲劇、小說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57]。
三、宋代文藝的典范性及其思想史意義
宋代是唐宋變革與宋元近世的交集,同一時代兼有中古與近世兩種特征,體現了不同文化類型的轉變與交融。與此同時,宋朝又與遼金夏蒙處于相同時空場域,宋朝的詩詞文等經典文學促進了遼金元文學的提升,而遼金元樂舞、說唱等民族文藝又促進了宋代文學的發展,不同質態的文藝融合共同促進了文藝革新,尤其以戲曲、小說為代表的綜合文藝興起。新的文藝類型、概念范疇、審美風格與價值觀念,讓宋調與漢風、唐韻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文藝思想中的經典范式。
首先,形成了古代經典文藝的宋型范式。史上從未有一個朝代像宋代那樣在諸多文藝領域取得了集成性、標志性成就,形成了群峰聳峙的景觀。宋詞是一代之文學,宋詩與唐詩分庭抗禮,宋代散文是古文典范(唐宋八大家宋占有六),宋畫、宋書、宋瓷、宋版、宋體、宋雜劇、宋話本等都是文藝史上有重要影響的經典范式。草書在創作精神、技法表現、風格特征等方面,改變了唐草的雄強狂放,由縱情宣意轉為重理適意。仕女牛馬成為中唐以來繪畫的主題,山水畫與風俗畫則在宋代成熟并達到高峰。國畫向以唐宋或宋元并稱,而宋畫則代表了中國古代繪畫的最高水準,有學者甚至認為“吾國畫法,至宋而始全”[58]。宋代也是瓷器發展的高峰,被西方學者譽為“中國繪畫和陶瓷的偉大時期”。幾乎所有手工業的傳統工藝,都在宋代發展成熟。宋代工藝美術的造型、裝飾與總體效果堪稱工藝史上的典范,成為明清工藝爭相仿效的對象。
不同藝術門類,都呈現出一致的審美風格與文化精神。宋人審美尚簡淡,梅堯臣認為“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平淡的審美風格要有豐富的言外之意,歐陽修《六一詩話》主張“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說:“發纖稼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王安石《題張司業詩》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種尋常和容易,實際是經過一番曲折探索和艱辛努力才達到的。蘇軾贊揚“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書黃子思詩集后》),宣情尚意的宋代行書及其崇尚平淡蘊藉的士人趣味獲得普遍認同。宋人山水畫“平遠”居多,用墨較淡,在平和之中把人引向“遠”“淡”境地。宋畫創作已不僅著眼于高山大川的恢宏和博大,而且轉向了物象本身的內在生命和意蘊,極大增強了繪畫的概括性、含蓄性和象征性。簡古、平淡中蘊含著豐腴雋永的深意,形成了“蕭散簡遠”“古雅淡泊”的文人畫美學思想。
學術思想史上歷來是“漢宋”對舉、“宋明”并稱。宋代佛教的“思無邪”說及“中和”“清雅”“尚簡”等觀念,對后世文藝審美產生了深刻影響。宋代五大名窯出產的陶瓷應用了新的制作工藝,代表了追求純凈、造型和材料的新品位。南宋后期,詞的雅化達到了極致,“清雅”“古雅”“淡雅”“騷雅”等詞語成為人們褒揚詞作的常用語言,受到廣泛認同和極力推崇[59]。唐君毅稱:“中國民族之精神,由魏晉而超越純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則由汗漫之才情,歸于收斂。”[60]收斂正是“平淡”的內向性宋型文化特征。“宋代獨特的審美精神,是古典審美意識已進入后期的表征,是古典審美創造已高度發展、成熟,高度精致化的產物,是古典后期的審美理想。”[61]后世文藝范疇幾乎都在宋人話語中開始形成,如與漢學相對的宋學、與唐詩派相對的宋詩派、與唐代書法重法度相對的重意趣、詞派中的婉約與豪放、音樂中的雅樂與俗樂、繪畫中的院體畫與文人畫、書籍中的宋版與宋體等,都是中國文藝思想的基本概念范疇。
其次,確立了近世文藝觀念的價值標準。社會結構和大眾風尚的變化往往決定了一種思想的興衰及其轉向,禪宗、內丹、理學的出現似乎都與唐宋時期門閥貴族的瓦解及士民階級的興起有著必然或密切關聯。“唐、宋、元、明時期,禪宗、內丹、理學的交替出現,佛、道、儒這三大思想信仰系統都出現了內轉化的趨勢,內在化、心性化、德性化、主體化是唐、宋、元、明時期中國思想演變的大趨勢,這種趨向也最終導致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現,使中國文化出現了一個相對靜態平衡的穩定結構。”[62]道教從佛教哲學中汲取養分,將其融入自身的養生思想向儒家士大夫滲透;同時吸納佛教因果輪回思想與儒家綱常倫理學說向普通百姓滲透。陳摶、張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綱常倫理與禪宗心性之學,建立了完善的內丹學,取代外丹術成為道教修煉的主流,為金元之際新道教的出現奠定了基礎[63]。宋代理學家幾乎都有出入釋老,以及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傾向。在日常生活中,儒佛道并行不悖、和諧相處,普通百姓也讀儒書、拜佛祖、做齋醮。從接受外來文化為主的唐代文化,“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64]。因此,錢穆將宋學精神概括為“明體達用”:“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65]
宋代改經、疑經和刪經之風盛行,走出了中古對經典的迷信和盲從。歐陽修、司馬光、蘇轍等人分別對《易經》《孟子》《周禮》等經典提出質疑,歐陽修在《易童子問》《詩本義》《春秋論》等文中對儒家經典頻發詰難,聲稱“世無疑焉,吾獨疑之”,要“一一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偽”[66]。在解經方法上開始關注義理大旨,不再拘泥于章句訓詁。王安石宣稱“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67]。朱熹指出:“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歐陽修)、原父(劉敞)、孫明復(孫復)諸公,始自出議論。”[68]程頤說“學者要自得”,“各自立得一個門庭”[69],以至當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人執私見,家為異說”[70]。于是,宋學各派“學統四起”,王安石創立新學,蘇氏父子創立蜀學,周敦頤及二程創立濂洛學,張載創立關學。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陳亮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雖然主張不一,甚至針鋒相對,但也能夠實事求是,各展所長。宋代理學思想對元儒和明儒影響深遠,宋代的懷疑精神和理性精神也是清代樸學的重要思想資源。
再次,宋代文藝對遼金夏元及東亞文化的影響。宋朝持續不斷地對周遭政權領地進行文化輸出,形成了新的漢文化秩序尤其是道統學統,塑造了東亞文明的基本形態。澶淵之盟后,圖書成為宋遼榷場貿易的重要商品。景德三年(1006),宋朝廷明文規定:“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71]盡管宋廷再三強調“賣書北界告捕之法”[72],但“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73]。“拓拔自得靈夏以西……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所為皆與中國等。”[74]西夏景宗李元昊“仿中國,置文武班,立蕃學、漢學”[75],“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76]。毅宗李諒祚“遵大漢禮儀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冊用仰華風”[77]。與此同時,北方文藝也南向流傳。吳曾《能改齋漫錄》載:“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并禁止支賞。”[78]“番曲”“北曲子”等遼金歌曲流行,促進了宋朝文藝樣式的革新。唱賺有時還要綜合“番曲”唱腔。北方歌曲流入南方,被吸收進新興曲藝唱賺之中,后又融入諸宮調、北曲等通俗文藝。宋遼尤其宋金互遣使臣,帶動和促進了南北文藝的交流。“宋方為五百多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為484 人。金方有295 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為291人。”[79]宣和間,“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皆歌之。……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80]。“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81]通使帶來流行歌曲的同時,金人還多次索要雜戲、倡優諸色人等不計其數。
北宋與金的兩次亡國,促使了文藝人才的大規模流動。靖康二年即金天會五年(1127),金人曾令開封府追尋到雜劇、說話、小說等伎藝人一百五十余家,押送軍前。“內侍內人歸酋長,百工諸色各自謀生,婦女多賣娼寮。”“《燕人麈》云:天會(1123—1137)時掠致宋國男、婦不下二十萬……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婦女……分給謀克以下,十人九娼,名節既喪,身命亦亡。鄰居鐵工,以八金買娼婦,實為親王女孫、相國侄婦、進士夫人。”[82]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過真定,發現還保存著北宋大曲歌舞:“虜樂悉變中華,唯真定有京師舊樂工,尚舞高平曲破。”[83]北遷藝人促進了當地俗文學尤其戲劇文學的繁榮,包括真定、東平在內的元雜劇中心的形成就得益于這種流動。金亡,藝人又流落南方,帶來了北方的通俗文藝。汴京淪陷,“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84]。“番腔”“番曲”等頻見于南宋文人的記載。劉辰翁《卜算子》云:“十載廢元宵,滿耳番腔鼓。”《柳梢青》云:“笛里番腔,街頭戲鼓,不是歌聲。”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一些樂曲不斷傳入中原,使北方游牧文化樂曲與中土文化相融合。一些民族樂曲流傳下來,成為元曲的主要曲牌。
周邊鄰國高麗受宋朝文學、繪畫、書法、音樂等影響較大,日本則在文學、佛教繪畫、雕塑藝術等方面深受影響。宋朝書籍大量流入鄰國尤其是高麗、日本和交趾。對高麗輸出了《大藏經》《文苑英華》《逍遙詠》等典籍和地理、日歷,高麗使者還陰訪書籍帶回國內。交趾時常向宋廷請求購書,并獲準購買除“禁書”以外的各類書籍。北宋新興瓷窯有河南鈞窯、浙江龍泉窯、河北磁州窯等,以及后來成為我國陶瓷生產基地的景德鎮。宋瓷品種繁多、器形多樣、色調優雅,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銷往西方。此外,宋代在醫學、媽祖文化、茶文化等方面也對東南亞、南亞及西亞等地有大量文化輸出。宮崎市定《東洋近代史》曾總結說:“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85]
最后,宋代文藝的近世特征及深遠影響。宋代主要文藝類型都發生了轉型,其精神、思想普遍呈現出鮮明的近世性。文學借由日常化書寫尤其是商業化,獨立發展成為一種審美、娛樂甚至商業藝術。主流字體和書法風格也發生了轉變,繪畫從彩色壁畫轉向更加自由的屏風畫和水墨畫。書法“尚意”與文人畫“寫意”都期望表達創作者的個性,標榜“自出新意,不踐古人”[86]。藝術精神方面,唐人畫氣度博大、壯麗雄美,宋人畫轉為靜遠、平和、內向,黃休復《益州名畫錄》首次將“逸品”置于“神品”之上。園林方面,從司馬光的獨樂園、邵雍的安樂窩到辛棄疾的稼軒,宋代園林也展現了士大夫的獨立人格與審美追求。建筑方面,“宋初秉承唐末五代作風,結構猶碩健質樸。太宗太平興國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百余年間營建旺盛,木造規制已迅速變更;崇寧所定多去前之碩大,易以纖靡,其趨勢乃刻意修飾而不重魁偉矣”[87]。可以說,幾乎各個文藝門類都在宋代發生了顯著、深刻的轉型,并且迅速確立了宋代特有的文藝范式。
宋代是中古文藝向近代文藝轉型的時期,開創了中國古典文藝的近世范式,具有廣泛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唐宋說話技藝在故事敘述上的發展,不但影響著宋金雜劇大量選用小說題材,也吸引其在敘事思維、體制、方式上向小說靠攏。戲曲在包括小說在內的多種文藝的促進下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演述體制、審美趣味和文學品格之后,又為小說所借鑒。宋元時期不僅是從抒情文學到敘事文學、從文士文學到市民文學的文學形態的變化,甚至也是文學性質的變革。文學開始從潤色鴻業向記錄生活、刻畫人性轉變,“與詩詞相比,戲曲、小說等俗文學篇幅較長,蘊含極深,所反映的社會背景更廣泛,對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為真正的人學的文學是從元開始的”[88]。
宋學對其后的哲學、倫理學、教育學、史學、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敘》說:“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89]嚴復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90]迪特·庫恩以其西方視角,在宋朝歷史中發現了“中國意識”及其在后世的延續:“由宋朝那些有創造力的統治者、士大夫和藝術家創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價值的復興和重建,為后世歷朝歷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會的發展建立了基礎,并強化了漢人子孫頭腦中的中國意識,這種意識在宋代之后持續了若干世紀。”[91]李澤厚也認為,“在中國民族性格與中國實踐理性的形成發展中,在中國民族注重氣節、重視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等建立主體意志結構等方面”[92],都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文化的普及,庶民階級的興起,根本改變了之前以貴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可以說,近世中國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觀點及情感模式均發端于宋代。宋明時代的社會文化和制度思想是相對漢唐的另一種經典范式,甚至可以說后來居上。王國維認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勢所不逮也”,因為“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93]。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94]后來,鄧廣銘多次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95]“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96]這些評價足以說明宋代在我國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當然,這種轉型意義也是相對而言的。轉型只是范式的更新,其基本知識與精神仍是連綿相承的。以往我們對“說話”的理解,主要是從民間文學角度考察,認為其低端、粗淺,但從經典文學的通俗化角度,“說話”正是經史的通俗化表達,是詩詞的民間化形態,無論說經、演史還是詩話、詞話,都是受眾極廣的主流文藝,孕育和引領了新的文藝發展方向。從單個文體出發,很容易突顯文體之間的差異,忽略相互之間的關聯。如果從知識傳承、主體擴大與形態更新等方面來看,它們之間的差異是形式大于內容,《史記》對《春秋》的重寫、《資治通鑒》對《史記》的重寫、《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的“按鑒重寫”,其中有一以貫之的知識與精神。
從政治軍事層面來看,宋朝尤其南宋是一個積弱王朝,相對于遼金元都是處于被動的守勢。但從經濟、文化等當代強勢話語和研究熱點出發,宋代反而贏得了政治軍事所不曾達到的話事權與正統地位。宋代成為歷史上最為文弱的王朝,沒有了漢唐開邊拓土、勒石燕然的氣概,也喪失了御敵戰勝的膽魄而經常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并最終傾覆。當時尤其是金元之際的北方文人并不是天然地認南宋為正朔。關漢卿[南呂一枝花]《杭州景》稱杭州為“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王實甫《麗春堂》[仙呂·點絳唇]則發出了“破虜平戎,滅遼取宋,中原統”之聲。金元文人這種以據有中原為正統的觀念與呼聲,最終還是湮沒于宋文化不斷發育和生長的滾滾長河。文藝的繁榮翼蔽了武功的貧弱,成就了宋代堪與其他盛世王朝相頡頏的歷史地位。
文化宋朝不僅相對遼金元有強大優勢,在中國歷代王朝中也是一座空前絕后的高峰。政治與軍事的落差已成為歷史,文化藝術成了衡量歷史地位和價值意義的主要標準,由此也形成了“盛唐隆宋”之說。這種認知是人們致力于從文化傳統角度重新發現歷史,重建價值認同與文化自信的結果。通過文化的相對優勢來強化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包括陳寅恪、錢穆、鄧廣銘等人的論述,其出發點也是基于這種現實需求。如果要對宋代文藝進行整體性與多維度的考察,除了對宋代文藝本身的發展梳理之外,還應該對唐宋轉型、宋元近世尤其近代以來歷史的文化主導觀念有所省思。
總之,我們要從不同視角看待宋朝,作出新的概括和界說,從而更為切實地把握宋代文藝思想的主流、本質、生成原因與歷史地位及影響。從“唐宋變革”到“宋元近世”的不同理論框架中審視宋代文藝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更為凸顯宋代文藝的轉型特征與歷史地位,尤其呈現向來被忽略的宋代通俗文藝思想。宋代文藝的典范性與近世性既是別開生面的,也是相反相成的。宋代處于從中古到近世的歷史轉型時期,宋明通俗文學與漢唐經典文學共同構成了我國古典文藝的兩種基本范式,共同塑造了我們民族的文藝精神和文化品格。
注釋:
①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子項“宋代文藝思想史”前期成果。
②彭雨新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五編第一章,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頁。
③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56頁。
④耐得翁:《都城紀勝》,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頁。
⑤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頁。
⑥吳曉亮:《宋代經濟史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頁。
⑦[美]施堅雅著、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24頁。
⑧《朱子語類》卷一二八,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3070頁。
⑨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四《崇政殿說書》,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71頁。
⑩錢若水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卷三十一,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22頁。
[11]宋真宗:《冊府元龜序》,曾棗莊:《宋代序跋全編》卷三,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65頁。
[12]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78—179頁。
[13]李約瑟:《李約瑟文集》,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5頁。
[14]朱熹:《楚辭后語》卷六《服胡麻賦》注,《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頁。
[15]宋孝宗:《原道辨》,姚瑩:《康輶紀行》卷十一,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01頁。
[16]程頤:《明道先生行狀》,《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頁。
[17]張伯端著、翁葆光等注:《悟真篇集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9頁。
[18]釋智圓:《中庸子傳上》,《全宋文》第15 冊卷三一五,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頁。
[19]據統計兩宋書院已有397 所,一說有229 所。參見陳元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20][美]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21]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9頁。
[22]郝經:《陵川集》卷十《溫公畫像》及卷三十九《使宋文移》,《四庫全書》本;趙汸:《東山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四庫全書》本。
[23]錢穆:《理學與藝術》,《宋史研究集》第七輯,臺灣書局1974年版,第2頁。
[24]金毓黻:《宋遼金史》第一冊第一章《總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
[25][法]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頁。
[26]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當習儒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頁。
[27]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頁。
[28]《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27頁。
[29]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頁。
[30]《西湖老人繁盛錄》,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年版,第2頁。
[31]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年版,第3頁。
[32]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
[33]《西湖老人繁盛錄》,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頁。
[34]《武林舊事·乾淳奉親》。
[35]《碧雞漫志》卷二。
[36]《都城紀勝·瓦舍眾伎》。
[37]繆鉞:《全宋文序》,《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38]劉克莊:《后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頁。
[39]漆緒邦等:《中國詩論史》,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726頁。
[40]張方平:《樂全先生文集》卷十一《雅樂論》,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709頁。
[41]楊湜:《古今詞話·無名氏》,《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5頁。
[42]張劍:《情境詩學:理解近世詩歌的另一種路徑》,《上海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43][日]吉川幸次郎著,李慶、駱玉明等譯:《宋元明詩概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頁。
[44]繆鉞:《論宋詩》,《宋詩鑒賞辭典·代序》,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
[45]胡仔:《苔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81頁。
[46]葛兆光:《從宋詩到白話詩》,《文學評論》1990 年第4期。
[47]陳師道:《后山詩話》,《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1頁。
[48]李清照:《詞論》,《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頁。
[49]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09頁。
[50]孔平仲:《談苑》卷四,《全宋筆記》二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頁。
[51]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頁。
[52]魯迅:《魯迅全集(八)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學史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287頁。
[53]吳自牧:《夢粱錄》卷二〇,第193頁。
[54]孟元老著、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二,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63頁。
[55]洪邁編、何倬點校:《夷堅志》,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1820頁。王明清:《投轄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6][日]岡本不二明:《睽車志與夷堅志——“科學與志怪”之一》,《甘肅社會科學》1995年第6期。
[57]龍建國、廖美英:《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文化藝術商品化》,《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58]潘天壽:《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頁。
[59]南宋詞集大量以雅詞命名,并不斷有詞論家對雅化理論進行闡述,如張炎《詞源》“詞欲雅而正”“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沈義父《樂府指迷》“康伯可、柳看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皆肯定詞體創作思想規范的雅正、詞調音律的規范、語言修辭的文雅和品格氣度的高雅。
[60]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中正書局1953年版,第70頁。
[61]薛富興:《中國美學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版,第148頁。
[62]翟奎鳳:《心性化與唐宋元明中國思想的內轉及其危機——以禪宗、內丹、理學為線索的思考》,《文史哲》2016年第6期。
[63]虞云國:《略論宋代文化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地位》,《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64]傅樂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國立”編譯館館刊》1972年第1卷第4期。
[65]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78、7頁。
[66]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中國通史論文集》,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頁。
[67]惠洪:《冷齋夜話》卷六,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7頁。
[6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2089頁。
[69]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96頁。
[70]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48頁。
[7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四《真宗景德三年九月壬子》,中華書局1980 年版。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中華書局1957年版。
[72]脫脫:《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
[73]蘇轍:《來城集》卷四二《論北朝所見于朝廷不便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640—3641頁。
[75]張鑒:《西夏紀事本末》,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 年版,第65頁。
[76]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3995頁。
[77]吳廣成、龔世俊:《西夏書事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頁。
[78]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頁。
[79]董克昌:《宋金外交往來初探》,《學習與探索》1990年第2期。
[80]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鐵圍山叢談·獨醒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頁。
[81]朱權著、姚品文箋評:《太和正音譜箋評》,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0頁。
[82]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之六《呻吟語》,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99頁。
[83]范成大:《真定舞》,《宋詩抄·石湖詩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741頁。
[84]劉子翚:《汴京紀事二十首》,《宣和遺事·后集》,《四部備要》本,第28頁。
[85][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 卷,巖波書店1992年版。
[86]蘇軾:《蘇軾文集》卷六九《評草書》,第2183頁。[87]梁思成:《中國建筑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148頁。
[88]喬光輝:《元文人心態與文學實踐》,《東岳論壇》1996年第3期。
[89]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頁。
[90]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 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68頁。
[91][德]迪特·庫恩著、李文鋒譯:《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9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頁。
[93]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國學論叢》第1 卷3號,1928年4月。
[9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77頁。
[95]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頁。
[96]鄧廣銘:《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