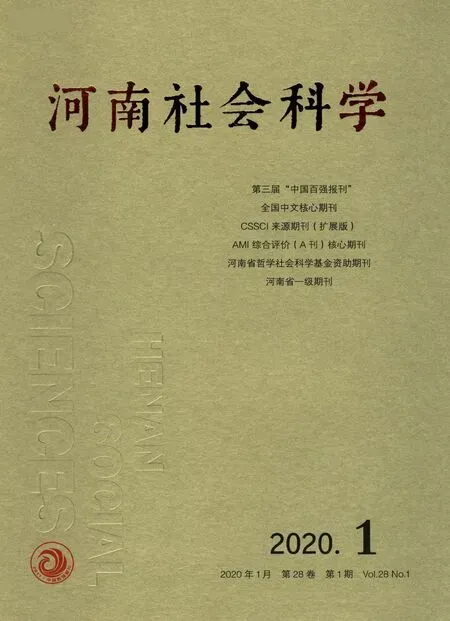從血緣到地緣:論北朝群體造像記的發展演進
——以家庭、宗族、村落和邑義等造像記為中心
李林昊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佛教大盛于北朝,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描繪了當時佛教的盛況:“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1]25從《資治通鑒》存錄的文獻中亦可窺其大略:“時佛教盛于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余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余間以處之。……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余寺。”[2]4594
北朝造像記是北方民眾積極參與佛事活動的真實記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朝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風貌,是研究北朝政治、社會、文化等的重要資料。隋末唐初高僧法琳在《辨正論》中提到,隋文帝時代“開皇之初終于仁壽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萬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許軀”[3]第52 冊,509,可見隋代之前的北朝造像數量之巨。造像記大都是以個體造像或是群體造像的形式展現出來,家庭、宗族、村落和邑義等造像記皆是群體造像記的重要類型。群體造像在發展過程中,由小的空間單位向大的地域單元不斷演進,在血緣關系、地緣關系與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特征。
一、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群體造像記
根據不同群體造像記的主要形成因素,可將家庭、宗族、村落、寺廟、邑義等不同類型的造像記按照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進行分類,其中家庭、宗族造像記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發展起來的,村落、寺廟、邑義等造像記則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構建的。
家庭、宗族范圍內的佛教信眾和造像活動以血緣關系為依托,將血緣共同體內的各個成員聯結起來,從信眾個體、家庭逐步擴散到所在宗族。換言之,宗族造像記是在個體造像記和家庭造像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一)家庭造像記
在論述家庭造像記之前,需要先提及個體造像記。因為個體造像出現時間最早且數量眾多,是造像活動中最基本的形式,家庭造像以及后來形成的大規模群體造像大都是以個體造像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
個體造像記往往短小簡約,每篇大都只有短短的幾十字,僅僅交代造像者、造像對象、造像題材以及進行簡單的發愿,不像群體造像記那樣長篇大論,對于佛法精妙的贊美與闡釋亦多省略。如北魏太和四年(480)《趙明造像記》:
太和四年四月二十日,下博人趙明為亡兒越寶造多寶佛。愿亡兒上生天上,常與佛會。[4]423
這是信眾趙明為亡子發愿祈福而作,反映了個體造像記的普遍特征:造像主多為自己或親人造像,其中為亡故親人祈福、為現存眷屬發愿更是占了半數以上,具有很強的現實黏合度。
與個體造像相比,家庭造像的參與成員更多,造像碑銘篇幅也較長,這些參加者皆為血脈至親,多是父子兩代人共同造像,有的囊括祖孫三代甚至四代人。家庭造像記往往反映了一個家庭整體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如《劉思祖造像記》:
大齊天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高城縣人劉思祖敬造玉石像一軀。上為國王帝主,下為七世父母現在。劉思祖妻嚴勾,息男景暈、伯安、伯雙、伯丑,愿生生世世,恒值佛。
清信仕女劉男生。孫子劉來寶。[5]173
該則造像記中的參與成員包括祖孫三代人,不單有男性成員,也有女性信眾,全家人一起供養佛像。需要說明的是,宗族內部等級森嚴,故宗族造像的發起者多是宗族內地位高、有威望的男性成員,但家庭造像在此方面并沒有嚴格的限制,北朝時期女性的家庭地位比較高,可以自由組織開展造像活動。如北齊武平三年(572)的《王馬居眷屬等造像記》有載:
清信佛弟子故人王馬居眷屬等,敬造觀世音菩薩一軀,上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一切有形,咸同斯福。
像主王馬居,夫曹臺,息法度,□妻李伏女,□妻麝苑端,□息通達,□子敕奴,□世通妻郭綾,通息子建,女阿瑞,女迎弟,女明月,□女阿肆。[5]279
由造像題名可以看出女性信眾王馬居是本次造像活動的發起人,其夫曹臺只是普通的參與者,這說明家庭內部女性并沒有受到太多限制,在宗教活動中可以自由參與,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趙暉等造像記》《侯顯妻造像記》《田僧敬造像記》《滑黑奴造像記》等對此均有明確的反映。該類型造像記之所以數量眾多,大抵是家庭成員之間既同歸于佛教信仰的統攝之下,又通過血緣關系聯結得更為緊密,這就為佛事活動的開展提供了便捷條件。
(二)宗族造像記
宗族造像是在血緣關系的維系下,個體造像和家庭造像不斷發展、壯大的結果。宗族造像的參與者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在血緣構建的家族網絡下組成一個富有凝聚力的佛教信眾集體,共襄佛事之舉。如《陳氏宗族造像記》:
夫真容虛寂,妙體精絕。湛□恒有,淵廓玄深。……自非建□□岸甯申余等借承漢高左右大丞相戶酉侯太□□平晉沖關□□一軍□□□長左馮翊太守□六世孫合宗等,信心沖廓,并同玄風,慧機俱發。遂名山采石,遠訪良規,造四面石像一軀。……
開□光明主威□將軍陳映族。加葉主陳思和。開光明主潁川太守陳伯 。……邑子步兵參軍陳僧略。邑子陳始和。邑子陳子云。邑子陳冷俊。[4]554-556
遍覽整篇造像題名,參與成員皆為陳氏族人,且人數多達幾百人。從參與者的身份來看,既有上層官員,如陳伯 官至潁川太守;也有中層官吏,如陳卷生為郡主簿,陳萌□為縣令;還有大量的平民族人,像陳始和、陳子云、陳延義等。從上層官員到下層平民,宗族造像通過血緣關系這一紐帶,打破階級、年齡、地位的界限,將全體族人團結為一個強有力的整體,彰顯出血緣力量的強大。陳氏族人全體參與,說明佛事活動已經成為宗族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宗族造像記不僅篇幅宏大,還出現了對仗工整、文采華麗的四六句,發愿文中對于佛法的領悟亦很精深,《李顯族造像碑記》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魏興和四年歲次降婁十月甲午朔八日辛丑,李氏合邑造□像碑頌文。
夫旨理虛沖,妙絕于言像之外;凝湛淡泊,超出于燕形之境。所以現應金容,詮言布教者,實由見聞之徒,三千同感。是以大圣降鑒,慈情曲接,影赴麈羈,悲拔昏識,故能托跡凈土,搶現元吉,開三為級小之心,演一為接大之則。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深是如來處有不有,居無不無者矣。但以眾生福盡,不善諸業,百八云張,邪風競扇,致令靈曜潛暉,遷感異域。自圣去遙延,世華道喪。……[4]586
這篇造像記長達兩千字,單是祈愿文就有近七百字,多用四六句對仗,有較強的文學色彩。李氏宗族中有大量的族人出仕,擔任的職務種類繁多,文職有太守、中散大夫、太尉府參軍、郎中令、縣令等,武職有蕩寇將軍、襄威將軍、殿中將軍等。此外,還有不少族人是庶民百姓。仔細對照之后發現,該家族文官的數量要遠多于武將,甚至有不少族人官位顯要,其中官至太守的族人就多達十幾人,中下層官吏更是不勝枚舉。根據李氏族人更多的是以文官出仕,可以推測該家族當以耕讀傳家,整個宗族內有著良好的文化氛圍,故而造像記中的祈愿文多駢辭儷句也就不足為怪了,同時也說明南朝的駢儷之風亦影響到了北朝文官宗族的造像記撰寫領域。而參與成員皆為平民的宗族造像記,因為整體的文化程度較低,祈愿文一般缺乏文采,也不追求對偶,甚至對于佛法的領悟都較少闡述,往往一筆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宗族造像記中祈愿文內容的書寫與宗族整體的文化氛圍密切相關。
二、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群體造像記
前文提到,村落、寺廟、邑義等造像記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構建的。需要說明的是,上述類別是按照其主要影響因子劃分的,并不意味著這些不同類型的造像記只有單一的影響因素,如宗族、村落和邑義造像既包含了血緣關系又囊括了地緣關系,但宗族造像受血緣關系影響較大,地緣因素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而以村落為基礎的聚落組織和以邑義為代表的特殊組織形式,因為其部分參與成員不囿于某個村落之內而出現了跨地域的性質,尤其是不同村落的聯合造像與跨地域邑義的形成更是直接受制于地緣關系,故本文將村落造像記和邑義造像記歸入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群體造像記之中進行討論。
(一)村落造像記
村落造像與宗族造像有一定的共同點,它在宗族造像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地域性的因素。宗族具有聚居性特征,而一個村落往往包括一個或數個不同姓氏的宗族,因此村落是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疊加之后產生的聚合體。如果說平民信眾參加的宗族造像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那么其參與的村落造像則是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地緣關系是其形成的主導因素。村落造像規模大,人數眾多,且造像記篇幅較長,一般都有幾百字,能夠將鄉村的生活圖景、人員構成細致地描摹出來,有助于進一步研究北朝的鄉里社會。如刻于北魏景明四年(503)的《劉雄頭等四百人造像記》:
大魏國景明四年太歲在未三月癸丑朔廿一日,幽州范陽郡涿人劉雄頭、高伏德、高道龍合四百人為皇帝造釋迦牟尼像一軀。
比丘法崇,比丘道□,智深,道歡……劉□惠隆,高定和,劉惡□,劉造扶,劉靈□。(下缺)高園□,劉天賜,劉□生,□□劉□。(上缺)劉云生,高道顯,劉龜,劉伏□□。比丘尼法,尼法珎,尼法幽□。[4]446-447
可將產生于同時期、同地域的《高伏德等造像記》與《劉雄頭等四百人造像記》比照參看:
大魏國景明四年,太歲在癸未,四月癸未朔二日,幽州范陽郡涿縣當陌村高伏德,像主維那劉雄合三百人為皇帝陛下□□造石像一軀(下缺)記。
高非,高副周,高無諱,劉永得,高卿世,高惠頑,劉黑堆……高宗敬,高 ,高勉興,劉僧達,高保蓋,高法顯,劉伏生,李午生,劉原始。……
比丘曇龜,比丘道能,比丘曇紹,比丘智深。[4]447-448
上述兩則造像記是關于北魏時期幽州范陽郡涿縣當陌村村民共同從事佛事活動的記載,參與者主要為當陌村的高姓與劉姓族人,也有少數其他姓氏的成員和數名比丘、比丘尼參加。兩次造像活動實質上當屬聚居于同一自然村落內的高劉兩姓之合作造像。《劉雄頭等四百人造像記》造于景明四年三月,發起人為劉雄頭;《高伏德等造像記》的鐫刻時間是四月,組織者是高伏德。從其造像題名來看,高伏德、劉雄頭、高樹、高道德、智深等人在這兩次造像活動中都有參與,并可根據題名看出當陌村的人員與姓氏構成:以高、劉兩姓族人為主,另有公孫姓、張姓、史姓族人零星分布。《劉雄頭等四百人造像記》載錄,當陌村有四百余人參加了此次造像活動,一個擁有四百口人以上的村落在人口總數約為三千萬的北魏(神龜年間)也算得上較大的自然聚落了。因為共處于同一個自然聚落的民眾擁有共同的活動范圍,他們或因血緣關系,或因地緣關系,或因村落的共同事務,彼此碰面和接觸的機會更多,這就為民眾之間的交往互動提供了便利。隨著僧尼的宣化與佛教信仰滲透到村落之中,這一特定空間內的信眾在宗教信仰的統攝下聚集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血緣觀念,不再僅僅以家庭、宗族為單位開展佛事活動,而是通過村落這一更大的空間單元組織信眾信佛、奉佛。同時,佛事活動也由單一走向多元,村落內的信眾不再僅僅囿于造像之事,講經、修齋、法會等活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在一個囊括數個姓氏居民共同生活的村落,宗教活動正是將不同姓氏的族群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二)寺廟造像記
寺廟是僧尼和信眾舉行佛事活動的中心場所,按照佛教禮佛的觀念,寺廟中大量的佛像提供了開展儀式和法會的“道場”,為佛事活動的舉行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也大大方便了僧尼和信眾對于佛像的禮拜供養。東魏天平四年(537)的《永寧寺比丘□諸法義等造像記》是以寺廟為依托進行造像的典型:
托經象以□暉范,古今始終共軌。青州永寧寺比丘□諸法義等造釋迦牟尼石像一軀。上□帝主,父母師僧,無邊眾生,亡過現存咸同斯。……比丘曇潤。比丘道暹。比丘道善。比丘道雙。比丘道稠。清信士□道果。王寶。……比丘尼法光供養時。比丘尼法陵供養時。比丘尼法暉供養時。姜明度,姜成銀。鄭□王姜□。張鴦,比丘尼曇□。傅敬姜。周男□侍佛時。[4]565
根據造像記題名和“永寧寺比丘□□諸法義等造釋迦牟尼石像一軀”,可以看出僧尼和男女信眾在永寧寺形成了專門進行佛教活動的佛社,“法義”就是佛社的幾種稱呼之一。該則造像記實質上是寺廟造像記與邑義造像記的結合,佛教邑義是在永寧寺這一特定空間內形成的。既然是以寺廟為基礎開展的佛社造像活動,其組織者和領導者自然是僧尼,但普通信眾對于造像亦有經濟和勞力上的支持。北魏中晚期以后,庶人及團體造像尤多。據佐藤智水先生考證,東西魏以后,團體中的邑義造像明顯增加。由邑義建造的石像、碑像多見于古寺院(如1953 年河北省曲陽縣修德寺遺址出土自北魏到唐朝石像二千尊以上)。與放在家庭佛壇上供奉的金銅像不同,邑義像多安置在寺院。由此可以推測,寺院是地域社會的共同場所[6]70。寺廟造像記反映的是僧尼以寺廟為中心開展的宗教活動,通過僧尼自身和所在寺廟向信眾直接施加影響。而以寺廟為中心形成的寺廟邑義,在組織形式和管理結構上更是直接借鑒了寺院的管理形式,如“維那”“都維那”“典坐”等稱呼就是源于僧官制度中某些僧尼首領、主事的稱號。相比于一般的佛社邑義,寺廟及以寺廟為中心形成的邑義組織,在結構上更加嚴密,活動類型更加多樣,造像記中對于精妙佛法的闡釋也更有深度。寺廟造像的發起者主要是僧尼,但也有組織者為信眾的情況,如《劉道景造像記》:
北徐州興福寺居士劉道景邑義等大像之碑。
居士劉道景邑義等今□超海踵像法以恒安……凝神寂寞,曉聞有而難名,知虛無而特妙。□邑義等(下缺)永夜,止火救危,逗川養命,伏外道于四居,降天魔于上界。□眸(下缺)磐資捨著,敬造珍國二丈八大像一軀,并建伽藍之所,上為皇帝(下缺)決水。不死之藥,天下共分;長生之府,門門自至。[5]305-306
本次造像活動是由興福寺居士劉道景發起的,既屬于邑義造像的性質,又帶有寺廟造像的色彩。劉道景作為興福寺的佛教信眾,其發起邑義、組織佛事活動當離不開興福寺及寺內僧眾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講,邑義造像是寺廟造像的拓展和延伸,是僧尼、信眾團體在合作造像方面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新的組織形式。
(三)邑義造像記
北朝時期產生了專門進行佛事活動的邑義組織,它的出現意味著擁有共同信仰的廣大信眾群體可以較為自由地結成佛社,一起組織、參與佛事活動。東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社,稱為邑、邑義的最多,法義次之。這里的“邑”字,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指某一地域內信奉佛教的人結成的宗教團體。郝春文先生認為,“這種由信仰佛教的人組成的邑,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結義性質,‘義’應該就是結義的意思”[7]90-91。日本學者山崎宏指出:“法義是以同樣信仰佛教的道義而組合之意,如同義兄系血緣以外結合而成之兄的意思,是以佛法集合的成員。”[8]768
邑義造像種類繁多,規模大小不一,少則有信眾幾人或十幾人,如《趙阿歡造像記》《賈致和等十六人造像記》《邑主孫念堂造像記》;多則有數千參與者,如《法雅與宗那邑一千人造塔碑》《比丘法悅等一千人造像記》《七帝寺造像記》。需要說明的是,個體造像在公元3世紀就已出現,現存最早的是西晉太康三年(282)的《張伯通造像記》。到了4 世紀左右,就已經有大量的個體造像、家庭造像存在了,而邑義造像直到5世紀才出現,其“噴發期”則是在6 世紀前后,兩者的“發展成熟期”相距百余年。從個體造像、家庭造像到邑義造像,這是一個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是以血緣關系為主要影響因素的造像活動轉向以地緣關系為主導的重要時期。《靈山塔下銘》和《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是早期邑義造像的代表:
維大魏太和元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八日壬戌,劉虎子、諸葛洪、方山二百人等敬造靈塔,愿六通三達,世榮資福,合家眷屬,慧悟法界,永離苦海,光祚群生,咸同斯慶。
邑主梁英才,維那牟文雍,塔主華智。[4]422
——《靈山塔下銘》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卅日,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甘寢昏境,靡由自覺。……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詡洪澤,莫能從□,是以共相勸合,為國興福,敬造石□□像九十五軀……上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轉輪,神披四天,國祚永康……又愿同邑諸人,從今以往,道心日隆,成行修潔,明鑒□相,暉揚慧日。[4]423-424
——《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
上述兩則造像記分別刻于北魏太和元年(477)和太和七年(483)。造像記的文本內容反映的佛事活動是多方面的,不僅包括造像、立碑、設齋,而且還有建寺、造塔、法會、講經等活動。《靈山塔下銘》反映的是二百人的邑義團體建塔題記之事,碑銘提到的邑主是邑義團體的首領,而塔主是建塔的主要出資人。建塔和造像一樣都屬于積功德之事,佛教對于造塔亦是采取鼓勵的態度,《佛說造塔功德經》有言:
欲請如來造塔之法,及塔所生功德之量。唯愿世尊為彼解說,利益一切無量眾生。爾時,世尊告觀世音菩薩言:“善男子,若此現在諸天眾等,及未來世一切眾生,隨所在方未有塔處,能于其中建立之者,其狀高妙出過三界……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終之后生于梵世……善男子,如我所說如是之事,是彼塔量功德因緣,汝諸天等應當修學。”[9]第16冊,801
由《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可知,該邑義團體共建造佛石像95 軀,對于一個僅有54 人的佛社組織而言,其造像數量可謂龐大,經濟上也必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信士女是俗家佛教信眾的稱號,該邑義的參與成員應皆為女性在家信眾。
佛社邑義的組織結構不似親朋故舊僅僅為奉佛而臨時開展的合作造像那般松散,反而等級森嚴、秩序井然。如果說早期的個體造像是自發的,是俗眾出于對佛教的虔誠,從為家人、為自己祈福的角度發起的;那么邑義造像就是自覺的,是北朝時期佛教高度發達的產物,是在佛教信仰廣泛滲透到北朝民眾的日常生活之后,信眾有意識結成團體的結果。在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作用下,擁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信眾有意識地結成群體,催生了佛社這一特定組織。佛社中還出現了許多特有的、與佛事活動相關的職務和稱號,主要有邑主、像主、邑師、維那、齋主、邑子等,這些佛社成員在宗教活動中各司其職,分工也日益明確,并逐步走向精細化。
從現存邑義造像記來看,在邑義造像出現的早期,其多以寺廟為中心開展佛事活動,從該角度講,邑義造像是寺廟造像的另一種呈現形式。大部分邑義組織的邑師、維那由比丘或比丘尼擔任,這些僧尼邑師既是邑義的精神領袖,又擔負著教化的功能;僧尼維那是邑義的管理者,對于佛事活動的開展有很大的發言權,他們又都屬于寺院的派出人員,寺廟可以通過邑師、維那控制邑義來達到指導、組織、管理信眾的目的。待邑義逐漸發展成熟后,其對于寺廟的依附性減弱,信眾自主性增強,邑義中的邑師、維那等職務也不再由僧尼壟斷,普通信眾亦可擔任。同時地域因素也逐漸成為邑義發展、壯大的主導因素,宗族、村落、縣邑內的佛社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
三、從血緣到地緣:不同群體造像記的“復合構造”與邑義組織對于北朝社會的多重作用
(一)不同群體造像記的“復合構造”
筆者在研究宗族、村落、寺廟與邑義等造像記時,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宗族、村落、寺廟等不同的造像類型大都或多或少地與邑義造像結合而得以呈現,筆者將此類造像形式稱為“復合邑義造像”,它們既具備原有造像類型的性質,又帶有邑義造像的色彩。如《李顯族造像碑記》就是宗族邑義的典型:“大魏興和四年歲次降婁十月甲午朔八日辛丑,李氏合邑造□像碑頌文。”至于村落邑義,比較著名的有《高嶺諸村邑儀道俗造像記》:“唯大魏武定七年,歲在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肆州永安郡定襄縣高嶺以東諸村邑儀道俗等敬白十方諸佛。”還有北齊河清二年(563)的《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記》:“阿鹿交村七十人等敢天慈降尊……人等深識非常,敬造石室一軀,縱曠東西南北,上下五尺。”通過對北朝佛教造像記的研究梳理,筆者以為,北朝佛教造像記的發展大致遵循這樣一個脈絡:從個體、家庭造像到宗族、村落造像,再到與宗族、村落相結合的邑義造像,造像的類型經歷了從小的空間單位向大的地域單元的演進;影響造像類型發展的主要因素也經歷了由血緣關系向地緣關系,再到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共同作用的轉變,即從單一因素的影響發展到多重因素共同發揮作用。
以往學者在論及邑義造像時,大都認為其主要受地域因素的影響,血緣因素卻較少提及。在佛社組織中,血緣關系雖不似地緣關系那樣重要,其作用卻也不容忽視。如村落邑義造像幾乎匯集了整個聚落內的成員,地域成為其形成的主導因素不言自明,而血緣關系影響下的宗族造像在與邑義造像結合時,宗族的血緣關系也在向邑義中不斷滲透,宗族邑義內部形成了特定的血緣網絡,將邑義成員之間聯結得更為緊密。需要說明的是,宗族也生活在村落這一特定區域空間,必然被烙上地域因素的印記;一個村落往往由一個或多個姓氏的宗族組成,血緣的聯結在其中亦起到重要作用。邑義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是血緣關系與地緣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絕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要之,在研究宗族邑義、村落邑義的復合構造時,要重視這些處于特定空間內的血緣群體、地緣組織是相互聯系的。在個體造像、家庭造像發展的早期,是以血緣為紐帶將信眾聚集起來的;在宗族造像、村落造像發展的階段,地緣因素成為串聯信眾的主要因素;到了宗族邑義與村落邑義快速發展的時期,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等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復合邑義造像這一高級的合作形式。與此同時,佛教造像的類型也從小的空間單位向大的空間單元不斷發展演進。
(二)復合邑義產生的原因
宗族邑義、村落邑義等復合邑義的出現,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造像活動自身的發展來看,與宗族、村落等相結合的邑義造像是合作造像的高級形式,是造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覺結果。從復合邑義造像的內部構成來看,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為依托的宗族邑義、村落邑義更容易將信眾聚集在一起,處于同一聚落的人群和有血緣關系的群體聯系得更為緊密,也就擁有了構成邑義組織的人員基礎;邑義成員共同出資、出力進行造像,佛社活動的開展也就有了經濟基礎。
論及佛教造像的問題,就不得不考慮信眾尤其是平民信眾的經濟條件。北魏孝文帝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均田制和租調制,其本質是以一夫一婦為單位的家庭生產模式,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其后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政權皆因襲了此種經濟生產模式。佛像的鑄造、題記的刻寫都是要消耗錢財的,而且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可從造像記的載錄窺其大略。《宋景妃造像記》有“今且自割釵帶之金,仰為亡考妣敬造釋迦佛像一軀”之語;《王令猥等造像記》載“以減割妻子衣食之分,為亡息延慶、延明、父母等敬造石銘一區”;《趙阿歡卅五人造像記》云“故各竭家財,造彌勒像一軀”;《邑義一百六十人等造像記》言“有諸邑義一百六十人等,減割資財,造石像一軀”。此類記載比比皆是,造像一軀就需要信眾節衣縮食,甚至集全家之財、傾邑義全體成員之力,因此,對于社會上最廣大的平民信眾來說,造像對他們造成的經濟負擔是相當沉重的。
《張龍伯兄弟造像記》載:“亡妣康存之日,有牛一頭,愿造像,今得成就。”[5]155鐵犁牛耕在古代是重要的農業生產方式,官府明確規定民間不得私自殺牛,表明牛的經濟價值和生產價值是非常高的,而該則記銘中張龍伯兄弟愿以牛換來錢財以造像,反映出造像有著高昂的成本。
對于個體造像而言,信眾單獨造像時的費用需要其獨自背負。即使是家庭造像,因為參與人數少,開展佛事活動時亦需要承擔較大的經濟壓力。前文提到的《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記錄了一個五十四人的邑義信眾團體鑄造了九十五尊佛像,如果由個人或普通的平民家庭來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團體造像中,造像費用由參與成員共同承擔,參加的人越多,個人分攤的錢財就越少,這就大大減輕了信眾的經濟壓力。故而邑義組織積極吸納信眾進入佛社,有的佛社成員多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也就不足為奇了。要之,邑義造像不但能夠滿足信眾對于以造像為核心的佛事活動的需求,亦能通過共同出資的方式減輕個人乃至家庭的經濟壓力,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邑義、村落邑義,作為合作造像的高級形式,便在此種狀況下應運而生。
寺院及僧侶有意識地發展、組織邑義,與封建政權對于邑義的支持、放任態度,促進了邑義組織的發展壯大。佛社邑義是寺廟向世俗社會的拓展和延伸,邑義造像當是從寺廟造像中分離、演變后的新形式。郝春文先生認為東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社實際上是佛教寺院的外圍組織,佛教寺院與僧人往往通過控制與利用佛社達到控制居民的目的,佛社成員則是佛教存在與發展的社會基礎[7]98。在邑義出現的早期,邑師大都由比丘或比丘尼擔任,他們屬于寺院的派出人員,在作為邑義精神領袖的同時,又肩負著寺院賦予的教化信眾的重任。邑師通過講經譯經、舉辦齋會、組織信徒造像等活動,擴大佛教的傳播范圍與影響力,將俗家信眾統攝于佛教信仰之下。寺院、僧尼在獲得信眾經濟布施的同時,又能讓信眾為自己服勞役。《開化寺邑義三百人造像記》《道充等一百人造像記》《比丘道璸造像記》等記載的邑義團體都是以寺廟為中心建立起來的。
封建統治者重視佛教改造民俗的作用,是故對于佛教的發展采取放任乃至支持的態度。《魏書·釋老志》有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10]3292造像記中有大量的祈愿文是為皇帝和國家發愿,直接以皇帝為造像對象的碑銘亦不在少數,這無疑迎合了統治者的心理期待。如《劉雄頭等四百人造像記》載“幽州范陽郡涿人劉雄頭、高伏德、高道龍合四百人為皇帝造釋迦牟尼像一軀”;《雷明香造像記》有言“愿皇帝延祚無窮,下及七世師僧父母、因緣眷屬,法界眾生,咸同斯慶,等成正覺”;《張祖造像記》云“仰為皇帝陛下,國祚永隆,人同因果,彌勒三會,愿登初首”等。無論是官員貴族,抑或是僧尼、百姓,他們在造像記中大都將皇帝、國家作為造像和發愿的對象,這于無形中增強了民眾的國家觀念和對最高統治者的認同感,有利于封建國家統治的維系。
(三)邑義組織對于北朝社會的多重作用
北朝時期,佛社的興起、發展既是佛教高度發展的表現,又是佛教中國化后的產物,亦是統治階級與廣大民眾接受佛教的結果。封建政權之所以對于邑義的發展持放任、支持的態度,在于信眾造像記中的祈愿迎合封建統治的需要,對于增強國家的認同感、提高皇帝權威有重要作用。同時邑義組織又促進了國家對于基層社會的整合與控制。
信眾通過對共同信仰對象的崇奉,在血緣和地緣關系基礎上,締結神緣紐帶,促進了群體內部的團結。在參與邑義造像的過程中,地方官府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滲入村落,而村落成員亦通過造像這種方式,表達對國家權力的順服與認同[11]89。《高嶺諸村邑儀道俗造像記》對于世俗政權通過邑義整合、控制村落和信眾有鮮明的體現,記銘如下:
唯大魏武定七年,歲在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肆州永安郡定襄縣高嶺以東諸村邑儀道俗等敬白十方諸佛……先有愿共相要約,建立法儀造像一軀。平治道路,刊石立碑,以□之功,上為皇帝陛下,渤海大王,延祚無窮。三寶永隆,累級師僧,□世父母,現存眷屬,復愿生生之處,遭賢遇圣,值佛聞法,常修善業,□至菩提,誓不退轉。愿法界含生,同獲此愿,一時成道。 .
州沙門都僧觀。梁寺曇高供養。比丘法智,邑子□。比丘曇遙。比丘道略。……
廣武將軍邢阿平。廣武將軍李洪賓。……勇士都將鐔伏安。王阿賓,馬延觀。賈社仁,呼延清郎。[4]626-627
一般的村落邑義是以一個村落為主要的空間單位而形成的佛社組織,但本則記銘反映的不是單個村落組織的邑義造像,而是定襄縣高嶺以東的多個村落居民組成的邑義,這就打破了原本相互隔離的地域單元,從一個村落擴展到周圍的聚落,帶有強烈的跨地域色彩。《高嶺諸村邑儀道俗造像記》中“先有愿共相要約,建立法儀造像一軀”,表明了邑義成員之間對于宗教活動、邑義內部的規則有約定,郝春文先生認為這是類似后世社條一類的規定[7]95。《程寧遠造像記》有“遂相約勸率,敦崇邑義”之語;《鉗耳世標造像記》云“志標正契,共相將勸,樹像一軀”;《普屯康等造像記》載“攜接身,敦崇義契,復敬造碑像四佛”。“約”“契”等字眼多次出現,說明邑義團體帶有一定的契約性質,佛社組織內部呈現出高度的嚴密性。
“平治道路,刊石立碑”表明邑義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善民生的作用。《張操造像記》載“采石冥山,匠盡奇思……置善會寺庭間者”。《李顯族造像碑記》云“于是敦契齊心,同發洪愿,即于村中造寺一區。僧房四周,講堂已就,建塔凌云,靈圖岳峻”。邑義組織信眾開展的修路、建寺、造塔等活動,都與民生息息相關。平治道路既有利于加強不同地域之間的聯系,又使得國家政令的下發更為快捷,便于官府對于基層社會組織的管理。建寺造塔滿足了俗眾信佛、奉佛的需求,又達到了世俗政權通過僧官制度控制民眾精神信仰的目的。有的佛社邑義中出現了“齋主”“八關齋主”等稱號,據劉淑芬先生考證,“齋主”是指供參加齋會者飲食的施主,他們可能同時也須負責在齋會后給予僧侶保施……齋會原來系指供養僧侶飲食之意,后來有時也包括對一般俗人飲食的供養[12]530。要之,邑義組織在增加民眾福祉的同時又有利于維系社會的穩定,對于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有重要作用。
北周天和五年(570)的《普屯康等造像記》也反映了封建政權以佛馭民的手段:
周國天和五年歲庚寅正月乙酉三日丁亥,新豐令普屯康……即告都督孫詳率鄉人共崇勝福,聘請邑師僧震三人以別菅會東西六千他步,南北半旬,泛徑屯郡,遠近云馳,競忻挹悅,率割珍賄,修莊嚴克佛像……豪杰延□三百四十他人,攜接□身,敦崇義契,復敬造碑像四佛,敕化四方……伏惟皇帝國祚延康,民豐萬世……邑師比丘法詳,邑主中堅將軍槃禾郡守張神覆,邑主征東將軍右紫光祿都督張賢。……邑子趙沙陁,邑子張魯,邑子趙和。[5]88-90
該邑義的參與成員有官員,有僧侶,也有庶民。官員普屯康既是邑義的發起者,也是邑義的管理者;比丘僧震、法詳作為邑師,則是該邑義的指導者;平民信眾大都只是普通的邑義成員。造像記中的題名往往按照由尊到卑的順序依次鐫寫,官員和僧侶的姓名刻在前面,平民的名字寫在后面,反映了森嚴的等級關系。
前文《高嶺諸村邑儀道俗造像記》提到的造像者題名中,有“州沙門都僧觀”“廣武將軍邢阿平”“廣武將軍李洪賓”名列其間,表明官員、僧人和平民共同參加了邑義造像。《普屯康等造像記》與《高嶺諸村邑儀道俗造像記》實質上都屬于官、僧、民三大群體合作的邑義造像,他們都是邑義組織的重要成員,但身份、地位卻大不相同。官、僧是統治階級,平民信眾則處于被統治地位。州沙門都是北朝僧官制度中州郡一級的官職,負責其所在州郡的僧尼、寺院及其所轄莊園、依附戶的管理,是封建國家派駐在地方的最高宗教領袖。由該碑文可知,僧官在不同村落之間的聯合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僧官不僅僅能管控其所轄區域的僧尼,又能通過宗教信仰影響到廣大佛教信眾。而僧官的權力是世俗皇權賦予的,其實質是在為國家政權服務,世俗官員與僧官能夠較為廣泛地參與邑義造像,表明世俗權力已經滲透到民眾生活和信仰的方方面面。
在佛教風靡的北朝,封建國家通過僧官體系加強了對于寺院、僧侶的管理,而僧侶又通過游方宣化、佛社邑義、造像活動等對信眾施加影響,參與邑義造像的官員、僧尼不僅僅是佛教虔誠的信仰者,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封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執行者。僧侶在為國家和最高統治者披上神秘的宗教外衣的同時,封建政權的思想觀念也通過僧侶這一中介滲透到民眾的精神世界。以官員為代表的世俗權力通過宗教來加強對于民眾的精神控制,與封建生產關系對于民眾的人身控制相互補充。
四、結論
系統研究北朝造像記后發現,造像形式的發展經歷了從個體、家庭造像,到宗族、村落、寺廟造像,再到宗族邑義、村落邑義造像,其規模和內部結構是從小的活動單位向大的活動單元不斷演進的;造像的維系也從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向地緣關系為主要影響因素過渡,最終在血緣、地緣的多重作用下產生復合邑義結構。復合邑義是合作造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高級形式,生活在同一聚落內的信眾構成了佛社的人員基礎,信眾共同出資減輕了經濟負擔,寺院的有意識的發展和封建國家的支持,促進了復合邑義的發展壯大。
邑義的發展對于北朝社會有著多元影響,尤其體現在世俗政權對于基層社會組織的控制與整合,以及增加民眾福祉等方面。邑義實現了血緣與地域的共通性,宗族組織和邑義組織的嚴密性相得益彰,村落則通過自身的地緣優勢將不同姓氏的族群連接起來。宗族、村落通過與邑義組織的結合,使得處在同一特定空間內的人群在生產、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聯系更為緊密,國家政權通過對于佛教、僧官與邑義首領的管控來達到控制民眾精神的目的,邑義造像在一定意義上也帶有國家意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