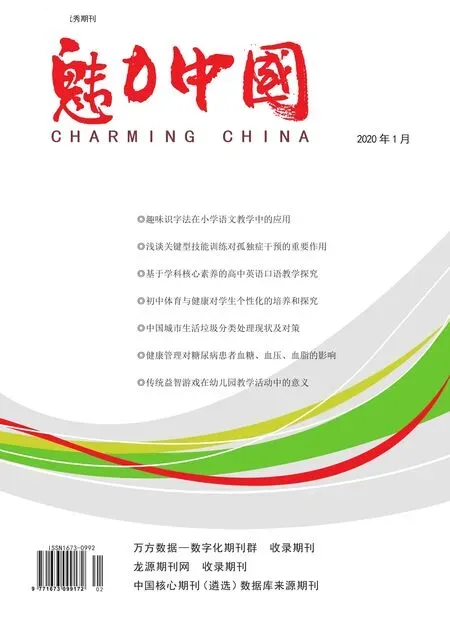探析數字繪畫
李泱 李化
(北京吉利學院,北京 昌平 102202)
自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數字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與融合,藝術的方式也被極大地拓寬,產生了具有聲光電的數字交互藝術、數字繪畫藝術、數字影像、數字雕塑等。藝術的數字化的趨勢正以萬馬奔騰之勢而來,尤其是近些的沉浸式藝術展,華麗的展示效果和全方位的感官體驗,極大的刺激了作為單一視覺的傳統繪畫。
數字繪畫是數字藝術中的一個方面,我在大學講數字插畫課的時候曾談到,數字藝術里面的種類分為:第一是數字交互式藝術,就是聲光電、多媒體藝術,第二個是數字影像,包括攝影、數字動漫、數字雕塑。還有人機交互的人工智能計算機繪畫,這個算不算數字藝術?還是智能藝術?暫時還沒有界定,其中涵蓋了數字繪畫。那么數字繪畫的定義,我的看法是以繪畫性為本體,以數字技術為輔助,能產生更多的數字時代新的繪畫語言的一種新的畫種。這兩者的交叉就會交互出更多新的可能性。
其實數字繪畫就是信息時代的一個新的畫種,應該說它就是繪畫畫種里面的其中的一個畫種。比如說國畫、油畫、水墨畫,過去叫國畫,現在叫水墨畫,油畫,版畫、水彩畫,水粉畫等等,各種畫法我們命名它的時候有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物質,它是根據用油畫來作畫叫做油畫,在版上刻我們叫做版畫,數字繪畫作為一個品種,它是一個新媒體,是一種新的方式和新的媒介,這個媒介不同于所有過去的畫種媒介。繪畫的物質依憑這一點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演進的,比如說原始時代給我們留下的藝術是彩陶,這個就是陶加上火煅燒以后形成的那樣的一些陶器,給我們留下來了,標志著原始時代的藝術的水準。那么藝術再發展它就不是彩陶了,變成青銅器了,青銅器就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代表性的一個器皿,也是代表性的藝術,但是它用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青銅。再往下發展漢代的磚和石又成為繪畫的瓶頸,再往下發展像帛,絹、紙等等藝術發展和過去發展就不一樣了,這些藝術的發展就可以看到中國的水墨畫,文人畫能夠發展到一個又一個的高峰,它的憑借就是那張宣紙,筆墨,這幾種物質加在一起形成了水墨畫特有的品質,這是在油畫里面找不到的品質。反過來說西方的油畫它在油畫的特殊材料里面找到的是油畫的品質,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代的不同發展,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又一個新的品種誕生了,我們用不著毛筆,也用不著任何的顏色,只有一臺電腦,在屏幕上你可以畫出各種各樣的圖畫來,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色彩。所以這樣的一個新的品種對我們來說,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新的領域里面做出一些新的探索和嘗試,這些探索和嘗試就可以使我們能夠在別的畫種里面找不到的那樣一種新東西,所以數字繪畫的價值正是在這里。
數字繪畫數字繪畫要通過不同的軟件進行制作。最常用的軟件有Photoshop、Painter、sai(漫畫繪制軟件)等等。借助數字軟件、繪畫板、觸摸屏,形成了新的一整套繪畫工具,但其背后的思維邏輯、運轉過程都是億萬級的數字運算,它超越了模擬世界的繪畫直接性,是一種以數字運算轉換人類行為的新介質,故它的新穎與潛在性都激發了人類的想象和探索。數字繪畫自此誕生,全世界的藝術探索者、先行者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探索數字繪畫的新圖式、新觀念的歷史潮流中。
傳統的繪畫技術已經變成了邊緣化。我舉一個簡單的實例。當初數碼相機剛剛流行起來之初,就被那些使用膠卷兒的。感光膠片的人們極端的反對和排斥。 各種謾罵聲也未能阻擋數碼影像的發展,同時,也把藝術拉到平民化,這是時代的必然之路,沒人能阻擋。傳統的繪畫技術會像傳統的京劇一樣;被作為古董保留。新技術的出現會改變已有的對藝術的定義。攝影技術如此,數碼繪畫技術也是如此。
而新技術出現之后,所謂的傳統藝術即定義改變之前的藝術或多或少會受到沖擊,但在這之后,新技術會成為藝術的一部分而為藝術所用。攝影技術如此,數碼繪畫技術也是如此。攝影技術的出現是現代藝術出現的導火索,同樣數碼繪畫作為新技術,它與攝影技術的共性在于“傳播性”,這個特性是能夠打破古典藝術“靈暈”的重要武器,同時也使它具有成為當代藝術表現載體的可能性。藝術不會消亡,藝術只會改變。
傳統繪畫在十九世紀學院派(受印象派色彩理論影響后)與攝影抗爭失敗后就算結束了,后印象派開始就不算是傳統藝術。然而數碼繪畫可以通過互聯網數以萬計的傳播,每一張都是原作,從藝術價值上來看,數碼繪畫很難超越傳統繪畫。但從商業角度來說數碼繪畫肯定是已經對傳統繪畫造成了不少沖擊了。
數碼繪畫,是隨著我們現在數字時代的發展而來的,它最初的目的是用來提高人們的生產效率,以及更便于現代從事相關工作人士的需求。慢慢的形成了一個新藝術門類,這跟傳統藝術本身的目的就不同。
數碼繪畫和傳統繪畫的藝術性其實是各自存在的,他們都有自己的藝術價值,兩者本身沒有可比性。這就好比葡萄和橘子都屬于水果,但你不能說橘子的某種成分含量比葡萄高,橘子就會取代葡萄吧。
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的科技和技術進步、新藝術門類的出現,它都不應該沖擊這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傳統藝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數碼繪畫取代了傳統繪畫,3D打印取代了雕刻匠人,流行音樂取代了京劇曲藝,那這真是絕對糟糕的一天。
從前的壁畫、木刻畫、竹簡畫,紙張廣泛應用以后,慢慢趨于衰敗,因為紙張更方便,創作成本更低,原料也更易獲得。一種形式的興起,無非是更簡便、更經濟,數碼繪畫相對于傳統繪畫就有這些優點。數碼繪畫無疑會對傳統繪畫帶來沖擊,但我不認為傳統繪畫會就此消亡。以木刻畫為例,它和紙張繪畫相比,簡便性和經濟性相差太多,相對而言,數碼繪畫和傳統繪畫之間的差距小得多,完全具備平分秋色的實力。
真正的藝術是包含細節的,這里面最讓人驚嘆的便是時間,如果一種載體,它本身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變化,那它所承載的藝術就比其他的載體多了一種變量,這個變量,造就了它的獨特性,也是另一種藝術,傳統繪畫就是如此,數碼繪畫無法模擬。
隨著時間的推移,非常有可能數字繪畫也變成了傳統繪畫的一種門類,而隨著科技的發展更新的藝術繪畫形式也會朝我們滾滾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