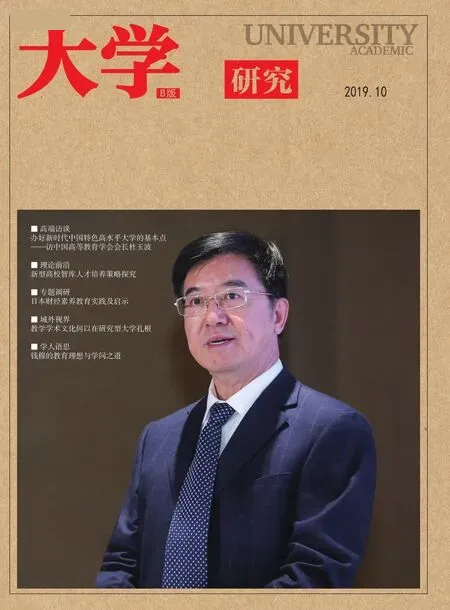教學學術文化何以在研究型大學扎根
——以東密歇根大學為案例
王占軍 林燕芳
教與學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項重要運動。這場運動要求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以“研究”作為“學術”的文化,使教學職業能夠通過持續的調查和以證據為基礎的文化從而建立自己的基礎。然而,要使教學學術在大學扎根,常常需要發生一種文化轉變,大學領導、變革推動者和促進者的行動為組織變革奠定了基礎。運用組織文化變遷模型對美國東密歇根大學引入教學學術的過程進行闡釋,通過推動組織自我探究,明晰核心特征為變革創設根基,取得內部決策者和關鍵推動者的支持并實現平衡外部要求和內部環境,教學學術在該校確立了合法性地位。
在西方的大學傳統中,學術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具備專業條件的環境中進行非實用性的探索活動。學術研究則是借助已有的理論、知識、經驗對科學問題的假設、分析、探討和推出結論,其結果應該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觀規律的,是對未知科學問題的某種程度的揭示。
隨著現代大學的發展和學術活動范圍的變化,學術概念逐漸窄化為研究(Research),研究意味著發現知識,甚至與發表論著等同起來,傳播知識、應用知識則被排斥在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前校長博克(Derek Bok)曾說:“學者們一般認為研究比教學更有價值,因為教學對教師來說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研究結果是時間和才能的表現”。教學即使有創新,由于這些創新還沒有以不可改變的形式固定下來,因而其本質上通常是嘗試性、探索性的。更為重要的是,教學難以讓同行去評價,特別是不受其他學校同行教師們的評價,而研究成果一經發表,學術成果就像硬通貨一樣,能夠被校際或國際同行們衡量和評價。因此,科學研究成為決定大學系統的地位的決定性因素。[1]針對這樣的問題,時任卡內基教學促進會主席的博耶經過仔細調查和認真研究后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重新理解學術的內涵,并最終取決于對其采取何種獎勵方式。他提出了教學學術概念,以賦予學術更廣內涵的視角來解答這一問題,嘗試建立溝通教學與研究隔閡的橋梁,由此高等教育領域興起一場教學學術運動,這場運動要求大學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以“研究”作為“學術”的文化,這意味著大學這種大型機構的主導核心技術將發生相應的變化。
本文以美國東密歇根大學(簡稱為EMU)為案例,分析該校如何通過組織文化變革確立教學學術合法地位的過程。東密歇根大學是一所坐落于美國北部密歇根州伊斯蘭提的公立大學,始建于1849年,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名,該校在地方性大學中排名第85,公立學校中排名27。
一、大學緣何需要教學學術
教學學術始于這樣一種觀點,即教學是嚴肅的、學術的工作,而不是與學術分離的工作。舒爾曼(Shulman)建議學者們不要過多地談論一般意義上的教學,而是應該建立在我們關于好的教學知識的基礎上,以建立一個圍繞它的學術體系,再造大學的學術文化。[2]但是大學作為科層組織,文化轉型不是易事,尤其是現代大學要么是通過教學立足,要么就是憑借研究獲得聲望,很少通過對教學的研究來獲取地位。如果“教學”的科研活動不能在大學取得合法地位,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教學學術運動。舒爾曼對教學學術(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以下簡稱為SOTL)的定義可以看到,教學學術作為一種公開的教學活動,可以經受同行的公開評價,能夠在學術共同體內被成員所討論,這與傳統的學科科研活動模式是一樣的。盡管教師個體鑒于時間和精力,不可能從事所有類型的科研,但對于整個大學組織而言,教學學術的繁榮則是必要的,正如赫欽斯(Hutchings)和舒爾曼所說,教學學術是一種條件,特別是卓越教學的條件。它通過教學職業的自我推動,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前進。[3]教學學術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教學方面,它還有助于支撐起學術共同體的家園,促進學科的發展。教學學術是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教學專業本身得以進步,通過這種機制,教學可以成為一種不是憑感覺和經驗完成的工作。因此,教學學術有潛力為所有的教師和學生服務。埃爾頓(Elton)提出了教學學術可以促進專業持續發展(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4]而后托菲德(Tofade)提出在此基礎上提出CPD 模型,[5]該模型可以用來評估教學目標的實現情況并能探索改進教學的方法。盡管良好的教學在不同的領域也具有共同性,但學科間教與學的差異也是比較明顯的。因此,教學學術的工作不僅可以推進一般的教學和學習,而且可以集中在個體所在的學科領域內,參與教學學術并不意味著放棄學科的研究工作。理想情況下,教學學術工作可以提高一個學者對他們所在學科的貢獻,盡管是以一種非傳統的方式。
二、大學組織變革的理論模型
(一)解釋組織變革的理論模型
關于大學組織變革,學界主要有六種理論模型,用于理解、描述和發展變化過程,分別是進化理論、目的理論、生命周期模型、辯證模型、社會認知模型和文化模型。每個模型都有一組關于組織為什么會發生變化、過程如何展開、什么時候發生變化、需要多長時間以及變化的結果的不同假設。
進化理論的主要假設是變化是對外部環境、制度變量和每個組織面臨的環境的響應,社會系統作為一種多樣化的、相互依賴的、復雜的系統,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外部需求而自然地進化。目的理論模型假定組織是有目的和適應性的,變革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領導者、變革推動者和其他人看到了變革的必要性,與進化模型一樣,變革的過程是理性的和線性的,但是個體管理者對變革的過程更有幫助。生命周期模型是從對兒童發育的研究演變而來的,主要關注組織成長階段、組織成熟度和組織衰退,[6]變化被概念化為人類或組織發展的自然組成部分。辯證模型,也被稱為政治模型,將變化描述為意識形態或信仰體系沖突的結果,[7]沖突被看作人際交往的固有屬性,變革過程被認為主要是討價還價、提高意識、說服、影響和權力以及社會運動。社會認知模型將變化描述為學習和心理改變的過程(如創造意義和心理模型),改變的發生是因為個體看到了成長、學習和改變行為的需要。在文化模式中,變化是對人類環境變化的自然反應,文化總是在變化,變化的過程往往是長期和緩慢的,組織內的變化是價值觀、信仰、神話和儀式的改變。一些研究人員建議綜合使用一些模型或類別,因為每個模型或類別都能揭示組織生活的不同方面。[8]多個模型的優點是它們結合了各種變化理論的見解。鮑爾曼(Bolman)和蒂爾(Deal)對組織的重新架構和摩根(Morgan)的組織隱喻說明了如何將目的論、進化、政治與文化、社會認知和生命周期模型的假設結合起來以理解變化。[9]
(二)解釋大學組織變化的模型
將上述模型遷移到高等教育組織變革研究中,需要考慮高等教育機構的獨特特征,包括:相對獨立的環境、學院獨特的文化、價值觀驅動、多重權力和權威、結構松散耦合系統、有組織的無政府主義決策、共享治理、終身教職制度、目標模糊等。雖然這不是一個詳盡的列表,但它代表了影響組織變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一些關鍵特征。鑒于這些獨特的組織特征,高等教育機構似乎最好是通過文化、社會認知和政治模式來解釋。對文化模型的需要很明顯,因為成員們創造和再現了歷史和價值觀、就業的穩定性、強烈的組織認同、對價值觀的強調以及多元的組織文化,符號和身份對于理解是否發生了改變以及如何發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松散耦合的結構、無政府的決策和模糊的目標使意義不明確,而社會認知模型對多重解釋因素的強調可能是識別和促進變化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共享的治理體系、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相互沖突的行政和學術人員的信念,以及模棱兩可的、相互沖突的目標,也表明需要政治模型的解釋力。進化模型對于理解環境因素對變化的影響非常重要,例如高等教育系統中的認證機構、基金會和立法機構,對大學組織的影響與日俱增。然而,即使高等教育機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也可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邏輯,而這種一致性和邏輯可能會被外部環境力量的入侵所破壞。
既然推行教學學術具有廣泛的價值,那么就需要大學組織樂于從事這項工作,要在組織結構與文化中確定其位置,又要使這項工作能夠強化大學核心使命的實現。凱澤爾(Kezar)指出,組織文化是研究機構變化的主要視角或理論之一。[10]組織文化是“當一個群體在一段時間內解決其在外部環境中的生存問題和內部整合問題時,該群體在一段時間內所學到的東西”。[11]組織文化具有穩定性,組織成員經歷了組織規范和傳統的洗禮,其反應和思維模式會變得更加自動化,并且對變革具有一定的恐懼和抵制,而不是積極面對新思想的不確定性。組織文化模式變革的關鍵機制之一是領導者,領導者提出一套信念和行為模型后,這些信念和行為是團隊成員認同并希望效仿的,或者當領導者表現出一種在組織內部被成員所重視的新信念時,比如自愿奉獻資源,他們可以鼓勵文化變革。領導者還可以通過正式聲明支持本組織來鼓勵文化變革,例如在戰略規劃中加入教學學術內容。利用領導力改變大學文化的挑戰在于,如果成員們發現領導者不可信,或者與他們自己的想法不夠接近,他們可能會不再追隨領導者,或者分裂成一個亞文化。
除了領導,還有其他兩類行動者扮演關鍵角色。第一個是變革的推動者,他們是基層的行動者,他們最強烈地支持變革。他們通常最強烈地希望看到這種變革發生,也最可能是從這種變革中獲益的人(如果這種變革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有害的后果,則風險最大)。變革推動者可能擁有領導者所不具備的具體的實質性專業知識,但可能缺乏影響變革的制度影響力或角色。因此,除了變革推動者之外,實現制度變革的過程可能還需要一個促進者,一個能夠在變革推動者(具有激情和實地專業知識)和領導者(具有促使事情發生的制度影響力)之間架起橋梁的人。理想情況下,促進者擁有足夠的影響力,以使文化變革發生。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不同角色在組織環境中扮演的角色對于采取行動或文化變革至關重要。[12]
松德樂(Sundre)使用問卷法對北卡羅來那大學格林斯堡分校的教師進行了調查,讓教師陳述哪些活動屬于學術范疇。在40 個活動項目中出版和科研占據其中的12 個,發表論文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項目。學科中的聲望(排序2)、廣泛的學科知識(排序8)、學科專門知識(排序10)、學科組織活動(排序17)、對學科的承諾(排序21),而卓越教學僅排在第10 位。[13]可見,科學研究是決定大學組織地位的關鍵性因素,研究型大學學術文化的核心就是科研學術文化。基于這樣的現實,教學學術要想在研究型大學扎根,并成為學術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就需要組織文化變革,因此凱澤爾的組織文化變革理論可以作為理論框架解釋研究型大學引入教學學術的案例。在組織學術文化變革過程中,領導者、關鍵行動者和推動者都在各種角色上發揮著不同作用,見表2-1。

表2-1 組織文化變革中的不同行動者角色
組織文化的變化是緩慢的,組織文化除了具有“延續并自我復制”的特征外,組織內的社會化也要一定的時間,當新成員加入組織時,比如聘任新教師,每個高級成員都要向新成員灌輸文化價值。這可以通過變革推動者、促進者和領導者來實現,每個人都扮演著相應的組織角色。在真正的文化轉變發生之前,信仰上的挑戰和沖突在文化變革時期很常見。[14]對于像教學學術這樣競爭激烈的新學術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凱澤爾提出了一套“復雜的以研究為基礎的原則”,[15]作為高等教育變革的基礎。借鑒該理論,本文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來研究東密歇根大學使教學學術成為該機構內公認的技術的文化變革過程,對該校組織變革的步驟所體現的變革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對創建教學學術文化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
三、東密歇根大學確立教學學術在其學術文化中的地位
借助以上提出的分析框架,本文對東密歇根大學進行案例分析,教學學術已經成為該校制度文化中一個更重要的組成部分。案例研究主要是按時間順序進行的,以凱澤爾組織文化變革理論作為框架。下面的表3-1詳細描述了案例研究的關鍵要素以及它們與理論模型的聯系,以及這些步驟首次出現的時間。

表3-1 東密歇根大學引入教學學術的組織文化變革原理
(一)推動組織自我探究教學學術的意義
該校政治科學系教授伯恩斯坦被卡內基教學促進會遴選為2005-2006年學者,作為項目條件,卡內基教學促進會要求該校必須為教學學術提供支持。該校采取的一個措施是由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同意伯恩斯坦在2006-2007年組織一次教與學學術論壇(后來連續了四年)。第一年,有10 位教師參與了論壇,來自5 個不同的學院。作為論壇的一部分,教員們在秋季學期設計了一項調查以了解冬季學期的教學和學習狀況,教員們整個冬季學期都在實施該項目,收集學生學習的數據,分析他們所擁有的數據。教師小組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經常一起討論那些被邊緣化的學生的學習問題,這些教師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相互支持這個活動,也向各個學院和學系提出倡議推廣教學學術項目。
每年研討會,參與者都會撰寫文章并由教師發展中心組織出版。這本著作本身就成了一個利器,人們可以人手一本,并指出人們在教學和學學術方面所能做的事情。隨著每一卷的出版,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大家所作的工作,每個章節前面編輯和作者都會簡短地介紹他們的章節。在研討會的參加者職稱晉升時,他們用這些章節作為展示他們教學水平的證據。一旦他們獲得終身教職,他們就會繼續支持教學學術活動。雖然大學最初只是按照卡內基教學促進會的要求,作為支持伯恩斯坦教授成為卡內基學者的條件,但是隨著相關活動的開展,特別是教師發展中心主任開始支持教學學術活動,學校進入了組織自我探尋的過程。
(二)幫助更多的成員明晰教學學術的核心特征
隨著研討會步入正軌,該校教師開始探索如何使這項工作產生更大范圍的影響,創造更多的機會讓人們參與教學學術的討論。于是他們建立了定期的學術會議機制,開展了一系列的教學學術活動。從2008年冬季學期開始,每學期舉辦四次研討會,大約半數的教師都參與了會議,平均每次會議有12 個人演講,參與者有教師,也有學生。第二個明晰核心特征的舉措是邀請外面的演講者在會議上做講座,比如他們邀請了著名學者蘭德·巴斯(Rand Bass)講學,他是教學學術的重要倡議者,他提出如果教師將教學學術工作公開、接受同行評價和批評,并與所在專業社團的其他成員進行交流時,這樣會加強教師自身的學術工作。這時教學就變成教學學術,而這些也是所有學術所具有的特點,這為教學能夠作為學術提供了理論依據。該校也邀請了伯恩斯坦做專門的教學學術工作坊,各種形式的教學學術活動幫助參與者更好的了解什么是教學學術,如何實施教學學術,學校也為新教師創設理解教學學術組織文化的活動。
(三)大學組織的變革需要內部決策者和關鍵推動者的支持
2007年,該校在兩位主要教學學術倡議教師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地區性的教學學術會議,以此盡可能擴大教學學術的影響,無疑舉辦會議可以吸引教學學術的研究者參與會議,交流經驗和成果,擴大該校在此領域的影響力。伯恩斯坦推動該校向卡內基教學促進會申請加入教學學術項目,并且與副教務長積極溝通,此時副教務長正在開展學生學習方面的研究,他有意擴展這方面研究的范圍。作為領導者,他擁有相應的資源可以舉辦學術會議,能夠持續推動相關工作有序開展,經過副教務長的努力,教學學術成為該校戰略規劃構成部分,很快成為整個學校的全景戰略。副教務長認為定期舉辦教學學術會議,可以有效地推行“本科教育第一”的戰略,并且可以為相關活動持續化提供合法性的撥款支持。SOTL 將對學校有價值,因為對它的支持可能對“教學優先”的技術有用處,這是該大學的宣傳口號。此外,副教務長也意識到推廣教學學術對擴大該校在美國公立大學中的影響具有積極意義,這為組織文化變革奠定了基礎。校方開始對SOTL 有了正式認可并以種子資金的形式向SOTL 活動提供關鍵的財政資源。副教務長以他的實際行動向大學領導者表明,SOTL 對學校很有價值。
隨即該校教學學術主要發起人積極與教師發展中心主任進行溝通,該中心主任也積極投身于教學學術運動,支持舉辦相關的會議,他為舉辦會議慷慨提供注冊費用,此外對于該校教師而言,中心主任的支持無疑釋放了有利的信號,讓教師更信服教學學術的價值。除外之外,發起人還積極與各學院院長溝通,一起討論在大會期間組織專題討論會的可能性,努力向院長游說支持教師參會是有意義的學術工作,例如技術學院院長為本院教師參與會議提供了注冊費,并同意組織專門的圓桌會議討論教學學術與信息技術運用。這些關鍵人物有能力將組織變革與教師個體之間關聯起來,創造支持教學學術會議的公共輿論氛圍。
(四)平衡外部壓力與內部環境的關系
發起人還要考慮到如何吸引其他大學參與教學學術會議。為此,他們組建了“教學學術合作體”聯盟,每個加入聯盟的組織需要繳納會員費500 美元,作為交換,會員單位成員參加會議可以打折25 美元登記費。該聯盟共吸引13 個高校加入,包括研究型大學、地區綜合型大學,以及文理學院。該聯盟還不斷從其他途徑募集資金,努力擴大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對于大學組織而言,外部壓力要求獲取資源,獲得支持,而在內部就需要凝聚共識,形成愿景,形成領導力,由此才能帶來組織支持教學學術的組織文化轉變。
理解環境與內部需求之間的交集,包括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之間的平衡,是實現變革的關鍵組成部分。外部環境可以通過提供資源,包括資金和無形的支持,如鼓勵和表示支持,使組織充滿活力。通過吸引外部社區的成員對變革過程進行投資,可以在領導者促進大學對SOTL 的貢獻的愿望和外部合作機構對自身成功的愿望之間取得了平衡。來自外部環境的同事對教學學術行動者的努力給予的價值認同感,投資越大,大學的領導者就越有可能因為看到了該校成為SOTL 運動領導者的形象而更加愿意支持建立教學學術文化。
四、結語
改變大型組織的文化需要長期的過程,本案例說明以研究為學術工作的研究型大學引入教學學術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尤其是大學內外部已經確立了明顯的“研究”學術信念,教學學術作為新的信念的確立需要在大學組織文化層面做出變革,需要領導者、行動者和推動者的合作,經過長時間的組織內部的社會化,將大學內部的各個部分工作集合起來,才可能帶來重要的內部文化變遷。當前國內大學也開始倡導教學學術,普遍建立了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了各種類型的推動教學發展的活動,并出臺了促進教學學術的各種政策,但這是否意味著教學學術已經成為大學的核心文化,可能需要更多實證研究的檢視。本案例提供的啟示是,有必要回顧我們已經采取的措施及其在改變大學的科研學術文化方面所取得的進展,以便對大學教學學術發展中的各種形式化問題做出更審慎的思考和判斷。
注釋:
[1]博克,D.C.回歸大學之道:對美國本科教育的反思與展望[M].侯定凱,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33-50.
[2]Shulman, L.S.Teaching as Community Property:Putting an End to Pedagogical Solitude[J].Change, 1993,(6):6-7.
[3]Hutchings, Pat, Shulman, L.S.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New Elaborations, New Developments[J].Change,1999,31 (5), 10-15.
[4]Lewis Elton.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The Role of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J].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9,(3):247-258.
[5]Toyin Tofade, MS, etl.Perceptions of a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rtfolio Model to Enhance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J].Journal of Pharmacy Practice,2013,(2):131-137.
[6]Levy, A., Merry, U.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Approaches, Strategies, Theories[M].New York:Praeger,1986:22-25.
[7]Morgan, G.Images of organization[M].Newbury Park, CA.:Sage Publications,1986:45-46.
[8]Van de Ven, A.H., Poole, M.S.Explain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3):510-540.
[9]Bolman, L.G., Deal, T.E.Reframing Organizations:Artistry, Choice, and Leadership[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1:27-29.
[10][15]Kezar, A.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ing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rst Century[R].ERIC Digest.Washington D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ED457763,2001.
[11]Schein, E.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A Dynamic View[M].San Francisco:Jossey Bass,1985.
[12][14]理查德·斯科特.組織理論:理性、自然與開放系統的視角[M].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16-119.
[13]Donna L.Sundre.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Content Domain of Faculty Scholarship [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2,33(3):29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