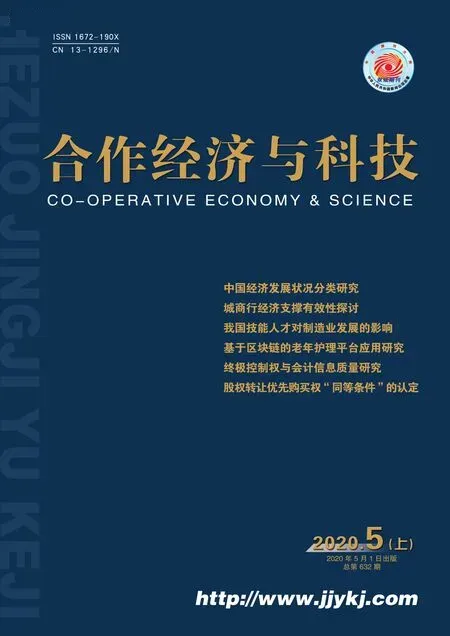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研究
□文/劉正之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
[提要] 人工智能生成物已進入大眾視野,但該生成物是否屬于“作品”尚未得到學界和法律的統一認定,現階段難以將其納入《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結合社會與市場的需求,人工智能生成物應當受到法律的規范和保護。可以考慮設立新類型的鄰接權,在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規制的同時,維護現行著作權體系的穩定性。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海量的大數據、深度學習算法以及云平臺等強大的計算能力讓機器得到了進化。在創作領域,人工智能從輔助者過渡到創作參與者甚至獨立創作者。它們可以根據人類的簡單指令或模板,半自動或自動生成與指令相關而區別于以往內容的文本,代替人類的一部分勞動和“思考”。2015年,騰訊自動化機器人Dreamwriter發表了一篇新聞稿件,會寫稿的機器人在我國首次亮相。2017年,微軟“小冰”出版了被稱為“人類歷史上首部由機器人100%創作”的詩歌集《陽光失了玻璃窗》。人工智能飛速發展沖擊著人類作品的定義和市場,法律法規應警惕地給予回應。
一、人工智能創作物納入現行《著作權法》的障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的規定,著作權保護的對象是作品。作品是在文學、藝術、科學領域具有獨創性的可復制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構成作品,在于其內容是否具備著作權法所要求的“獨創性”。
從《著作權法》的主體來看,根據傳統的著作權理念,獨創性的源泉是人類。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在其《著作權法》第二條中明確要求了“個人”的主體身份。歐美法系的美國在“猴子自拍案”中通過否認猴子的人格主體,從而否定其著作權,實質上是排除非自然人的創作。我國國家版權局明確表示,作品“必須是人類意志的產物”。人工智能并非“血肉之軀”,難以獲得《著作權法》的主體資格。
如果不討論人工智能和人類之間天然的鴻溝,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備“獨創性”,從而使其納入《著作權法》有了可能?王遷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本身并不理解“創作”目的和其“創作”產物之間的關系,其創作本質屬于“執行既定流程和方法”,而非“創造”,遑論創造性。這種“創造性”的標準仍然是基于“人類”的精神生產,通過人工智能的非人類身份而否定其創造性。吳漢東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只要獨立生成內容,就構成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至于其用途、價值和社會評價則在所不問。熊琦教授從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表現形式上進行分析,認為既然無法根據表象來分辨人工智能生成物和人類作品,則應當認定前者在客觀上滿足最低創造性的要求,認定其為作品。總體來說,學界對“創造性”的標準尚無定論,難以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定性。
二、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必要性
與學界膠著的討論相對比,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根據烏鎮智庫發布的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企業融資規模達157.54億美元,占亞洲人工智能企業融資的93.09%,占全球人工智能企業融資數額的46.94%。根據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發布《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布局最多的國家,數量略微領先美國和日本,三國占全球專利公開數量的74%。
從積極必要性角度看,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助于繁榮文化市場,推動人工智能應用,迎合國家戰略需要。創作時效短、內容有創作價值的機器生成物為市場帶來了新的競爭力,從而促進人類作品向高質量發展。將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立法保護,也能趁機對其進行梳理和規制,引導其健康、蓬勃發展。
從消極必要性角度來看,未來人工智能自主性會更高,創作能力會更加突出,對現有《著作權法》的沖擊將愈發猛烈。如果其生成物不受保護,那么大量沒有版權的機器生成物將充斥市場,成為新類型的“無主作品”和“孤兒作品”,這不利于著作權市場的穩定性。從作品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既然存在無版權的作品,他就沒有必要選擇有版權、需付費的作品,那么除了依賴作者名聲威望或本身具備高度獨創性的作品外,大部分人類作品的版權將失去市場,急速貶值。人類作品的傳播性被大幅削弱,人類自主創作失去了經濟動因,這明顯和著作權促進人類創作激情、推動文化事業繁榮的立法初衷相違背。
此外,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受保護,對其進行使用就沒有了限制;如果有人對有創造性價值的機器生成物進行二次利用,那么會產生如下問題:首先,人類作品和機器生成物會混雜在一起,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可能通過人的行為而受到保護,本來不作為甚至不存在的著作權人可能享有作者權利,這會給司法實踐帶來大量負擔;其次,模糊的界限可能使得投資人有所憂慮,為避免風險勢必拘束其投資欲望,這對所涉行業的發展不利;最后,許多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現形式上與人類創作作品無本質區別,在機器本身緘默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知情者舉報,二次利用的行為很難被發現。綜上,著作權法有必要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法律保護。
三、我國學術界對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護模式
(一)降低作品的獨創性要求,將人工智能生成物歸于法人作品。大陸法系國家要求作品具有“作者個性的烙印”,這導致人工智能生成物即便在表現形式上符合作品的要件,也會因其創作者并非人類而被拒之于被保護的范圍之外。如果降低對作品獨創性的要求,將人工智能生成物視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即可用著作權進行保護。在此基礎上,有學者認為可以用法人作品制度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法人等組織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與其利用人類來創作相仿,因此可以將人工智能生成物視為代表設計者或者訓練者意志的創作行為。將人工智能的作品歸為法人作品的行列,將著作權歸屬于法人等組織,既避免了創設新的法律法規,也避免了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上的作者。但是,學術界對獨創性的標準本來就不明晰,又要以何標準進行降低呢?降低后的獨創性標準又應如何規制?而且,降低獨創性標準可能使著作權保護對象的范圍擴大,這會引起新的問題。人工智能本身不具有意志,又如何“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采用法人作品保護模式,其實忽略自然人的主體,如果人工智能的所有權人是個人,則無法適用法人作品要求,因此這種保護模式在實踐中依然面臨很多困難。
(二)擴張鄰接權的權利種類,為人工智能生成物設立鄰接權。鄰接權最初是為保護那些“未能體現創作者個性或創造性程度不夠的勞動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獨創性”標準上遇到的阻礙和上述勞動成果類似,這為人工智能的法律保護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能。
通過擴張鄰接權的種類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保護,其優勢有兩點:一是這可以維護現行著作權體系的穩定性。設立鄰接權不會對現有作品要件進行沖擊,同時還避免了著作權因過多或不當賦予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帶來的法律糾紛,這間接地排解了人工智能編程人員、投資者和人工智能生成物使用者的憂慮。二是它還避免了人工智能與自然人的身份糾葛。鄰接權不僅避開了著作權法中獨創性對自然人限制,還杜絕了人工智能被賦予人格權的可能。鄰接權一般不包括人格權,而對財產權的內容也會因鄰接權保護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區分。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歸于法人作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享有署名權等人格權利,主體和客體的權利混淆不清。
當然,以鄰接權作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護模式也存在問題。根據傳統觀點,鄰接權主要是保護傳播者在作品傳播中的投入,如不能合理解釋這與人工智能生成物之間的聯系可能會產生混亂。
(三)承認人工智能主體地位,單獨立法對其生成物進行保護。歐盟數據庫指令所建立的特殊權保護模式單獨設立新的法律法規,以便更加全面地對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以及其生成物的權利歸屬、保護內容、保護期限等進行詳盡的規制,而避免其與現行著作權法可能產生的矛盾沖突。但是,單獨立法的時間成本和人工成本很高,從初步確定單獨立法到最終發布還需要很長的過程,可能無法及時解決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現實問題。
綜上觀之,第三種保護模式雖然可以對人工智能的生成物進行詳盡全面的保護,但與人工智能的現實發展狀況不匹配;第一種雖然在程序設立者和人工智能之間找到了平衡,但是在實踐中很難執行。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從鄰接權入手。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具體保護路徑
鄰接權也稱“相關權”,在我國《著作權法》中被稱為“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根據WIPO在《知識產權手冊》的解釋,鄰接權包括表演者權、錄音制作者權和廣播組織者權,這也是狹義鄰接權的概念。
隨著時代變遷,現代鄰接權制度的種類已大大豐富,很多國家根據自身國情對鄰接權進行了拓展。比如意大利將獨創性不高的攝影作品、戲劇的布景作品、個人書信和肖像等歸入了鄰接權之中;法國將計算機軟件列入鄰接權的保護范圍;德國《著作權法》規定的鄰接權多達十一種;我國《著作權法》將出版者權加入到鄰接權保護范圍。由此可見,鄰接權本身并不必然被拘束于狹義鄰接權的概念之中,它的本質是彌補因獨創性標準過高無法受到法律保護的生成物,這為人工智能生成物被納入鄰接權的保護范圍提供了基礎。
那么,如何具體地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法律保護?這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量:
(一)鄰接權的權利主體。人工智能生成物從其產生到最終傳播到市場主要涉及三方: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開發者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傳播者。人工智能一直作為權利的客體出現在大眾視野。《德國民法總論》認為,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之間的法律地位不得轉換,那么作為權利客體的人工智能“永遠無法成為權利主體,而只能是法定支配權的對象”。雖然現行著作權法中將法人視為主體,但法人的本質也是對自然人意志的集中體現,依然沒有跨越自然人的邊界。如果將人工智能視為鄰接權的主體,那么法律主體為自然人的界限將會被打破。無限制地擴大主體的內容,將會最終導致權利主體失去意義;另一方面,賦予人工智能以權利主體的地位,還會衍生出其相應的權利義務問題。因此,應將鄰接權的權利主體歸于后兩種情況。
人工智能的開發者制造了人工智能這一客觀存在,賦予其數據和算法,為人工智能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將開發者視為權利主體的觀點有國外立法依據,比如英國版權法就是將計算機生成作品進行必要程序者視為該作品的作者。但是,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開發者已經在計算機程序及軟件開發等方面享有著作權,如果將鄰接權的權益也賦予開發者,則會出現雙重激勵的情況。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傳播者是“對生成物之傳播進行必要工作安排者”,其應當在推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傳播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現階段,人工智能生成物仍需要人類對其進行最后把關,尤以新聞稿件為例,這就需要傳播者對內容進行處理,最終將其公之于眾。即便是依賴性較小的美術、音樂等作品,也不可能完全脫離傳播者的勞動。將其視為鄰接權的權利主體,符合鄰接權對促進“作品”傳播的理念,也不會產生權利重疊的情況。
(二)鄰接權的內容。鄰接權的權利內容,即鄰接權主體享有的具體權利。一般認為鄰接權的內容不包括人身權,這與人工智能的非人類性不謀而合。有人認為可以將署名權賦予人工智能,以便讓人工智能和其生成物之間產生紐帶,這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市場傳播效率。但是,賦予人工智能署名權可能使人工智能和自然人的權利義務再次產生混淆,對鄰接權的權利內容也做出了改變,在這種可能的后果面前,署名權是否仍然足夠便利,以使得人工智能享有該人身權?
筆者認為,還是應該回到鄰接權對財產權的規定,并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權益限制在財產權之中。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五)至(十七)項規定了十三項關于財產權的內容。然而在“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中,財產權的內容被大大縮減。比如在第四十二條中,錄音錄像制作者對其制作的錄音錄像制品只享有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而非全部財產權。
在實踐中,除去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制度設計中的障礙,還要考慮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護和權利限制。如果不加區分地給予人工智能生成物全部權利,很可能導致反公地悲劇。人工智能相對于人類而言,具有信息捕捉快、數據儲備多、生產效率高的優勢,未來可能出現機器生成物數量在某領域遠超人類作品數量的情形。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過剩的法律保護,可能導致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護成本和使用成本激增,反而會阻礙其流通和傳播,這和保護初衷不符。
人工智能在音樂、美術、視頻等方面雖然可以創作出和人類作品表現形式別無二致的內容,但是在文字類創作上的創造性和價值還有待提高,比如新聞稿件。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財產權也應被適當縮減,可以考慮只賦予其復制權、發行權和網絡傳播權。這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主要傳播途徑和法律糾紛可能產生的領域,只對這部分進行規制,一方面可以有效保障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鄰接權,另一方面也避免過多權益導致的保護過剩問題。
(三)鄰接權的期限。根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對狹義鄰接權的三種權利類型的保護期限為50年,而對圖書、期刊的版權設計權的保護期為10年(第36條)。根據《保護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第十四條,對上述權利的最低保護期限是20年。德國的《著作權法》對鄰接權保護期限的規定更加豐富,比如對數據庫的保護期為15年,對狹義鄰接權的保護期限為50年,對特定版本的保護期限為25年。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對鄰接權的保護期限設定不同,即便是同一國家,對不同鄰接權類型的保護期限也有所區別。一般來說,越接近著作權對作品的要求,其保護期限越長。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產效率高,作品更迭快,也很難具備經典作品的內容價值高度,如果賦予過高的保護期限,可能對市場不利。因此,可以參考德國對數據庫的規制,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護期限設定為從人工智能生成物發表之日起15年;對于創作完成后15年未發表的,法律不再對其進行保護。
五、結語
如今,我國正在對著作權法進行修整,迎面撞上人工智能的熱潮,應考慮在布局人工智能發展前景的同時,借機在著作權法中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回應。從法教義學的角度,人工智能難以尋求現行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突破對著作權法的挑戰被擴大到作品的源頭和創作過程,這對著作權法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沖擊;同時,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現形式與人類作品沒有區別,而在生產效率上遠高于人類作品,這對文化市場造成了沖擊。因此,對人工智能生成物進行法律保護勢在必行。在考察國內外現有法律法規和司法實踐、分析國內學術界現有的對保護模式的討論后,鄰接權制度的優勢和合理性凸顯出來,或可作為突破口。可以預想,未來的人工智能會更加精妙發達,其生成物也將更具創造力和價值,法律法規要跟隨實際情況作出深入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