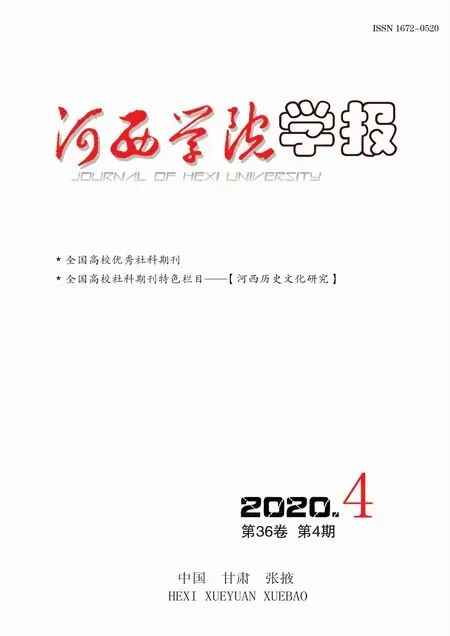《廣韻》《集韻》所見河西地名異寫考校九則
何茂活
(河西學院文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河西地區古代地名異寫較多,有的不為學者所知,有的形音關系復雜,令人疑惑。今以《廣韻》《集韻》這兩部韻書為出發點,選取九例,試作簡單考校,借以觀察這些異寫的形成及傳承使用情況。同時,也以此為視角,對這兩部韻書的體例特點試作對比。
一、溺水
溺水,即弱水。《廣韻·藥韻》而灼切:“溺,水名,出龍道山。其水不勝鴻毛。”[1]502《集韻·藥韻》日灼切:“溺,《說文》:‘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2]1484
按:溺,是“弱水”之“弱”的加旁分化字,但后世不從,仍作“弱”。上引《廣韻》所釋“出龍道山”,“道”為“首”之誤。龍首山,位于山丹縣西北部,當地人稱“龍頭山”。清戴震《水地記》:“大通河源,為甘肅涼之祁連、合黎、龍首、焉支等山。”自注:“龍首山,在山丹縣西北二十五里邊外。”[3]412道光本《山丹縣志·山川》:“龍首山:城西北三十里,一名甘凌山,俗名北山。《通志》曰:‘甘凌,又名甘峻。山陰有泉,旱禱輒應。內石洞三,有龍眼石,土人以晦明卜歲焉。’”[4]77-78按:甘凌,實為“甘浚”之訛。①
查《廣韻》諸本,“溺”下“龍首山”之“首”皆作“道”,周祖謨《廣韻校本》、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及蔡夢麒《廣韻校釋》等均未出校。這一訛誤,影響了后世多種韻書,《五音集韻》《洪武正韻》等均相沿而訛。《集韻·藥韻》“溺”字條下引錄《說文》,文字無出入。
沉溺之“溺”本作“?”。《集韻·錫韻》乃歷切:“?,《說文》:‘沒也。’或作溺。”此義之“溺”與柔弱之“弱”,古音相近,意義相通。漢劉熙《釋名·喪制》:“死于水曰溺。溺,弱也,不能自勝之言也。”清畢沅疏證:“《說文》‘溺’即《禹貢》之弱水。然則‘溺’固有‘弱’音,故此以‘弱’訓‘溺’。”[5]407可見“弱水”寫作“溺水”,不僅是字形上的加旁繁化,而且在字音字義上也有同源孳乳關系。明人田藝蘅的《留青日札·三弱水》說得更清楚:“東海中有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故名。又,西海中亦有弱水。西海,今西寧衛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西。”[6]360
二、潶水
潶水,即黑水。《廣韻·德韻》呼北切:“潶,水名,在雍州。”[1]529《集韻·德韻》迄得切:“潶,水名,出黑山西。”[2]1576
按:“潶”字的成因與上條所論“溺”字相同,屬加旁區別字,但后世流行不廣。《正字通·水部》對此有辨析:
潶 舊注:“音黑,水名,在雍州。”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自鄭玄、酈道元,皆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漢《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未詳其地。獨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入會川為瀘水。瀘水即黑水。本作黑,舊注黑訛作潶,謂水在雍州,并非。[7]40
《正字通》的主要觀點有二:其一,“潶”是“黑”的訛字。這一觀點大體可取(準確地說應當是加旁分化字,或曰俗字,而不應稱為訛字)。該書羊部“”字條下也說:“,俗字。黑羊作,誤。與水部黑水作潶同。”[7]281可以參考。其二,認為舊注說黑水在雍州是錯誤的。這一說法欠妥。《正字通》只注意到了《禹貢》中的“華陽、黑水惟梁州”,但沒有注意到《禹貢》中還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之句。因此說黑水在雍州,并無錯誤。事實上,黑水所流經的張掖等地古屬雍州,與《禹貢》所述是吻合的。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上文所述字書韻書中對“潶”的收錄和考辨以外,歷代典籍中鮮有對此字的使用。可見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既會通過添加形旁明確義類,從而產生新字,也受趨簡求易心理的影響,限制上述新字的滋生與傳播。在這種矛盾和制衡中,漢字總量的增長總是有所節制的。
三、甘峻
甘峻,山名。山在張掖,為甘州得名之由。《廣韻·談韻》古三切:“甘,《說文》作,美也。又隴右州,本月支國,漢匈奴觻得王所居。后魏為張掖郡,又改為州,取甘峻山名之。界有弱水、祁連山,上有松栢五木,美水茂草,冬溫夏涼。又有仙樹,人行山中,饑即食之輒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可見也。”[1]223-22《4集韻》“甘”字頭下注釋簡略,無此內容。
甘峻,亦作紺峻,今多作甘浚。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三七:“甘浚山,在都司城西南八十里,有泉甘冽,因名,又名紺峻。”[8]940清趙一清《水經注釋·河水二》:“《太平寰宇記》甘州張掖縣下云:‘甘峻山,一名紺峻山。《水經注》云:張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今本無之。”[9]43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陜西十二·甘肅行都司》:“甘州左衛,本匈奴昆邪王地,漢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意,后漢因之。晉仍為張掖郡。西魏置甘州,取州東甘浚山為名。隋、唐因之,亦曰張掖郡。”[10]2973-2974今張掖市甘州區有甘浚鄉。
此外,本文第一節所引道光《山丹縣志》例,謂龍首山一名“甘凌”,又名“甘峻”。今按“甘凌”實為“甘浚”之訛。乾隆《甘肅通志·山川》載:“甘浚山,在(山丹)縣西北三十里,延袤至甘州,一名甘峻山,俗名龍頭山。山陰有泉,旱可禱雨。”[11]220清許鳴磐《方輿考證》卷四十對此曾有討論:“《明統志》:‘甘凌山在山丹衛西北,連亙甘州,中有三石洞,其下有泉,歲旱于此取水,禱雨有應。’按其方位,正古甘竣山也。而《明統志》以為甘凌山,乃別載甘竣山于都司城西南八十里。《方輿紀要》因之并誤。”[12]據此可知,甘凌、甘浚實為一山,“凌”當為“浚(竣、峻)”的形訛。
五、番和③
番(pán)和,為漢代所置之縣。據《漢書·地理志下》,張掖郡轄縣十:觻得、昭武、刪丹、氐池、屋蘭、日勒、驪靬、番和、居延、顯美。其中番和為農都尉治。后世亦名番禾。《辭源》“番和”條釋義:“郡、縣、鎮名。漢番和縣,屬張掖郡。晉改番禾,屬武威郡。南北朝皆置番和郡。北周廢郡置鎮。唐天寶中改為天寶縣。”[16]2809
《廣韻·桓韻》薄官切:“縏,番和,縣名,在涼州。”按:此條有誤,脫漏了“縏”的釋義和“番”的字頭。余迺永改訂為:“縏,小囊。番,番和,縣名,在涼州。”[1]126是。
《集韻·桓韻》蒲官切:“番,番和,縣名,在張掖郡。”[2]310
《集韻》與《廣韻》對“番和”的轄屬關系表述不同,但也各有依據。《廣韻》依據的是當時的建置情況,《集韻》則重在存古溯源。從這一點看,《集韻》與《廣韻》的編輯原則有明顯不同。
關于番和為何要改名為番禾,我們暫未找到確切的理據,但關于唐代將番禾改名為天寶縣之事,《舊唐書·宣宗本紀》有如下記載:“三月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縣天寶山有醴泉涌出,嶺石化為瑞麰,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改番禾為天寶縣。”[17]218時在天寶年間,如此上言并更名,頗有諛上之嫌。
番禾,亦作蕃禾。《宋史·外國傳·吐蕃》:“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18]14155
六、麗靬
麗靬,即驪靬,漢代縣名。《說文·革部》:“靬,干革也。武威有麗靬縣。”[19]60《說文》中“麗靬”的寫法,在《廣韻》中未見承襲,但在《集韻》中則有之。《集韻·翰韻》墟旰切:“靬,《說文》:‘靬,干革也。武威有麗靬縣。’”[2]1142這種寫法在正史中亦有所見。《晉書·禿發利鹿孤載記》:“傉檀大悅,釋其縛,待之客禮。徙顯美、麗靬二千余戶而歸。”[20]3147
但在歷代典籍中多作“驪靬”,《廣韻》《集韻》亦有存錄。《廣韻·元韻》居言切:“靬,干革。又驪靬縣,在張掖。”[1]115《集韻·元韻》居言切:“靬,干革也。一曰驪靬,縣名,在張掖。”[2]281又《脂韻》陳尼切:“驪,驪靬,縣名,在張掖。”[2]93
據《集韻》“陳尼切”的注音,“驪靬”之“驪”當讀chí。《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驪”下均如此處理。但是此字為何有此讀音,令人疑惑。
其實關于“驪靬”的讀音,古今學者早有討論。《漢書·地理志下》張掖郡所轄縣“驪靬”下,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靬。”④顏師古曰:“驪音力遲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驪靬,疾言之曰力虔。”[13]1613岑仲勉先生認為:“讀驪如遲,必漢代西北方言如是。師古之力遲反,諒只就唐初音讀而為注,不能據以改正李音也。”[21]186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依從《集韻》(亦即信從李奇說),可以算是比較慎重的做法。但是從其異寫形式“麗靬”來看,我們認為顏師古之說更為可取,即仍如字讀“力遲反”(lí)。再者古人多認為“驪靬”與西域黎靬(又作犛靬)國亦即大秦國有關,如此則更可證明“驪”不讀chí。
又有作“轢德”者。清顧炎武《肇域志》卷四二:“觻得縣,《漢書》觻作鱳,又作轢德。在郡西九十一里。”[23]1527乾隆《甘肅通志·古跡一》載:“[觻得故城]《地理志》:張掖郡,故昆邪王地,太初元年開,治觻得縣。孟康曰:鱳音鹿。按:《漢書》觻作鱳,又作轢得。”[11]600
八、樂?
漢代酒泉郡有樂涫縣。《說文》:“涫,也。從水,官聲。酒泉有樂涫縣。”[19]235這一寫法后世廣有傳承。《廣韻·桓韻》古丸切:“涫,樂涫縣,在酒泉。”[1]125《集韻·桓韻》沽丸切:“涫,《說文》:‘也。酒泉有樂涫縣。’”[2]307清顧炎武《肇域志》卷四二:“樂涫縣,在衛西二百里,漢置。前涼改為建康郡,唐為軍,今名駱駝城,立高臺所。”[23]1527
但樂涫之“涫”,或亦訛作“?”。《廣韻》《集韻》均收錄有這一訛字。《廣韻·東韻》居戎切:“?,縣名,在酒泉。”余迺永校注:“《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有樂涫縣。涫字誤作?而有是音,當刪。”[1]25《集韻·東韻》居雄切:“?,縣名,在酒泉。”[2]27《漢語大字典》引方成珪《集韻考正》:“‘?’乃‘涫’之訛。前后《漢志》可證。此沿《篇韻》而失考也。”[24]1831
查古代史籍,確有將“樂涫”訛作“樂?”者。唐李林甫《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祿福縣]本漢樂?縣,屬敦煌郡。后魏太武帝平沮渠茂虔,改縣為戍,隸敦煌鎮。孝文帝改為樂?縣。”[25]對此,張駒賢所作考證以《漢書·地理志》為據,指出“?”為“涫”之誤。并說:“《廣韻》《集韻》兩名并收,殊少別擇。敦煌宜作酒泉,方與《地理志》合。”[26]1181由此可見,《廣韻》《集韻》所收“?”字,并非一個簡單的形誤之字,它也是有一定的文獻依據的。當然如果加以“別擇”,安排在“涫”字頭下作為異體,而不是按其聲旁“宮”收列于東韻,那樣會更為妥帖。
此外,“樂涫”還有寫作“濼涫”者。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二四:“唐于濼涫古城置福祿縣,蓋從《續志》名也。”[22]396“濼”系受“涫”感染而誤增“氵”旁。這種情況,是漢字俗字、訛字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九、燉煌
燉煌,亦作焞煌,今作敦煌。《說文·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19]224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發源注海”;“《漢書》云:‘燉煌本酒泉地,《春秋左傳》所謂允姓之戎所居瓜州也。發原獨至于海,故曰瀆。’”[27]213王筠《說文系傳校錄》認為大徐本作“焞”和“燉”是訛字:“大徐‘敦’訛‘焞’,本書引《漢書》又訛‘燉’。”[28]526其實這樣的寫法在歷代典籍中并不鮮見,不必視為訛字。如《漢書·張騫傳》:“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唐顏師古注:“祁連山以東,焞煌以西。”[13]2691-2692陳直先生在《漢書新證》中說:“敦煌在文獻記載及金石刻辭中,無作焞煌者(如《裴岑紀功碑》《曹全碑》,敦煌、居延兩木簡之類)。本文蓋為當時別體。”[29]322其中認為“敦煌”在文獻及碑刻中無作“焞煌”者,未免失之武斷,僅《說文》與《漢書》即可為其明證。
上述異寫也存錄于《廣韻》《集韻》中。《廣韻·魂韻》徒渾切:“燉,火熾。又燉煌郡,燉,大;煌,盛也。”[1]117“燉煌”之名在《廣韻》中凡12見,除此例以外,其他均見于姓氏及地名用字的釋義中。《集韻·魂韻》他昆切:“燉,火色也。一曰,燉煌,郡名。”[2]294又徒渾切:“敦,大也。一曰敦煌,郡名。”[2]296
《廣韻》與《集韻》二者比較,前者未見敦煌之名,而燉煌之名出現達12次;后者二名俱見,各有一例。前者對姓氏、地名注解比較詳細,而后者這方面內容極為簡略。可見《集韻》對《廣韻》雖有繼承,但在體例方面調整變化很大,對姓氏、地名等不再作詳細解釋。
以上我們對見于《廣韻》和《集韻》的九個地名異寫作了簡單考校。通過考校,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古代地名,異寫紛呈,有必要進行系聯比證。通過比證,可以解決音義方面的疑難問題,如通過“驪靬”與“麗靬”甚至“黎靬”的聯系,可知“驪”音chí之不可信。
第二,添加類化符號亦即累增意符是產生地名異寫的一個主要原因,如:弱—溺,黑—潶,番—蕃,樂—濼,敦—燉。其中后兩例,“樂”因“涫”而成“濼”,“敦”因“煌”而成“燉”,系受同詞另一音節字形感染而累加意符。
第三,《廣韻》與《集韻》雖然都是宋代官修韻書,后者比前者晚出三十年,但是二者之間在編輯體例上有明顯的差別。從本文所舉諸例來看,《廣韻》收列文字的形音義較為精要,所錄又音及異體較少,而《集韻》則務求賅廣,因此頗顯繁細。如“驪”,《集韻》收錄的又音“陳尼切”就不見于《廣韻》。《廣韻》對姓氏及地名用字,尤其是姓氏,注解過繁,顯得很不平衡;《集韻》克服了這一缺點。《廣韻》釋義多采取綜合概括的方法,而《集韻》釋義以《說文》為依據,保留故訓原貌,在文字訓詁方面更有參考價值。當然二者各有特點,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我們注意體會并合理利用。
本文曾于2019年10月在甘肅高臺參加駱駝城與五涼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交流討論,承蒙馮培紅教授、崔云勝教授等多位學者惠示高見,謹此致謝!文中仍有淺陋疏誤之處,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注釋:
①詳參下文“甘峻”節所引《甘肅通志》等。
②本節討論中所說的“樸”“撲”,古籍中實為“樸”“撲”。下文“麗”“驪”“濼”,古籍中實作“麗”“驪”“濼”等,恕不一一說明。
③本條討論的情況與其他各條不太相類。其他各例是見于《廣韻》《集韻》的地名“異寫”,而本條的“番和”是漢代所設縣名的正常寫法,“番禾”是后代所改之名,只有“蕃禾”是真正的“異寫”。但寬泛地說,也算一個地名的不同寫法,所以也放在這里一并討論。
④如淳所謂“音弓靬”,是說“靬”音“弓靬”(意為弓衣)之“靬”,而不是說“驪靬”讀作“弓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