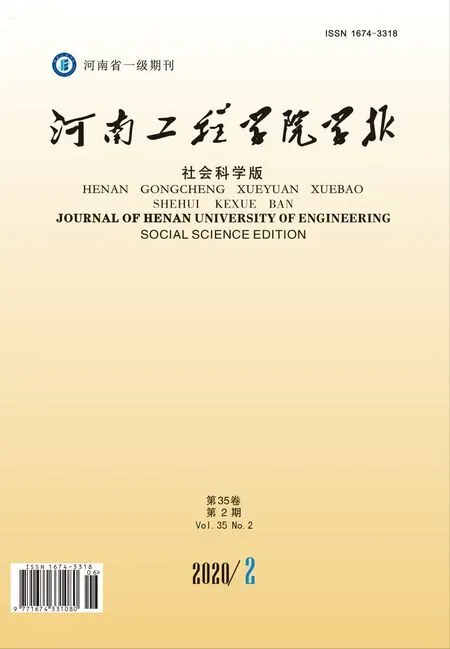金兆燕《旗亭記》中女性形象探析
王方好,黃文奇
(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
歷史上皖籍戲曲作家數量眾多,從元代的孟漢卿到明代的朱權、朱有墩、汪道昆、鄭之珍,再到清代的吳震生、龍燮、方成培、金兆燕、汪應培等,他們的作品至今流傳于世,對后世戲曲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清代的安徽全椒作為人文薈萃之地,戲曲創作十分發達,出現了一批戲曲創作的名家,其中以金兆燕最為突出。清代李斗的《揚州畫舫錄》贊其“工詩詞,尤精元人院曲”[1]。今人王長安主編的《安徽戲曲通史》一書給予金兆燕很高的評價,稱其“以唱和為樂,其文章,詩詞俱佳,尤擅度曲”[2]。金兆燕創作的戲曲作品諸多,其中以傳奇《旗亭記》和《嬰兒幻》兩部作品最為突出。有學者指出,“金兆燕詩、文、詞、曲皆長,成就最高的則是他的傳奇作品《旗亭記》”[3]。可見《旗亭記》在金兆燕整個戲曲作品中地位之突出。
目前,學界對于金兆燕及其戲曲的研究起步較晚,關于《旗亭記》的研究依然呈現碎片化的態勢。近些年,隨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全清戲曲》整理編纂及文獻研究”的開展,越來越多的高校學者開始關注金兆燕及其戲曲創作。目前,除了南京師范大學曹冰青的碩士論文《金兆燕及其戲曲研究》將金兆燕及其戲曲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其余碩博論文大多將金兆燕詩詞、交流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戲曲作品則是附帶提及。對于《旗亭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考辨、版本考述、創作主旨等方面,對于人物形象的研究,特別是女性人物形象的關注相對較為缺乏。因此,研究《旗亭記》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旗亭記》題材源流
歷史上有關“旗亭畫壁”這一故事最早記載于唐代薛用弱《集異記》中,但記載較為粗略,主要講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詩風日盛,詩人王之渙、王昌齡、高適在東都游學,他們互相傾慕對方,在雪天共赴旗亭小飲,其間聆聽歌妓唱詩畫壁的故事。《集異記》簡略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主要人物,其核心情節相對較為簡單,即“旗亭畫壁”,對于故事之中的歌妓、伶人的姓名,作者沒有提及。
《集異記》簡略的記載為后世的戲曲家提供了敷演故事的主要素材。明清兩代出現了多部根據“旗亭畫壁”創作的戲曲作品,有張龍文創作的雜劇《旗亭宴》、恒居士的雜劇《喝采獲名姬》、裘璉的雜劇《旗亭館》、唐英的雜劇《旗亭》及金兆燕的傳奇《旗亭記》。徐子方在《晚明雜劇六題》一文考證出明人恒居士的雜劇《喝采獲名姬》與清人唐英的雜劇《旗亭》都已散佚,僅存《旗亭宴》《旗亭館》與《旗亭記》三部作品。
雜劇《旗亭宴》收錄于明末清初鄒式金所輯的《雜劇三集》之中,作品開頭交代作者“掌霖張龍文著”,整部作品共兩折,主要敷演的是“旗亭畫壁”的故事。作品對主要角色進行了交代,比如生扮演王之渙、外扮演王昌齡、小生扮演高適、末扮演李龜年、旦扮演李十二娘、老旦扮演潘昭、貼扮演張云容等。整個故事情節較為簡單,就是“旗亭畫壁”三才子品評詩才的故事。在《旗亭宴》中,主要角色性格基本定型,為日后劇作家的再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但需要注意的是,張龍文雜劇《旗亭宴》屬于明代中后期興起的文人題材劇的一種,主要抒發文人內心的憤懣與不平。正如鄒式金在編輯《雜劇三集》時所說:“北曲南詞,如車舟各有所習……南詞調短而節緩,柔靡傾聽,難協絲弦;又全部宏編,意在搬演,不重修詞。臨川而外,佳者寥寥。不若雜劇足以極一時之致。”[4]這段話講述了文人偏愛雜劇的深層文化心理,雜劇更容易作為抒發個人情感的工具。在《旗亭宴》中,作者并沒有花太多的筆墨描寫生旦之間的愛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作為一種功能化的人物而存在,這與整個明代雜劇創作的大環境有關。
到了清代,這種創作風氣依然在延續。清初的戲曲家在進行戲曲創作過程中自然而然受到了明代文人雜劇的影響。裘璉創作的《旗亭館》是其雜劇集《四韻事》系列的一部,依然有著十分強烈的主體性。清康熙裘氏絳云居刻本《明翠湖亭四韻事四種》第四部《旗亭館》共三折,主要講述的依然是王之渙、高適、王昌齡三人旗亭賭詩的故事。相較于張龍文的《旗亭宴》,裘璉在《旗亭館》中增加了王之渙與歌妓之間的愛情這條線索。“這部雜劇只增加了一段兒女風情,將唱王之渙詩的歌妓定名于‘雙鬟’,傾慕王之渙的才名,一番相逢之后,兩人順理成章傾心鐘情,得高適襄助成其好事。”[5]清人裘璉在創作這個故事時將旦的姓名定為“雙鬟”,并且第一次增加了生旦之間的愛情故事線索。
金兆燕《旗亭記》共三十六出,是一部傳奇作品。傳奇鴻篇巨制的基本形式,使得《旗亭記》的故事情節更為豐富。金兆燕主要活動于清乾隆年間,這一時期的傳奇開始走向衰落,即戲曲史上傳奇創作的余勢期。這一時期傳奇創作具有明顯“詩文化”的特點,出現了大量宣揚教化的戲曲作品。而金兆燕的《旗亭記》則一舉打破了傳奇作品“道德化”的傾向,作者采用傳統的才子佳人故事作為故事的主要題材。《旗亭記》的核心情節是唐代詩人王之渙、王昌齡、高適三人旗亭沽酒聽歌妓唱詩畫壁,評判優勝的故事,在這個核心情節之外,又增加了一條線索,即王之渙與歌妓謝雙鬟的愛情線,且這條線索在整部作品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多位性格迥異的女性人物,旦扮演謝雙鬟,貼扮演雙鬟的母親張又華,丑扮演雙鬟的侍女翠筠,老旦扮演酒媼鄒氏、莫氏,兩個小旦分別扮演楊國忠的夫人裴氏與皇后張氏,這七個女性角色呈現出迥異多樣的人物形象。
二、《旗亭記》中的女性形象
金兆燕在《旗亭記》中一共塑造了七個有臺詞的女性角色,這七個女性角色的臺詞或多或少,她們在劇本和演出中的功能不盡相同。除旦角謝雙鬟之外,另外六個女性角色在文本中的功能主要有兩種。第一,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如酒媼鄒氏、莫氏,為后文生旦的相遇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又比如張又華,為生旦兩人的相識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第二,使劇場演出時的角色不再單調。如丫鬟翠筠、皇后張氏都是這樣一類人物。還有一類人物在劇本中不具有以上兩種功能性作用,是作者獨立刻畫的女性人物,如旦角謝雙鬟,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一)謝雙鬟形象的發展
早在唐代薛用弱的《集異記》中就已經出現了謝雙鬟這一形象的原型——一位吟詠王之渙詩詞的歌妓,文本沒有交代這一歌妓的姓名,僅僅對其外貌做了簡要介紹。
在張龍文的雜劇《旗亭宴》中出現了一位名叫李十二娘的歌妓,這一歌妓吟唱王之渙的詩詞,這便是后來戲曲作品之中謝雙鬟的最初形象。劇中的“李十二娘對于王之渙,也沒有什么仰慕之情,唱他的詩,純粹出之偶然;最后雖然借歌唱委婉地表明伶官生活凄清、孤單,羨慕日常百姓生活、青年男女雙宿雙飛,卻沒有產生追求幸福生活的強烈愿望”[6]。
如上所述,謝雙鬟這一形象的定名最早出現在裘璉的雜劇《旗亭館》中。通過細讀文本不難發現,雙鬟是一位生活在行院里的妓女,身份卑微,平時喜歡閱讀詩詞,不過始終處于被動的狀態,當其遇到心中的才子王之渙之后,并沒有能夠主動追求幸福,只是一味地感慨命運,最后高適出錢,令其伺候王之渙。裘璉筆下的雙鬟是一位可悲的煙花女子。
金兆燕《旗亭記》中旦扮演的謝雙鬟成為劇中十分重要的女性人物。《旗亭記》總共三十六出,謝雙鬟出場的有十七出,即第二出《曉妝》、第四出《教歌》、第五出《畫壁》、第六出《訂盟》、第十二出《勸逃》、第十四出《嘆月》、第十八出《謀遁》、第十九出《搜山》、第二十出《羈貞》、第二十四出《友說》、第二十五出《誅逆》、第二十七出《除孽》、第二十八出《清宮》、第三十一出《榮覲》、第三十三出《上頭》、第三十五出《合巹》、第三十六出《亭圓》。雖然謝雙鬟出場的次數不如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人出場的次數多,但其形象具有獨特意義。金兆燕的《旗亭記》開始以生、旦為主角,用了不少筆墨描繪王之渙和謝雙鬟的愛情故事,這條線索被作為主要線索加以呈現。作品細致描寫了王之渙、謝雙鬟從旗亭畫壁到私訂終身及得罪國舅后王之渙出逃、安史之亂謝雙鬟出逃被捕、制服奸賊、最終生旦團圓的悲歡離合的全過程。
(二)謝雙鬟——才貌雙全的“勇士”
1.雙鬟之才
謝雙鬟是金兆燕在《旗亭記》中塑造的最為成功的女性人物,作者在劇本之中多次描寫了謝雙鬟的才氣。謝雙鬟的才氣首先體現為詩書之才。第二出《曉妝》中的一段賓白:“奴家謝氏,長安人也,偶因愛梳了髻,因此名喚雙鬟。今年一十四歲,謫從仙侶……生小讀靈光之賦,最愛詞華,閑時效柳絮之篇,遂工吟詠。”[7]作為歌妓的雙鬟從小頗通詩詞,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日后與王之渙的相遇奠定了基礎。李龜年帶來了幾位名士的詩作,交給雙鬟閱讀。謝雙鬟仔細閱讀李龜年留下的詩集,從王楊盧駱讀到沈宋再到李白和杜甫,這一讀便讀到了王之渙的《涼州詞》,雙鬟徹底被王之渙的才氣吸引。第四出《教歌》一支《針線箱》曲子唱出了雙鬟對于王之渙的欣賞:“我知你,塊壘滿胸難寫酒杯兒。”[7]正是因為謝雙鬟如此精通詩書,所以才能夠慧眼識才,被王之渙的才氣所吸引。精通詩詞音律的謝雙鬟正是古代才女的典范。
除了詩書之才,謝雙鬟的才氣還表現為處世謀生之才。在不同的環境下,謝雙鬟總是能夠展示出自己過人的才能與智慧。在與王之渙訂盟之后,謝雙寰便將自己視為王之渙的妻子。第十二出《勸逃》中,李龜年匆匆忙忙過來告訴王之渙,楊國忠對其有殺意,勸其趕快逃難保命,王之渙希望以死表明忠心,謝雙鬟勸其萬萬不可。此時,作者刻畫了謝雙鬟在應對危機時候的鎮定與機智。謝雙鬟為王之渙清醒地分析了當時的局勢:“相公,此說大錯,那楊國忠勢焰熏天,既然囑托兩部弩人,相公一去,即成齏粉,還有你分辯的嗎?”[7]這段賓白充分展現出謝雙鬟具備處世謀生之才。賓白之后的曲子《南撲燈蛾》唱出了謝雙鬟又提出自己的想法:“依妾所言,唯有奔家鄉,藏匿待雞竿。”[7]正是在謝雙鬟的提議下,王之渙才成功逃脫。金兆燕的《旗亭記》對于謝雙鬟處世謀生之才的描寫主要集中在后半部分。安史之亂后,雙鬟與母親張又華、師傅李龜年、酒媼莫氏一起逃難謀生。與母親及師傅失散后,雙鬟與酒媼莫氏在路上遇到了楊國忠的妻子裴柔,三人在山上被捕,裴柔被殺,酒媼被放,安祿山被雙鬟的美貌所吸引,欲納雙鬟入后宮。謝雙鬟對安祿山的無恥行徑早已不滿,一直拒絕安祿山,安祿山讓李豬兒前來當說客,謝雙鬟再一次展示了自己的果敢才智,在第二十四出《友說》中,謝雙鬟將眼前的形勢分析給李豬兒聽,兩人商定計策,決定次日刺殺安祿山。第二十五出《誅逆》中謝雙鬟假裝前來謝恩,故意扶著安祿山進里屋休息,李豬兒按照之前設計的計劃,成功刺殺了安祿山,謝雙鬟又設計讓安慶緒繼位,最終成功將安祿山父子鏟除,自己也化險為夷。
金兆燕《旗亭記》中的謝雙鬟身上所展現的“才”是立體化與多方面的。這種“才”不僅僅表現在能夠作詩填詞唱曲這種文才上,更表現在能夠謀生、有膽略的武才上。
2.雙鬟之貌
金兆燕的《旗亭記》除了重點突出謝雙鬟的才智,對謝雙鬟容貌的描寫內容也占了很大比重。作者著重突出了雙鬟的美貌,將其作為重點刻畫的對象。在雙鬟美貌描寫上,作者多次采用“旁見側出筆法”,即互見法。這一手法是中國古典敘事文學寫人時經常采用的手法之一,早在漢代司馬遷《史記》之中便被使用。后世的小說家、戲曲家在進行人物描寫時,大多繼承了這一手法。有學者指出:“‘互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求得人物在本傳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確單一, 以便于評判,而這又與史官的撰述傳統相聯系。”[8]“旁見側出筆法”對于人物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在第四出《教歌》中,作者借用李豬兒的口對謝雙鬟的容貌進行了描寫:“好個標致女子,侄兒在主嫁下,教演那些擄掠的番漢女子,美貌的盡多,卻從沒見過像妹子的。”[7]從側面描寫出謝雙鬟的容貌之美。再如第六出《訂盟》中,作者又借王之渙的口對謝雙鬟的容貌進行了描繪:“我看此女風姿秀異,皎若天人,豈是風塵中物。”[7]第十九出《搜山》寫被哥舒翰等人搜到后,又通過崔乾佑的口再一次突出雙鬟之貌:“這個美貌女子,進到宮中必然寵眷。”[7]在金兆燕的《旗亭記》中,謝雙鬟的容貌成為重要的敘事媒介,對情節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正是謝雙鬟出色的美貌,才使得其有接近安祿山的機會,為其日后設計刺殺安祿山父子、剿滅安氏勢力起到了輔助作用。
3.雙鬟之勇
作者在作品之中除對謝雙鬟的才與貌進行細致的刻畫外,對謝雙鬟的“勇”也進行了十分深入的刻畫。劇中的謝雙鬟具有古代“俠女”所具備的精神特質。在唐傳奇作品中,出現了許多被后人稱贊的“俠女”形象。無論是裴铏的《聶隱娘》,還是袁郊的《紅線》、薛用弱的《賈人妻》、孫光憲的《荊十三娘》,作品中的“俠女”身上都有個共同的特質,即膽識過人、疾惡如仇,表現出灑脫豪邁、自由張揚的精神氣質。明清戲曲作品中出現了大量這種具有“俠女特質”的女性形象。金兆燕《旗亭記》中的謝雙鬟符合這一特質,作者花了很多的筆墨刻畫其英勇的一面。第二十出《羈貞》寫謝雙鬟與楊國忠的妻子裴柔一同被崔乾佑等人搜到,裴柔被處死,安祿山被謝雙鬟的美貌吸引,欲納其入后宮。面對安祿山的這一想法,謝雙鬟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今日已戴頸血而來,只求死后,埋我旗亭之側。”[7]將謝雙鬟的英勇初步展示在觀眾面前。在第二十五出《誅逆》中,李豬兒在刺殺安祿山的關鍵時刻畏畏縮縮,謝雙鬟便說道:“與你干大事,怎么這樣一筒膽兒。”[7]在謝雙鬟的謀劃下,兩人成功將安祿山制服,并且拿到安祿山的頭顱,將謝雙鬟作為女性的英勇充分刻畫了出來。第二十七出《除孽》中,又是謝雙鬟設計將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成功鏟除。金兆燕《旗亭記》筆下的謝雙鬟所具備的俠女特質成為其最為獨特的形象特征。
三、《旗亭記》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成因
金兆燕在《旗亭記》中刻畫了性格多樣、身份多樣的人物形象,其中刻畫最為詳盡的人物便是謝雙鬟。謝雙鬟作為劇作家著力刻畫的女性形象,其背后具有復雜的文化成因。
(一)“才女形象文人化”創作手法的影響
(二)符合當時社會的“教化”要求
郭英德將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719—1820年)的傳奇創作定位為傳奇的余勢期。[11]結合金兆燕的生平,金兆燕生于1718年,卒于1789年,整個創作活動大體上都是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處于清朝的中期,相對于清朝初期思想上的相對寬松,這一時期統治者加強了對民眾思想的監管。乾隆皇帝對程朱理學推崇備至,因此,“傳奇內容的道德化是這一時期的第一個特點”[11]。這一時期的傳奇作品大多以宣揚忠孝節義這些倫理作為主要內容,出現了夏綸、董榕、吳恒宣等一大批以宣揚倫理道德為題材的傳奇作家。金兆燕作為這一時期的作家,在傳奇的創作上自然而然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金兆燕的傳奇作品《旗亭記》雖然是以才子佳人為題材,但具有明顯的宣揚“忠君”與“堅貞”的思想。對于謝雙鬟,作者突出了其作為女性“堅貞”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宣揚女性的“忠貞”。“自送王郎別后,不覺又是新秋。我媽媽見王郎消息全無,便來勸奴改節,奴家誓死不從。”[7]第十四出《嘆月》表現出謝雙鬟作為女性的堅貞。第二十四出《友說》中,當得知安祿山想要納自己入其后宮時,她十分堅定地說:“倒不如留清白好見閻羅。”[7]并且告訴李豬兒,自己決定誓死遵守與王郎的誓言。謝雙鬟的堅貞與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女性觀相符合。此外,謝雙鬟展現出過人的膽識,通過自己的才智,成功將安祿山一黨殲滅,在很大程度上宣揚了正統的“忠君”觀念,安祿山這樣的叛賊自然而然會受到眾人的唾棄。
(三)清代中葉特殊的文人心理的展示
如上所述,清代中葉,隨著統治者對民眾思想控制的加深,出現了越來越多控制民眾思想的手段。一方面,清朝中期的文字獄手段更為嚴厲。根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 乾隆朝文字獄最多。[12]另一方面,隨著科舉考試手段的定型化,八股文成為文人讀書做官的唯一道路,許多文人窮其一生都在科場上顛簸。因此,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創作時借用古代“俠女”替天行道的行徑來抒發內心的憤懣。有學者指出:“理想型俠女嬗變模式以‘慧眼+婦德+英雄’為特點, 體現出明清文人實踐教化思想的積極探索, 即在和平歲月里, 女俠則回歸傳統女性特點。文人極力塑造俠女貌美如仙、女紅伶俐, 且有智慧才能, 即重點刻畫“慧眼+女德”;當自身有冤仇尤其是國難當頭時,女俠則一改柔弱本性, 要么手刃仇人、報仇雪恨,要么沖鋒陷陣、殺敵報國。”[13]金兆燕《旗亭記》筆下的謝雙鬟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俠女的特質,作品的后半部分,謝雙鬟依靠自己的才智與勇氣將造成國家動亂的奸賊鏟除。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文人知識分子極為復雜的心理狀態。
總之,金兆燕在《旗亭記》中為我們刻畫了性格多樣、身份多樣的女性人物形象。其中,最具內涵的便是謝雙鬟這一人物形象,這也是這部傳奇作品的最大閃光點。對于 《旗亭記》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其形象的發掘,而且有益于探索劇本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