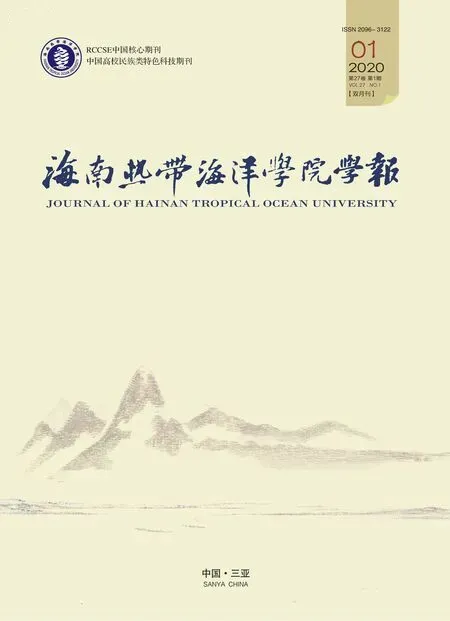六朝隋唐文學中的鯨魚意象談略
王 星,夏增民
(華中科技大學 歷史研究所,武漢430074)
引 言
學界關于鯨魚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鯨魚的自然屬性、文化意蘊和象征意義三個層次。其中,關于鯨魚生物學上(自然屬性)的研究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茲不過多贅述。文化史學者對古代鯨魚問題關注頗多,楊秀英及其碩士研究生沙大禹[1-3]曾對鯨魚的歷史稱謂、分布及其形象變遷做過系列研究,晏新志[4]、陳敏學[5]則從鯨魚與陰陽數術、災異感應的角度入手,考察了鯨魚在古代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相較于魚意象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成熟,學界對鯨魚意象的關注起步較晚,吳振華[6]《論韓愈詩歌的魚意象與釣魚詩的文化內涵》一文,是較早對韓愈詩中的鯨魚意象進行分析的文章,隨后龔慧蘭[7]《現世與理想的雙重關注—論李賀詩歌魚意象的深層含義》、田文青[8]《論唐詩中的魚意象》、余紅芳[9]《唐詩動物騎乘意象研究》等文均或多或少涉及唐詩中的鯨魚意象。然上述研究并不專門針對鯨魚意象,只是在各自研究內容之下偶有論及。系統考察唐詩中鯨魚意象的是景遐東、劉逸飛[10]《李白詩歌中的鯨意象及其影響》和張麗莎、路成文[11]《論唐宋詩中的鯨意象——以李白、杜甫、陸游詩為個案》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以李白、杜甫等詩人的鯨魚書寫切入,重點考察了鯨魚意象在詩人詩作中的占比情況,并進一步探討了鯨魚的具體象征意義。總體而言,學界關于鯨魚意象的專門研究還是較少,對鯨魚意象在中古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亦缺乏通融性的認知。鑒于此,將鯨魚意象放在中古文學(詩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系統梳理鯨魚意象的流變,重點考察流變過程中的關節時間、要素,及其與中古文學演進之關系,就顯得極其重要。
《莊子·內篇·逍遙游第一》有“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有幾千里也”句,崔撰(今可見《莊》注中最早的一家)云:“鯤,當為鯨。”[12]3其稍后的郭象釋“鯤”時則言:“鯤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12]3唐人成玄英[12]3疏該句時引用了東方朔的《十洲記》和郭璞的《玄中記》。《十洲記》和《玄中記》中所記的“大魚”與鯨類似,然“鯤”、“大魚”到底是否為鯨,已然成了一段學術公案。實際上,拋開《逍遙游》不論,從先秦至明清,鯨魚一直反復進入文本書寫之中,特別是中古時期[關于中古,歷來眾說不一。本文所言的中古,專指魏晉至隋唐這一歷史階段。當然,文中有些探討可能會推延到先秦秦漢及宋代,這視具體情況而定,當不全受“中古”拘泥。],其不僅成為文人筆下的一種典型意象,更參與塑造著時代文學的品性:鯨魚或被實寫,或被虛寫,在社會思潮轉關之際,敏銳地反映著文學走向,有時甚至成為滌蕩、扭轉前代文學風尚的“開山之斧”,在塑造新的審美范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 魏至盛唐鯨魚意象的演變
史書上有關鯨魚的記載,最早見之《左傳》,其卷十九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13]365杜預注曰:“鯨,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13]370鯨魚是“不義之人”的代名詞。《史記》卷六載始皇連弩射鯨事言:“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卜博士曰:水神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漁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14]263所謂“鯨,海大魚也”[15],始皇射殺的“巨魚”很可能就是鯨魚,此處“巨魚”也是邪惡的象征。秦漢以前,鯨魚基本以負面形象存在于時人的觀念之中,再如《淮南子》卷六所載:“晝隨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鯨魚“死于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16]鯨魚與彗星出沒同被人們看作是不祥的征兆。
(一)魏晉時期
就文學發展而言,魏晉是鯨魚書寫的第一個密集時期,此階段,鯨魚意象緊承先秦秦漢的典故、傳說,多以此指代亂臣賊子。與之相關,“斬鯨”亦自然成為袚除讒逆,標榜功業的象征。如漢末《魏鼓吹曲十二曲?其三》所歌:“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掌中。”[17]《宋書》釋此民歌的產生背景時言:“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18]644時人將呂布比作“鯨鯢”,曹操“芟夷鯨鯢”,故而“驅騁群雄”。類似的民歌還有《晉鼙舞歌五首·其三·景皇篇》云:“欽乃亡魂走,奔虜若云披。天恩赦有罪,東土放鯨鯢。”[18]631景黃帝即司馬師,此詩反映的乃是司馬師平定淮南二叛事。正元二年,鎮東將軍毌丘儉及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反魏,司馬師大敗叛軍,“亡魂”指在奔逃途中被射殺的毌丘儉,而文欽最終逃到了吳國,故此詩將其比作“東土鯨鯢”。
值得注意的是,鯨魚在漢代也被美化過,其幽潛海底的特性曾被用來象征隱逸、高潔的情懷。最為著名的,如賈誼《吊屈原賦》:“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19]“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于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于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20]3鯨魚與螻蟻對喻并非賈誼原創。《莊子·雜篇·第二十三》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12]772《文子·下》引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于螻蟻。”[21]《戰國策》卷二載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22]然而,春秋戰國時期,鯨魚與螻蟻的關系僅用來說明“勢”的某種變化,并不摻雜任何褒貶意義。賈誼借用鯨魚失水而為螻蟻所食的故事,賦予鯨魚高潔的品性,以失水之鯨自比,抒發自己謫貶長沙的怨憤之情。賈誼筆下,鯨魚具有了正面象征意義。王褒《九懷·其二·匡機》亦云:“鯨鱘兮幽潛,從蝦兮游渚。”這里“鯨鱘”指“大賢”,“從蝦”指“小人并進在朝廷也”[23]。遺憾的是,漢以后,鯨魚的正面形象并未出現過在魏晉時期的詩歌中。究其原因,如果我們將此種現象與屈原在漢代的遭遇聯系起來,則答案就不言自明。漢初,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稱贊屈原“蟬蛻濁污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24],司馬遷在《史記》中亦惋惜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14]2503。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特別是至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以后,儒家“詩教觀”得到了空前強化,班固在《離騷序》中就云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24]。揚雄雖然對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然亦批評其沒有做到“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揚累之蛾眉”[25]。與屈原一樣,賈誼在《吊屈原賦》中以鯨魚自比,實際上也是“露才揚己”,違背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故漢以降,自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以來,隱逸、高潔的鯨魚意象自然就被士大夫過濾出來。
(二)南北朝至隋唐初年
魏晉時期的鯨魚書寫并不成熟,這主要體現在:(1)與鯨魚相關的詩歌數量較少,沒有形成集群效應;(2)在這些詩歌中,鯨魚僅作為某種象征意義出現,大多是虛寫,無直接、專門的實在書寫;(3)鯨魚的象征意象單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詠昆明池詩大量出現,直接促使了鯨魚書寫在以上三個方面得到突破。
《史記》卷六載始皇“夜出逢盜蘭池”,張守節引《擴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筑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14]251始皇以后,皇家苑囿多有在池中“刻石為鯨”的習慣,如《三輔黃圖》載漢武帝時的昆明池“有豫章臺及石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26],又載“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鯨,魚長三丈”[26]。因昆明池始為武帝“修習水戰”而建,后又演變成帝王巡游的重要景觀,故其往往成為表現帝王功業、頌美盛世的重要象征。相應地,石鯨亦被后人反復摹寫。如梁朝劉孝威《奉和六月壬年應令詩》“雷奔石鯨動,水闊牽牛遙”[27]卷九十八、陳朝周弘正《詠石鯨應詔詩》“石鯨何壯麗,獨在天池陰”[28]、隋朝薛道衡《從駕天池應詔詩》“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鯨螭”[27]卷一百十八、唐初李世民《冬日臨昆明池》“石鯨分玉溜,劫燼隱平沙”[29]等。除了應詔詩多以石鯨起興,此時期,幾乎所有有關昆明池的詩作都會吟詠石鯨,再如梁朝戴皓《煌煌京洛行》“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28]卷四十二、陳朝江總《秋日游》“蟬噪金堤柳,鷺飲石鯨波”[28]卷九、隋朝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詩》“池鯨隱舊石,岸菊聚新金”[30]140。《初學記》中有“昆明池”條,在其所輯錄的詩歌中,“刻石”已成為固定的“事對”[30]149。《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石第八”下“魚”條亦有“昆明池刻石鯨魚,雷雨則鳴吼”[31]卷二,又“昆明池第五十”有“牛女石鯨”條:“漢武帝于池中置二石人相對,以像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每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31]卷二。《初學記》和《白氏六帖》均為唐人作詩查檢的常備書,“石鯨”作為穩定的“事對”被唐人所承認,也從側面說明了此前詠石鯨詩的繁榮。
南北朝至唐初出現的大量詠“石鯨”詩,表面上看描摹的對象是鯨的模型,但實際上,在這些詩作中,鯨魚的外形、特性以及相應的象征意義都得到了充分展現,因而至少是“想象的真實”。此外,此時期的“石鯨”擺脫了以往鯨魚意象的單一面孔,或被用來象征帝王氣象,或指代京洛華貴,或以石鯨寥落來抒發歷史興亡之慨,鯨魚的象征意義更加多元,這也為盛唐、中唐鯨魚意象地進一步發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盛唐時期
杜甫《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詩中有“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尾鯨”句。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三云:“劉禹錫詩:華茵織斗鯨,知唐時錦樣多織鯨也。”[32]唐人織錦多用鯨魚圖樣,蓋因“鯨魚起而魑魅走,高枕上風濤涌而形神清”[33]。從這個小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唐代,鯨魚與時人生活緊密相關。這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此時期的鯨魚書寫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意象表達的深度與廣度上,較南北朝時期均有巨大飛躍。由于此時期鯨魚書寫的詩作太多,為方便觀覽,我們茲統計書寫次數在六次及以上的詩人詩作,如附表所示。有唐一代,諸如“李杜”“韓柳”“元白”“皮陸”,幾乎所有大家文集中都有鯨魚的身影,特別是“李杜”二人,分別以書寫次數26和16次登頂鯨魚書寫的第一、二位。實際上,如果我們將統計標準下降至3次及以上,則張祜、皮日休、溫庭筠、陳陶等人亦會榜上有名,如果下降至2次及以上,則需要統計的詩人詩作將更數不勝數。不僅在數量上井噴式爆發,此時期的鯨魚意象也被時人系統、全面地挖掘出來。如李白《贈張相鎬二首·其二》[29]卷一百七十、杜甫《觀兵》[29]卷十八、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韻》[29]卷四百五十等詩繼承前代文學傳統,以鯨魚象征亂臣賊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29]卷二百二十四、元稹《胡旋女》[29]卷四百一十九、貫休《觀李翰林真二首·其一》[29]卷八百二十九等詩以鯨魚游泳跳躍的姿態象征人輕盈、瀟灑的體態;杜甫《戲為六絕句·其四》[29]卷二百二十七、《八哀詩·其五·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29]卷二百二十二、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29]卷二百四、韓愈《劉生詩》[29]卷三百三十九等詩以鯨魚象征雄健的筆力、險怪的文風。他如“掣鯨”“騎鯨”“鯨吸”“鯨吞”“鯨隔”“鯨牙”等亦已成為固定意象,被反復應用于詩歌之中。前文已述,賈誼在《吊屈原賦》中以鯨魚象征隱逸、高潔的情懷,而后人因儒家“詩教觀”的束縛,并未將其納入文學傳統之中。入唐以后,李白《雜曲歌辭·枯魚過河泣》“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反遭螻蟻噬”[29]卷二十六、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29]卷二百一十六、元稹《蟲豸詩》“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成。攻穿漏江海,噆食困蛟鯨”[29]卷三百九十九、白居易《寓意詩五首》“君為得風鵬,我為失水鯨”[29]卷四百二十五等詩都沿著鯨魚與螻蟻的典故進行了深入書寫。其中,杜、元、白三人詩中鯨魚的象征意義更是與賈文如出一轍,《杜工部草堂詩箋》釋“螻蟻”與“鯨魚”時即言:“螻蟻,物之微者,甫自喻鯨鯢,大魚偃蹇滄海,理之常也。甫志在于致君澤民,其志甚大。復自責我誠螻蟻小輩,但可自求其冗,何敢過擬大鯨而偃蹇于滄溟哉。”[34]其有意接續前代文學傳統的意圖十分明顯。唐人從文學書寫的現實需要出發,把鯨魚當作特定的意象進行生發、運用,連“鯨魚”與“螻蟻”這種長時間被摒棄在文學傳統之外的意象都可以被重新發掘,此時期鯨魚書寫的完美程度可見一斑。從某種意義上講,唐人頗有“為文學而文學”的意味。
二、 鯨魚意象與中晚唐險怪文風
詩歌發展到貞元、元和年間,風格多種多樣,流派層出不窮。其中,以韓愈、孟郊、賈島等人為代表的“韓孟詩派”,追求震蕩光怪、瘁索枯槁的審美境界,形成了崇尚險怪的創作傾向,對后世影響極大。如果我們從鯨魚書寫的角度去重新審視中晚唐文學,則會發現鯨魚意象是建構“韓孟詩派”險怪美學特征的核心意象之一,在塑造新的審美范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實不只是“韓孟詩派”,整個中晚唐均有追險求怪的詩歌創作風尚。
(一)“韓孟詩派”筆下的鯨魚意象
鯨魚首先大量出現在李白、杜甫的詩歌創作中,“韓孟”、“元白”、劉禹錫等人踵續前賢,繼有一眾關于鯨魚的詩作出現。中唐詩人筆下,鯨魚意象一方面繼承了盛唐的文學傳統,象征意義復雜多元。另一方面,鯨魚深潛海底、常人不易得見的生活習性,與中唐文學對險怪意象的渴求一拍即合。鯨魚對險怪文學的塑造,就集中體現在韓孟詩派詩人的詩歌創作中。
韓愈現存十四首鯨魚詩,韓氏筆下,鯨魚是營造怪奇刺戾意境的重要意象。如《劉生詩》“青鯨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29]卷四十八、《送無本師歸范陽》“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啖……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29]卷三百四十、《調張籍》“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29]卷三百四十。宋人文讜《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五釋《調張籍》詩曰:“以喻得二子(李杜)之奇怪刺戾也。”[35]。清人方世舉《韓昌黎編年箋注詩集》卷九同釋此詩云:“魏泰云:髙至于酌天漿,幽至至于拔鯨牙,其思頤深遠如此……‘拔鯨牙’,以喻沈雄汗漫。”[36]上引三首詩作,或可看作是韓氏的文論,韓氏“思頤深遠”,以鯨魚來形容他人(劉生、無本、張籍)“怪魅”“奸怪”的詩歌風格,其詩本身亦險怪起來。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即將《調張籍》詩與《送無本師歸范陽》相聯系,認為韓氏能將險怪意境描摹得如此純熟,“蓋作文以氣為主也”[37]。除了韓愈,孟郊也作有兩首《戲贈無本》詩,其一云:“文章杳無底,斸掘誰能根……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為吞。”[29]卷三百七十七“拾月鯨口”既用來形容無本險怪的文學創作風格,又同時營造出孟詩怪奇刺戾的意境。
“韓孟詩派”詩人借鯨魚意象來營造光怪枯槁的審美境界,還集中體現在他們的聯句詩中。如《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29]卷七百九十一、《會合聯句》“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疏冗”[29]卷七百九十一、《遠游聯句》“觀怪忽蕩漾,叩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29]卷七百九十一。《城南聯句》為韓愈與孟郊共同創作,《會合聯句》為韓愈、孟郊、張籍及張徹等人共同創作,《遠游聯句》為韓愈、孟郊及李翱共同創作。“恣韻激天鯨”“狂鯨時孤軒”“海鯨吞明月”應分別指詩歌創作中的聲律、意象和構思等問題。“激天鯨”當指詩律的不求法度。《爾雅翼》云:“蒲牢者,大聲如鐘,而性畏鯨魚,食于海畔,鯨魚或躍,蒲牢輒鳴,故鑄鐘欲聲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斫撞為鯨形。”[38]鯨魚在古代,常與聲音相聯系。結合上下文來看,《遠游聯句》中的“狂鯨”和“虎豹”“蛟鼉”“幽狖”等動物一致,均是險怪意象的鋪排;“觀怪”“叩奇”所言正是詩歌創作中觀覽、構思的過程,所謂“海鯨吞明月”與“思壯鯨跳渤澥寬”大致相同,當指作文構思之敏捷、想象之跳躍。聯句詩體現的是一群人的詩歌創作追求,“韓孟詩派”詩人多次以鯨魚入詩,且鯨魚意象指向怪奇審美趣味的象征意義明確、集中。
(二)“韓孟詩派”以外的鯨魚“書異”
元稹被貶通州期間,曾作《書異》一詩,全文如下:
孟冬初寒月,渚澤蒲尚青。飄蕭北風起,皓雪紛滿庭。行過冬至后,凍閉萬物零。奔渾馳暴雨,驟鼓轟雷霆。傳云不終日,通宵曾莫停。瘴云愁拂地,急溜疑注瓶。洶涌潢潦濁,噴薄鯨鯢腥。跳趫井蛙喜,突兀水怪形。飛蚋奔不死,修蛇蟄再醒。應龍非時出,無乃歲不寧。吾聞陰陽戶,啟閉各有扃。后時無肅殺,廢職乃玄冥。座配五天帝,薦用百品珍。權為祝融奪,神其焉得靈。春秋雷電異,則必書諸經。仲冬雷雨苦,愿省蒙蔽刑。[40]
元稹作為土生土長的北方人,難以習慣南方氣候,此詩展現的全是讓元氏感到驚異的氣候現象。元氏用“噴薄鯨鯢腥”來形容當地雨水腥臊的氣味,“鯨鯢之腥”與“澤蒲尚青”“皓雪滿庭”“水狀怪形”等現象一道,成為其表達“異”的一種重要意象。此詩無論在情感抒發還是在書寫策略上,均與曹植《盤石篇》如出一轍。《盤石篇》作于黃初四年(223),曹氏遷雍丘之時,全詩圍繞“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海東?”展開,運用大量筆墨來渲染“太山人”至“海東”的種種不適:“蒹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云霄,浮氣象螭龍。鯨脊若丘陵,須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戲中鴻。”[27]卷二十七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六評此詩即言:“起四句一篇之意已出,后乃極力寫之,‘蒹葭’以下,其地之物則如此……我獨何為而在此地乎?不極寫,令荒異感之懷不盡欲。”[41]曹詩異域書寫中,鯨魚亦占據大部分篇幅。元氏之詩是否受到曹氏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然可以明見的是,用鯨魚來營造荒異怪奇的審美體驗,在魏晉時期已經發軔,這或許是中唐險怪文風的淵源。回到元稹詩歌上,除《書異》以外,其另有十四首詩用到鯨魚意象,其中,在《有酒十章·其四》“幽妖倏忽兮水怪族形,黿鼉岸走兮海若斗鯨”[29]卷四百二十、《有酒十章·其八》“鯨歸穴兮渤溢,鰲載山兮低昂……顧千珍與萬怪兮,皆委潤而深藏”[29]卷四百二十中,鯨魚均是參與營造險怪意境的重要意象。
如果說元稹是“韓孟詩派”以外,中唐詩人中借鯨魚意象“書異”的典型,那么陸龜蒙則是晚唐詩人的代表。陸氏有六首詩歌用到鯨魚意象,其《奉和襲美古杉三十韻》一詩將炫彩夸博的工夫發揮到了極致。“虎搏應難動,雕蹲不敢遲。戰鋒新缺齾,燒岸黑黑茲黧。斗死龍骸雜,爭奔鹿角差。肢(一作胈)銷洪水腦,棱聳梵天眉。磔索珊瑚涌,森嚴獬豸窺。向空分犖指,沖浪出鯨鬐。”[29]卷六百二十三陸氏用“向空分犖指,沖浪出鯨鬐”來形容古杉直插青天的支脈,視角不可謂不奇特。從“虎搏”“雕蹲”“缺齾”“黑茲黧”“龍骸雜”及“鹿角差”等意象的運用上,我們亦不難看出陸氏求奇求異的創作傾向。關于陸氏對險怪文風的認可與追求,其在《記事》詩中說得很清楚:“雖然營衛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粗言環怪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披落雜唱。”[29]卷六百十九“粗言環怪狀”“文律”“鯨牙”等字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韓愈的《調張籍》《城南聯句》等詩,“粗言怪狀”使得陸氏“精神王”,可見在對險怪文風的追求上,陸氏與韓孟等人并無二差。
除元稹和陸龜蒙,中晚唐詩歌中借鯨魚意象來營造險怪審美意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陳陶《喜符郎詩有天縱》“海鯨始生尾,試擺蓬壺渦。幸當禁止之,勿使恣狂懷”[29]卷三百八十、章孝標《覽楊校書文卷》“情高鶴立昆侖峭,思壯鯨跳渤澥寬”[29]卷五百六。杜牧在《李賀集·序》中評價李賀詩歌時亦云:“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42]中晚唐詩人如此熱衷通過鯨魚意象來表達對險怪審美趣味的追求,以致后人在談到鯨魚時多將其與“奇”“怪”相聯系,如《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詩病門”:“王靖學蘇子美作壯語曰‘欲往海上吞鯨鯢’,又近有士人好為怪語。”[43]再如《四溟詩話》卷三在論述詩歌的幾種風格時,亦專有“奇絕如鯨波蜃氣”[44]類,來形容突兀怪奇的詩歌。
如果說初、盛唐是詩歌定型、輝煌的時代,那么中晚唐則是詩歌創新、變革的時代。我們認為整個中晚唐均有追險求怪的詩歌創作風尚,并不是指每位詩人都認同險怪的審美趣味,亦不是指中晚唐每個小時間段都有進行險怪文學創作的詩人,我們想強調的是:鯨魚是塑造險怪文學的核心意象,它不光出現在“韓孟詩派”詩人的詩作中,也同時大量出現在此時期其他詩人的詩作中。中晚唐時期鯨魚意象被廣泛認可和接受,實質上反映的正是對險怪審美趣味的追求,是此時期頗為風靡的詩歌創作現象。
三、 杜甫文學批評中的鯨魚意象
盛唐是鯨魚意象蓬勃發展時期,此階段,鯨魚復雜多元的象征意義不僅為塑造中晚唐險怪文風埋下了伏筆,同時,其亦開始染指文學批評。至宋代,鯨魚已成為古典文論的一個重要理論范疇。
杜甫最早將鯨魚引入文學批評,其《戲為六絕句·其四》云:“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錢謙益《草堂詩箋》云:“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為六絕句》,蓋寓言以自況也。”[46]406杜氏題雖為“戲”,用心卻十分嚴肅認真。關于此詩批評的文學現象及鯨魚所指稱的具體內涵,歷來注杜者皆有言明,宋人魯訔編次,蔡夢弼箋校《杜工部草堂詩箋》補遺卷一云:
以翡翠喻,言今之為文者只得其小巧耳。郭璞游仙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異物志》:赤而雄曰翡,青而?曰翠。‘未掣鯨魚碧海中’,言為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鯨魚之掣浪也。[47]
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二云:
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趙云:此兩句言數公者不過文采華麗而已,而公所自負其出群雄者,如掣鯨魚于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48]
黃希《補注杜詩》卷二十二云:
趙曰:“郭景純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輝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未掣鯨魚碧海中”,洙曰:“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49]9
“翡翠蘭苕”是從辭章角度出發,言詩歌“文采華麗”,諸家均無異義。“鯨魚碧海”,蔡氏認為當形容“文之雄健”,郭氏、趙氏則認為此乃指稱作詩者“氣力之雄”,鯨魚的意義指向似乎并不明確。清代學者基本承襲宋人看法,但亦有所創見。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十云:“蘭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匯萬狀,兼古人之所有之。亦退之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46]1851。錢氏在宋人基礎上,對“翡翠蘭苕”與“鯨魚碧海”的認識都有所突破,“翡翠蘭苕”除指辭章華麗以外,亦指當時“研揣聲病”的習氣,“研揣聲病”是詩歌聲律上問題。“鯨魚碧海”除指“渾涵汪洋,千匯萬狀”的詩歌面貌,還多了一層險怪意義在其中。仇兆鰲《杜詩詳注》與浦起龍《讀杜心解》對“鯨魚碧海”的解釋基本因襲郭氏和趙氏,“鯨魚碧海”指“鋸力驚人”,“鋸力驚人”正與作詩者“氣力之雄”同。宋人從文章風格與詩人才力兩個角度去闡釋“鯨魚碧海”,表面上看似有分歧,其實二者相互融貫。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即云:“夫翚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50]作詩者氣力博大,文章自會呈現出雄健剛猛的風格面貌,所以“鯨魚碧海”的意義指向是明確的。至于錢謙益所言“鯨魚碧海”兼有險怪意義,當是“過度闡釋”:此組詩是借古諷今,杜甫對“鯨魚碧海”明顯持贊揚態度,六朝時期安有以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為美的風尚呢?
除《戲為六絕句·其四》,鯨魚作為文學批評術語還多次在杜甫的其他詩作中。如《八哀詩·其五·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歘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埽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遰。[45]200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二十四釋“鯤鯨噴迢遰”云:“喻邕詩之雄健也。”[47]764《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四云:“鯤鯨,取其勢之強壯。”[48]210《補注杜詩》引顏師古云:“鯤鯨,喻其雄健。”[49]11杜甫“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盈川即楊炯,特進即李嶠。愛楊炯之雄,不愛李嶠之麗,正與“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所傳達出的文學指趣異曲同工。又如《贈翰林張四學士》:“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29]卷二百二十四張四學士即張說第四子張垍,“鯨力破滄溟”有言“此喻張翰林才力之健也”[47]338,亦有言“其勢大”[32]45。“才健”“勢大”亦與“鯨魚碧海”“鯤鯨”的指稱意義大同小異。再如《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29]卷二百二十(此詩與《贈翰林張四學士》同,茲不贅言)杜甫筆下,鯨魚用來象征雄勁剛健的詩歌風格(或才力博大的詩人),指稱意義明確且集中。晚唐釋齊己《風騷旨格》中有“詩有十勢”,其一即云:“鯨吞巨海勢,詩云: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51]又明人謝天瑞評唐人詩曰:“李杜韓三公詩如金鳷摩海、香象渡河,龍吼虎哮、濤翻鯨躍,長槍大刃、君王親征,氣象自別。”[52]“鯨吞巨海”與“濤翻鯨躍”代表的均是氣力博大之詩,鯨魚意象頻繁用于文學批評中,儼然已成為中古文論的重要理論范疇。
齊梁文學綺麗艷靡,對文學獨立自是一件好事,然時至盛唐,六朝駢麗習氣仍然籠罩詩壇,這就嚴重了妨害文學的長遠發展。杜甫以鯨魚作喻,樹立雄勁剛健的審美范式,鯨魚意象對括廓清駢儷文風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杜甫巨大的文化影響力,后人常將“登鯨海”“掣鯨”等所象征的雄健筆力與文學書寫的真諦相聯系,如陳陶《贈江南從事張侍郎》“幾處談天致云雨,早時文海得鯨鰲”[29]卷七百四十六、宋人王炎《用元韻答蔣簿》“詩來驚老眼,筆力掣鯨魚”[53]、王洋《再賦前韻五首·其二》“子美才高不自期,卻言蘇李是吾師。若人欲逞蘭苕句,試掣鯨魚與對治”[54]、劉才邵《贈劉升卿》“方知掣鯨手,不足臨淵羨”[55]、劉克莊《竹溪生日二首·其一》“兩翁雖老殊精悍,筆力縱橫可掣鯨”[56]、陸游《睡起》“白頭漫倚詩豪在,手掣鯨魚意未平”[57]等皆是此意。
杜甫將鯨魚意象引入文學批評,是對中古文論的重要理論貢獻。杜甫以后,經后人反復闡釋,鯨魚意象的內涵進一步擴大,其除用來象征雄勁剛健的詩歌風格外,還多了一層風雅意蘊。杜牧最早將鯨魚意象與風雅傳統相聯系,其《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云:“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29]卷五百二十一“鯨海動”即找到了詩歌創作秘旨,杜氏認為,李杜上承“風騷”“風騷”正是杜甫詩歌價值所在。陸游《雨霰作雪不成大風散云月色皎然》亦云:“安得人間掣鯨手,共提筆陣法莊騷。”[57]卷四十九前文已述,“掣鯨”常被用來形容詩歌創作真諦,“掣鯨”與“莊騷”并提,鯨魚意象實際被納入文學正統中來。關于鯨魚意象與風雅傳統之關系,宋人詩話表述得很清楚,阮閱《詩話總龜·百家后集》卷之十二言:“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43]卷二十八太白詩的源頭在《大雅》,少陵詩的源頭在《離騷》,這正與杜牧等人的看法一致。
結 語
“鯨魚在古代就分享著海洋的激進、神秘、歧義的他者性,象征著神圣的力量,無論其懷有善意還是充滿威脅。”[58]古人海洋知識匱乏,對鯨魚的認識模糊錯亂,不僅是歷史時期,即使同一時期,人們對其的看法也千差萬別。可以說,中古時期,人們對鯨魚的認識是真實與想象摻半,鯨魚書寫往往并不出于生活經驗,而是來自前人記憶與時代思潮的雜糅。我們考察鯨魚意象的歷史演化,實際是在探索中古文學書寫方式的歷史演化。魏晉時期的鯨魚書寫零零散散,鯨魚的象征意義單薄且單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詠昆明池詩的大量出現,使得鯨魚書寫的數量陡增,相應的,此時期鯨魚意象的象征意義亦開始變得多樣化,這為盛、中唐鯨魚意象的進一步發散打下了良好基礎。盛唐時期,鯨魚全面進入文人視域之中,不但此前有關鯨魚書寫的文學傳統被毫無保留地挖掘出來,同時,鯨魚意象的內涵也更加廓大,變得復雜多元。中唐時期,鯨魚被文人有意識地引入詩歌創作中,成為塑造震蕩光怪、瘁索枯槁文學風格的核心意象,這對中晚唐文學的定型、發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鯨魚對中古文學的滲入不僅體現在其自身的書寫形態上,更體現在以鯨魚來言說其他:鯨魚意象被納入中古文論的理論范疇之中,這本身即標識著其得到了文人的認可,鯨魚意象名正言順地參與著中古文學的建構。總而言之,鯨魚意象從文學塑造再到塑造文學,久遠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古文學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