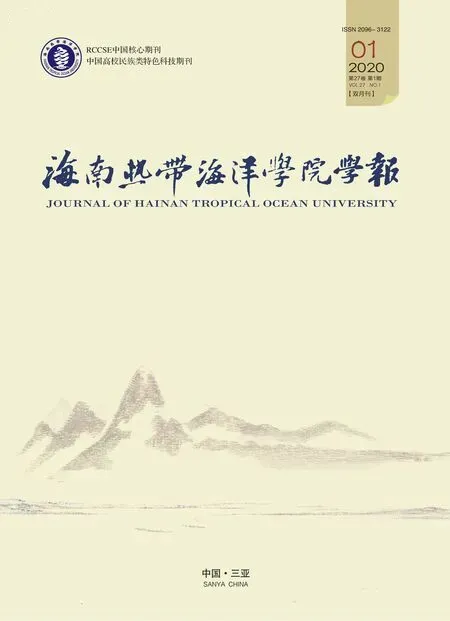論英國對南沙群島主權歸屬認知的轉變(1930—1980)
趙沁雨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南京 210023)
縱觀世界歷史,國家間領土主權的爭端始終是國際沖突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二戰以來,以國際法為武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趨勢。20世紀30年代后隨著法國占領南沙九小島和日本加緊對南海島礁的侵占,南沙群島主權紛爭逐步公開化。從此以后,這一主權爭端便始終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神經。英國作為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大國也曾積極參與到南沙爭端之中。起初他曾試圖運用國際法相關原則,尋找歷史及法理依據,以增強自身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主權聲明的效力。但是二戰后,隨著其在東南亞殖民勢力的瓦解,英國對群島主權歸屬的認知產生顯著轉變。由于國際法院在審理領土爭端問題時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傳統,因而英國方面對領土爭端的觀點,對我國維權存在較大的參考價值。
對于英國在南海島嶼爭端中扮演的角色問題,國外學界已運用一系列檔案進行深入研究[1-3]。而國內學界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英國南海政策上[4-6]。基于此,本文將從國際法角度梳理英國對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觀念的轉變,分析英國視角下獲取島嶼主權的關鍵因素,為我國維護南沙群島主權提供借鑒。
一、 國際法上領土主權取得的幾種方式
領土主權在國際法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英國法學家羅伯特·詹寧斯[7]曾指出,傳統國際法的任務和目標便是以地域為基礎劃分各國行使主權權力的界限。任何國家均不得在他國領土內行使本國的主權。而時代變遷并未削減領土的重要意義,事實上當前領土爭端已成為國際社會中較為敏感的問題,極易引發國際沖突。因而解決領土爭端成為國際法的重要任務之一。針對此種情況目前解決爭端的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通過談判制定條約,二是通過提交仲裁或國際司法程序。這兩種方式的執行據需要依靠國際法規定的一般原則。
國際法承認領土取得有5種方式。我國著名的國際法專家周鯁生[8]將其翻譯為先占(Occupation)、時效(Prescription)、添附(Accession)、割讓(Cession)和征服(Subjugation)。20世紀后,其中一些方式已被時代拋棄。目前,先占和時效這兩項原則仍被多次被討論。而相較而言,“先占”獲得的公認度更高。
先占也稱占領,一般而言指某國有意識地獲取當時不在其他國家主權之下的土地,使其成為本國領土的一部分,并對其行使主權。先占規則的完成需要兩個條件:首先,占領的客體必須是無主地,即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無人居住的土地。其次是有效的占領,這意味著僅僅發現無主地僅能獲取“初步權利”,這種“初步權利”只能在一定時間內阻止他國對該地進行再次占領。土地的占領國只有在此后一段時間內完成實際的、有效的控制才能取得主權。而所謂的“有效控制”意味著:其一,先占國必須明確將某個無主地置于其主權之下,為此該國需要對此舉動進行公開聲明;其二,先占國在無主地上實行有效的占領和管理,并要求這種主權的行使在發生爭端時能保持[9]。
然而,這一有效控制的概念也是隨著歷史發展而演變,其含義并非絕對。著名國際法學者奧本海(Oppenheim)便曾指出:“現在,占有和行政管理是使占領有效的兩個條件。但在從前,這兩個條件并不認為是用占領方法取得領土所必要的……直到18世紀,國際法才要求有效占領;直到19世紀,多國實踐才與這種規定相符合。”[10]在1928年美、荷雙方關于帕爾馬斯群島的爭端中,國際仲裁法院闡述了“對行使領土主權的持續、和平的顯示,與權利一樣重要的觀點”[11],從而確認“有效控制”規則的重要性。不過在近一個世紀的實踐之中,這一原則的應用并不穩定,這是因為各國對其規則的基本含義并不存在統一的認識。其主要體現在各國對“出示何種類型的證據可以被認為是符合有效控制”這一問題的爭論,而一般常見的證據包括行政管理、巡航、公共設施建設等[12]。
當前世界已不存在無主地,因而先占的方式已經失去現實意義。正如周鯁生[8]469所言,先占規則完全是從殖民國家爭奪土地的便利出發的一種政治安排。殖民者所做的規定亦是歷史的產物,不能將其視作從古至今永恒的鐵律。這是當前國際法上討論先占方式必須確定的前提。不過,鑒于當前大部分國家的領土是通過先占方式取得,因而在國際上領土爭端中運用有效控制原則始終是國際法院進行裁決的關鍵。該原則在討論南沙群島主權爭端問題時也曾得到多位法律學者的闡釋。
時效方式指一國占有他國某塊土地后,在長時間內不受干擾地占有,進而取得土地的主權。而時效得以適用也需要滿足幾項條件:其一是這一占領行為并未受到他國的抗議與反對,或他國的反對已經停止。其二則是這一占有持續一定時間。不過,由于時效原則在實際個案中往往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利用它解決領土爭端的情形在國際法庭的歷史上極為少見。
從上述解決領土爭端的方案中可以發現,在關于領土取得的法律理論與實踐中,歷史依據與法律依據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當國家間產生領土爭端之時,國際法庭總是先用大量篇幅對事件的歷史發展進程進行描述,并分析爭端雙方歷史論據的真實性與客觀性。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曾提及歷史性權原(Historic Titles),以此說明國家基于歷史性的證據可以使其取得部分既得利益,從而構成歷史性權原。因此領土爭端的解決應從歷史的演變看事實的、持續有效的占有,以考察其包含的國際法意義[13]。
目前為止,已有大量考古發現及史料記載證明中國最先發現南海諸島,并通過千年來“長期持續和平地占有”[14],獲取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利。中國方面所提供的大量史料不應被人為地忽略。不過,自20世紀30年代南沙島嶼爭端激化以來,西方部分國家曾多次不顧國際法的慣例要求,刻意忽視中國千百年來發現、管理南沙島嶼的基本史實,試圖以此達到削弱中方主權效力的目的。由于國際法院在審理領土爭端問題時“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傳統”[15],因而英國方面對領土爭端的觀點便有了較大的參考價值。
二、 20世紀30年代英國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歸屬的考察
自20世紀30年代起至70年代末,每當南海地區爆發島嶼爭端時,英國外交部均會咨詢相關法律顧問,對島嶼爭端的由來及發展進行回顧,判斷究竟哪一方的主權聲明在國際法層面更為有力。而相關法律人士則主要通過“有效控制”的原則來判斷島嶼主權的歸屬。不過,隨著時代發展,英國對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的認知與態度有了重大的轉變。
20世紀30年代,英國在遠東仍存在廣泛利益,其殖民地遍布東南亞,香港至新加坡的重要航線恰好途經南海諸島。自20世紀30年代初至二戰爆發前,在英國對南沙群島主權的基本認知中,英國自身與法國才是南沙主權的主要競爭者,而英方在討論中較少關注中方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南沙問題中只著眼于與其存在密切關聯的南威島及安波沙洲。
20世紀30年代的南沙爭端起于法國妄圖占領南沙部分島礁一事。1930年4月英國駐香港領事告知外交部,稱法國決定占領南沙群島,并對其宣示主權。因法國所圖謀的島嶼包括與英國存在密切聯系的南威島及安波沙洲,英國外交部急令駐法大使同法方進行交涉,稱:
英國人詹姆斯(H.G. James)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及美國人格拉漢姆(George Frank Graham)曾于1877年向納閩殖民地登記,將南威島及安波沙洲列為英國領地。此事曾得到英國外交部的許可。不過由于兩座島嶼位于納閩殖民地領土范圍以外,因此英國政府建議三人在婆羅洲總領事處登記這兩座島,并在島上豎立英國國旗,由英王頒布許可證。于是,在英國放棄之前,這兩座島礁屬于英國領土。[16]
由此可見,在面對法國的挑戰時,英國最先想到的方法便是通過“先占”原則來維護其主權要求。而法國外交部經研究后則認為1877年詹姆斯等人的行為在法理上僅屬于私人行為,這并不意味兩座島嶼屬于英國。更為重要的是,法方認為英國并未將島嶼納入海峽殖民地或香港的管轄范圍,因而無法說明英國對島嶼進行了管理[17]69。當時的國際法認為,發現只是領土主權產生過程的一個步驟,它只能創造初始權源,而要使權源變得完整,一國需要對其進行有效占領[18]。
對此,英國外交部也意識到若要獲得島嶼的主權,根據國際法必須對其進行有效占領。具體而言,英方應尋找證據證明自己曾在行政上將上述二島納入英國殖民地管轄。英國外交部于5月12日在交付殖民部的信函中承認詹姆斯等人向納閩殖民地登記的行為“不能被視作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納入英國殖民地”,“雖將島嶼名稱列入《殖民地名錄》,但此舉亦無法證明對島嶼進行實際管轄和占領”[19]。
外交部法律顧問為理清南沙問題的主權歸屬,翻閱當時相關島嶼爭端的判例,于1931年11月出臺一份相關報告,認為:“英國是否擁有兩島主權取決于以下兩個問題:首先,英國是否通過占領的方式獲取了兩島的主權;其次,若之前的條件成立,則英國是否在1930年前由于未能持續占領島嶼而喪失主權權利。”[16]在英國法律顧問看來,這兩座島嶼應屬于無主之地,而為了獲取這類土地的主權,必須采取某種形式的兼并及確認“實際所有權”(physical appropriation)的行為。而1877年英國人的登記行為可視作“實際所有”的行為。但不管如何,英國在此之后始終未對島嶼進行有效控制和管轄,這被視作英國主權聲明在國際法層面的主要缺陷。而此后英國也主要依據“有效控制”的原則對其他國家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聲明提出質疑。
為謹慎起見,英國外交部同時也征詢了國王的法律官員(Law Officers of the Crown)的意見。國王的法律官員在經過詳細研究后于1932年7月末致函外交部,認為英國的主權聲明存疑,若想國際仲裁法院提起訴訟,其結果不容樂觀[17]73。這是因為由于缺少事實上的占領及其他公開展示國家權力的行為,不能僅憑1877—1879年以來的一系列行動便認為英國獲取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主權的“初步權利”[20]。依據當時的國際法,“初步權利”僅在一段時間內存在效力,若一國未能在此時間內完成對領土的占領,則“初步權利”會失效。英國法律人員認為英方在19世紀70年代后并未對南沙兩島嶼進行“有效占領”,這便使英方喪失了“初步權利”,由此也說明英國并未獲取島嶼的主權。此外,在20世紀30年代的南海島嶼爭端中,英國主要同法國展開外交溝通,卻未就此事與中國進行接觸[17]56。
由此可知,在這一時期,英國無視中國先民在南沙海域長期勞動作息的歷史,將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稱為無主地,認為是西方航海家最先發現這些島嶼。英國雖然通過發現,及豎立國旗等一系列行為獲取對島嶼的“初步權利”,但其后并未采取進一步手段對其進行有效管理。如此一來,英國關于這些島嶼的主權聲明在國際法層面便不具備法律效力。
由于自身在主權聲明中的局限性,經過評估后,英方仍然偏向于對法方妥協。但這并不意味英國政府承認法國方面的主權聲明,相反,英國并未放棄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的主權。外交部曾指出,除非國際仲裁法庭有所宣判,否則英國政府將不對南海島嶼主權歸屬問題做出任何公開聲明。
三、 戰后英國對南沙島嶼主權歸屬認知的轉變
戰后初期至50年代中葉,隨著東亞、東南亞局勢的變化,英國在東亞及東南亞勢力日漸式微,但其仍對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保持較高的關注度。而這一時期它對于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的認知較戰前發生明顯變化,這主要體出英方關注中國出示的歷史性證據。
1955年7月,英國外交部東南亞司的官員薩瑟蘭(I.J.J.Sutherland)[21]撰寫了相關報告。他認為雖然北京方面聲稱對南海大量島礁擁有主權,并將這一意圖展現在中國出版的地圖之上,但共產黨政府并未對任意島嶼進行有效控制。戰后以來,是國民黨政府與法國分別占據若干島礁。而絕大部分體積較小、位置偏南的島嶼仍無人占領。對于部分島礁而言,中方的主權要求是較為牢固的,但仍有部分島礁面臨與法國、日本及英國的競爭。
1956年6月14日,英國駐北京代辦福特(J.F.Ford)致信外交部,其中附有中國學者引用英國航海文獻來論證中國南海主權的文章。外交部據此對相關出版物進行檢索,發現在1894年第三版的《中國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第三卷有如下記載:“中國政府于1909年占據西沙群島,并時常派遣船只進行巡視工作。……海南籍的漁民經常在12月至次年一月造訪鄭和群礁(隸屬于南沙群島),又于西南季風2之前離開島嶼。”[22]
從這些出版物中可以發現中國漁民長期前往南沙海域捕魚勞作的記錄。其中一些漁民在島上長期駐扎,他們用海參等物品同攜帶補給而來的海南船隊進行交易。外交部遠東司的官員表示這些出版物將為中國的主權聲明提供有力證據[22]。與戰前情況有所不同,這一時期,英國根據相關航海志等史料,開始將中國視作南沙主權之爭中重要的參與方。但與此同時,英方仍然不愿承認中國曾在較長時間內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
進入20世紀70年代,受冷戰局勢變化影響,中英關系迅速緩和。隨著馬來亞、新加坡等東南亞殖民地紛紛獨立,英國逐步減少在東南亞的防務開支,并最終決定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方面決定放棄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的主權聲明。
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后,英國政府意識到應當應盡快統一對南沙島嶼主權歸屬的意見。外交大臣就此建議應將英國過往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的所有聲明作廢[23]。他認為從現有的證據上看,英國似乎在十九世紀末擁有過南威島、安波沙洲主權,但此后由于對島嶼資源管理和開發不善,英國主權聲明逐漸削弱。英國內閣防務與海外政策委員會也認為,在法律層面,英方在20世紀上半葉中并未采取有效手段對島嶼進行管理及開發,因而其聲明便缺乏法律效力[24]。在此狀況下時任英國首相霍姆接受放棄南沙相關島嶼主權的建議[25]。
而在當前哪個國家的主權聲明最為有力這一問題上,英國方面認為中國及法國已占得先機。這一觀點的代表是英國外交部研究室的法律顧問鄧扎(E.M.Denza)。她曾于西沙海戰爆發之際撰寫關于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的備忘錄,指出:“只有法國及中國的主權要求確有機會得到國際仲裁的認可。”[25]但根據巴黎方面傳來的消息,法方認為自身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要求正在逐步失效[25]。如此一來,中國方面則將成為島嶼爭端的“領先者”。
為證明其判斷,鄧扎首先梳理了中國發現、管理南沙群島的歷史。她首先援引美國資料,指出中國對島嶼的主權要求可以追溯到15世紀。其中的論據包括由中方準備的地圖,這些地圖顯示幾個世紀以來,南沙群島均是中國的領土。很長時間以來,每年都有前往南沙水域捕魚的中國漁民在島上駐扎生活。19世紀90年代英國殖民部的檔案冊(Colonial Office List)也曾記載,中國漁民每年都會到南沙水域捕撈海龜[25]。
其次,鄧扎強調,進入20世紀后中國政府利用一切時機對侵犯南沙的行為進行抗議,包括1933年法國的占島行為;1939年日本的入侵;1951年和會時日本放棄對南沙的權利;近年來菲律賓的奪島行為。這一系列舉動表明其從不允許因國際法上的實效性原則(prescription)削弱自身對南沙的主權[25]。這便基本肯定了中國對他國侵犯南沙島嶼提出抗議的行為屬于有效維權的行動。由此可見,在英國的觀念中,我國對他國的抗議行為在法理層面強化了對南沙群島主權的主張,成為中國在國際仲裁中獲勝的重要依據。
此外,鄧扎又提出一個觀點: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似乎早已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這或許是因為南沙群島在1877年前就已屬于中國;也可能是由于英方主權聲明的效力衰落后,中國的聲明得到恢復[25]。如果承認這一事實,那便意味著法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占島行為并未使其獲得島嶼主權。英方認為根據實效性原則,法方占領島礁后并未在長時間內對其行使主權。與此相對照,當1945年日本放棄南沙群島后,中國船只迅速進入太平島設立石碑,建設氣象臺與無限電站以宣示主權。由此觀之,中國方面在更長的時間段內對南沙群島進行了管理。
當然鄧扎也對中方訴求的弱點進行分析。她認為若忽略臺灣當局在南沙群島上的維權活動,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并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大陸并未對南沙群島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活動。鄧扎指出:“中國臺灣地區并非主權國家,因此在國際法上不具備獲得這些島嶼主權的能力。在英國眼中,蔣介石政府自1950年1月以后為管理南海島嶼而頒布的法案并不意味著鞏固中國(the State China)對島嶼的主權,因為這些法案并未被國際上唯一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批準。”[25]在鄧扎看來,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對南沙島嶼進行有效控制的事實或將遭到質疑,這將成為中方在島嶼爭端中面臨的主要挑戰。
綜上所言,戰后自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對南沙主權歸屬問題的認知產生重要轉變,其主要特點便是開始承認中國在南沙群島的歷史性權利及對島嶼進行有效控制的事實。由此英方推斷出中國將成為島嶼爭端中的領先者。
四、 影響英國判斷的主要因素及對中國的啟示
通過對英國外交部相關文件的解析可以發現,從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其對南沙群島主權的認知產生重要轉變,其主要觀點從認為英國可以對其中某些島礁提出主權要求演變為承認中方主權聲索在爭端中的領先位置。而影響英國判斷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點:
首先,英國判斷島嶼主權歸屬的理論依據始終是當前國際法,而有效控制原則始終是英方最為重視的基本要素。根據國際法相關規定,在不具備既有條約和殖民地背景下,“有效控制”是解決爭端的首要原則。一國為獲取主權,必須控制爭議島嶼的行政及司法管轄權,并進行持續的宣示活動。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在探討其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主權聲明效力時,主要任務便是判斷自身在19世紀末登島豎立國旗、在殖民地名錄中登記島嶼等行為是否構成有效占領。然而,正如英王法律顧問所言,這些行為在法律層面無法滿足“有效控制”的標準。更為關鍵的是,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英國并未持續地對島嶼開展主權宣示的活動。正因如此,英國不得不在20世紀70年代最終放棄對南威島及安波沙洲提出主權要求。與此相對,中國方面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通過巡航、設置行政機構、勘測繪制地圖、頒布相關法律等多種手段以宣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同時每當有他國侵犯中方在南沙的利益時,中方均會正式發出警告與抗議。在英方看來,這些行為無疑為中國的主權訴求提供堅實的基礎。
其次,英國方面的認知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主義理念的殘余。事實上當前國際法本身便是西方法律體系的延伸,19世紀末,國際法的參與范圍逐漸擴大,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逐步被納入歐洲主導國際體系,開始參與其中的立法活動。當然,這一時期的國際法體現出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形態,維護著殖民者的利益,保持了對非西方社會的優越感。當時英國法學家約翰·韋斯特萊克(John Westlake)[26]便稱,在任何時候,世界上任何地方,大國都未承認小國與其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法律領域仍然不能脫離這一現實。這可以解釋為何在20世紀30年代之初南沙群島爭端爆發后,英國將主要精力投入與法國的交涉之中。因為英國殖民者長期以來便否認亞洲及非洲統治者的主權,忽略了長久以來中國在南沙海域生活生產的事實。英國將早已由中國人民發現并進行管理的南沙島嶼視作“無主地”便是最好的例證。他們認為西方國家有不受任何約束的擴張領土的權力,而中國并不具備占領、管理南沙島嶼的可能性。二戰后,隨著西歐殖民帝國紛紛瓦解,第三世界民族獨立的運動浪潮此起彼伏,英國重新對國際法上關于領土取得的原則進行反思,在南沙島嶼爭端問題中開始重視中國在此地區的歷史性權利。盡管如此,英方仍然傾向于對20世紀之前中國當局管理南沙海域的證據保持沉默。
第三,英國對南沙主權的認知亦受其遠東戰略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法國為保證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安全,試圖將南海諸島據為己有;而日本也將南海地區視為向南擴張的必經之地。日本的擴張使英國感到焦慮,在此情況下,法國是否善意中立抑或惡意中立,對英國東亞海上軍事布局和行動產生一定影響[27]。于是,英國試圖通過聯合其傳統盟友法國來阻止日本在南海地區的行動。而在南沙主權問題上開罪法國是并不明智的,因此這一時期,盡管英國法律顧問并不認為法國的聲明具有多少法律效力,但英國當局未對法方的行為進行公開駁斥。如此一來,對于島嶼的具體歸屬問題,英方只能含糊其詞。戰后受冷戰進程影響,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極度警惕中國向西太平洋方向上的擴展的趨勢,正如美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所言,“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遠東地區的支配性強國,……如果西方各大國還想在這一地區保持影響力,它們就必須為自己的海空力量尋求島嶼基地”[28]。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顯然不希望中方在南海地區獲得大量可用作軍事目的的島嶼。但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英關系的緩和及英國東南亞戰略的重新調整,英方失去了對南沙群島的興趣。這一態度轉變顯然使英國外交部官員不再過分執著于證明自身歷史上與南威島及安波沙洲的聯系,因而能相對全面地審視整個南沙群島主權的歸屬問題。
綜上所言,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相關報告中已經肯定了我國在南沙主權爭端中的優勢地位。為此我方可以通過收集來自英國的“第三方”證據,維護我國的領土權益。需要注意的是,自21世紀以來,隨著域外大國的進一步介入,當前南海島嶼爭端形勢再次復雜化。越南、菲律賓等國也試圖運用“有效控制”原則為己所用,曲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重要條約文件為其理論所服務。自20世紀70年代起,這些國家早已占領南沙大量島礁,并試圖通過立法、行政等多項手段形成對島礁的實際控制。對此,我國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加強研究有效控制原則應用的實例,厘清其基本應用規律,收集有利于我方的相關證據,在法理層面為我方維權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我國應繼續以確實掌控島礁為基礎,加強對島嶼的行政及司法管理,對一切侵犯我南沙主權的行為進行公開抗議與譴責,以此維護我國南沙群島主權,為未來通過和平、合法手段解決爭端提供基礎。
結 語
縱觀20世紀以來英國對南沙群島主權歸屬認知,其核心便是依據國際法上“有效控制”的相關原則對各方所出示的證據進行評判。但該原則的運用在不同時期卻呈現出不同的結論:二戰前英國試圖基于該項原則來證明其自身對其中某些島礁擁有主權;戰后,英國方面同樣依據這一原則,卻開始重視中國方面發現和管轄南沙群島的歷史證據。由此可見,國際法上對何為“有效控制”仍存在較大分歧。到底何種行為可稱之為對島嶼的有效控制,這一判斷標準也隨歷史發展而不斷演變。然而英國作為當今政治大國,在國際法的認識及使用之上擁有豐富經驗,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能夠為我國提供法律維度上的參考。隨著當前南沙群島主權爭端的演進,我國應積極收集西方各國政府關于主權問題的觀點,深化對國際法相關法則的研究,積極運用國際法武器,通過和平方式維護我國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