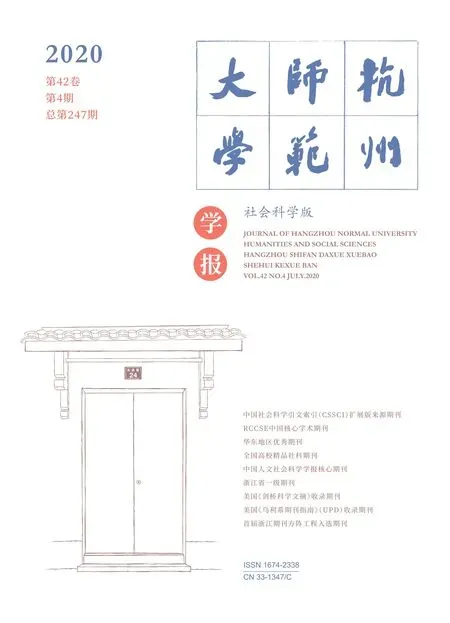儒學本體論如何統攝科學?
——以“良知坎陷”為中心
韓立坤
(南京林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7)
科學時代,儒學何為,這是現代新儒家聚焦之主題。牟宗三試圖重建形上學以處理二者之關系。他用“良知坎陷”為科學提供“儒學本體論承諾”,以此“新內圣”為科學民主之“新外王”提供超越依據。但其用“本體論之體用模型”去統攝科學,無法化解道德理性與科學理性之內在沖突。若將之修正為“價值論之體用模型”,依據良知的倫理價值邏輯,建立“儒家的科學解釋學”模型,既可以保證價值選擇意義上“坎陷”的合法性,又可實現儒家價值形上學對科學之“超越統攝”。
一、科學與儒學的理性向度差異:架構表現與運用表現
牟宗三認為,雖然儒、釋、道三教的“共同的問題”,就是知識問題,但古人既并不關心知識及合法性問題,又輕視技術發明創造,從而認識論、知識論不發達,亦發展不出科學。通過比較,他發現中國文化關注內在德性之“內容真理”,西方文化注重經驗真相之“外延真理”,二者源于“心智”(mentelity)即理性之不同運用方向:中國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體用合一,乃“理性之運用表現”;西方文化注重天人二分、主客二分,將萬物推開以做分析研究之對象,乃“理性之架構表現”。[1](P.161)而“凡是運用表現都是‘攝所歸能’、‘攝物歸心’。這二者皆在免去對立:它或者把對象收進自己的主體里面來,或者把自己投到對象里面去,成為徹上徹下的絕對。……這里面若強分能所而說一個關系,便是‘隸屬關系’。……而架構表現則相反。它的底子是對待關系,由對待關系而成一‘對列之局’。是以架構表現便以‘對列之局’來規定。”[2](P.52)
正因理性運用不同,西方文化體現“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中國文化體現“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此“綜合”乃是就中國文化“上下通徹,內外貫通”之觀念說,“盡理”則是從“盡心、盡性、盡倫、盡制”說。可見,中國文化始終關注倫理道德與意義價值,而輕視經驗器物。尤其受儒學影響,多基于良知仁體秉持“智的直覺”,將本該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客體“收攝”進所創造的有機主義、整體主義、道德主義的宇宙觀。因而主體與客體之“對列關系”始終無法建立,經驗器物無法獲得獨立性,而成為研究對象。相比科學以“觀解理性”或“理論理性”來觀察事物,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學慣用“實踐理性”去“觀照或寂照”萬物,其特點如下:(一)是非經驗的,既不借助耳目感官,又不受耳目感官限制;(二)非邏輯數字的,既不是以理論形態出現,不需通過辨解的推理過程,亦不需要邏輯的程序和數學的量度。此理性作用是基于“道德心靈”展開,追求“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知體明覺之感應(智的直覺,德性之知)只能知物之如相(自在相),即如其為一‘物自身’而直覺之,即實現之,它并不是把物推出去,置定于外,以為對象”。[3](P.121)而既然此種特殊“心智”運用,“既不經由經驗,又不經由邏輯數學,當然不能成科學知識”[2](P.50)。
如上所述,牟宗三為中西文化尋獲了兩種理論邏輯:體現“綜合的盡理精神”之中國文化擅長“內容真理”(形而上學、道德哲學),主要受“理性的運用表現”限制;體現“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之西方文化擅長“外延真理”(科學、邏輯學)得益于“理性之架構表現”。兩種學問本無價值高低,但中國轉型急需科學,為此,思考“如何從運用表現轉出架構表現”,“如何能由知體明覺開知性”,始終是中國哲學彰顯合法性之重要課題。
而牟宗三雖延續晚清以來基于儒學天道心性框架統攝、安置科學之意識,且亦從形而上學之“體”“用”框架入手,但卻超越前人對科學與儒學關系之外在拼湊式認識:如魏源、馮桂芬、薛福成、嚴復等人設定的“技”(科學)—“道”(儒學)關系。表現在,牟宗三雖同樣堅持以儒家形上道德本體統攝形下科學,但他卻試圖“徹底反省外延真理背后那個基本精神”——科學理性[4](P.37),進而在儒家形上本體與科學理性間建立邏輯關系。
不過,他仍沒能超越儒學內圣開外王之老路。事實上,在寫作《理性的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之前,牟宗三就明確:“中國要在現世界站得住立得起,必須由內圣開出外王處有一轉折,繞一個彎,使能顯出架構表現,以開出科學與民主,完成新外王的事業。”[5](P.97)而在《政道與治道》書中,他開始明確將科學、民主置于儒家內圣外王邏輯之中,指出:“運用表現自德性發,是屬于內圣的事。講內圣必通著外王。外王是內圣的通出去。”[2](P.54)但根本問題在于,古代外王內涵中,并不包含科學、民主這些“特殊結構”“材質條件”。為此,就需將此新“結構”、新“材質”與道德本心建立理論關聯,即從理性之“運用表現”轉出“架構表現”,將儒學“道德理性”轉出科學“觀解理性”。
二、認識心如何可能:“一心開二門”
儒家形上學乃天道心性相貫通之道德的形而上學,其觀念表現為“仁智合一而以仁為籠罩者”;而“智的全幅就是邏輯、數學、科學”[6](P.144),為此,儒學必須將“仁智合一”觀念“轉折一下”,以開出智心(科學心、認識心)。但問題在于,作為本體之本心良知,僅具有道德規定性,而與科學理性相沖突、相違背。為此,牟宗三從佛學“一心開二門”與康德的“兩層存有論”模型中,尋求理論支持。
佛教《大乘起信論》中言“一心開二門”,實質是一種形上學的本體論。一心,即本體——“如來藏清凈心”;二門,即“生滅門”和“真如門”。牟宗三以此“二門”來對應現象世界和形上世界:認識現象世界的是認識心;認識形上世界的是超越心。而“生滅門”又相當于康德所說的“感觸界”(phenomena),“真如門”則相當于“智思界”(noumena)。他還受康德影響,將科學稱為“執的存有論”(現象界),將儒學稱為“無執的存有論”(本體界)。
通過上述界定,他即將認識心或科學心與經驗界或現象界,從中國哲學道德宇宙觀中分列出來。但問題是,認識心是與道德心完全不同之理性能力與觀念系統。具體言,“認識心的全相”包括“直覺的統覺”之心發展為“客觀的心”或“邏輯的心”的過程。因此,其實際包含兩個維度:一個是基于時空、范疇的“直覺的統覺之心”,其以經驗現象作為對象;一個是使得千頭萬緒、千變萬化的經驗現象得以貞定,使其客觀化、規律化、系統化的客觀邏輯心。“直覺的統覺之心”是客觀邏輯心的必要基礎。[7](P.489)兩維度之認識功能,共同為科學認識得以可能提供基礎。
顯然,上述認識心之能力絕非儒家道德心、倫理心所具備。也即是,牟宗三必須面對“道德本心實體→本心自我‘曲通’→認識心即科學理性(1)包括“直覺的統覺之心”(類似認識論意義上的感性認識)、“客觀邏輯心”(類似認識論意義上的理性認識)兩維度。→科學知識”的復雜邏輯。所以,“一心開二門”并非“橫列之平行關系”,而是“縱貫之體用關系”。良知本心“開出”認識心之問題,亦非認識論問題,而是形而上學之問題(2)將認識心置于形而上學之中,牟宗三還使用了“兩層存有論”的理論框架進行解釋。認識心對應的是“執的存有論”,其理論系統表現為科學,道德本心對應“無執的存有論”,其理論系統表現為形而上學。。為此,牟宗三亦明確,對客觀認識心而言,“邏輯理性不能保證之,必須有一超越形上學擔任之”[8](P.419)。
但“惟精惟一”之良知本心,乃是天道心性貫通之德性范疇,認識心之“觀解的”、“架構的”思維,則堅持主客對立原則,二者顯然不類。牟宗三亦坦言:“德性,在其直接的道德意義中,在其作用表現中,雖不含有架構表現中的科學與民主,但道德理性,依其本性而言之,卻不能不要求代表知識的科學與表現正義公道的民主政治。而內在于科學與民主而言,成就這兩者的‘理性之架構表現’其本性卻又與德性之道德意義與作用表現相違反,即觀解理性與實踐理性相違反。即在此違反上遂顯出一個‘逆’的意義。它要求一個與其本性相違反的東西。這顯然是一種矛盾。它所要求的東西必須由其自己之否定轉而為逆其自性之反對物(即成為觀解理性)始成立。”[2](P.56)這樣,如何既保證儒家德性本體之超越地位,又可從道德心轉出認識心,從“德性”(道德理性)“逆”著轉向本與其“違反”的“知性”(科學理性),就是搭建儒學與科學內在關聯的核心要義。
三、科學的“本體生成論承諾”:道德實體自我“坎陷”
儒家之良知本心,歷來被視為可生化萬物的無限的、絕對的、必然的道德實體。作為其彰顯者與實踐者,道德心亦能呈露無條件之道德意識,踐行無條件之定然命令,推動無條件之道德實踐。自此而言,超越實體即是道德心。而道德心之能力,即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良知良能。還原此形上學邏輯,道德實體乃是理論上之“必然”,道德心乃是本體必然規定性之普遍現實化,是為“本然”,而良知(知體明覺)乃是必然本體之普遍屬性,在具體時空中之具體呈現,是為“實然”。按照牟宗三對道德理性與科學理性之區分,道德實體是形上學本體,道德心是本體在現實世界的普遍樣態,而良知則是此樣態之具體能力呈現——道德理性。
在古代儒家中,對此“道德實體”→“道德心”→“良知(道德理性的仁智合一觀念)?經驗”之邏輯論域尚未形成明晰之界定。尤其是古人多從良知良能去論證本心之先驗性,因而在賦予良知能動性的同時,消解了其本該具有之經驗面向;而儒學良知本體若要與認識心建立理論關聯,就表現為以下邏輯:“道德實體”→“認識心”→“科學(觀解理性的對列觀念)?經驗”。這樣,先驗之良知實體與經驗之認識心如何關聯,就成為核心環節。為此,牟宗三提出良知“自我坎陷”(self-negation)。
(一)“良知”與“坎陷”的本意
不過,在闡述“良知坎陷”時,他不斷論說從道德心開出認識心,從道德理性轉出科學理性,因而又始終給人如下錯覺:一是,道德心就是超越本體,認識心是經驗產物,因而上述形而上→形而下的“必然→本然→實然”的本體現實化邏輯,就變成“必然→實然”的邏輯斷裂。二是,道德心并非超越本體,而是本體現實化的普遍規定性。這樣,“坎陷”說就會遭遇道德心(心的普遍道德規定性)→認識心(心的個體時空中的經驗面向)的解釋困境。
而欲準確厘清“良知坎陷”,首要問題是把握“坎陷”之意。事實上,在20世紀40年代末完成的《認識心之批判》一書中,他說:“理解陷于辯解中,始能成知識,而陷于辯解中必有成就其辯解之格度。是以格度之立全就理解之坎陷一相而言之。此一坎陷是吾人全部知識之形成之關鍵,是以論知識者皆集中于此而立言,寖假遂視此為全部理解相狀之所在,而不復知其只為一坎陷之相狀。”[8](P.196)此“坎陷”,僅是從認識論之維度去討論認識何以可能的特殊概念,通過“坎陷”,理性能力開始聚焦時空、邏輯、概念、命題等科學知識系統得以可能的基本要素(3)顏炳罡也就此認為,牟宗三在《認識心之批判》中理解之坎陷,主要是理性思維之運用或起用,所以坎陷的全過程,就是知識的完成過程。參見顏炳罡《整合與重鑄——牟宗三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頁。。可見,“坎陷”之落腳點,正是科學知識得以可能的現實時空、經驗對象。
其次,要把握能夠“開出”認識心即科學理性的“良知實體”之本意。牟宗三視儒家為“德性之智”“超越之智”,而科學乃“知性之智”“分解之智”。而與科學“分解之智”相對,儒學又可謂“圓智”。他指出:“因為圓智神智是無事的。知性形態之智是有事的。唯轉出知性形態,始可說智之獨立發展,獨具成果(邏輯、數學、科學),自成領域。圓智神智,在儒家隨德走,以德為主,不以智為主。……智只是在仁義之綱維中通曉事理之分際。……一個文化生命里,如果轉不出智之知性形態,則邏輯、數學、科學無由出現,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無由出現,而除德性之學之道統外,各種學問之獨立的多頭的發展無由可能,而學統亦無由成。”[1](P.172)也即是,作為一種道德理性的“良知”,其本是對應“仁義之綱維”之類的經驗去呈現。
可見,“良知坎陷”本意是基于“道德理性”轉出“科學理性”,進而開出科學經驗。而本為“仁智合一之心”若要轉出“認識心”,就要回答“道德理性”與“科學理性”之邏輯關系問題。牟宗三承認,與古代由“道德理性→道德實踐”之“直接實現”不同,良知本心在面對經驗現實、現象世界時,要“向下曲折一下”方可轉出“知性”。也即是,兩種理性間之關系,并非實然的“直接實現”,而只能是“間接實現”。[9](P.33)
(二)兩類“理性”沖突與“辯證發展”
顯然,儒學與科學均是理性之表現,道德理性攝物歸心,科學理性與物為對,自然不存在誰開出誰的可能。但為轉出認識心,就必須依靠理性主體自身“把‘所’與‘物’推出去,凸顯出來,與自己成一主賓對列之局”[5](P.102)。將以往消解于道德宇宙中之萬事萬物的個別相、差異相、生滅相凸顯出來。在《現象與物自身》書中,他也說:“知體明覺之自覺地自我坎陷即是自覺地從無執轉為執,自我坎陷就是執,坎陷者下落而陷于執也。不這樣地坎陷則永無執,亦不能成為知性(認識的主體)。”[3](PP.122-123)
問題在于,儒家的“知體明覺”根本是作為形上本體的良知本心或道德實體的現實呈現,其本質是知善知惡知是知非的道德理性。作為“坎陷”之主體,其有且僅有道德的規定性。因此,良知(道德理性)“坎陷”出“認識心”(科學理性),哪怕是他運用了含混與模糊的“曲通”“轉折”字眼,來強調道德心與科學心之關系,是“在曲通之下,其中有一種轉折上的突變,而不是直接推理”,卻始終無法解決兩種理性能力間之理論張力。
按照牟宗三所說:“從理性之運用表現到架構表現,是轉折上的突變,不是直線之推理,故雖說架構表現必以運用表現為本,但直接卻推不出來。……凡直接推理可用形式邏輯之方式把握之,但轉折上的突變,卻是一辯證的發展。”[5](P.100)而可依據“辯證的發展”開出科學理性之主體,正是超越的良知本體。他還說:“知體明覺不能永停在明覺之感應中,它必須自覺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陷),轉而為‘知性’。此知性與物為對,始能使物成為‘對象’,從而究知其曲折之相。它必須經由這一步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實現其自己,此即所謂辯證的開顯。”[3](PP.122-123)可見,“坎陷”本質是形而上之實體自我發動的革命,此革命它是“在自己而又對自己”,以及“它在躍起之自覺中建立其自己,同時即在此中客觀化其自己”。[8](PP.107-108)
顯然,牟宗三之良知“坎陷”認識心,并非兩種理性之“平列”,而是“內在貫通”意義上的形上道德實體開出形下科學功用之“客觀的實現”。只是,此一實現,并非一般的“本體生成論”邏輯或“存在體用論”邏輯所能勝任。這是因為,若按上述邏輯,良知“坎陷”認識心:“德性實體”(良知)→“認識心”→“科學(觀解理性的對列觀念)?經驗”。這樣,認識心就作為形上實體與形下經驗之“邏輯中轉”或“過渡環節”存在,亦符合“坎陷”乃是良知面對經驗現象開出科學理性之流程。但隨之遇到的問題在于,認識心從“必然”→“本然”→“實然”的本體生成邏輯中獲得了“本然”地位,認識心就與道德心處于同一邏輯維度。顯然,這不但直接消解了道德心對認識心之主宰、范導與統攝能力,亦凸顯出儒家內圣開外王式的“本體生成論”邏輯或“存在體用論”邏輯在良知“坎陷”設定中之錯位。
(三)“主體之能”
而幫助我們理解“坎陷”邏輯的,是牟宗三強調良知開出認識心,絕不是直接符合“邏輯推理”的“主觀實現”,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在良知本體與科學觀念間建立“曲通”關系,運用一種特殊邏輯所建立的“客觀實現”。[2](P.56)在筆者看來,學界之所以圍繞“良知坎陷說”聚訟不已,正是沒能準確理解牟宗三所立論之特殊邏輯。而回到此說之焦點,“坎陷”一詞乃是源自《周易·說卦》的“坎,陷也”。一般易學研究認為,坎卦之卦象,有上下貫通之意。顯然,牟宗三正是針對百年來儒學始終遭遇科學“拒斥”與“驅逐”之困境,而試圖將二者之“橫列”沖突轉為“縱觀”之順成,從“形而上學”之高度去建立儒學與科學之理論關聯。
但是他基于儒學良知本體論之話語范式來解釋良知“坎陷”,始終給人以良知本心“轉生”“轉出”科學知識之強為之感,讓人對這種“本體生成論”邏輯以及“內圣開外王”的道德理想主義充滿懷疑。余英時批評牟宗三過于依賴“超越的證悟”,將儒學變為“道德主義”。林毓生認為以科學實存為前提的“良知坎陷”只是把結論預設在前提之中的“循環定義”。傅偉勛認為“坎陷”說“仍不過是張之洞以來帶有華夏優越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老論調的一種現代式翻版而己,仍突破不了泛道德主義的知識論框架”[10](P.448)。景海峰批評其根本是:“一種觀念提純式的運作,沒有了歷史真實,沒有了當下情景,只剩下一大堆抽象概念的博弈和滑轉。”[11]林安悟也認為“良知自我坎陷”乃是使用了“存有的發生學方法”,是采用了一種倒退論證的方式,這個方式本身是一種“理論的次序”,而非科學實踐的“發生的次序”,而林安梧本人則主張放棄對理性的過度依賴,放棄對科學理性之理論建構,而是采用“學習的次序”,與科學平等對待。蔣慶批評牟宗三將良知從生命證悟的精神境界具化為認識論上的“理性概念”,將良知的“呈現”物化為“生成”,“良知坎陷”最終背離了儒家良知學。楊澤波則從體欲、認知、道德等維度去理解,將“良知坎陷”視為“道德坎陷”。
事實上,學界在討論“良知坎陷”時,忽略了牟宗三的“主體活動之能”說。也即是,他擱置了“良知”實體的“生化”之意,而僅從道德理性之求善、求好、求真為科學之出現提供“理性的接引”,他說:“誠心求知是一種行為,故亦當為道德理性所要求,所決定。無人能說誠心求知是不正當的,是無價值的。……既要求此行為,而若落下來真地去作此行為,則從‘主體活動之能’方面說,卻必須轉為‘觀解理性’(理論理性),即由動態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轉為靜態的成知識之觀解理性。這一步轉,我們可以說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經此坎陷,從動態轉為靜態,從無對轉為有對,從踐履上的直貫轉為理解上的橫列。”[2](PP.56-57)
此解釋同樣是一種“本體生成論”邏輯,只不過,此種生成論無需從作為形上本體的道德實體那里獲得邏輯依據,而僅是從人之求好求善之理性能力立論。顯然,此種角度的“坎陷”在現實維度更合理。否則,我們就無法回答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后發國家,能夠學習、引進科學技術,實現社會科學化、技術化之顯著成就。但是,這種“主體之能”不過是承認儒家道德理性有轉換為科學理性之理論上的可能性。并且,僅有“主體之能”,不過是科學產生之“形式的必要條件”,而非“實際的充足條件”。否則亦無法解釋恰恰是非儒家文明主宰與影響下之生存共同體,才率先發明科學之基本事實。
所以,從”本體生成論”與“內圣開外王”邏輯去理解“坎陷”,始終會遇到如下問題:
1.科學理性的獨立性難以保證。牟宗三樂觀地認為,道德理性轉出科學理性后,即“暫忘”與“退隱”,以賦予科學理性獨立性,但無論是經驗道德觀念抑或超越道德實體,均會始終籠罩在科學人格之上。受其影響,儒家道德宇宙觀與科學宇宙觀在“天人合一”與“物我兩分”、“萬物有生”與“研究實驗”、“應然判斷”與“實然解釋”間之沖突,很難得到化解。
2.若真正保障科學與科學理性之獨立性,就要真正做到各種良知觀念在現實維度的“暫忘”與“退隱”。但這同時會出現如下問題:或者道德理性之內圣為確保新外王之獨立性而喪失原有的普適影響,或者新外王遵照自身之“分解的盡理精神”而形成獨立的理性王國,而走上與古代圣王仁政的外王學的對立道路。所以,科學時代,依然堅持儒學內圣外王之義理架構,并試圖重釋新內圣的做法就多此一舉了。
3.即便不考慮“主體活動之能”對儒學內圣外王邏輯之消解,其問題仍在于,顯然不止是儒家文明或儒化社會才具此種“主體之能”。由此,即便有此理性能力,亦與真正運用科學、認識科學、創造科學沒有必然聯系。所以,即便道德理性“坎陷”后具備科學理性,但仍然要承認:“有了德性,亦不能直接即有科學與民主政治。”[2](P.55)可見,“坎陷”之后,道德良知與科學本身仍處于邏輯的潛在性與可能性關系中。
四、“價值體用論” :儒學“統攝”科學的另一種選擇
“良知坎陷”本意是以形上學實現儒學良知本體對科學之“超越的統攝”(林安梧語);而通過上文分析,筆者認為,“本體生成論”或“存在體用論”式的“坎陷”,并不能實現這種“超越統攝”之理想。根本上,以良知本體“保住科學知識的必然性(necessity)”,已然溢出了其解釋效力之范圍。為此,我們可探索從“超越性生成”轉向“超越性規范”,即基于儒家一貫的“價值優位性”原則,以知識價值、行為判斷維度的價值本末邏輯或價值主次邏輯,提供另一種“體用論”模式——“價值體用論”,從而既可以化解道德理性與科學理性之張力,又可以激發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學”之時代生命力。
在此“價值體用論”中,依然可采用“體—用”框架作為形上邏輯。此“體”,依然是儒家天道心性相貫通的良知本心,此“用”依然是科學觀念、科學知識、科學實踐。只是,“價值體用論”范式中,并不以“先驗生成”式的“本體論承諾”為主題,而是以“后驗規范”式的“價值論判斷”為核心。作為科學價值判斷之“體”,良知本心,更類似賀麟的“邏輯意義的心”,是“理想的超經驗的精神原則”與“經驗行為知識以及評價的主體”。只有從此種意義,才可說此良知本心“乃為經驗的統攝者,行為的主宰者,知識的組織者,價值的評判者”。[12](P.131)才可說此良知本心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化的統攝者、主宰者、組織者、評判者。從此意義仍可說,此良知本心乃一切文化之“體”,一切文化乃此心之“用”。
而此“體—用”關系,乃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與生命理想展開,其二者間并非生成與被生成之邏輯,而是價值本末、主次之邏輯。正如方東美所言,一切存在均與人的“生命心靈”“生命情調”對其的“美化,善化以及其他價值化的態度與活動”有關。而包括科學、道德、藝術、文學、詩歌、音樂在內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切知識體系,既是主體理性之創造,顯然亦是主體意愿之選擇,主體生活之需要。這樣,作為“生命情調”體現之科學,就始終服務于人類生活的實踐理想、價值訴求、意義審視而被納入到理性主體之“創造的世界”中,科學價值與科學信仰也被納入生命多維價值訴求為標準的“立體的結構”中。[13](P.43)
顯然,在此“創造的世界”中,依然可說“識心之執與科學知識是知體明覺之所自覺地要求者”,此“知體明覺”依然承擔“創造實體”“創造本體”之使命。也即是,作為行為實踐、知識實踐之理性主體,可依據“主體之能”聚焦科學對象,培育科學理性,創造科學知識,推動科學實踐。在此“立體的結構”中,道德良知、道德理性仍然具有“德行的優先性與綜綱性”。在科學信仰、科學實踐之“制衡”與“規范”上,以儒家擅長之“道德觀念”“人文精神”依然可以作為最高原則,以對治科學的濫用、科學信仰一元化。
總之,此種“價值的體用論”,仍堅持了儒學主體性,秉承了其道德形而上學主旨;但同時,它規避了良知“坎陷”科學理性那種“生成”“轉出”所帶來的“先驗的困境”,而建立了一種良知以道德意識、人文意識聚焦科學實踐,以發揮“評價”“規范”“統會”作用的“新坎陷”效用。這樣,既可在儒學與科學間建立一種“價值形而上學”的邏輯,又可在保障科學獨立性之同時,通過道德良知對科學理性、科學實踐之“范導作用”,始終防止科學泛化、濫用,保證道德本體對科學理性之“超越的統攝”。